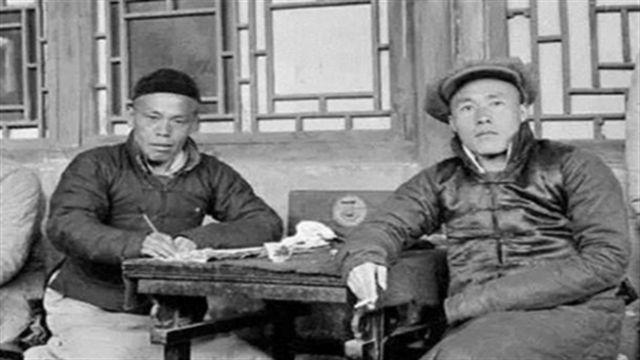1946年,地下党前往指定地点与人接头时,突然看到来人是国军中将,大惊之下脱口而出:“父亲,您怎么在这呢?”
这位地下党名叫吴群敢,他父亲是国民党军队的高官吴仲禧,因为父亲的原因,他不仅自小吃穿不愁,还能够“呼风唤雨”,可他并没有染上纨绔子弟的恶习,反而勤奋好学,志向高远。
吴群敢自幼喜欢读书,特别是喜欢读各类描写时局的书籍,这其中不乏很多进步书籍,他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吸收了很多进步思想。
而吴群敢之所以能入党,也与他喜欢读书有直接关系,吴群敢在广东韶关仲元中学读书时,从图书室借阅了一本《西行漫记》。
《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创作的纪实文学,主要描述了其1936年在中国西北的所见所闻。
这本书是第一本,把红军的实际情况和真实面貌,告诉全世界的书籍,里面生动形象地描述了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将士的真实情况。
吴群敢读了这本书后深受感染,他十分向往红军,可惜正在上中学的他,没有与组织接触的机会,由于喜欢书中的内容,他反复阅读该书,导致忘了按时把书还回图书馆。
直到图书馆管理员催吴群敢还书,吴群敢才恋恋不舍的把书还了回去,原本这是一件小事,可 吴群敢这个举动,却引起了另一位学生刘渥丹的注意。
刘渥丹当时在仲元中学读高一,与吴群敢算是校友,不过刘渥丹还有另一层身份:仲元中学党支部书记。
刘渥丹得知吴群敢喜欢读《西行漫记》后,就开始留意吴群敢这个人,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刘渥丹发现吴群敢非常具有进步思想,就主动找到吴群敢,开始对吴群敢进行思想教育。
1941年,经刘渥丹介绍,吴群敢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秘密为组织工作,并进一步接受组织的教育。
后来,由于吴群敢的父亲吴仲禧工作调动,吴群敢跟随家人搬到了上海,由于走的匆忙,再加上当时联系不便,吴群敢来到上海后,一度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吴群敢虽然非常着急,但他并没有病急乱投医,他始终谨记刘渥丹的话:“如果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不要乱找关系,等组织觉得需要的时候,自然会派人找你。”
就这样,吴群敢边在上海工作,边等待组织的召唤,而这一等就是3年,1946年,始终没有等到组织联系的吴群敢,决定主动出击,想办法寻找组织。
不过,吴群敢是非常谨慎的,他先是在上海参加了民盟,并凭此见到了王绍鏊,王绍鏊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也是吴群敢父亲的朋友。
吴群敢认为,王绍鏊很可能会帮他找到组织,而且至少看在父亲的面子上,不会出卖他,于是吴群敢就跟王绍鏊说:“民盟太松懈了,总感觉干不出什么成绩来。”
王绍鏊听了吴群敢的话后,思索了一会儿:“如果你想到严密的组织工作,我能帮你想办法”,见王绍鏊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吴群敢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把自己与组织失去联系的事情讲了出来。
在王绍鏊的帮助下,吴群敢很快就与组织恢复了联系,并开始为组织工作,由于父亲吴仲禧是国军中将,吴群敢不敢让家人知道自己的身份,就拜托王绍鏊帮着保密。
一天,吴群敢接到组织的任务,前往一秘密地点与人接头,吴群敢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的后,就准时来到了接头地点。
很快,接头的人就来了,双方在夜色下对起了接头暗号,虽然双方说的暗号都对,可吴群敢却疑惑起来,怎么前来接头的人,声音这么熟悉呢?
这时,对方非常平静的伸出手,做了一个与吴群敢握手的姿势:“同志你好,我是你的接头人”,吴群敢仔细一看,包裹着围巾的接头人,不就是自己那个国军中将父亲吴仲禧吗?
吴群敢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怎么也想不到,严厉的父亲竟然和自己是同事,吴群敢当时的脑子非常乱,他起初以为是王绍鏊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父亲,惊慌失措的说了句:
“父亲,您怎么在这呢?”
父亲吴仲禧也没想到,来接头的人竟然是自己的儿子,不过震惊之后,吴仲禧很快就恢复了平静,而且也没有多说什么,传递完情报后,就各自离开了
其实,吴群敢不知道的是,父亲吴仲禧早在1937年就入了党,而引荐父亲吴仲禧入党的人,同样是帮吴群敢找到组织的人——王绍鏊。
经此一事,虽然父子二人都知道了对方的真实身份,但也都严格按照纪律要求,完成各自的任务,彼此之间并没有聊太多,不过组织知道详情后,开始安排吴群敢做组织和父亲吴仲禧的联络人。
当时,吴仲禧由于身份特殊,需要经常出差,组织和吴仲禧的联系并不方便,现在有了吴群敢,一切都好办了,毕竟这种父子关系实在太罕见了,很难引起别人怀疑。
不过,有一件事情,吴群敢一直没敢问组织也没敢问父亲,那就是他和父亲,到底谁是谁的上级,谁应该向谁汇报。
虽然父亲吴仲禧是具体负责获取情报人员,而吴群敢是帮忙联络并传递情报的人,但双方到底谁领导谁,在当时却真的不一定,这需要组织的任命。
当然了,即便没有明确的说法,父子二人的配合也是非常默契的,此后父子二人联手,为组织传递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并屡建奇功,多次受到组织的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