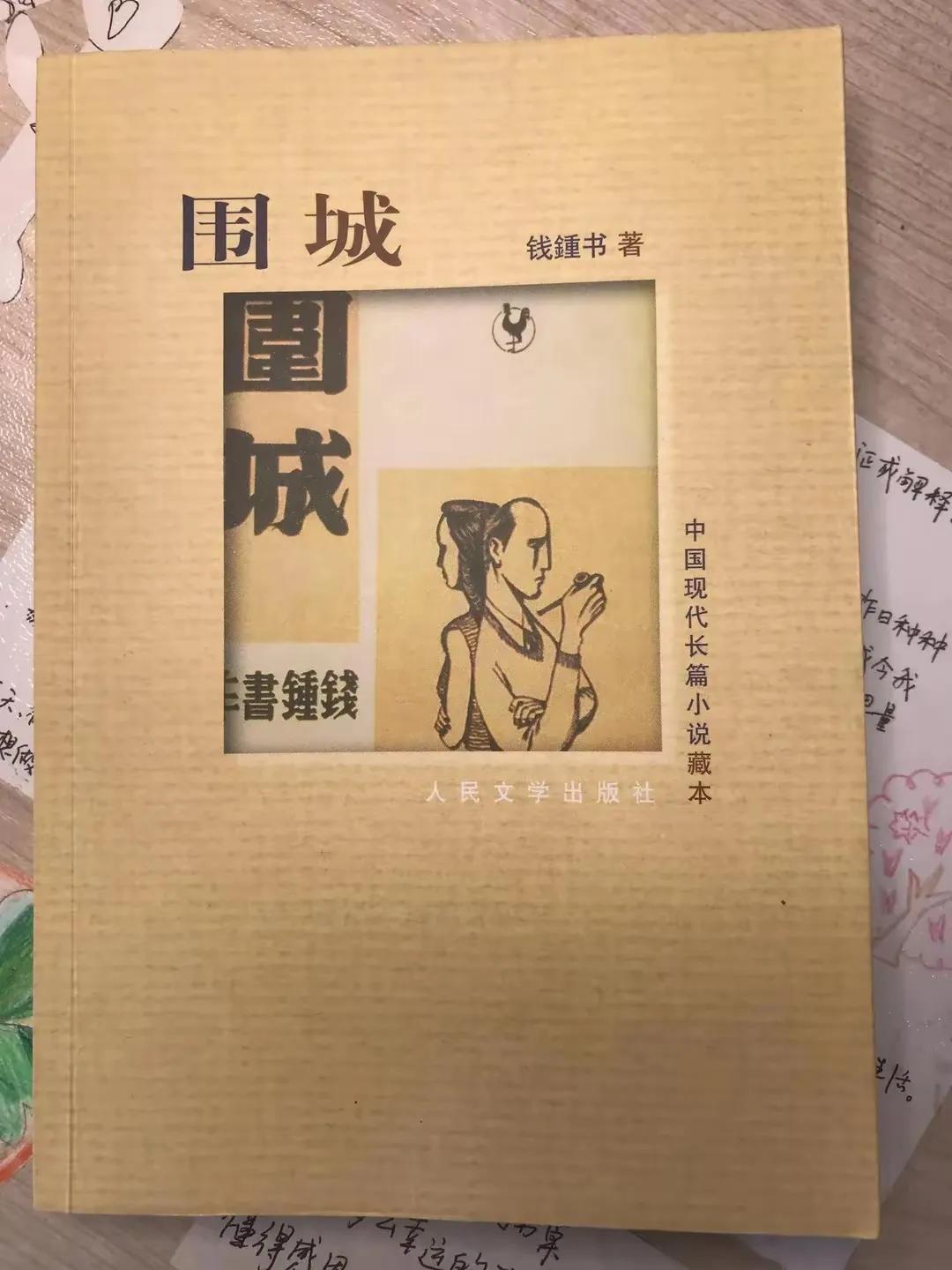书评(三)《围城》(钱钟书) 中国现代文学的另类 —— 浅析钱钟书的小说《围城》 《围城》是钱钟书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它创作于1941年,出版于1947年,兴盛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被誉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新儒林外史”,也就是说它描摹了抗战初期知识分子的群像,具有一定的讽刺性。 也不知是先入为主的缘故,还是对钱钟书所处的那个时代不够了解,我在读《围城》时,并没有感到特别的讽刺意味,而能明显感觉到的是杨绛所说的“锱铢积累”,也就是琐碎和平淡,甚至在读到方鸿渐一行五人赴湖南三闾大学途中的那一段,感到有些冗长和累赘。 从整体来看,我觉得,《围城》就是钱钟书对他所历经的一段生活的记录,通过人物的嫁接拼凑成了方鸿渐和他的女人们的一段情话—— 在回国的船上,方鸿渐与鲍小姐热恋并有了一夜情,而当船抵达上海后他却遭到鲍小姐的抛弃,可以说,方鸿渐是鲍小姐一时解闷、消遣、娱乐的过客。在上海银行工作时,百无聊赖,寂寞难耐的方鸿渐主动去找到他的大学同学苏文纨,这时的他却成了鲍小姐的化身,欲拿苏文纨来解情感之渴,不料早就对方鸿渐关注且爱慕的苏文纨分外热情,缕缕暗示芳心,但意外的是在苏家偶然遇到的苏文纨的表妹唐晓芙却掳掠了方鸿渐的心,他在苏文纨和唐晓芙之间游弋摇摆,他喜欢唐晓芙的青春靓丽,纯洁活泼,他也不敢断然拒绝苏文纨的痴情和爱恋,他在享受着一个女人对自己的爱意,同时也在追求着自己倾心的另外一个女人,这样的徘徊犹豫总不会长久,终究会见分晓,当苏和唐悉知真相后,给方鸿渐留下的只是凄苦和伤悲,以及孤身一人,这或许就是这山望见那山高要付出的代价。在三闾大学,方鸿渐看似与孙柔嘉顺理成章的相恋,在香港,方鸿渐貌似与孙柔嘉水到渠成的结婚,岂不知这都是孙柔嘉的心机和算计,都是孙柔嘉在处心积虑,不露声色的言谈举止中俘获了方鸿渐,也就是说方鸿渐是在孙柔嘉的掌控下一步一步的走进了婚姻的“围城”,这种懵懂的爱恋、被迫式的婚姻容易为最后的决裂埋下隐患。在《围城》中方鸿渐与鲍小姐、苏文纨、唐晓芙、孙柔嘉的情爱之路几乎都遵循着一个模式,开始时热情似火,亲密无间,最后都分道扬镳,甚至反目成仇,这样不断重复,没有矛盾冲突的情节未免寡淡、平庸,甚至啰嗦,但它却被奉为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有趣味、最深邃、最有可读性的长篇小说,何也? 我觉得《围城》最鲜明、最直接的可读性就是它的语言,其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哲理性。钱钟书在故事的叙写中不时的流露出他对生活,对社会,对人生的真知灼见,流溢于笔端的就是一针见血,或者是直指本质的精言妙语,如,他认为”医生是职业化的杀人“,”医学要人活,救人的肉体;宗教救人的灵魂,要人不怕死“,再如,”丈夫是女人的职业,没有丈夫就等于失业“,“嫁女必须胜吾家,娶妇必须不若吾家“,这些令人彻悟的箴言警语今天读来依然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二是幽默性。从《围城》的语言表述来看,钱钟书并不是一位迂腐而古板的学者,他是一个富有生活情趣的人。在《围城》中,他不时的用调侃、挑逗的腔调生发出幽默的趣味,让人时而忍俊不禁,时而会心一笑,时而开怀大笑,如,”人生最原始的睡,也是死的样品“,”亚当和夏娃因为好奇心失去了天堂“,再如,“中国人丑得像造物者偷工减料的结果,潦草塞责的丑;西洋人丑得像造物者恶意的表现,存心跟脸上五官开玩笑,所以丑得有计划,有作用”。三是鲜活、形象生动而贴切的比喻。可以说,《围城》把汉语语言的比喻推到了极致,如对自然景物的比喻多浸入拟人的手法,形象而亲切:”满天的星又密又忙,它们声息全无,而看来只觉得天上热闹。一梳月亮像形容未长成的女孩子,但见人已不羞缩,光明和轮廓都清新刻露,渐渐可烘衬夜景。小园草地里的小虫琐琐屑屑地在夜谈。不知哪里的蛙群齐心协力地干号,像声浪给火煮得发沸。几星萤火优游来去,不像飞行,像在厚密的空气里漂浮,月光不到的阴黑处,一点萤火忽明,像夏夜的一只微绿的小眼睛。“再如,对人物的比喻鲜有正面的描绘,多是通过纵横的类比,生动而有趣:”唐晓芙妩媚端正的圆脸,有两个浅酒涡,天生着一般女人要花钱费时,调脂和粉来仿造的好脸色,新鲜得使人见了忘掉口渴而又觉嘴馋,仿佛是好水果。她眼睛并不顶大,可是灵活温柔,反衬得许多女人的大眼睛只像政治家讲的大话,大而无当。古典学者看她说笑时露出的好牙齿,会诧异为什么古今中外诗人,都甘心变成女人头插的钗,腰束的带,身体睡的席,甚至脚下践踏的鞋袜,可是从没想到化作她的牙刷。她头发没烫,眉毛不镊,口红也没擦,似乎安心遵守天生的限止,不要弥补造化的缺陷”。《围城》中这种俯拾皆是,唾手可得的比喻,让人感到作者有刻意卖弄文采之嫌,但正是这一点,让它在阅读中充满了的快感和情趣,让它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无可比肩的另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