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一个湖北穷小子高考考了289分,因消息不灵通,他就报了华中师大。没想到,华师大录取分数线才189分,北大分数线也只要270分。有人故意逗他:你后悔当初选的吗? 1977年,戴建业怀着激动又忐忑的心情走进了高考考场。在湖北一个偏远农村,这一年的高考像一场轰动的盛事,无数像戴建业一样的青年,手捧书本彻夜苦读,希望能通过高考改变命运。他与村里的伙伴们不同,他们大多认为考大学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戴建业凭着三个月夜以继日的努力,不仅参加了高考,还考出了全县罕见的289分高分。 考完试后,志愿填报成了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在信息匮乏的农村,谁都不知道北大的录取分数线是多少,甚至很多人都不了解北大和其他大学的区别。戴建业也只能听从老师的建议,选择离家较近的华中师范大学。那时,他心里想得很简单:能上大学就不错了。 入学通知书寄到家时,全家人围着看了半天,母亲抹着眼泪感慨道:“咱们家也能出个大学生了!”父亲沉默不语,但喜悦从脸上溢了出来。村里的邻居们听闻后也纷纷赶来祝贺。 虽然戴建业知道自己考得不错,但直到邻居家有人提到:“听说北大只要270分呢!”他才惊愕地意识到,自己竟然远远超过了北大的分数线。消息传开后,村里一些人也开始调侃他:“哎哟,戴建业啊,你是不是傻?考那么高的分,却没去北大,跑去啥师范学校!”话语间夹杂着揶揄和不解。 对于这些话,戴建业只是笑笑,没有多说。他家里没有通电,他依然晚上点着煤油灯看书。比起别人眼中的“错失北大”,戴建业更专注于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 刚到学校时,戴建业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即将面对全新的生活。华中师范大学当时的校舍是几栋简陋的红砖房,教室里的桌椅也是陈旧的木制结构,窗户上贴着几层泛黄的旧报纸以挡风。宿舍内同样条件艰苦,几张上下铺挤在狭窄的空间里,床铺上仅有一条薄薄的草席。 戴建业没有任何抱怨。他每天起早贪黑,按时上课、做笔记。他用普通的稻草本记录下每一堂课的要点,课后总是第一个跑到图书馆找相关书籍补充知识。 尽管生活艰难,但在校园里,戴建业遇到了让他一生都感到幸运的事——他的妻子。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戴建业正在图书馆翻阅一本《唐诗三百首》。旁边的座位上,一个穿着白衬衫、梳着整齐马尾辫的女生正在专心地写着笔记。 她时而低头思考,时而抬头皱眉,似乎在琢磨某个难题。戴建业本想开口询问一个问题,但迟迟没有鼓起勇气。他悄悄观察对方的一举一动,直到女生抬起头,对着他微微一笑:“同学,你也在研究诗词吗?”这句简单的问话打开了两人交谈的闸门。慢慢地,他们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戴建业经常自嘲,说自己是个“放牛娃”,根本配不上城里来的“好白菜”。他说得坦然,语气中却带着一份由衷的感激:“像我这样的穷小子,能娶到这样的姑娘,真是老天爷开恩。”起初,这段恋情并不被女生的家庭看好。 女生的父母认为,戴建业家境贫寒、前途未卜,无法给予女儿稳定的未来。戴建业从未退缩。他用自己的努力和真诚,赢得了对方父母的理解。 大学毕业后,戴建业留校任教,开始了自己的教师生涯。尽管人生的起点低于很多人,但他从不懈怠。他的普通话很不标准,课堂上时常引发学生们的哄笑。 有人甚至在背后窃窃私语:“这样的人也能教书?”校长也劝他另寻出路。但戴建业没有退缩。他买了一台旧收音机,每天晚上拿着书本模仿播音员的语调,一句一句地纠正发音,直到能够流利地用普通话讲课。 正是这种坚持和执着,让他逐渐赢得了学生们的认可。特别是他以幽默风趣的方式解读古诗词,让学生们耳目一新,渐渐成为校园里的“明星老师”。每次上课,他的教室里座无虚席,走廊里都站满了学生,甚至还有其他专业的学生慕名而来旁听。 有人问戴建业:“如果你当初知道自己能上北大,还会不会选择华师大?”他哈哈一笑,回答道:“北大虽好,但我遇不到我的‘白菜’。人生有遗憾,但也因此有了更多的惊喜。” 在错过北大的选择背后,戴建业用乐观、执着和努力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 成名后的戴建业并没有飘然自得。他一方面继续在华中师大深耕教育,另一方面开始利用演讲和写作赚取额外收入。 天不遂人愿。2020年2月,戴建业的妻子因病去世,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在一次课堂上,他讲到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时,哽咽到泣不成声。 他说,只有经历过生离死别的人,才能真正理解这句诗的深情与悲凉。妻子的离世让戴建业的家变得冷冷清清,但他并没有被悲痛击倒。他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教学和写作中,用工作来填补内心的空白。 如今的戴建业依然活跃在教育领域。他用幽默和风趣感染着学生,用深情和真诚打动着观众。他的经历也告诉世人,人生的路并非一帆风顺,有时充满遗憾和波折,但只要心怀热爱与责任,就能在平凡中活出不平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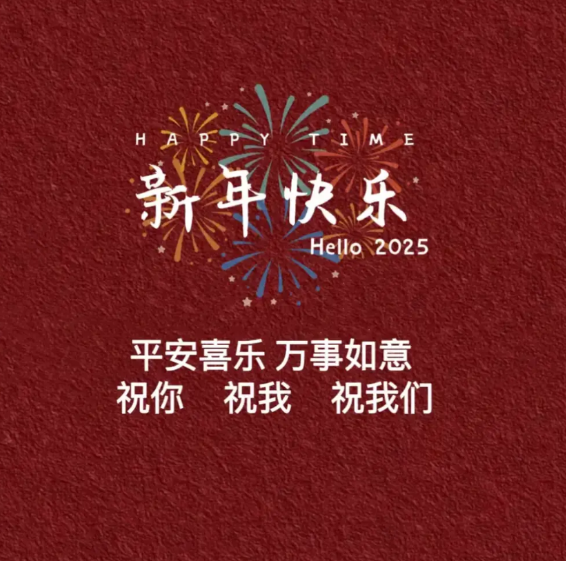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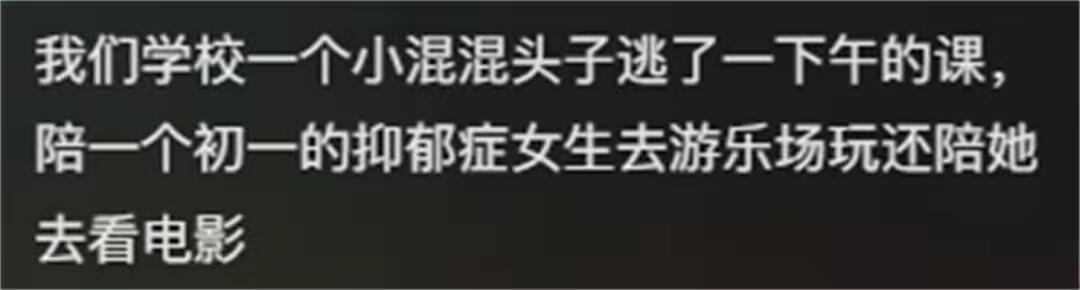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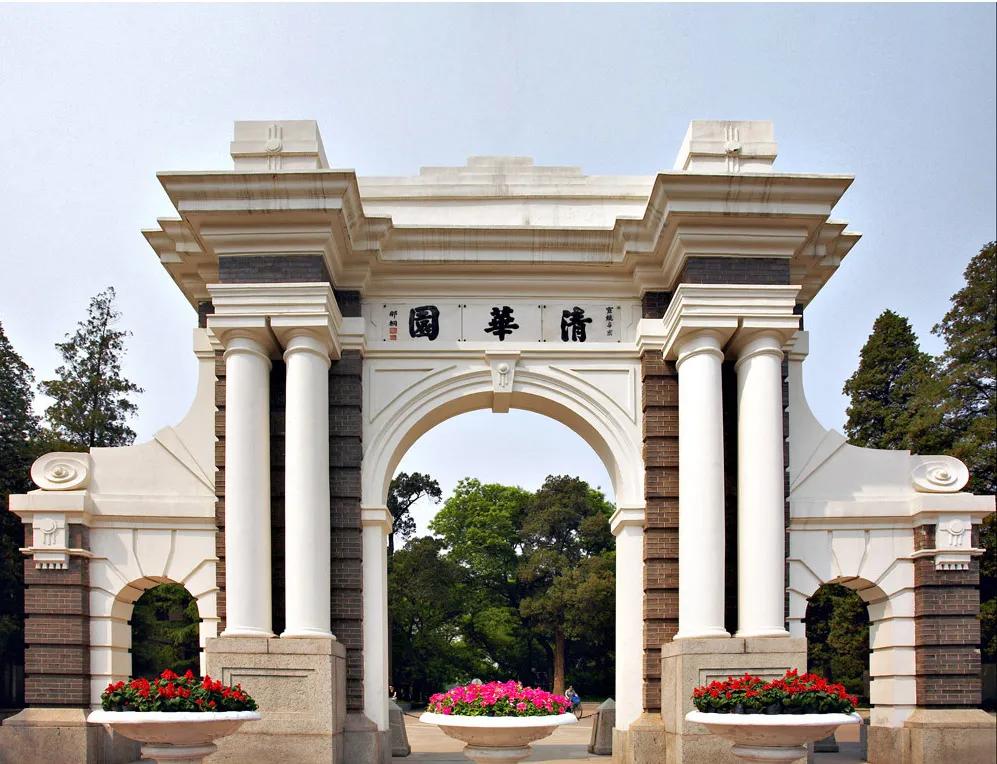

闫佳会
扯蛋,那时候是考前填志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