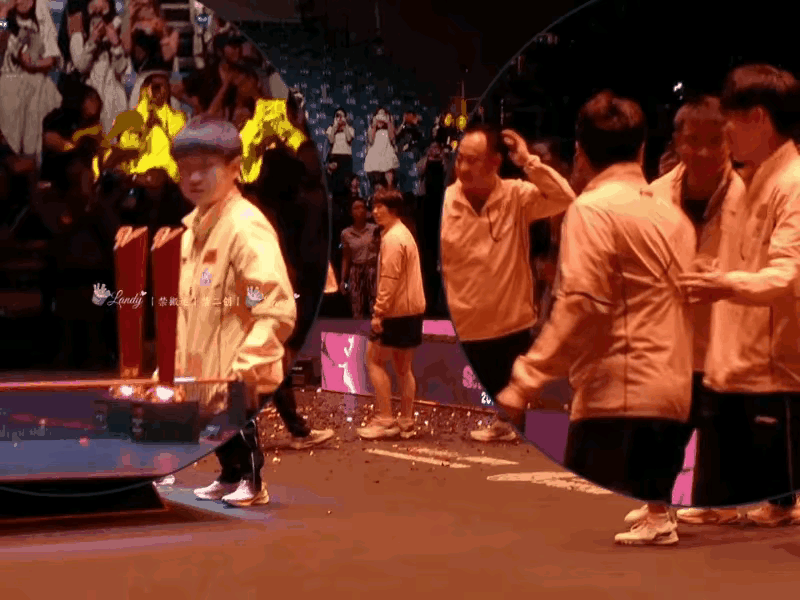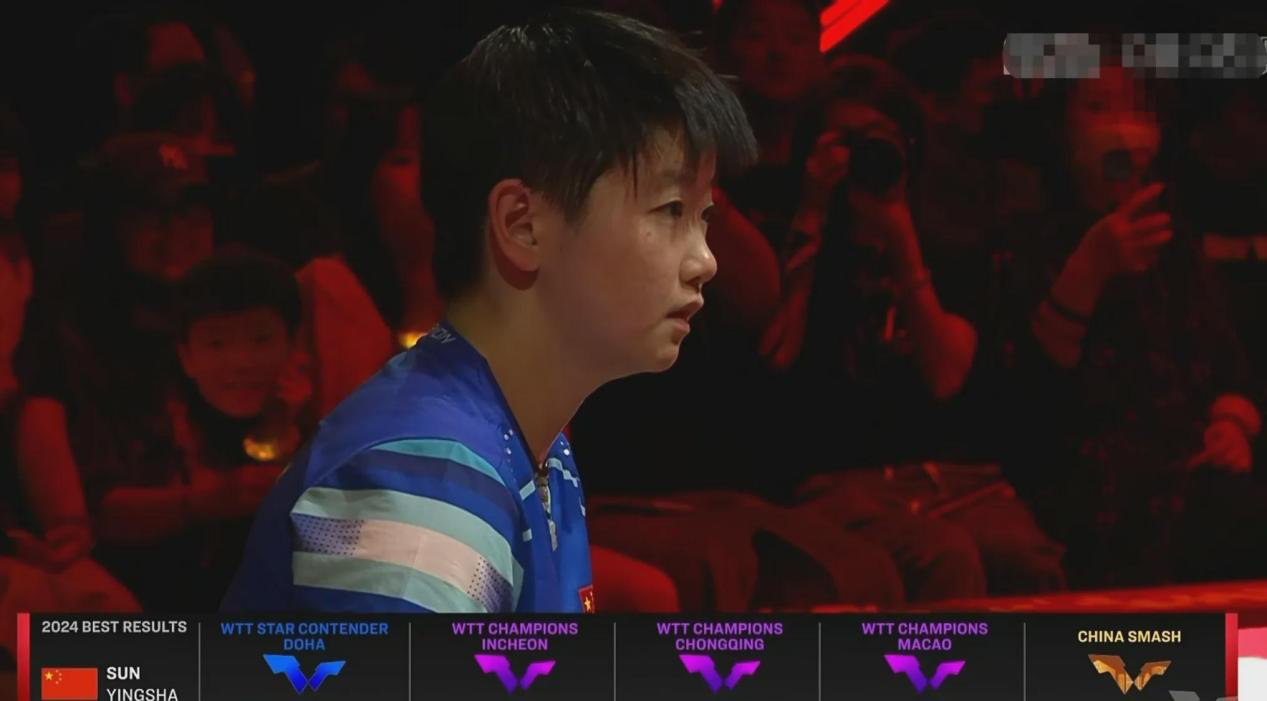1979年,51岁的褚时健接任快要倒闭的玉溪卷烟厂厂长,当时厂里领导层不仅架子大,而且还不把他放在眼里。 1979年10月,褚时健正式走马上任玉溪卷烟厂厂长。眼前的这个烂摊子让这位年过半百的新厂长一时不知从何下手。 在1960年以前,玉溪卷烟厂年产12.23万箱香烟,年创税利3000多万元,是全国知名的卷烟大厂。然而到了1979年,这个曾经的"明星企业"已经沦为当地的笑柄。 玉溪卷烟厂有着2000多名职工,却只能年产5.3万箱香烟,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企业负债率高达500%,工人们只能挤在十几平米的土坯房里过日子。 工厂生产的"红梅"牌香烟质量极差,当地人形容这是"砖瓦厂出的饼干、钢铁厂生产的香烟"。这种香烟抽一口就能呛得人连连咳嗽,市场上根本无人问津。 产品卖不出去,库房里的存货堆积如山。工厂的仓库都放不下了,只能让职工把成箱的香烟搬回家存放。可工人家里连睡觉的地方都不够,哪还有空间放这些卖不出去的烟? 表面上看是企业经营不善的问题,实际上却是权力之争的结果。玉溪卷烟厂内部分为"炮派"和"八派"两大阵营,每个派系都掌握着五名领导干部的支持。 这种派系之争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正常运转。从车间的生产安排到人员的调动,都要看是哪个派系说了算。两派势力此消彼长,谁也不服谁。 对这两派来说,褚时健是个彻头彻尾的"外来人"。他们认为这个"空降兵"不懂卷烟生产,也不了解厂里的情况,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 开会时,不管褚时健提出什么建议,总有人站出来反对。即便是最基本的生产管理措施,也会因为派系之争而难以推行。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平日里水火不容的"炮派"和"八派",在对抗新厂长这件事上却达成了一致。他们宁可维持现状,也不愿意接受改革。 两派人马给褚时健安排了一间年久失修、只有14平方米的破旧宿舍。这间堆满灰尘和蜘蛛网的小房子,就是他们给新厂长的"见面礼"。 面对厂内的重重阻力,褚时健首先找到了玉溪地委书记胡良恕。他提出一个请求:"在我站稳脚跟之前,请地委暂时驳回卷烟厂干部的一切无理诉求。" 有了地委的支持,褚时健开始着手处理厂内的各项事务。他暂时集中处理权,不给两派钻空子的机会。 对于那些无故旷工、消极怠工的职工,褚时健采取了严格的考勤制度。对于散布谣言、煽动对立的人员,一律按照规章制度处理。 当"炮派"的领导人杨副厂长到地委告状时,却碰了一鼻子灰。地委领导不但没有支持他的诉求,反而要求他好好配合褚时健的工作。 在处理完"炮派"的阻挠后,褚时健又遇到了"八派"的刁难。党委书记采取了更为隐蔽的不合作态度,表面上同意厂长的决定,背地里却处处设障。 1981年8月,一件意外事件让褚时健有了展现能力的机会。厂里的一台锅炉突然出现故障,这是烘烤烟叶的关键设备。 当时的修理组组长声称需要40天才能修好,工程师也表示自己不懂锅炉维修。这种敷衍的态度让褚时健当场决定:"我来修,愿意跟着我的留下来。" 褚时健带领18名工人分成三组,采取三班倒的方式连续作战。他不但自掏腰包给加班的工人买饭,还亲自在现场指导。 4天后,锅炉修好了。褚时健立即为参与维修的工人申请了加班工资,还批准他们休假两天。 褚时健深知,光靠制度还不够,还要解决职工的实际困难。当时的工人住房条件极差,一家三代挤在十几平米的土坯房里。 褚时健决定建设职工宿舍楼。当基建科消极怠工时,他立即撤换科长,重新调配人手,加快工程进度。 四个月后,一栋可容纳72户的宿舍楼建成了。首批入住的都是住房困难的一线职工,这让全厂职工看到了希望。 1981年,褚时健开始着手改善产品质量。他首先针对红梅烟"又苦又辣"的问题,从原料采购开始严格把关。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原料问题,1985年褚时健在考察美国后有了新的想法。他请来农业专家,在云南寻找最适合种植烟叶的地区。 在解决了原料问题后,褚时健又从英国引进了89套世界先进水平的卷烟设备。新设备的引进,让玉溪卷烟厂的生产能力有了质的飞跃。 这些努力很快就收到了成效。1983年,玉溪卷烟厂的年产量达到了46.5万箱,创造税利2.3亿元,一举打破了行业记录。 从1984年开始,玉溪卷烟厂进入了快速发展期。短短5年时间,年产量就翻了一番,成为中国第一个年产量突破百万箱的卷烟企业。 到了1988年,玉溪卷烟厂在利润、人均创造利税等八项指标上,全面超越其他企业,成为全国烟草行业的标杆。 进入1990年代,玉溪卷烟厂的发展更上一层楼。它不仅成为亚洲第一的烟草企业,在世界烟草企业排名中也名列第五。 1991年,玉溪卷烟厂成为全国烟草行业唯一的"国家一级企业"。这一时期,企业年创利税高达200亿元,占据云南省财政收入的60%。 1995年,玉溪卷烟厂正式更名为"红塔集团"。这个名字来源于工厂旁边的红塔山,也象征着企业如山一样的稳固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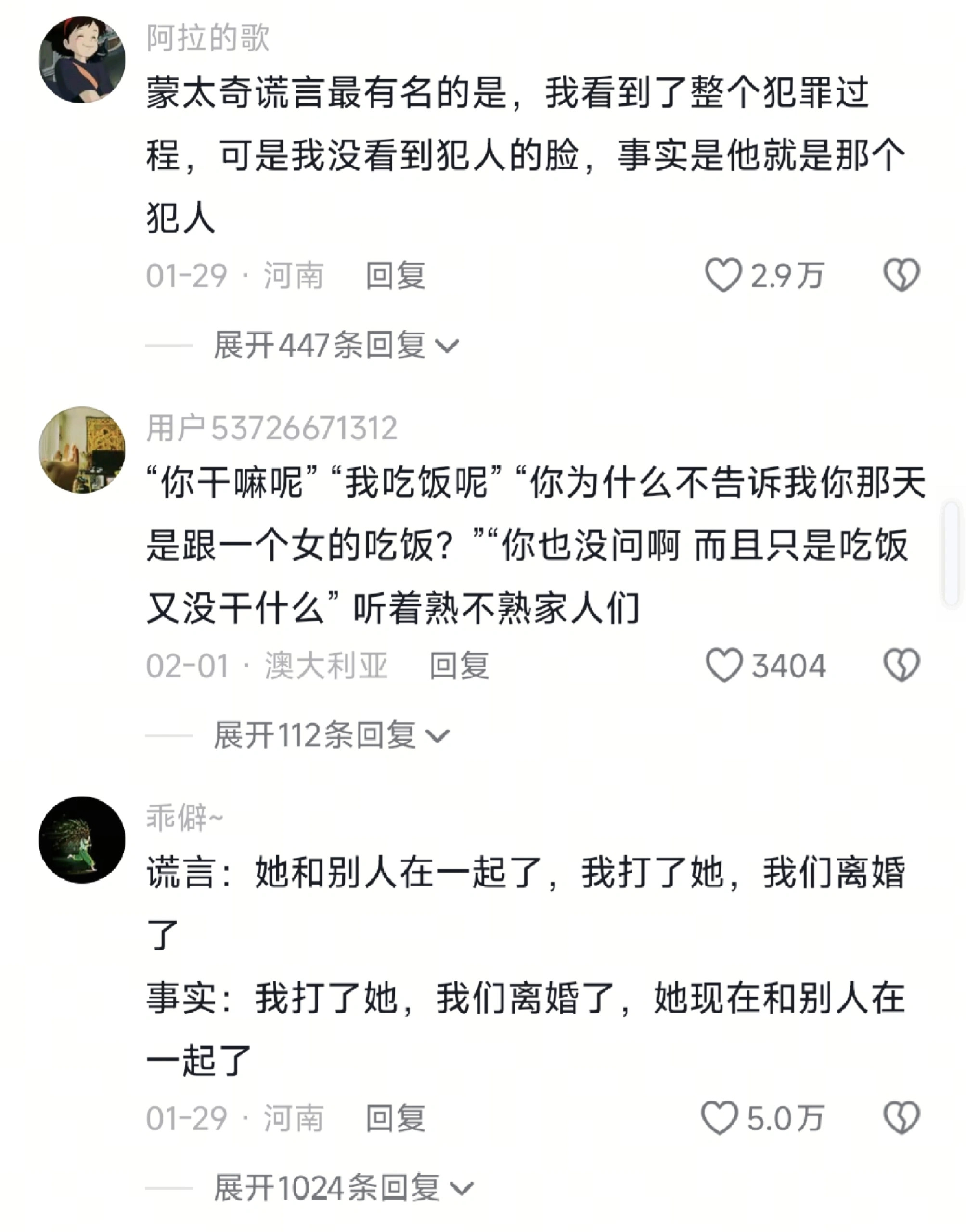




![饺子:早知道十亿十亿画了[哭哭]](http://image.uczzd.cn/3072074448941798162.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