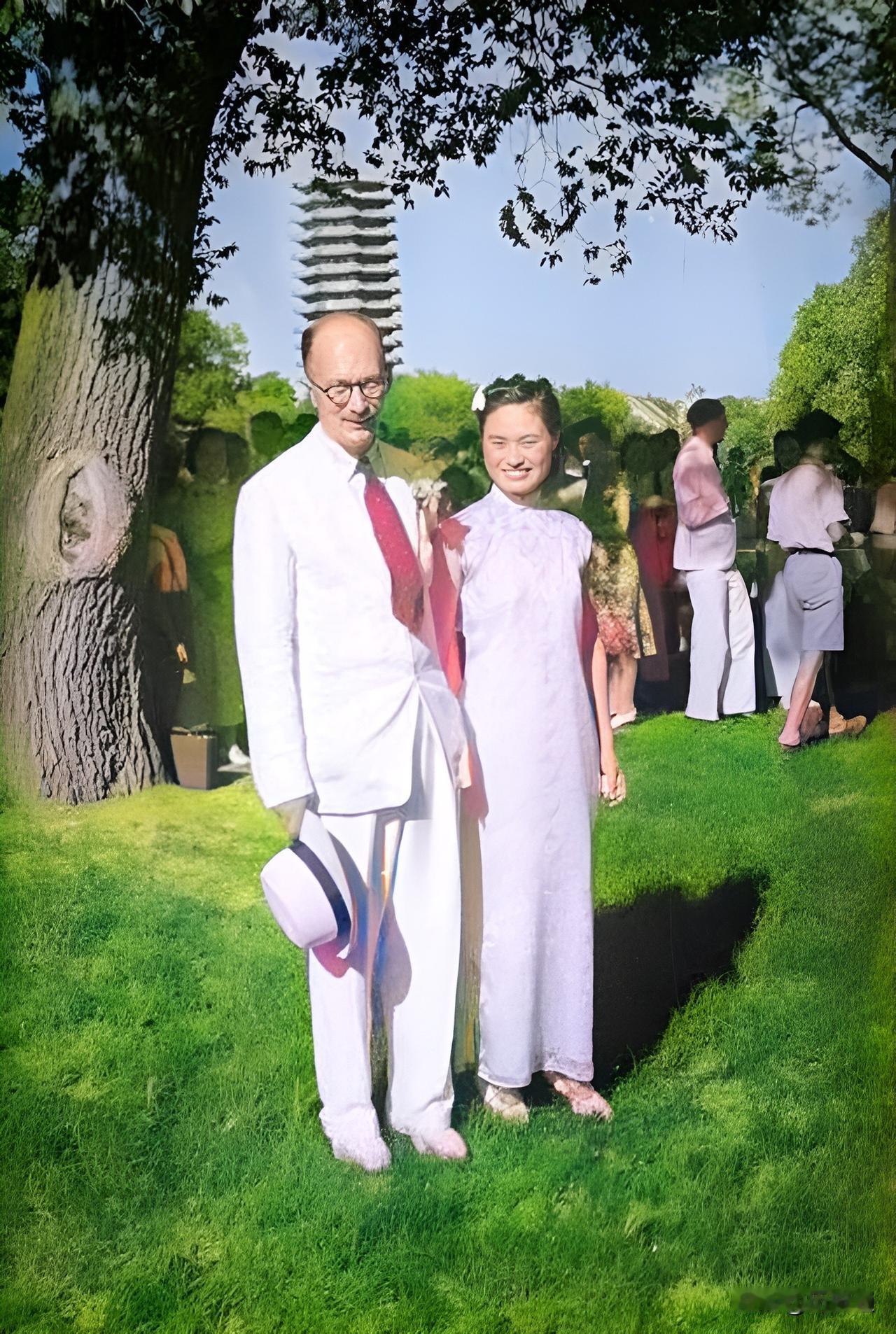1955年,一甘肃女子正在院内晾衣服,一位四处转悠的男人,突然径直闯了进去,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脚看,女子十分尴尬,不料男人竟柔声问道:“脚后的陶器可否给我看下?” 一阵急促的脚步打破了院子的宁静,1955年的甘肃农村,春风拂过黄土,韩翠兰刚抬起头,一个男人已经站在她面前,指着脚边的陶罐低语:“这东西,能给我瞧瞧吗?”韩翠兰愣住了,手里的湿衣服差点滑落。 她低头一看,那个红褐色的破陶罐歪歪斜斜地靠在墙根,满是尘土,平时她压根没当回事。这男人是谁?怎么突然闯进她家院子,还盯着这么个不起眼的东西?她皱起眉,后退一步,心里泛起警惕。 男人见她神色不对,赶紧摆手,脸上挤出一丝笑:“别误会,我是县文化站的,叫刘志强,下来收文物用的。”他边说边从布包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上头盖着鲜红的公章。韩翠兰瞟了一眼,字不认识,但那公章她见过,村里开会时支书也拿过类似的。 她松了口气,可还是有点疑惑:“这破罐子有啥稀奇的?”刘志强没急着回答,蹲下身,小心翼翼地捧起陶罐,像捧着个稀世珍宝。 罐子不高,16厘米左右,宽25厘米,口小得只能伸进两根手指,通体红褐,表面粗糙得像刚从土里刨出来,两边还伸出两个横木,肩上有俩圆环,活像个歪七扭八的小船。 “这个啊,可能比你想的重要得多。”刘志强终于开口,语气里带着点兴奋。他指着罐身上的圆环说:“你看这儿,能穿绳子挂身上,古代人用它装东西,估计是酒。” 韩翠兰歪着头,越听越糊涂:“装酒?就这玩意儿?”她心里嘀咕,这东西扔院子里多少年了,连鸡都不稀罕啄两口,能值啥?可刘志强却越看越起劲,翻来覆去地瞧,手指轻轻摩挲着罐身,像在跟它对话。 这事儿还没完。几天后,村里传开了消息,说韩翠兰家有个“宝贝罐子”,连县里人都看上了。邻居张婶跑来凑热闹,探头探脑地问:“翠兰,那罐子真值钱啊?”没等她回答,张婶的侄子——一个跑古董买卖的小贩李二狗——风风火火赶到。 他一进院子,二话不说蹲下去端详那陶罐,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这可是好东西!夏朝的,少说五千多年了!我出五百块,你卖给我咋样?”五百块!韩翠兰眼睛一亮,那年头,五百块能盖半栋房,她差点就点了头。可就在这时,门吱呀一声开了,她男人王大柱扛着锄头回来,一听这茬,脸立马沉下来:“卖啥卖?这不是咱私人的东西!” 王大柱把韩翠兰拉到一边,低声说:“翠兰,这玩意儿是文物,国家的,咱不能卖。万一这家伙转手卖给外国人,咱不就成罪人了?”韩翠兰一听,气得直跺脚:“有钱不赚,你傻啊?”可转念一想,又觉得有点道理。 她听说过村里老辈人讲,洋人早年间从中国弄走不少宝贝,现在想看自家的东西还得跑国外去,多憋屈啊!两口子争了半天,最后韩翠兰咬咬牙,挥手把李二狗打发走:“不卖了,你走吧!” 这陶罐最终没落进古董商手里,而是被刘志强带回了文化站。几天后,他托人捎信回来,说这东西鉴定过了,叫“船形彩陶壶”,是夏朝时候的喝酒器具。 那年头的人把罐子做成船形,可能是盼着酒像鱼一样多得喝不完,透着股朴实的浪漫。韩翠兰听完,咧嘴笑了:“原来是个酒罐子,怪不得做得这么怪。”村支书还特意跑来表扬她,说她为国家文物保护立了功,县里会给点奖励。 她摆摆手,没太在意,继续晾她的衣服,可心里却多了一丝得意。 故事到这儿还没完。这件“船形彩陶壶”后来被送到了中国国家博物馆,成了国宝级的展品。专家研究发现,它出自新石器时代晚期,比夏商周还早,可能是仰韶文化或龙山文化时期的产物。 那时候的人刚学会酿酒,技术粗糙,拿红土烧出这么个罐子,既能装酒,又方便带着走。壶身上那简陋的渔网纹和船形设计,像在诉说古人对丰收和畅饮的向往。 国家博物馆里有个类似的船形陶壶,出土于陕西宝鸡,1958年挖出来的,长24.8厘米,高15.6厘米,跟韩翠兰家的差不多,也许是同一时期的“兄弟”。 这小小陶罐,串起了5000多年前的酒香和1955年的乡间烟火。它不光是个喝酒的家伙什,更像一面镜子,照出古人的智慧和今人的抉择。如今,它静静躺在展柜里,等着每一个路过的人,去听它背后的故事。 韩翠兰大概没想到,脚边那个不起眼的陶罐,竟藏着五千年的秘密。从远古的酿酒人到她的院子,再到博物馆的灯光下,它见证了时光,也提醒着我们:历史就在身边,珍贵的东西,值得好好守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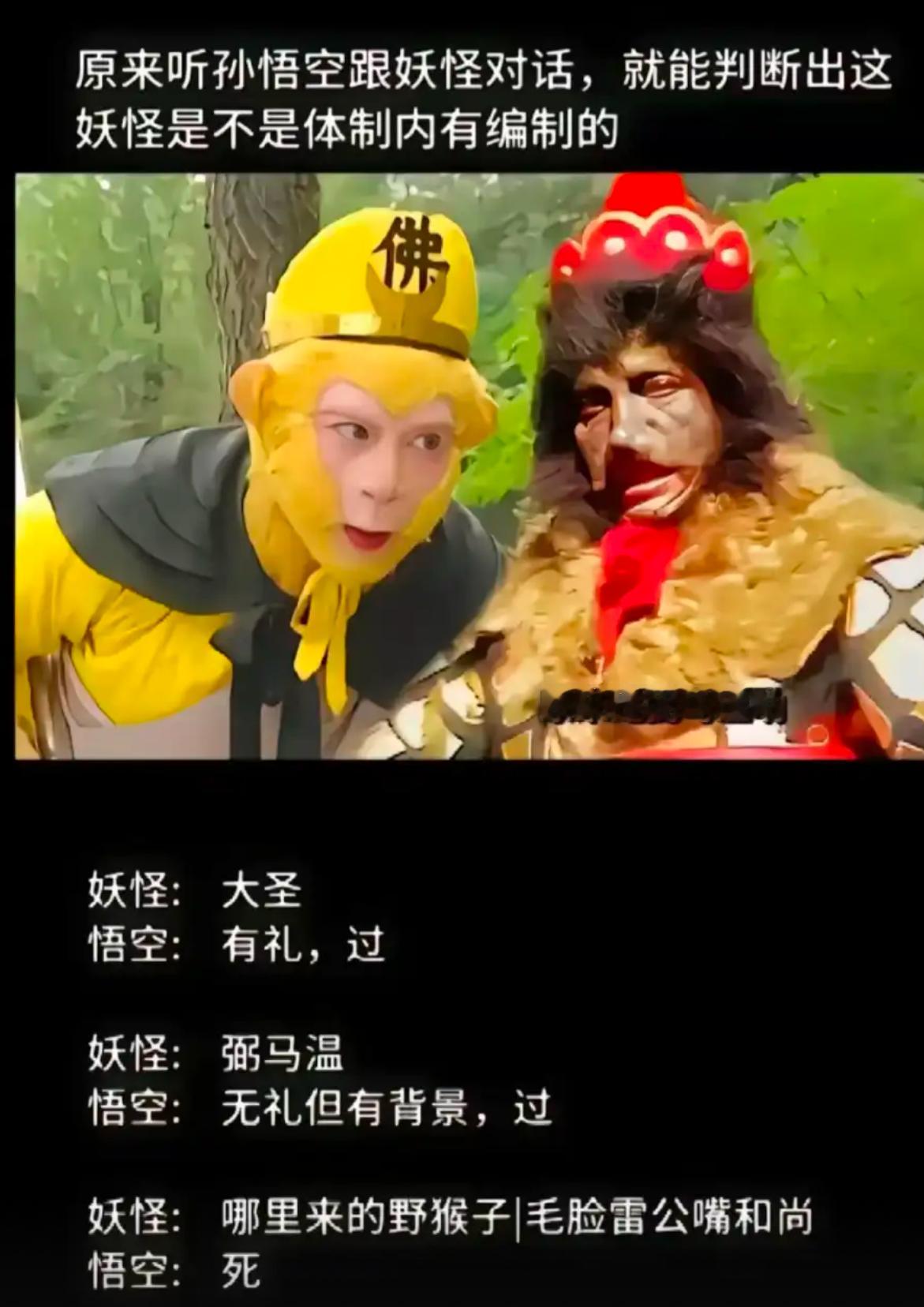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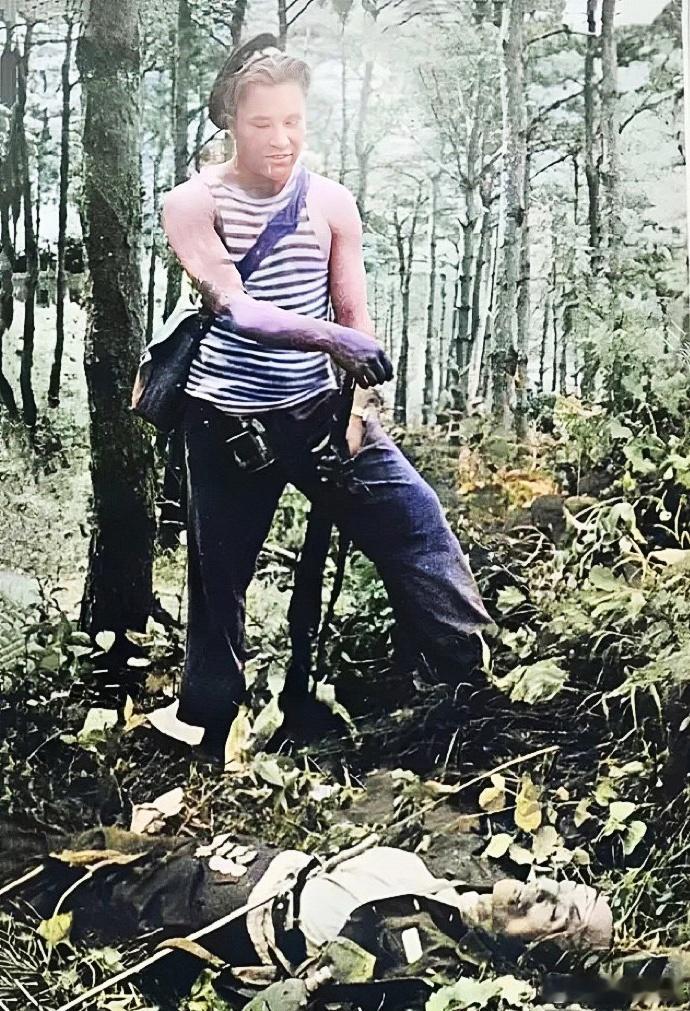


![吴敬平老教练不甘寂寞,又发和樊振东的老照片[捂脸哭][捂脸哭][捂脸哭]吴教练一相情愿](http://image.uczzd.cn/2250288134115468044.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