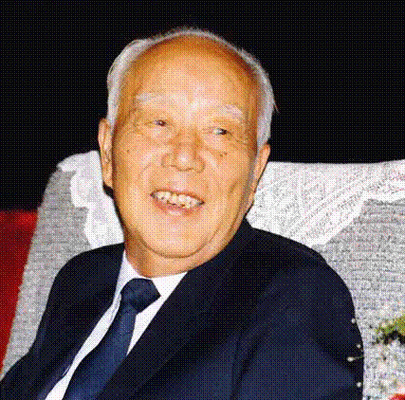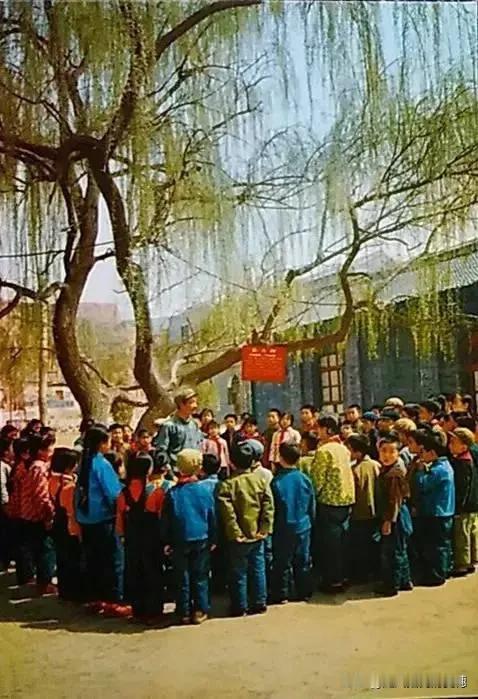3月2日,万里主持国家农委党组会,对陈永贵等人提出批评,态度强硬且措辞严厉:“你们不和群众一道想办法,改善生活,发展生产,只是学大寨,大呼隆,只念大寨经,不调研,只搞穷过渡,是习惯性的。” “农民吃不饱,不见你们说个啥话;农民吃饱了,不见你们高兴。农民搞了包产到户,你们坐在楼上评头论脚,说破坏了社会主义。”“那是你们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农民不需要!” 万里还点名批评了有的部长。万里要求,农口领导干部“深入农村调查两个月,亲身感受一下,广大农民在想什么、在做什么。”“下去一看,就有生动活泼,朝气蓬勃的局面”。随后,国家农委组织有关农口各部140余人,其中部级干部20余位,分成15个调查组,从4月开始,深入农村两个月。6月中下旬,调查组回京,先在各部门总结。7月18日,万里听取部长们汇报。这次调研被称为中央农口的整风活动,是农口机关政策氛围转变的标志性事件。 包产到户历经了各种挫折。 时间回到1961年2月,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挺身而出,创造性地提出了“按劳动力分包耕地,按实产粮食记工分”的联产到户责任制,这一大胆尝试首先在各个县的“责任田”试点中落地生根,随后迅速蔓延,短短两个月内,便覆盖了全省39%的生产队。曾希圣还于3月底亲笔致信毛泽东,为“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举措据理力争。国家粮食部对此高度重视,特别选取肥东县的路东和路西两个生产队进行对比调研。 结果显示,实行责任田的路东队夏收粮食亩产达到112斤,秋收更是增至245斤,而依旧吃大锅饭的路西队,夏收和秋收亩产则分别为100斤和195斤,差距一目了然。几乎与此同时,广西龙胜县也悄然开启了分田单干的试验,全县1994个生产队中,有一半毅然决然地将土地分包给了农民。时任农村工业部部长的邓子恢亲赴南方调研,并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 其子邓淮生后来回忆,当问及父亲对包产到户的看法时,邓子恢深邃地指出:“包产到户绝非单干,而是农村经济管理的一种创新形式,因为土地的所有制并未改变。这就如同工人计时与计件工作的区别,只是计算单位时间内能生产多少个零件。农民亦如此,需要核算一年内能交出多少粮食。工人可以包工包料,农民为何不能尝试这种灵活的方式呢?” 安徽与广西的勇敢探索,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激烈辩论。《人民日报》特设专栏,成为各方观点交锋的阵地。支持者视之为激发农民积极性、提升粮食产量的灵丹妙药,而反对者则担忧这是步向农村资本主义的歧途,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一次重大倒退。 面对巨大的外界压力,安徽省委于7月郑重向中央提交报告,渴望得到政策的明确支持。至同年11月,安徽的“责任田”已扩展至91%的生产队。甘肃、浙江等地也纷纷效仿,正如《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一书所引用的甘肃农民的那句朴实而深刻的话:“我们的心向往进步,可肚子却太‘实事求是’了。” 自1961年起,邓子恢带领工作组深入福建、黑龙江、广西、河南等地,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基于扎实的调研数据,他于5月24日向中央和毛泽东呈交了《关于当前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在这份意见中,他深刻剖析了农村集体所有制存在的诸多混乱现象,如机关、企业侵占社队土地,社与社、大队与大队之间的土地平调问题未能彻底解决,以及虽然许多地方已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至生产队,但土地和耕畜仍归大队所有等。 邓子恢敏锐地指出,这些混乱的根源在于各级干部思想上固化的“不断革命论”,而忽视了革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对于以小队为核算单位30年不变的政策,普遍被视为权宜之计。 1961年秋,尽管已年逾六旬且身体抱恙,邓子恢仍坚持带领工作组南下调研。从河南到江西,再到他魂牵梦绕的家乡闽西革命根据地,每到一处,群众都纷纷表达了对包产到户的迫切渴望。年底,当他结束调研准备返回北京时,途径安徽合肥,决定稍作停留。他早有耳闻安徽农村悄然推行的“责任田”(因“包产到户”中的“户”字带有资本主义色彩,故巧妙改称为“责任田”),这次他渴望亲眼见证这一变革。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向他汇报,安徽已有39.2%的生产队试行了责任田,所到之处,社员责任心显著增强,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粮食产量增加,群众反响热烈。这是邓子恢首次亲密接触责任田,他一贯秉持的务实精神使他从安徽的实践中看到了农村复苏与发展的曙光,心中燃起了浓厚的兴趣。他当即表示:“你们的做法很好,我全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