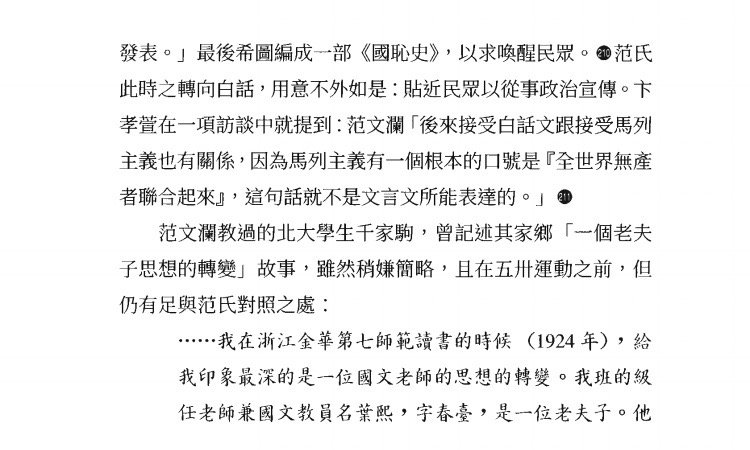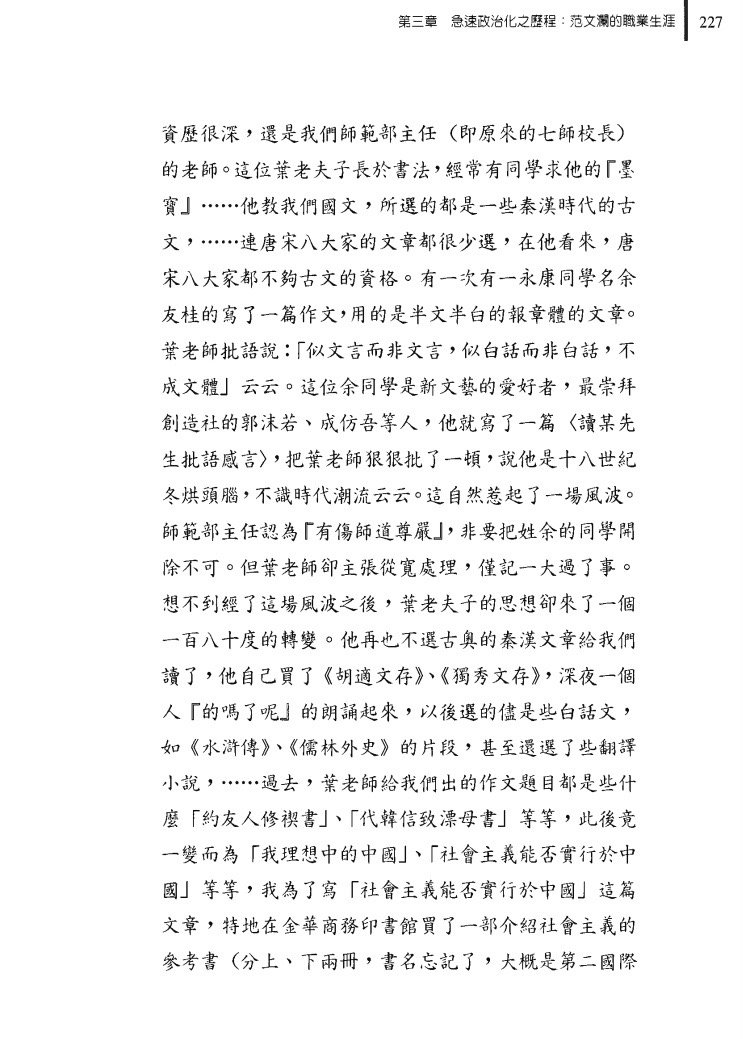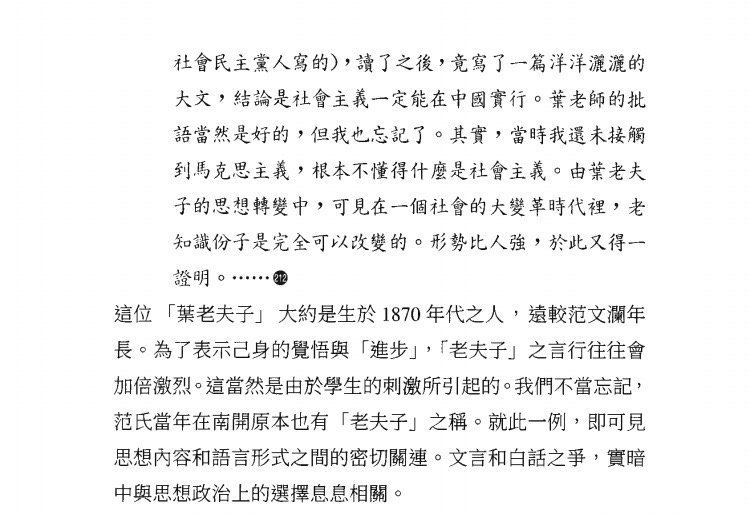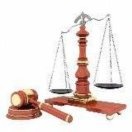范文澜从章黄门生、「选学余孽」一跃成为用白话文写作的左翼史学旗手,政治光谱从深右跨进深左,这样激烈的转变在风云激荡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并非个案,例如千家驹所举的一位叶老夫子(如图)
正如王汎森精彩地指出,“《新青年》 不停地变,新知识分子却不一定能赞同它每一阶段的主张。譬如南社领袖柳亚子,他赞同攻驳孔教,但不同意胡适的文学革命。又如胡适,他提倡文学革命,却未必赞同 《新青年》 往社会主义方面发展;而能同意其讨论社会主义的,也不一定同意它成为共产主义的喉舌。所以 《新青年》像一部急驶的列车,不断地有人上车,不断地有乘客下车,能共乘前一段路的,不一定能共乘后一段路。”
上车最晚的人,往往也“走的最远”(gone too f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