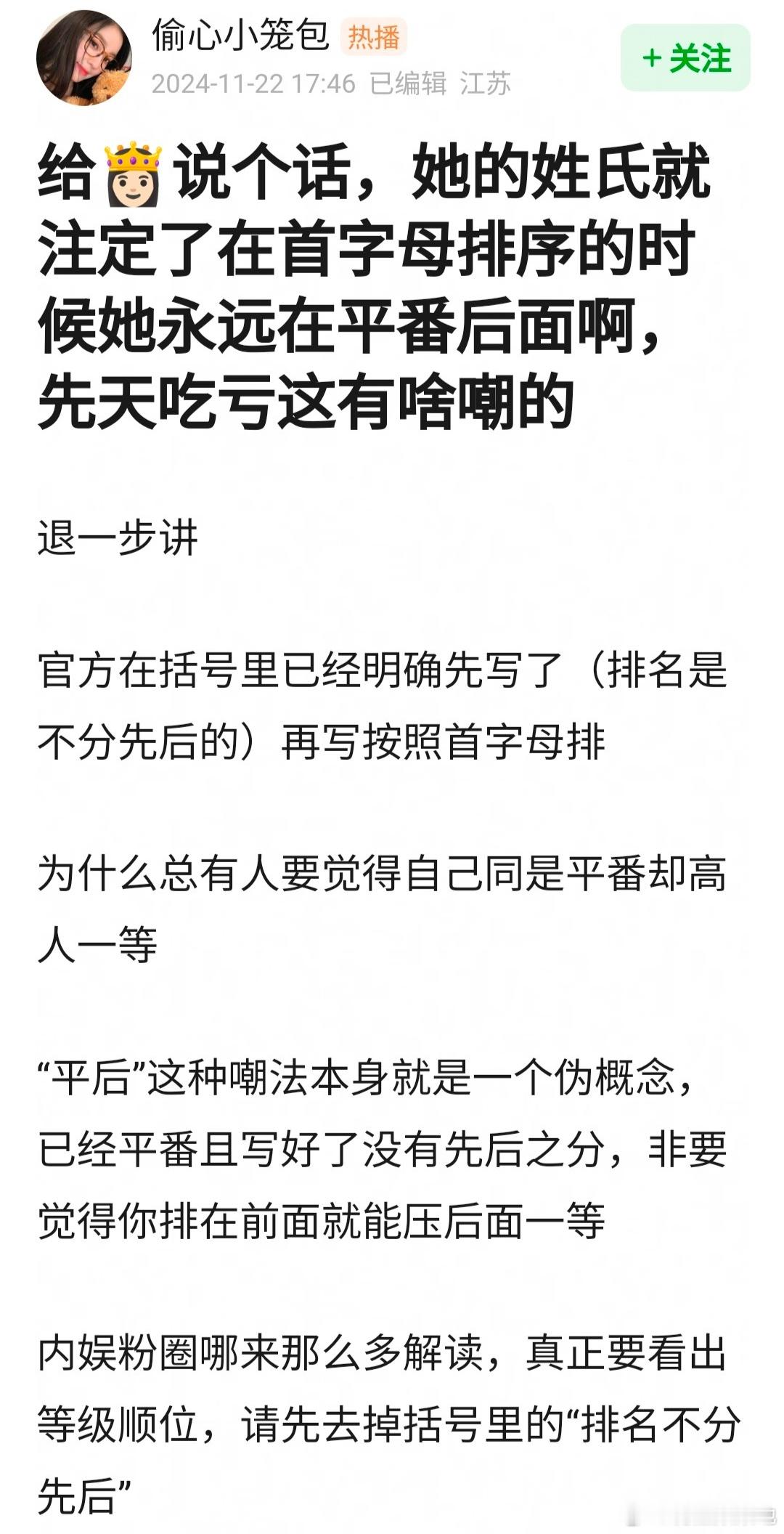简介:
据说,京城里妇孺皆知的人有两个,一个是皇帝,一个是甄家老女。
据说,京城里人人闻风丧胆的人也有两个,一个是自称黑山老妖的采花大盗,一个是一连克死了六个未婚夫的甄家老女。
我姓甄名离春,正是这个据说中的甄家老女。
其实,我并不老,堪堪正是曼妙双十年华,但人生苦短,我嫁了六次都未成功,谁知道在我有生之年,还有没有第七嫁呢。

精选片段:
据说,京城里妇孺皆知的人有两个,一个是皇帝,一个是甄家老女。
据说,京城里人人闻风丧胆的人也有两个,一个是称黑山老妖的采花大盗,一个是一连克死了六个未婚夫的甄家老女。
我姓甄名离春,正是这个据说中的甄家老女。就在方才,我试图跟桥头边卖肉的张麻子搭话,他一见我,顿时嗷的一声扔下杀猪刀,夺路狂奔而逃。他一边逃一边惊恐尖叫:“唉呀妈呀,甄家老女啊!”
霎时,街上男子,不管老少,顿如惊弓之鸟,纷纷躬身含胸,抱头鼠窜。
传闻所言不虚,我果然让人闻风丧胆。
我觉得心酸的很。其实,我不过就是想告诉张麻子他的钱袋子掉到地上了而已。
遥想几年前,我堪堪二八青葱年华时,京城里曾流传着一首脍炙人口的歌谣,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甄家好女,君子好逑。
那个时候,京城方圆数十里的世家公子青年才俊,扎了堆儿似的马蜂窝一样,蜂拥而至,纷纷上门提亲,什么情书啊,诗帕啊,纸条啊,我收了足足两箩筐,各大媒婆更是扛着严寒酷暑,没日没夜蹲守在甄府大门口,对我和爹爹围追堵截,生生踩扁了我们甄府二十又二副门槛。
七瞧八看,千挑万选,终于,某日爹爹两手一拍,给我定下了一门亲事。然正当两府大红灯笼高高挂,派帖子张罗喜事时,新郎暴毙了。
爹爹扼腕叹息一番,扬扬袖子,然后大手一挥,又给我定了一门亲。可悲的是,这次尚未等到红灯笼挂起来,新郎就提前暴毙了。
第三次,仍旧暴毙。
然后第四次,第五次……如此一直到第六次,这厢方才定下亲,那厢新郎骑马回去,脚一沾地,又暴毙了。
一连克死了六个未婚婿,于是,自然而然的,我被京中热爱八卦的长舌大妈大婶们讹传成妖了。是以,京中男子皆避我如避瘟神一般。不过短短四五年间,我就一跃从人人趋之的甄家好女落魄成了人人避之的甄家老女,中间的曲折起伏,着实令人欷歔。
我想,如果人生是出戏,那我这出戏也算得上是跌宕起伏荡气回肠了,只可惜的是,却是一出悲剧。
想至此,我不免叹了两叹,抬头望望天,天空湛蓝如洗,暮风将云朵吹得飘忽松散,有成群的乌鸦麻雀呼啦啦飞过,我在心里安慰自己,其实生活还是很美好的。
从兜儿里摸出几块铜板放到张麻子的钱袋子里,我挽起袖子,操起案上杀猪刀哐当哐当砍下两条猪腿,然后递给丫鬟小桃道:“等会回去炖了。”
我喜欢吃猪腿,这不是个秘密,但我喜欢吃猪腿的原因却是个秘密,这个秘密除了小桃和醉花荫的花魁瑶玉,就只剩我一个人知道——因为我喜欢云非白。
果然,小桃笑嘻嘻的说:“小姐,你又想云公子了。”
翩翩少年郎,冠盖满京华。我想京城里当得起这句话的非云非白莫属。
第一次见到云非白是在我克死了我的第六个未婚婿的第九九八十一日。那日他作为新近迁京,久负盛名的江南第一钱庄的少庄主,应我阿爹的邀请前来甄府赴宴。
犹记得那是个蝶舞蜂忙,夕阳染幽草的黄昏,圆圆的夕阳像个摔烂的红柿子挂在半空中。我坐在后花园里的一个亭子里满嘴流油的啃着猪腿,忽听一个声音问我:“猪腿这么好吃吗?”
我从碗里抬起头来,这才发现旁边不知何时站了个男子,蓝衫广袖,清雅温润,嘴角噙了丝微微笑意怔将我望着。
我抹了一把嘴,想了想郑重答道:“淡定使人长寿,猪腿使人忘忧。”
他脸上闪过一丝错愕,旋即又忍不住笑了起来,又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我在心里斟酌了一番又斟酌了一番,然后干脆利落的回答:“甄家老女。”
甄家老女这几个字满京城里谁人不知谁人不晓,纵然他才来京城不久,想必也早听了我这个叫人如雷贯耳的大名。
我原以为他会面色一白,惊叫一声,然后双手捂胸夺路而逃。哪知他只是微微一愣,唇边的笑意愈发的深,然后走到我面前来,从袖子里掏出一块白色绢帕递给我,道:“你嘴角的油渍还没擦干净。”
我惊了。倒不是因为我嘴巴上的油,而是第一次见人听到甄家老女这四个字后,还能镇定如斯,淡定如斯。于是,惊了之后,我望着他傻了。
等我回过神,他已经走远了。
翩翩风姿,黑发如墨,我心里一动,顿时拍案而起,扬着帕子高声叫道:“喂,你叫什么名字?”
他在一棵凤凰树下驻足,回过头来,冲我微微一笑,道:“云非白。”
已记不得是他的这一抹笑醉了我的眼,还是他的那方白手绢惑了我的心,我忽然间就开了情窦,动了春心。咳,简而言之,我对他一见钟情了,并且从此恋上他了。
但我的这个恋是暗的。作为一个一连克死了六个未婚婿的老女,我实在没有理由正大光明的明恋。
暗恋让人憔悴,也让人冲动。
某日,我心情愁闷的去醉花荫找瑶玉诉我对云非白的衷肠。她一听,戳着我的脑袋,道:“敢爱敢恨才是真女子,似你这般畏畏缩缩,简直丢人。那些个所谓被你克死的男人,是时辰到了,被阎王爷收回地府干活去了,与你何干?你且莫要庸人自扰,大大胆胆的去跟他表明心事。”
我那时喝了几口酒,脑子模糊,一听,深以为然,于是回去提了把菜刀去向云非白表白。
他当时正在后院石桌前看书。我悄悄的爬上院墙,拿着菜刀,默默的在心里把我事先演练的表白过程在脑子里过一遍。
我开口叫他,他放下书朝我走来,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跃下墙,然后纵身扑上去将菜刀架到他脖子上,恶狠狠的问他:“我要嫁你为妻,你从是不从?”
他若答从,那么皆大欢喜。若是答不从,我便把鼻子一哼,恶狠狠的威胁他:“那我就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孰料,我正认认真真的温习着,忽听一个声音响起:“阿离,你这是在做什么?”
哐当,我手上的菜刀掉地上去了。
我觉得他这个阿离真真是叫的美妙又动听。虽则是第一次听,我却觉得亲切的很。
我干哈哈一笑,指着他院子里栽的竹子,道:“我见你这院子的竹子长的颇好,想砍一根回去栽栽。”
他将菜刀捡起来,拿在手上,温言笑道:“砍的竹子怎生栽的活,明日我着人给你送几株去。”
我干干一笑。他个子高,院墙却矮,是以,我骑在院墙上恰恰与他平视。
正是黑夜里,风乍起,吹起他耳边发丝,我一时看傻了眼。正怔然间,他却忽然上前来握住我的手,微微蹙眉道:“夜里寒凉,怎生穿的这样薄?
我一个激灵,从墙上滚下,落荒而逃。佛说,人生总是充满着变数和意外,以一颗平常心处之,方能拈花一笑,坐看庭前浮云变幻。
我深以为然。
但很显然,我远远未达到这个境界。
狼狈奔逃回去后,我很是对月欷歔感叹了一番。
第二日傍晚,金乌西沉时,小桃端上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猪腿,我正欲举筷,丫鬟突然来报,云公子带着家丁,扛了几根竹子来。
我怔了一怔,然后啪嗒放下筷子,起身奔到铜镜前,画眉点唇。
云非白正同爹爹在前厅喝茶,见我进去,唇角一扬,眼里是满满笑意。
我并未做亏心事,却被笑得面上发烫。
座上爹爹忽然两手一拍,惊道:“嗳哟,我怎么忘了还有公文未批完!”
言毕,扼腕叹息着同云非白作辞,扬一扬袖子,走了。身姿甚是潇洒。
这厢云非白走到我面前,望着我含笑道:“你昨天说想栽竹子,我从院子里挖了几株给你送了来。”
我做出一个得体的笑容:“倒多谢了。”
他却未答话,只把一双眼睛含笑将我望着。我干干一笑,正欲讲话,忽听他开口:“你的眉,画的很好看。”
我顿时像被迎面泼了一盆滚油,面皮滚烫滚烫。
云非白这厮,作孽。
我揉了揉眉毛,干笑两声,道:“是么。”
他脸上笑意愈发的深。顿了顿,问道:“竹子想栽在哪儿?”
我想了想,道:“栽在后院池塘边罢。”
于是,我们扛着竹子慢慢踱去了后院。
金乌已沉,有风起,池塘水中野鸭三两只。
云非白放下肩上竹子,回头笑对我道:“我挖坑,你栽竹子。”
我大惊。想他名冠京城的天下第一钱庄少庄主居然亲来我家挖坑栽竹,这是多么奇妙又值得八卦的一桩事。
惊过之后,我把他这话细细品味一番,顿觉和“我织布来你耕田”有异曲同工之妙,于是心下窃喜之,欣然答应。
家丁小厮见我二人亲揽了这个体力活,顿时欢喜了得,兴奋的奔走相告,取来铁锹、水桶,便一哄而散。
栽树确是个体力活,我素来惫懒,此番却做的极是兴趣盎然。当然,乃是因为某人。
他栽树来我挖坑,他提水来我培土。私以为,这是个很容易滋生某种情愫的氛围和时机。
果然不负我所望,在我第三次将竹子栽歪时,云非白放下铁锹,微微笑着上来握住我的手,轻声道:“再往右一点。”
我强忍着没将喜形露于色,顺势将手往他手掌心里缩了缩。
佛说的很对,人生无时无刻不充满着变数和意外。我也无时无刻不深以为然。于是,悲剧发生了。
就这么一缩,但闻“喀嚓”一声巨响,一道闪子当空劈下,竹子“咔”的一声被削掉半截,落到池塘里,惊起野鸭哀叫连连。再一看,那竹子恰恰的从我和云非白握在一起的手边截断,正滋滋冒着青烟。
我目瞪口呆。我一连克死了六个未婚婿,方才不过只是碰了碰云非白的手,便引来天雷,我登时不由得将自己惊为妖孽。
我觉得沮丧又哀伤。我果然是个孤独终老的命么?
云非白拉着我往后退了一步,皱眉望望天道:“许是想下雨了,这些竹子暂放在这儿,且先回去罢。”
孰料,他话音这厢落下,那厢便见天色陡变,乌云翻滚,如注大雨霎时顷下。
于是,自然而然的,我们酣畅淋漓的被大雨瓢泼了一回。待到家丁丫鬟们将伞送来时,雨已骤收。
彼时,我正靠在云非白胸口前,哆哆嗦嗦的抖着,那些个家丁丫鬟掩嘴偷笑,将伞递过来,嘻嘻乱笑着撒腿跑走了。
我这才惊觉自己整个人几乎都贴着云非白,顿时把脸一红,跳开身,撑伞欲走。
云非白却忽然握住了我的手。
我回头,撞击他幽深的眸里。他轻声问:“阿离,我若娶你为妻,你愿意吗?”
我望着他发梢啪嗒啪嗒往下滴着的水珠,怔住。
“阿离?”
我回过神,涩然一笑:“我是甄家老女,你难道就不怕……”
他低笑一声,截断我的话,道:“若怕,我就不会说这话了。”
我觉得鼻子酸酸的,仰头朝天眨了眨眼,然后望着池塘中的一双戏水寒鸭,道:“雨过天晴,鸳鸯成双,适宜求婚。”
他忍俊不禁,握了握我的手,道:“明日我便来提亲。”
夜晚回去,我开始欢欢喜喜的找花样子,准备给自己做嫁衣。但人生中有些事情是注定的,谁也预料不到。
我一连等了三日,也未见云非白登门提亲。着人去打听,才知他因淋雨伤了风,回去突然高烧,一连数日昏迷。
小厮回来疑惑与我说:“听说云公子身体一向很好,此番不过是伤风而已,却奈何高烧不退,一直昏迷,着实叫人奇怪。”
我默然不语。
又过了几日,云家忽然闭门谢客。
再过了几日,听说他醒了,但,却失忆了。
是真的失忆了。我爬到院墙上,骑在上面,看见他一个人静静的坐在院子里,夕阳黄昏里,影子在地上拉的老长。
我叫他:“非白。”
他回过头来,微微一愣,问道:“姑娘是?”
他病了一场,面容憔悴了许多,就连脸上的一如既往的温煦笑意也显得有几分苍白。
我歉意朝他一笑,然后默不作声的从墙上下来。
就在方才,我在街上突然遇到他,他从我身边过,带过一阵香,很快又隐没到如织人流中。
我想,他是真的忘了我,那个说娶我的温润男子,也真的是一去不复返了。
一株竹子引发这样一场悲剧,说来,着实叫人欷歔,细一想,我不免略有些伤感。但是没关系,幸好,我还未失忆,我还可以一边吃猪肉,一边想一想念一念他的笑。我想,老天终究还是待我不薄的。
回时,从一家卖花的摊子旁过,我一如既往的买了一盆君子兰。
经过云府时,我抱着花又一如既往的爬上了院墙。
云非白失忆后,我每天都会偷偷来给他送一盆君子兰。谦谦君子,温润如玉。我想,再也没有比君子兰更配他的花儿了。算一算,这是第六十一盆了。
已经整整两个月了。
院子里空空落落,风从墙角的竹子里穿过,吹起叶子飒飒作响,院当中的石桌上斜躺着一本书,翻开的几页被风掀起,在薄薄的夕阳中颤颤巍巍的立着。
我骑在墙上,看的忧愁又哀伤。
“你在看什么?”耳旁一个声音忽然响起。
“看人。”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有人吗?”
“没有。”
那声音便停了下去,良久未言。
我下意识的回过头去。
一张带着些许玩味的笑脸霎时撞进我眼底。是个陌生男子,眉眼出于意料的竟和云非白有六七分相像,只是脸上少了几许温润谦和,多了一分风流不羁。
我愣了一愣:“方才是你在和我说话?”
他耸了耸肩:“你以为呢?”
我朝一旁站着的小桃瞟眼过去,她绯红着一张脸,对我嗤嗤一笑。
我抚额望望天,放下花,正欲从墙上下来,却听得那男子慢悠悠道:“小包子,这么多年没见,你这爱爬墙头的习惯怎么还没改?”
喀嚓,我顿觉一记闷雷从我脑门上劈下。包子,包子,包子。我脚下一软,噗通,从墙上滚下去了。
小桃惊叫一声,听起来惨绝人寰。
面前这个杀千刀的罪魁祸首将我从地上扶起来,双手扣着我的腰,好似春风拂面一般浅浅一笑:“怎么,小包子见到我竟这么激动么?”
“你,你,你是……”我大惊。
“云洲。”他接下话。
果然,果然!我觉得心肝疼。冤家路窄,狭路相逢,这个世界多么奇妙又缺德。
我稳了下心神,仔细将他打量一番,这厮虽则长变了许多,但细一瞧,仍可见当年幼齿时轮廓模样。
他少时便生的面皮干净风流,如今添了身形和成熟气韵,愈发显得风流倜傥。
好是好的,然我觉得,不及某人。
那厮突然将脸凑到我面前,望着我道:“小包子为何这般脉脉含情将我望着?”
我一寒,回过神来。摸了摸脸,肃然道:“你看错了。”
他不以为然一笑,把手在我腰上加了几分力,“小包子怎么会在这儿?难道是听闻我今天进京,特特的赶来与我相会的么?”
我又一寒,推开他的手,认真的望着他道:“确然不是的。”
“哦?”他挑了挑眉,“那你骑在我们家院墙上做什么?”
喀嚓,我踉跄了一下。
缓了半晌,我指着云府,木然道:“这……是你家?”
他郑重点了点头。
“云非白是你什么人?”
“我大哥。”他说着顿了下,双眼微微一眯,“怎么,小包子认识我大哥么?”
我忽的心里一酸,岂止认识,岂止认识。
我望了望天,忽记起这几日京城里传的沸沸扬扬的一桩事,说是云府二公子将从苏州来京,和云非白共同接管第一钱庄事务。
我先前只晓得他姓云名洲,却从未料到他竟是久负盛名的第一钱庄的云家少公子。
看来,就连生活也是个奇妙又缺德的东西。
我扯了扯嘴角,答道:“不认识,只是听说,听说而已,云大公子名冠京城,谁人不知。”
“哦?”云洲那厮脸上笑意颇为意味深长,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目光里却透着些许冷冽,“那你爬到我们家院墙上来看什么人?”
我面不改色心不跳,微微一笑,答道:“我的风筝断了线,飞到你家院子里不见了,我在看是谁给拣去了。”
云洲嘴角抽了抽:“这半阴天的,你放风筝?”
我淡定的抖了抖衣裳上的灰,然后对他做了一个大家闺秀式的端庄笑容:“有何不妥么?”
“那,这盆花呢?”
这厮,真真好耐心,打破砂锅问到底,审犯人的么?
我瞥了他一眼,垫着脚将花抱下来,道:“差点忘了拿,多谢提醒。”
他嘴角又抽了抽。
我抱着花转身欲走,却被他一把扯住。他皱着眉将我望着,幽幽道:“你就这么走了?”
我望着他认真问道:“不然呢?”
他一噎。眼睛里明显窜出那么两簇火焰。这厮,还和当年一样德行。
我沉思了一下,我同他虽说小时候很有些过结,然毕竟是年少无知,算不得多大的深仇大恨。况又这许多年未见,今日也算是他乡遇故知,我若就这么刺啦啦的走了,的确显得有点人情淡薄世态炎凉。
于是我将花递到他手上,道:“这盆花送给你,算是为你接风洗尘。”
语毕,我冲他端庄一笑,举步离开。
走了好半晌,忽听背后传来他似低笑又似低叹的一声轻叹。
我想起云非白,也不由得轻叹了声。
小桃提着两条猪腿,摇摇晃晃的小跑着跟在我后面。
“小姐。”她叫了我一声。虽小心翼翼却掩盖不住八卦的兴奋和好奇。
我瞥了她一眼,挥挥手:“说吧。憋坏了,小姐我还得花钱给你请大夫。”
她扭捏一笑,道:“小姐,这个云二公子真真是风流倜傥的很呢。”
我默然不语。
“小姐,原来你还有个小名叫小包子啊。”
我继续默然不语。
然后听得她又继续八卦道:“小姐,你和云二公子像是以前就认识,你们……”
我打断她:“你是想问我和他之间有没有什么不得不说的故事,是么?”
她兴奋的连连点头:“小姐你好英明。”
我咬牙切齿道:“当然有,不仅有,还很多。”
和云洲认识那会儿,本老女还不是个老女,那时候,我还只是个白嫩嫩水灵灵的小姑娘,才刚刚不过九岁。
一晃十多年,樱桃红了好几茬,芭蕉也绿了好几茬,时间已够长,然我却记他记的比我喜欢吃猪腿这个事实还要清晰。
当初他回扬州,临走时在我胳膊上狠咬了一口,威胁我一定要记住他。至今我胳膊上还留着他的毒齿印子。
我也果然不负他所望,时刻将他铭记在心。偶尔啃完猪腿闲暇时,便将他曾经送给我的那块据说价值连城的玉石拿出来,磨一磨绣花针,然后一边绣花一边在心里咬牙切齿的将他腹诽一番。
我之所以记他记得如此不渝,绝然不是因为被他咬了一口,而是妖孽如他,给我留下了一段不堪回首,一回首便让我抑郁的往事。
话还得从我外祖父说起。
我的外祖父是个妙人,妙到何种境界呢,套用他自己的话就是:“你外公我不在江湖,但江湖一直流传着你外公我的传说。”
我深以为然。
我的外祖,姓展名扬,乃是名震天下的药师谷谷主展神医。神到什么境界呢,套用他自己的话就是:“没有你外公我治不好的病,除非那个病你外公我治不好。”
我深以为然。
我曾经问外公是怎样炼成神医的,外公语重心长的与我道,“把死马大胆的当活马医。”
语毕,又神秘兮兮的叮嘱我,“不可与外人道也,不可与外人道也。”
但这句话在我见到云洲的第一眼,就一不小心道了出去。
我打小身体就不好,因我娘亲去的早,爹爹又常年在任上,因此,我便一直跟着外祖住在药师谷里。云洲来药师谷的那年我已记不大清楚是哪一年了,那日我也记不大清楚具体是哪一日了,唯独记得的是,那个时候药师谷的桃花开的正盛,灼灼桃色,耀花了我的眼。
记得那日是个风和日丽,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好日子,我翻了翻黄历,曰,黄道吉日,宜嫁娶、纳婿、动土、沐浴。
于是我欢欢喜喜的去了药师谷南面的夏园里泡温泉。温泉在茂林掩映深处,泉边栽了几株柳树,垂柳拂面,彩蝶翩翩,我就这么泡啊泡,泡啊泡,睡着了。
醒来时,已是傍晚,晚风拂柳,夕阳山外山。一个锦衣华服小公子坐在柳树杈上,正一脸大方的将我望着。眉眼约摸不过十一二岁。
我傻了。
他却对我一咧嘴,笑了。
这一笑,带着三分的烂漫,七分少年老成的风流痞气,好似“倏”的一声,霎时间,千树万树梨花开,不仅耀花了我的眼,也耀伤了我的心。
我望着他悲悯道:“果然病的不轻,这回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外祖曾我与说,偷窥是种病。自然,偷窥别人洗澡也就是一种病了。但能将偷窥发扬到如此高的境界,面不改色心不跳,大方如斯淡定如斯,恐怕已是病入膏肓了。
作为神医的外孙女,我甚感悲痛。
那小公子显然没有领略到我话后面所蕴含的深厚悲痛之情,却把嘴角弯了弯,又是一笑,然后抬起手指朝我身后指了指。
我一回头,咔嚓,真他娘的黄道吉日,本神医外孙女的衣裳鞋袜正被一只大白雕刁在嘴里,迎风猎猎飞舞,煞是好看。
那白雕在半空中盘旋了几圈,很快振奋精神,翅膀一拍一抖,一头扎进云里,很快消失在了天外。
我于是又傻了。
好半晌,我才回过神来,望着树上幸灾乐祸的那张脸,问道:“这白雕哪儿来的?”
“我带来的。”他答的理所当然。
果然,果然。于是本神医外孙女怒了。
但我那时不过只是个八九岁的娃娃,怒了的结果只有一个,我哇的一声哭了。
我哭得声嘶力竭,惊天动地,惊起谷中乌鸦数只。
树上那小屁孩子顿时慌了手脚,从树上跳下,急道:“小包子,你莫哭,莫哭。”
包子,包子。我哭声嘎然而止,望着他怒气冲冲道:“我不叫小包子。”
他忍俊不禁,伸手摸了摸我的耳旁的两团发髻,道:“你扎个包子头,不是小包子是什么?”
我忿忿的瞪着他,觉得包子真真是委屈了我作为神医外孙女的形象,于是嗓子一转,继续嚎啕起来。
他来捞我:“莫要哭了,久泡温泉不好,你都泡了这么些时辰了,该上来了,不然一会儿该手脚发软了。”
我死命缩在水中。
他继续捞我。
本神医外孙女忍无可忍,终于爆发,声泪俱下控诉:“你这个大色鬼!”
他愣了一愣,停了手,半晌,忽的扬起唇一笑,很有些倜傥风流气派的与我道:“你放心,本公子会对你负责的。”
我继续扒着泉池子嚎啕,他无奈,抓耳挠腮一番后,得了一个绝妙法子,三下五除二便将自己外衣脱了,放到池边道:“你起来穿上衣服,我背过身去,保证不偷看。”
说完,便背过身去了。
本神医外孙女慢慢的停止了嚎哭,从侧面偷瞄了他几眼,发现他确是闭着眼的,于是这才从池子里迅速爬上来,捡起衣裳裹在了身上。
他笑嘻嘻的转过身来,将我上下一打量,道:“小包子,这件衣裳就当做你我之间的定情信物,送你与罢。”
我那时尚小,并未懂得定情信物是个什么物什,于是撇撇嘴巴,道:“我才不要你的东西,我也不叫小包子,你再叫,我就让我外公把你活马当死马医。”
他愣了愣,旋即面上浮出笑意:“原来你就是展神医的外孙女。”
本神医外孙女骄傲且傲慢的挺了挺胸,昂首阔步,准备离开。孰料,脚才一抬,扑通一声跌了个狗啃食。
真他娘的黄道吉日。
我被那小屁孩子扶起来,揉着膝盖,眼泪止不住啪嗒啪嗒往下掉。
他伸手往我脸上抹了一把,道:“小包子,莫哭,哥哥背你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