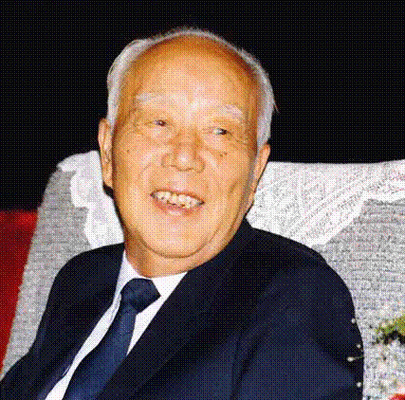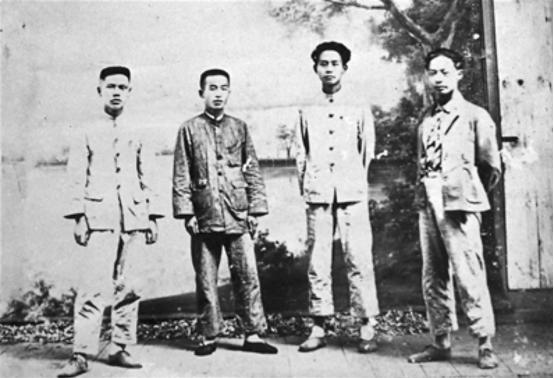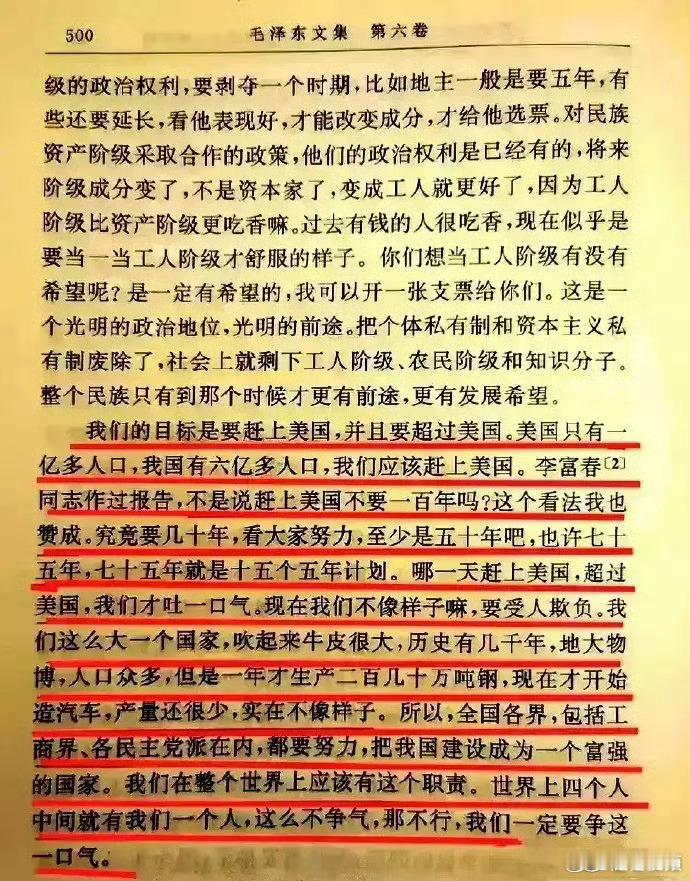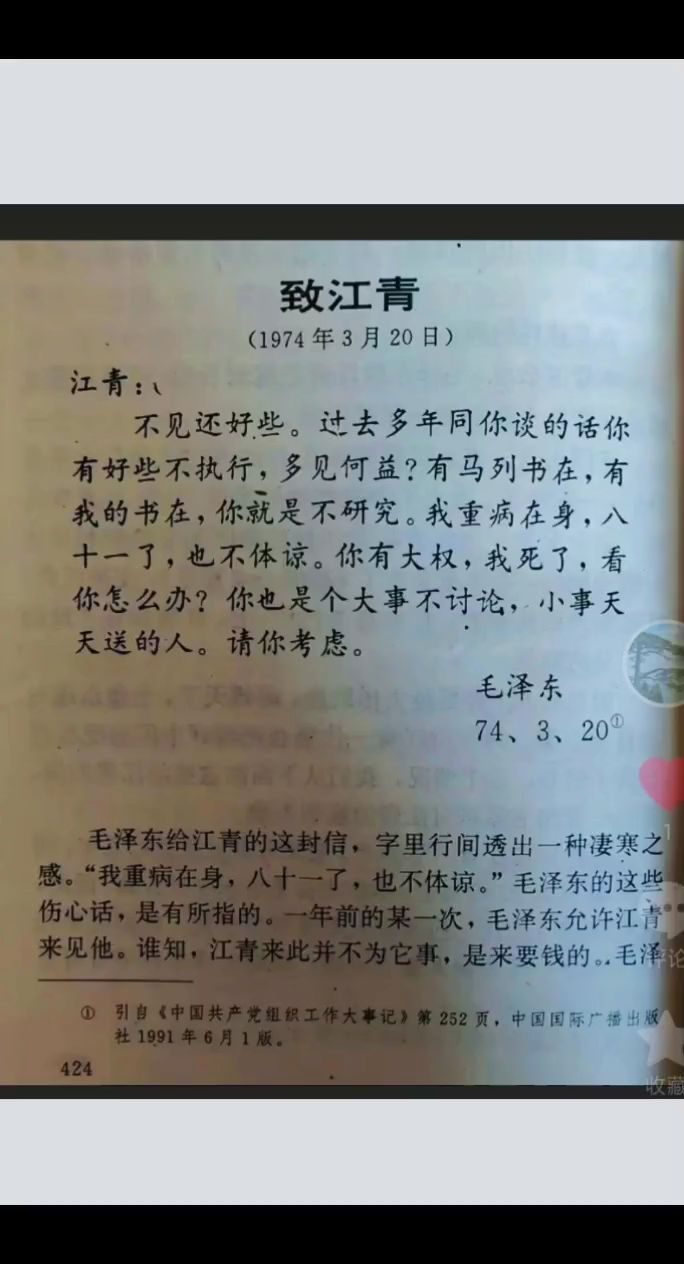纪登奎曾对万里说:我就问一句,田都分了,之前毛主席指引我们的道路还要不要接着走下去?分田单干就是瓦解集体经济,解不解散公社,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万里听罢,久久不语。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毛主席的话没人反对,但不能把包产到户认为是单干,如果非要搞平均主义,群众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生产上不去,就会给资本主义活动以可乘之机,其结果,必然出现真正的贫富差别。 1955年,党内对于农业合作化的速度问题,由起初的分歧逐渐演变为激烈的争论,并最终公开化,这场争论如同巨浪般席卷全国,引发了一场关于农业合作化道路选择的大辩论。争论的核心聚焦于一个关键问题:农业合作化究竟应该稳步前行,还是加速推进?邓子恢同志,基于对当时我国小农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深刻认识,力主合作化应脚踏实地、稳步推进。他强调,应继续对农业合作社进行整顿与收缩,并通过建立严密的生产责任制来巩固其基础,以避免合作社匆忙建立后迅速瓦解的尴尬局面。邓子恢的担忧直击要害,他指出过快的发展速度与生产力水平脱节的风险,坚持认为稳步推进才是合作化的正道。 然而,在合作化运动的高潮期,一些基层干部盲目追求速度,将合作社的数量视为衡量工作成效的唯一标尺,忽视了本地的实际情况,结果导致生产效率大幅下滑,农民的积极性遭受重创。农村生产关系的急剧变革与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这与毛泽东初衷中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来提振生产力的美好愿景背道而驰。 在此背景下,中共浙江永嘉县委农业书记李云河,深受1956年《人民日报》上《生产组和社员都应该“包工包产”》一文的启发,毅然决然地提出了试行包产到户的倡议。在李云河的亲自督战下,永嘉县燎原社于同年5月勇敢地迈出了包产到户的第一步。得益于领导与群众的紧密配合,燎原社的包产到户实践进展得异常顺利。 经过三个月的摸索与实践,他们总结出了宝贵的经验,形成了《燎原社包产到户总结》这一理论成果。该文基于社员的切身体会,详尽阐述了生产责任制的诸多优势,并通过对比包产到户前后的变化,有力地证明了包产到户对于改善合作社经营状况、扭转亏损局面的显著效果。这一积极成果迅速引起了永嘉县委的高度重视,同年9月,县委召开了全县高级社主任会议,决定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包产到户。在县委领导的强力推动下,永嘉县以燎原社为起点,包产到户的星星之火迅速燎原,全县实行包产到户的合作社数量激增。 1959年5月,党中央高瞻远瞩,发出了《关于人民公社夏收分配的指示》,明确要求“认真执行包产、包工、包成本的‘三包’责任制和奖惩制度”,以彻底根治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倾向和经营管理中的混乱局面。这一举措深得农民群众的拥护与欢迎。随后,包产到户如春风拂面,迅速在江苏、甘肃、湖南、湖北、河南等省份落地生根。为了深入贯彻党中央的精神,各地纷纷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至生产队,有的地区更是大胆尝试包产到户,普遍实行“四定一奖”制度,即明确生产指标、投资额度、上交任务、增产措施,并对超产部分给予奖励。部分地区则根据实际情况,灵活采取“三定一奖”或“三包”(包产、包工、包投资)制度。 与此同时,农村中还存在着一部分因年龄、健康等原因难以进城的老弱病残群体。他们同样需要社会的关爱与帮助。因此,在中国广大的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农村地区,形成了四种截然不同的农户类型:一是举家进城、生活富裕的农户;二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半工半耕的农户;三是留守农村、自力更生的中农家庭;四是生活困难、需要照顾的老弱病残家庭。 面对小农户分散经营难以抵御市场风险的现状,乡村建设运动再次提上了日程。搞合作社成为了乡村建设的重要途径。然而,合作社的建设并非易事。农民并非不愿意加入,但如果让他们无偿入股成立协会,往往难以持久,因为缺乏利益纽带。因此,我们搞的合作社非常正规,要求社员每户必须交纳一定的入社费。但农民对此往往心存顾虑,不愿轻易交钱。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我们采取了带头示范的方法。我率先交纳了一万元入社费,并告诉农民这是我从个人存款中拿出的真金白银,比他们多交了许多倍。同时,我还承诺我的入社费只做股份,不计利息,将来合作社有收入了将用于公益事业。此外,我还表示如果合作社亏损了,将首先用我的钱来抵补,不让农民承担风险。这样一来,农民看到了我的诚意和决心,纷纷表示愿意加入合作社。通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方式,我们成功发动了一个又一个村庄的农民加入合作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