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发家日常》
作者:张佳音

简介:
钢铁直女厉长瑛穿越成古代猎户女,练就一身打猎的本事,剽悍之名传遍乡野。
但始终无人敢上门提亲,教厉家人愁的挠头。
厉长瑛无所谓,她靠自己的本事衣食无忧,最大的目标是:攒钱,退休!
成亲只会影响她赚钱的速度。
然而,乱世忽至,大战将起,厉家人不得不收拾起行囊,背井离乡,开始逃难。
厉长瑛安贫乐道,新的目标是寻一处山清水秀、没有战乱的地方,重建家宅,继续攒钱,早日退休!
不过目的地还没到,路上先捡到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魏堇。
魏堇长得没话说,就是太麻烦。
“阿瑛!救我!”
“阿瑛!我与你一道!”
“阿瑛,你可是厌了我……”
诸如此类,屁事儿贼多。
厉长瑛每每拳头硬,一看他的脸,又熄了火。
平安落脚后,厉母暗示厉长瑛家里人太少了,魏堇面红耳赤地瞄她。
厉长瑛不解风情:“那正好,我俩结拜,一个够不?还有。”
三人笑容凝固。
而魏堇面上斯文无害,背后对每一个潜在情敌露出獠牙,“阿瑛是我的。”
精彩节选:
晋朝高祖善兵,盛极之时,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各部轻易不敢犯,常有朝贡。
然由盛而衰,不过百年。
当今陛下刚愎无道,即位后便大兴土木,南北征战,杀伐不断,劳民伤财,以致中原动荡,盗贼蜂起,民不聊生,各地接连爆发起义,群雄虎视眈眈,外族亦是异动频频。
天下崩颓,顷刻之间。
贫苦百姓只求片瓦遮身,衣食无忧。
大兴十二年,朝廷横征暴敛更甚,许多百姓为躲避祸乱,逃往北地,屯据山险而自保。
月黑风高,山路上人烟皆无,万籁俱寂,唯有难听的驴叫,“啊啊--哦,啊--哦,啊--”
一只驴子拖着个木板车前行,木板车两侧堆满了东西,中间却留了宽裕的位置,半靠着一个女子。
驴车左右,两人徒步。
他们便是刚北上逃难两日的厉家三口人——父亲厉蒙,母亲林秀平,独女厉长瑛。
厉长瑛听着驴叫,嘴角抽搐,额头神经一跳一跳,“咱们夜里赶路,是为了避人,免得遭横祸,它叫这么响亮,不是明摆着告诉山匪,有驴,快来抢吗?”
厉蒙性子和猿臂狼腰的身形一样粗犷豪放,“夜里都睡着呢,听见也不敢随便冒头,有三两只小蚂蚱,也用不着担心。”
他是北狄胡人和汉人混血,血脉里就带着强悍基因,多年猎户生涯,更是骁勇,自然自信。
况且,虎父无犬女,厉长瑛也继承了父亲的体质,身材高挑,腰身劲瘦,紧实的肌肉裹着骨骼,手臂和双腿摆动时,一弯一折间皆是力量感。
而林秀平是童生女儿,柔顺温柔,女红、厨艺极佳,还识得些字,会算账、会包扎……厉蒙虽是个大老粗,但稍有家底,夫妻俩成婚以来,他没教林秀平吃一丝一毫的劳苦,哪怕现在长途跋涉地逃难,也尽可能地让她舒适。
父女俩都是粗人,便可劲儿造了。
驴车上,林秀平嗓音轻柔,担忧道:“夫君,还是要小心为上。”
厉蒙怕吓到她似的,粗嘎的嗓子夹起来,轻声安抚:“娘子,你放心,我跟咱爹逃荒过来,有经验,这段儿路劫道的山匪多,夜里抓紧赶路,也省的碰到起义军,等过了这几个郡,越往北越地广人稀,就不用这样提心吊胆了。”
林秀平完全信赖,“我相信夫君。”
厉蒙越发膨胀,展示他的深谋远虑,“这时候走,到关外正好夏末,来得及建房过冬,有我和阿瑛,不会让你吃苦。”
林秀平满目柔情似水。
厉蒙与妻子对视,虎变猫,悍变憨,百炼钢化成了绕指柔。
老夫老妻,周身都散发着爱意浓稠的酸臭味儿。
“……”
肉麻!
厉长瑛面无表情,熟练地当自个儿不存在。
一板车之隔,厉蒙温柔地叮嘱妻子:“安心闭目养神……”
厉长瑛顺手甩了驴脑袋一巴掌。
“啊啊啊————哦。”驴叫更嚣张。
厉长瑛又给了它一记重掌。
驴叫卡壳,圆溜溜的眼睛上睫毛翻飞,屈服于淫威,这下子老实了。
夜色里,只剩下厉蒙嘘寒问暖的声音和林秀平句句回应。
厉长瑛本来没这么有眼色,但没办法,她有一个成年人的芯子,小时候在夫妻俩身边儿痛苦装睡,稍长大点儿就赶紧要求搬到小屋去,依旧没少听见隔壁屋的响动。
厉蒙还当她是真小孩儿骗,说什么“闹耗子”,闹什么耗子是那动静儿。
他不要脸,厉长瑛还得顾及柔弱母亲的脸面,假装被骗了过去。
如今她都是一个个头比演技高的十七岁大姑娘了,多年养成的眼力见儿,在这个夜晚强制传给了家里的重要财产,唯一的驴。
厉长瑛并不是土生土长的晋朝人,她前世就是个普通人,靠着毅力拼了个长跑二级运动员,上了个不错的综合大学,成绩平平地毕业,头脑一般,天赋一般,就是心脏强劲,四肢发达。
前世为了早日退休,厉长瑛正职兼职轮番干,好不容易要见着曙光了,突发意外,成了厉家女儿。
属于是绩效归零,一世白干,又来一世困难模式。
世道艰难,贫民百姓举步维艰,厉长瑛没有什么发家致富的本事,不过厉蒙打猎的本事厉害,她便从小跟父亲学打猎。
脑子没变,四肢更发达了。
厉家有两个猎户,还算衣食无忧,但他们所在的东郡被一支起义军占领,在各县□□烧,还征召男丁入伍。
乱世将至,鹿死谁手不一定,厉蒙一个小小猎户根本没有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厉长瑛也没有,她的志向跨越两世,仍旧是攒钱、早早退休。
于是一家人一商量,当即收拾家当,跑了。
他们有驴,有家当,有吃食,有温柔的娘……混进难民中就是一块儿肥美的肉落入饿得前胸贴后背的狼群里,纵是有父女二人震慑,也绝对挡不住饥饿的难民们铤而走险。
不能冒险,便尽挑着偏僻小路走,晚上才敢走大路。
如此日夜兼程又行了两日,厉家三口人进入到魏郡境内,再三避人走,还是碰到了一小股难民。
绕路要回转十几里路,厉家人只能继续前行。
白天,林秀平遮了面巾,头上戴着披风连帽,除了一双眼睛,一点皮肉都没露出来,看不出什么。
但厉蒙和厉长瑛父女俩虽然肤色略黑,面上也有疲色,却是一副气血充足、不缺吃的模样。
老老少少二十多难民,个个衣衫褴褛,瘦骨嶙峋,眼窝凹陷,贪婪觊觎的目光如同蚂蟥吸附在皮肉上,全都黏着在他们身上。
有些目光,甚至带着令人作呕的恶念。
林秀平直面这种恶意,一瞬间头皮发麻,蜷缩起来避开视线,担忧地望向父女俩。
厉蒙撸起袖子,攥起拳头,露出了肌肉鼓胀、青筋暴起的小臂。
厉长瑛手伸进行李下,握住一根打磨光滑的木柄,没有多余动作,目光如隼,防备地扫着那些难民。
这年头,敢这样在路上行走的人,必然有所倚仗。
瘦骨嶙峋的难民们有一瞬的忌惮畏惧,但很快又直勾勾地盯着他们板车上。
驴车与难民越来越近,气氛紧绷。
厉蒙和厉长瑛警惕更甚。
林秀平手指不由地攥紧捆绑的麻绳,屏住呼吸。
驴车和难民渐渐持平。
风来。
树枝摇摆,嘎吱嘎吱……
草丛窸窣,枯黄的落叶打着旋儿,转啊转。
风止,叶落。
静。
“跑!”
厉蒙大喝一声大掌,猛地拍在驴屁股上。
“啊——”
驴一疼,撒开蹄子哒哒地狂奔。
林秀平紧紧拽着麻绳,放低身体,扒住板车。
方才还步履蹒跚的难民们忽然暴起,各个满眼猩红,发狂似的扑向驴车,一副要啃食殆尽的疯魔样子。
“吃的!我要吃的!给我吃的!”
声音粗嘎,嘶厉可怖。
厉长瑛下意识跟着父亲的指令跑了两步,刷地抽出行李下藏的武器--一根打磨光滑、乌漆嘛黑的烧火棍。
她单手握着棍子,脚下蹬地,猛地反冲向难民们。
“阿瑛--”
林秀平惊呼。
厉蒙片刻不停,抓着缰绳使劲儿拍打驴屁股。
林秀平手上不敢松,伏着身子扭头,焦急地喊女儿的名字,叫她小心。
驴车太重,跑得不算快,颠得她口中吐出的每一个字都带着颤音。
厉长瑛不管三七二十一,冲上去就是莽。
她五官俊俏,鼻梁高挺,眉眼深邃,双目炯炯有神,眉骨锋利,烧火棍抡起来,虎虎生威,全无半点儿世人以为的女子娇软,尽是野性和攻击性。
人生第一次正式与人对战,气势如虹。
第一棍,砸在了打头男人的肩膀,男人追跑的动作滞住片刻,又继续不怕死地向前扑。
厉长瑛一震,继续挥舞烧火棍,棍棍不落空。
但几乎所有难免都带着撕烂她的气势涌向她。
前方,驴车慢慢拉开和难民们距离,厉蒙嘴里喝着风,安慰妻子:“放心,都是乌合之众,手上没有利器,阿瑛不傻,打不过还不会跑吗。”
林秀平回望的脸上表情骤然变得更难看。
厉蒙边跑边回头瞄了一眼,不禁干笑,“真虎啊,不愧是我厉蒙的女儿……”
林秀平:“……”
半个时辰后,无名的荒郊野岭,彻底甩掉难民的一家三口呈三足鼎立之势。
驴吐着舌头侧翻在地上,呼哧呼哧喘气。
它背上磨烂了,林秀平沉默,小心地往伤口抹药膏。厉蒙常年上山,也会采草药回来,为了以防万一,她熬制了许多。
厉长瑛左脸颊上有一块儿淤青,头发些微凌乱,袖子也撕烂了一块儿,绷着脸蹲在地上,依然一身正气。
她对面,厉蒙大马金刀地坐在地上。
好一会儿都安静的诡异。
“冲动!莽撞!”
厉蒙拿腔拿调的教训打破了安静,“你怎么不拿砍柴刀呢?”
板车上还压着一把砍柴刀,她要是拿砍柴刀,一刀砍一个,见了血,伤及人命,必然能震慑住那些难民。
可她根本不敢杀人,竟然还敢往上冲。
“你别以为你力气大,会点儿三脚猫的功夫,就了不起了。”
厉长瑛理亏,丢脸,一声不吭地听训,也不去辩解她是想要拖一拖时间,好让驴车跑远一些再脱身,只是没想到那些难民为了抢吃的这么不要命。
原来世道乱了,人会变成这样,没真正走出来之前,始终是体会不深……
厉长瑛神情郁郁。
厉蒙厉声道:“咱们的粮食本来就不够吃,现在又损失了一袋粟米,你好好反省!”
厉长瑛恹恹地抬眼,一副别以为我不知道的神情,“你明明是怕板车太重,跑不快,被那些难民追上,再害我娘受伤,才扔的。”
她跑得快,哪里需要扔东西来绊难民的脚。
厉蒙厚颜,不以为耻。
林秀平嗔怪地睨了他一眼,方才忧道:“只剩下一袋半粟米,怕是坚持不了多久,日后怎么办?若是又遇见人来抢,万不能再这般不要性命地与人撕扯。”
他们不是那等已走到绝处的难民,还有牵挂,自然要以性命为先。
父女俩则不约而同地望向了重要财产。
或许,他们还有储备粮?
林秀平轻轻瞪了两人一眼,药膏扔向女儿,不轻不重地表示不满,“自个儿擦。”
“……”
厉长瑛控诉:“不是,娘,我跟驴擦一个啊?”
新手上路,出师未捷。
同样受了皮肉伤,厉长瑛不需要休息,驴却得停下休养,以防沉重的板车加重它的伤情,无法顺利走完后面漫长的路途。
那就真成储备粮了。
他们得寻个暂时落脚的地方。
厉蒙经验丰富,瞅了眼天色,“明日应该没雨,沿着这条山路往前,看看能不能找到山神庙,找不到,就临时搭一个棚屋……”
厉长瑛二话不说,起身,“那走吧。”
厉蒙还没说完,她已经扛起一袋粟米,迈出去几步远了,再多废话几句,她能干出去二里地。
“你看看她这火燎腚的性子。”
林秀平抿嘴笑,手轻轻抚了抚丈夫的手臂。
厉蒙瞬间被她捋顺了脾气,双手抓着箩筐,双臂鼓胀,举起装杂物的箩筐抗在身上。
父女俩力气都大,很能给人安全感。
做得好便需要鼓励。
林秀平眼里盛满崇拜之色。
厉蒙霎时浑身充满力气,又单手提起铁锅。
厉长瑛一回头,便见五大三粗的爹在那儿孔雀开屏,实在看不下去,头飞快地回转正,走得更快。
林秀平也下来步行,减轻驴子的负担。
她力气小,没额外背什么,只牵着驴,随时安抚它因为麻绳勒磨而生出的脾气。
这头驴家里养了四年,主要是她在照顾,颇有感情。
三人一驴车循着干草几乎铺满的山路向上。
最前面,厉长瑛开路,拿着镰刀刷刷扫。
中间,林秀平拽着驴。
先前他们逃跑时,出了难民的视线,怕又被找到,便砍了些树枝,拖在板车后面,扫净痕迹,此时仍拖着,随着行进哗哗作响。
厉蒙则殿后。
日头西斜,三人终于找到了一座山神庙。
庙高约四尺,差不多与厉长瑛腰线齐平,三面墙一个顶全是石头垒的,荒废许久,破败不堪,周围长满了杂草,里头的山神像根本看不出原样儿。
一家三口并排站在前面,默然。
良久,厉长瑛吐出一句:“荒山野神,香火是差了些哈……”
何止是差,这情况,真要靠香火,得饿死。
厉蒙环视一圈儿,“就在这儿驻扎吧。”
此处背风,地面平整宽阔,方才还经过了一处小溪,有水源,正适合暂时修整。
厉长瑛立马挥舞镰刀,以山神庙为中心开始割荒草。
厉蒙解了驴车,从板车上翻出一盒香,接过林秀平递过来的风干肉,摆放在山神庙前。
猎户,以狩猎为生,尤其厉蒙祖上信奉万物皆有灵,得了馈赠,自然要敬山神。
一家三口虔诚地拜过山神后,四周都仔细撒了防虫蛇的药粉,才各自忙碌起来。
厉蒙拿着砍柴刀钻进林中砍树枝。
林秀平收拢干草到一处。
她双手灵巧,如今逃难在外,也不讲究保护绣花的手了,直接抓取干草编起来,没多久便有了席子的雏形。
厉长瑛动作麻利地割完附近这一片儿的草,选好木棚的位置,又拿锹在安全距离挖了个烧火坑。
没多久,厉蒙抱着一捆树枝回来,扔在地上,好不停歇地转身再次回了林中。
厉长瑛找了工具和麻绳,先用几根树枝在烧火坑上支了个可以吊锅的木架,又折好细枝整齐地堆放在旁边,方才去搭木棚。
厉蒙第二次抱着树枝回来,驴在吃草,厉长瑛在盯驴。
确切地说,是盯驴屁股。
厉蒙表情一言难尽,“你这是什么癖好,老盯着驴腚瞅什么。”
厉长瑛招呼:“爹你来看,不对劲儿。”
“有啥不对劲儿……”厉蒙走到她身边儿,也盯着驴腚,盯着盯着“嘶--”了一声。
驴屁股明显的一边儿高一边儿低。
是厉蒙干得。
厉长瑛眉头一挑,兴冲冲地告状,挑拨夫妻感情:“娘!我爹没轻没重的,把驴屁股打肿了!”
厉蒙:“……”
生孩子真烦。
林秀平走过来,瞧了一眼驴,柔声道:“先前急于脱身,你爹是无心之失。”
厉蒙表情瞬间展开,乐呵呵地盯着妻子。
林秀平浅浅一笑。
厉蒙的表情更傻。
这下子轮到厉长瑛无语了,识相地撤出夫妻二人的世界,安分做她的小工。
天彻底黑下来,木棚的骨架搭好,火堆燃起,照亮野外这一方小天地。
光亮之外的山林中,黑压压的,诡谲而幽深,但他们头顶上的一片星空,澄净灿烂,一如家中仰头便可望见的那片星空。
厉蒙砍完足够的树枝,将细的干树枝围绕四周密密麻麻地摆了一大圈儿,轻踩上去咔嚓咔嚓响,可作警示之用。
随后,父女俩一起在火光的照应下进行后续搭建。
锅里,熬了许久的粟米粥咕嘟咕嘟地冒着香气,可供三人平躺的简易木棚终于搭好。
长短不一的粗壮树枝做梁柱,两根横梁全支棱出来,一根柱子特立独行地高出一大截,直插天际;细枝用麻绳粗略地绑成墙,又用干草细密地塞满;顶上也铺了草,用两根树枝横压住。
林秀平编的两张草席,小的挂在门上做门帘,大的铺在木棚中。
厉长瑛叉腰欣赏。
这算是她第一次作为主力搭木棚,糙是糙了点儿,实用性还是可以的。
林秀平招呼父女二人,“快来吃饭。”
厉长瑛扬声应:“来啦!”
“我四下瞧了一眼,干草下才刚泛绿,没有能挖的野菜,不然便挖一些鲜野菜煮粥了。”
林秀平盛了两碗一一递给父女二人。
她切了点干肉丁干野菜在粟米粥里,只放了一点点盐,一锅粥虽然米不算多却熬得粘稠软烂。
父女俩丝毫不挑剔,如出一辙的吃相,端着碗几乎是扣在脸上,呼噜呼噜地喝,一碗完事儿又去盛下一碗。
那架势,猪食都能吃得香,好养活的很。
二人一整日消耗极大,头两碗吃得快,空了一整天的肚子垫了底,便慢下来,等林秀平吃饱再包锅底。
他们家一直都是这样,一开始是厉蒙等母女俩吃完再划拉剩的,后来厉长瑛长大,就变成父女俩等林秀平吃完再收尾。
也算是粗人疼人的一种方式。
等一锅粥全都喝完,只剩下一道一道的黏糊糊贴在锅壁上刮不干净,林秀平倒了点儿水架在火上烧,一点儿不浪费。
喝稀粥,肚子是满的,可水当当的,完全没有饱腹的踏实感。
厉长瑛眼巴巴地盯着锅里翻腾的水汤,感觉肚子更空了,艰难地转移注意力,“爹,咱们接下来怎么走?”
厉蒙随意道:“咱们又没有舆图,一路往南,走哪儿算哪儿,肯定能到。”
厉长瑛:“……”
平民百姓买不了地图这是没办法,可赶路全靠直觉,他们真的能顺利出关吗?
她爹如此盲目乐观,还是得靠她。
“不急着赶路,明日一早我就进山,如若能多打两只猎物,便进城换粮食,顺便问问路。”
他们刚丢了一袋粟米,只剩下一袋半粟米,几块儿方便保存的干肉和一些干野菜、干蘑菇,以及一小罐盐。
粮食不够吃,就尽早想办法弄。
其它问题也是一样,发愁没有用,想办法解决才是。
而夫妻俩不反对打猎,他们本就是猎户,打猎是生存手段。
林秀平不放心的是厉长瑛要进城,“吃的省着些,走远些再进城吧,或者让你爹去。”
厉长瑛艺高人胆大,“不就是进城吗?又不是龙潭虎穴,真有啥事,我打不过指定撒腿儿跑。”
林秀平还要再说,厉蒙拦住她,“她想去就去。”
厉长瑛精神头尚足,赶紧催促:“上半夜我守夜,爹娘,你们快去休息!”
厉蒙半搂着林秀平进了木棚,方才得意地低声道:“你可别觉得我这个当爹的粗心,还得靠我考虑深远,你看,她经了白天的教训,肯定不会莽撞,去长长见识有啥不好,以后才能经得住事儿。”
林秀平不是不赞同,只是叹气,“她到底是个姑娘,往后总得找个可靠的男人过日子,以前就因为跟着你打猎婚事一直不成,再这么继续下去,万一孤独终老,你我能安心?”
“我女儿可靠就行了,大不了招赘,养得起。”
他口气颇大。
林秀平噎住,良久才没好气道:“那样有本事,咱们何必逃难。”
厉蒙不免低落,将她整个圈在怀里,歉疚道:“总归是我这个男人没本事,不能让你们母女过安稳的好日子。”
这又不是他的错,只是他们没生在好世道罢了。
林秀平不是埋怨,含混过去,不再多言。
半夜,父女俩交换守夜,木棚里变成厉长瑛跟林秀平裹一床被子,抱着取暖。
之后,一连几日,厉长瑛都是上半夜守夜,隔天天蒙蒙亮,便钻出木棚,背着弓箭,拿着砍柴刀或者短矛、铁锹,精神抖擞地进山。
她空手而归也不见气馁,若是打到猎物,整个人便精神百倍。
偶尔,父女俩也换着进山,但劲头完全不一样。
更不要说林秀平这个常在家中做事的人,与她比体力天差地别。
夫妻俩看着她活力十足的雀跃身影,每每无言。
旁人逃难,形容狼狈,灰心丧气。
她精力是真旺盛啊。
厉蒙现在身上有不少陈年旧伤,可就算是他年轻的时候,也没像她似的,不管何时何地都浑身使不完的牛劲儿。
又一回,林秀平忍不住对丈夫神色复杂道:“其实,等咱们安稳下来,招赘也不是不成……”
休养生息的几日,厉长瑛猎到了两只野鸡,一只兔子,便暂时离开父母,一路翻山越岭,从晨光熹微走到日跌,方才寻到官路。
她在出山口寻了一棵形状奇特的树,划了个特殊的记号,继续沿着官路前进。
她脚程快,大概走了一个时辰,前方出现了几个难民,形状与先前遇到的那一大波难民外观上完全没有两样,衣衫褴褛,步履艰难。
厉长瑛先发现了他们。
她挨过揍,长了教训没长心理阴影,脚步丝毫没有停顿,大步流星地往前。
倒是那几个难民,听到有力的脚步声便慌作一团,避到路边儿,小心翼翼地观察来人。
厉长瑛一身破旧的粗布短衫,头发束成一个单髻,随便用布条缠着,没有刻意遮掩女性特征。
可她身材比一般女子高挑,身上背着一只半身高的箩筐,脊背一丝不弯,行走间毫不费力,手里还握着一把锋利的砍柴刀。
哪怕厉长瑛是个女子,难民们也没有胆子觊觎,视线一触即离,生怕惹麻烦。
厉长瑛直接越过他们,又走了许久,绕过一座小山,终于远远瞧见了县城的轮廓,规模比他们原来县城大上一倍不止。
她加快步伐,赶在日落之前,风尘仆仆地到达城外,箩筐上头还多了一捆柴。
城门上方写着县名,此地名为邺县。
难民不能入城,全都挤在离城门处有些距离的空地上,有的两三人相互倚靠在一起,有的一群人聚在一处,形如枯槁,寂若死灰。
厉长瑛穿得破旧,难民们麻木的视线在她背得箩筐上扫过。
这时,一辆马车并一队随从从远处驶过来。
许多难民从活死人醒过来一般,全不怕马车冲撞到他们,直接围了上去,挡住了马车的前路。
“求求了,给点儿吃的吧~”
“快饿死了……”
“求求大善人……”
其他难民也都在观望。
随从们推搡叱骂他们“滚开”,甚至还动了手,难民们依旧不离。
场面有些混乱。
厉长瑛谨慎地绕开,径直往城门口去。
城门口排着一条长队伍,门口的守兵呼来喝去,盘查严苛。
有人没有通过盘查,苦苦哀求,守兵不留情地厉声喝骂,驱赶其离开。
那人如丧家之犬,摇摇晃晃地从厉长瑛身边经过。
厉长瑛不知前方情形,喊住他询问为何没通过。
那人惨然一笑,缓缓抬起手,伸出一巴掌,虚握着,“一升米,因为没有一升米,呵、呵哈哈哈……”
他不敢说出来,可笑声里是无尽的讽刺。
长队中几个人听见那人的话语,颓丧地退了出来。
从未听过进城还要交粮。
但厉长瑛箩筐里还真有一小布袋粟米,约莫两升,是临行前林秀平给她装得。
粮食和布匹是硬通货,这是为了以防万一。
常言道穷家富路,一家人背井离乡自然不是全无准备。
他们一家三口都很能干,林秀平可以接绣活赚钱,父女俩轮着上山打猎,收获也不算少,太平世道,日子必然会越来越好。
可惜,不太平。
田地荒废,粮食价高,打猎所得能换到的粮食越来越少,且吃食以外的其他日常花销也不能免除。
除此之外,他们家每年还要拿出一部分收入为厉蒙免除徭役,从前能够支撑,这几年徭役越来越重,便越来越吃力。
起义军打进来,算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促使他们下定决心离开。
他们吃食上并不紧缺,因为板车空间有限,天暖之后他们可以就地打猎果腹,逃难之前便将去年囤的山货和一些值钱的东西都换成了粟米和绢布。
至于曾经为小家置办的家当,如今早就卖不上价了。
另外,还有一张收藏好几年的皮子也没舍得卖,加上各种工具和驴,这就是厉家全部的家当了。
一升米看起来不多,可厉家的家底经不起造啊。
实在是肉疼。
厉长瑛这样不纠结的人,也难免犹豫。
下一个城或许不需要交,也或许会出现别的问题……
总不能空手而归,继续无头苍蝇似的乱撞……
如此想着,厉长瑛依旧排在队中没动。
同一时间,马车摆脱了难民,直接越过排队的人,行到城门前,稍作沟通便进了城。
没有人敢有怨言。
天色渐晚,盘查更快,厉长瑛来到守兵面前。
平民不能随便游荡,得有充分的理由,否则会被抓起来服劳役。
厉长瑛随口找了个寻未婚夫成亲的借口,将提前分出来的一小包粟米悄悄塞给了那名守兵。
守兵手腕一翻,那一小包粟米便消失在他的衣服里,随后意思意思地检查了一下她的箩筐,便放行。
“行了,进去吧。”
城门内,蹲守着不少的乞丐,看见衣着稍整齐些的,便冲上来乞讨。
厉长瑛穿得再不好,也是有粟米进城,且她一走近,许多乞丐的鼻子便动了动。
饥饿的人嗅觉格外敏锐。
箩筐里有腥味儿。
乞丐们蠢蠢欲动,两个小乞儿抢先跑到厉长瑛面前。
其他乞丐没有再凑近。
两个小乞儿,大的到厉长瑛胯骨,小的才到她大腿高,全都头大身子小,眼睛也大的惊人。
周围无数双贪婪的眼睛,厉长瑛纵是不忍心,也不可能开这个头去施舍他们,打算直接甩开他们走人。
却不想,大些的小乞儿并未开口乞讨,而是热情道:“你不是本地人吧,你想去哪儿我都可以给你带路,不用绕弯儿,不用耽误事儿,只要给我妹妹口吃的就行。”
妹妹?
厉长瑛多瞧了另一个小孩儿一眼。
女孩儿可不容易活。
而且,有骨气地付出些什么来获取报酬,比起手脚健全却乞讨,肯定是要更值得尊重一些。
尤其这样艰难,两个人还这么小。
人生地不熟,总要找人打听,或许他们也能给她有用的信息,找谁不是找。
厉长瑛便同意了男孩儿的带路。
男孩儿表情霎时欢喜,牵着女孩儿的手,走在厉长瑛身旁,边指路边介绍了他和妹妹的名字,他叫小山,妹妹叫小月。
厉长瑛她要去卖猎物,让小山带她去。
小山拍胸脯:“包我身上。”
直接引着厉长瑛往城西北走。
小女孩儿一句话没说,乖乖地跟着哥哥。
三人走到一条有些萧条的街上。
小山指着前方道:“这几家铺子,都收猎物。”
厉长瑛问他价值几何。
小山为难道:“具体的,不太清楚,但是,生意难做……”
他的意思,是卖不上价。
厉长瑛猜到了,也没再多问,上前去询问。
商户没生意,厉长瑛也不是什么人物,态度皆不算好。
第一个铺子,不分是什么猎物,只愿意给四十钱一只。
第二个铺子,野鸡三十五文钱,兔子稍贵些,五十文钱。
之后两个铺子,价钱稍有起伏,却也都不高。
他们在故意压她的价。
厉长瑛面无表情。
小山怕她不满意似的,小心翼翼道:“还有两个酒楼……”
厉长瑛点点头,随他去了酒楼。
酒楼给出的价格同样不高。
他们这是欺生。
厉长瑛也不是非卖不可,转身便走。
小山扯着妹妹追上,紧张道:“要不,我再带你去城里的大户人家问问?”
两双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她,生怕她不愿意给口吃的了。
厉长瑛问:“就没有别的办法,卖得高些?”
小山抿抿嘴唇,试探地问:“我知道一个人,很有本事,但找他帮忙,要抽几个钱的。”
卖几只山货,抽完钱能剩什么,不过真有本事,出些钱,问清楚前路也好。
“那就带我去吧。”
……
那是个泼皮一样的男人,蹲在巷子口,抖着腿,嚣张地告诉厉长瑛:“你一个外来的,不管怎么讲,要是能卖出满意的价来,老子都跟你姓。”
“我也不怕你知道,我能卖到一只七十文以上,看在你是这小子带过来的,你拿走五十五文。”
他说着,朝小山扬了扬下巴。
厉长瑛问:“可否问个路?”
泼皮男人吊儿郎当地点头,示意她问。
“我要出关,从哪里走更安全更顺?”
泼皮表情滞住,呆愣中有些许傻气,“……”
这问的,超出他的认知了。
还以为是问邺县东西南北通往哪儿这种路。
而厉长瑛看着他的神色,意识到问错人了。
两人四目相对,彼此都察觉到了对方的某种浅薄。
小山转了转眼睛,开口提醒:“肉……还卖吗?”
泼皮回神,趾高气扬地问她:“卖不卖?老子忙得很!少耽误老子时间!”
他都蹲巷子口了,还忙?
厉长瑛腹诽,又问:“能换等价的粮吗?”
来都来了,进城还不是免费的,总不能亏一笔再把猎物原样儿带回去。
泼皮答:“能。”
不远处,一个着陈旧儒衫、瘦削模样的中年读书人路过,听到两人的对话,摸了摸腰侧的瘪钱袋,瞅着厉长瑛,欲言又止,一声长叹。
浑身的囊中羞涩之气。
泼皮瞧见他,忽然伸手指道:“你要问路,可以找他,他进京赶考过。”
厉长瑛顺着视线瞧过去。
中年男人冲着厉长瑛文质彬彬地拱手,“在下翁植,只是虚读了几本书,不足为外人道也。”
“你是举人老爷?”
中年男人落寞苦笑。
泼皮嘴里叼起一根干草,讥笑,“他还是进士老爷呢,嘿,被剥夺了官身和功名~”
厉长瑛意外。
中年男人不愿再提旧事,对厉长瑛道:“翁某愿意帮姑娘指路,只是可否请姑娘便宜卖我一只野鸡?”
他说到“便宜”,满脸的惭愧之色。
厉长瑛还未说话,泼皮先不高兴了,“嘿,你这酸腐,抢老子的生意呢。”
翁植歉疚行礼,“翁某实在有用,还请见谅。”
泼皮呸了一声,撸袖子起身,“老子最烦你这种假正经!”
翁植颇有风骨,并未畏惧,闭眼,一副任君处置的不屈模样。
小山害怕地抱紧妹妹,往后退了退。
厉长瑛莫名其妙,她就是卖个鸡,问个路,怎么就成冲突导火索了?
泼皮要动手打人,气势汹汹地迈开步子……动不了。
他向前挣了挣,依旧纹丝不动,震惊地侧头,看着肩膀上多出来的一只手。
翁植和小山小月兄妹也都睁大了眼。
厉长瑛不容置疑道:“我卖你两只。”
泼皮气弱地吞了吞口水,眼神游移了一瞬,“两只……两只就两只。”
双方友好地一拍即合,很快完成了交易,泼皮带走了鸡和兔子。
厉长瑛转头招呼小兄妹俩,将她应允的报酬——一把粟米给了小山。
小山道过谢,便牵着妹妹飞快地跑开。
此处只剩下两人,翁植没急着问鸡,又向厉长瑛拱了拱手,“不知姑娘从何而来?”
“东郡。”
翁植疑惑道:“东郡至魏郡要途经汲郡,有渠水,虽说如今各处皆乱,多使些银钱,找找门路,仍可乘船直达涿郡。”
厉长瑛:“……”
他们确实过河了,还过了不止一条河,但是为了避人,根本不清楚当时具体过得是哪条河……
不过没关系,便是知道,他们也没钱寻门路。
厉长瑛完全不内耗,继续请教陆路如何走。
翁植通情达理地不再多问,认真答道:“如今河北诸郡已被河间王符兆掌控,当今陛下已下军令,要讨伐谋逆之人,战火将起。河东诸郡尚在朝廷治下,姑娘或可经上党郡、太原郡至雁门郡,进而出关。”
厉长瑛详细问了问,脑中霎时便有了个大概的行进路线。
厉蒙乃至于大多数人,对除出生以外的地域都几乎没有概念,她不一样,她脑子里有一个完全忘不掉的地图可以稍作对比。
问清楚了关外的位置和环境,她心下也稍有数了。
开荒是难,可怎么不算有金手指呢?
意识到这一点,厉长瑛本就昂扬的精神状态还增添了神清气爽。
翁植发现后,眼神有些诡异。
从没见过要跑去苦寒之地还兴致高昂的。
“谢过翁先生。”
厉长瑛抱拳,随即便拿出野鸡,递向他,打算随他给多少钱皆可。
歪脖子的死野鸡出现在眼前,翁植吓得退后,双手抬至胸前,十分抗拒地摆动。
厉长瑛稍收回手,“先生怕?家中可还有旁人能来取?”
翁植稍放松,摇头,“并无,家中只我一人。”
厉长瑛不解:“先生一人,又怕,那这鸡……”还能自己跳锅里炖自己吗?
翁植长叹一声,“我买它并非要自用,乃是得知尚书令魏老大人途经此地,便想送去为老大人补身,聊表心意。”
“尚书令,送鸡?”
厉长瑛一副“我年轻,你不要骗我”的神色。
她再孤陋寡闻,也知道尚书令是个大官,送鸡表心意?尚书令不在东都,在这儿?还缺他一只鸡?
而且,厉长瑛打量了一眼翁植的衣衫,绝不是她刻薄,属实不像是能和大官有牵连的样子。
翁植面露苦涩,幽幽道:“姑娘有所不知,魏公高洁,上忠于陛下,□□恤百姓,对我等寒门子弟更是不吝照拂,可惜其次子魏振恶俗鄙陋,胡作非为,致使济阴郡百姓揭竿而起,朝中损失惨重,百姓流离失所,罪大恶极,陛下判其死刑,其余魏氏族人则念在魏公劳苦功高的份上,流放涿郡。”
厉长瑛听着听着,忽然恍然,“攻占东郡的起义军不就是……”
翁植颔首,“济阴军首领邓常已占领河南数郡。”
他似是起了谈兴,对天下大势侃侃而谈起来。
河间王智谋如何,朝廷若讨伐,胜算分别几何;
济阴军邓常虽勇却冒进自负;
河东诸郡太守何等性情;
淮南江表一代又有几支势力蠢蠢欲动……
厉长瑛很想认真听,但她没忍住,打了个哈欠。
让她干活肯定猛猛干,让她听课,难为她了。
翁植猛然止住,歉道:“翁某失言了,姑娘见谅。”
厉长瑛爽利道:“先生所言极有用,是我粗人一个,牛嚼牡丹。”
她谈吐分明不像是只会犁地的牛。
翁植掩住眼神,“姑娘谦虚。”
厉长瑛从箩筐里掏出一根麻绳,困住野鸡脚,再次递给他,“今日先生为我解许多惑,这野鸡便赠予先生,也聊表我对先生和魏公的敬重。”
翁植闻言,大喜,“姑娘大义。”
厉长瑛摆摆手,提着箩筐便告辞离开。
翁植目送她身影消失,转瞬就变了个脸色,气质也从文质彬彬变成了轻浮滑头,“今日白赚了一只鸡,幸哉!”
另一头,厉长瑛刚走出巷子,想起城门落锁,明早才能再出去,白给一只鸡,寄宿一晚应该无妨,便又回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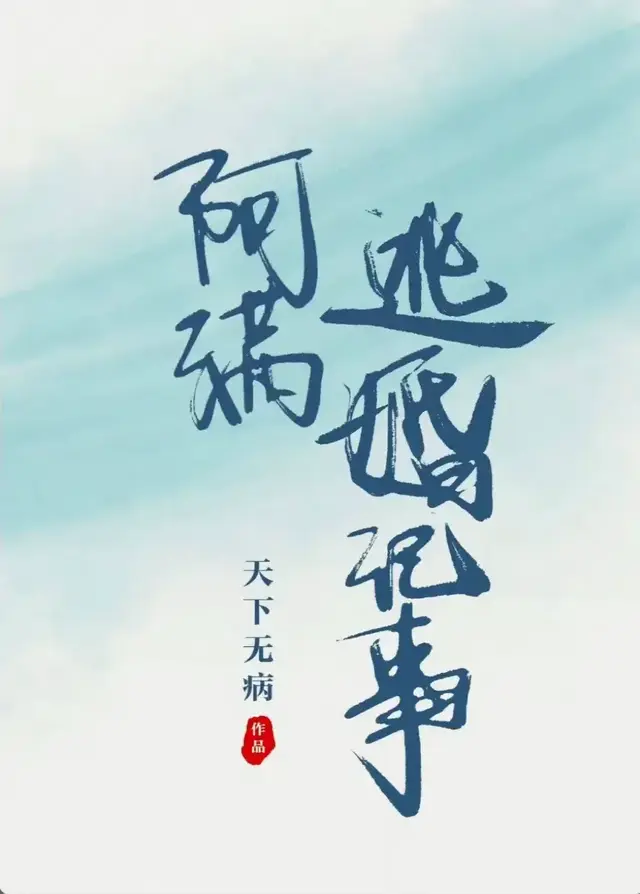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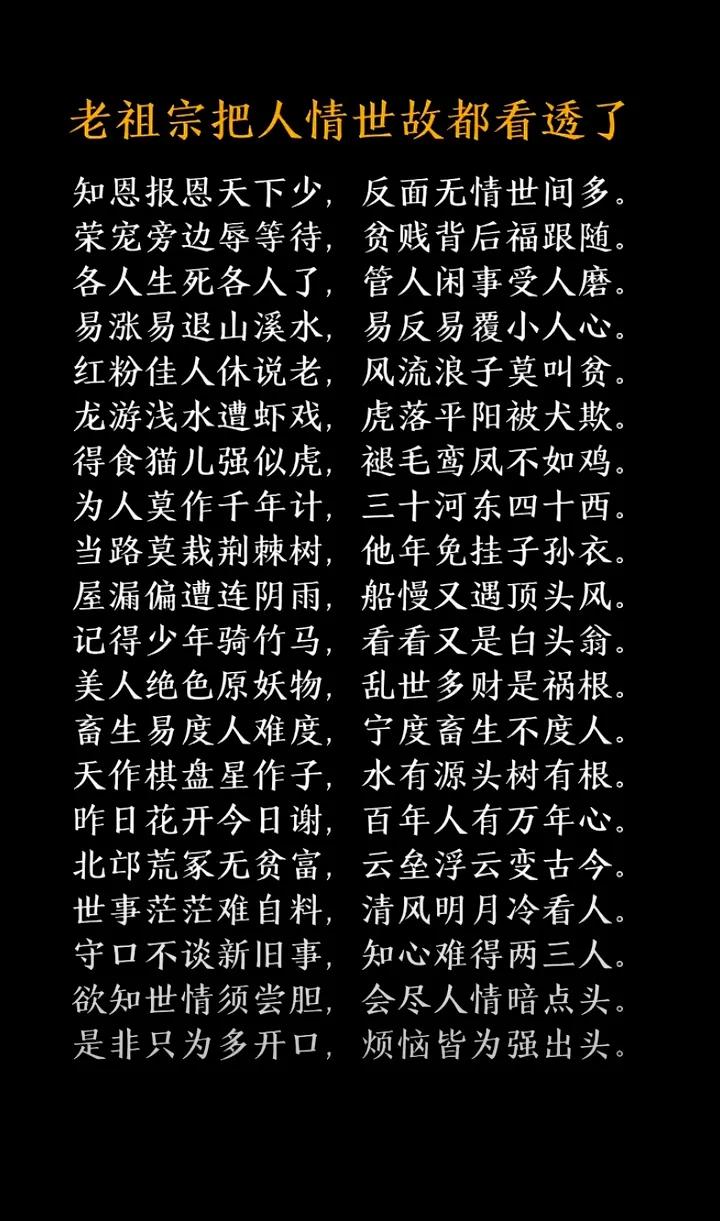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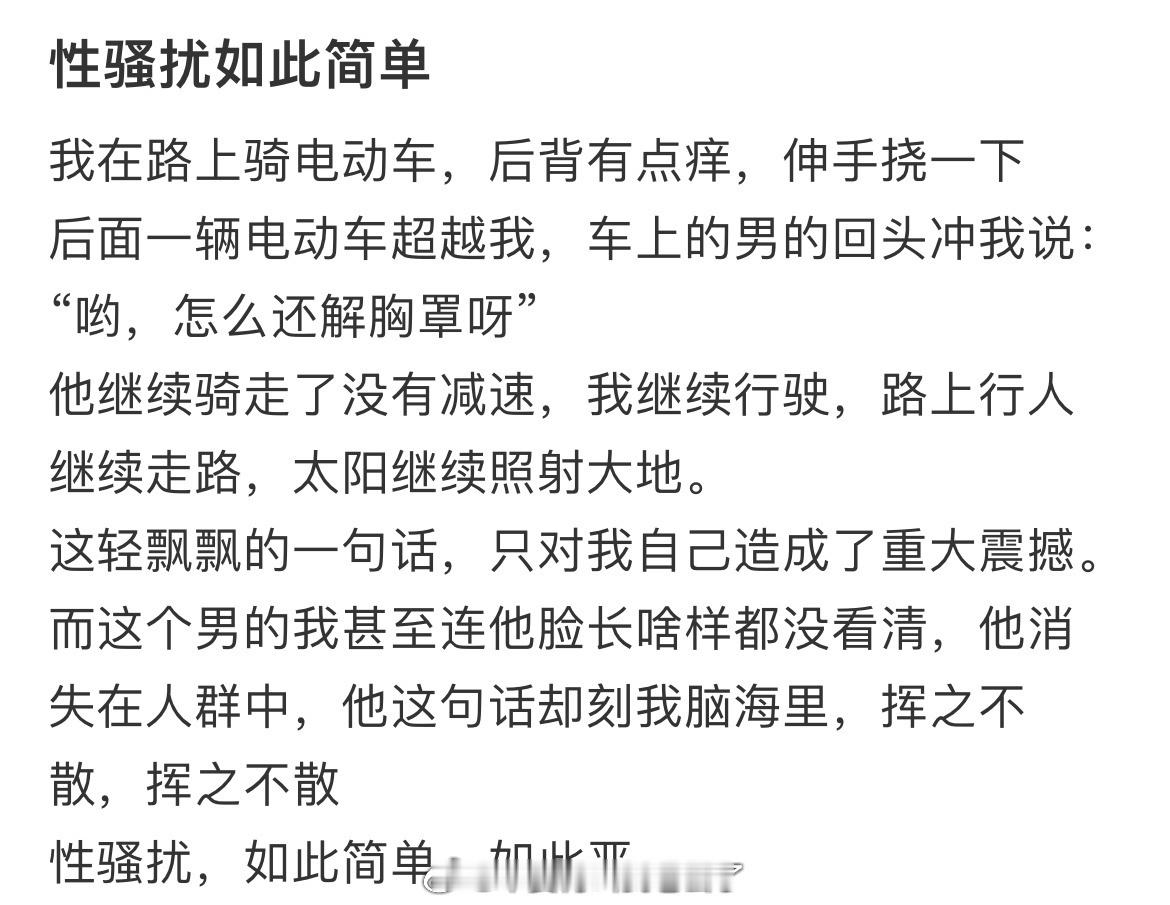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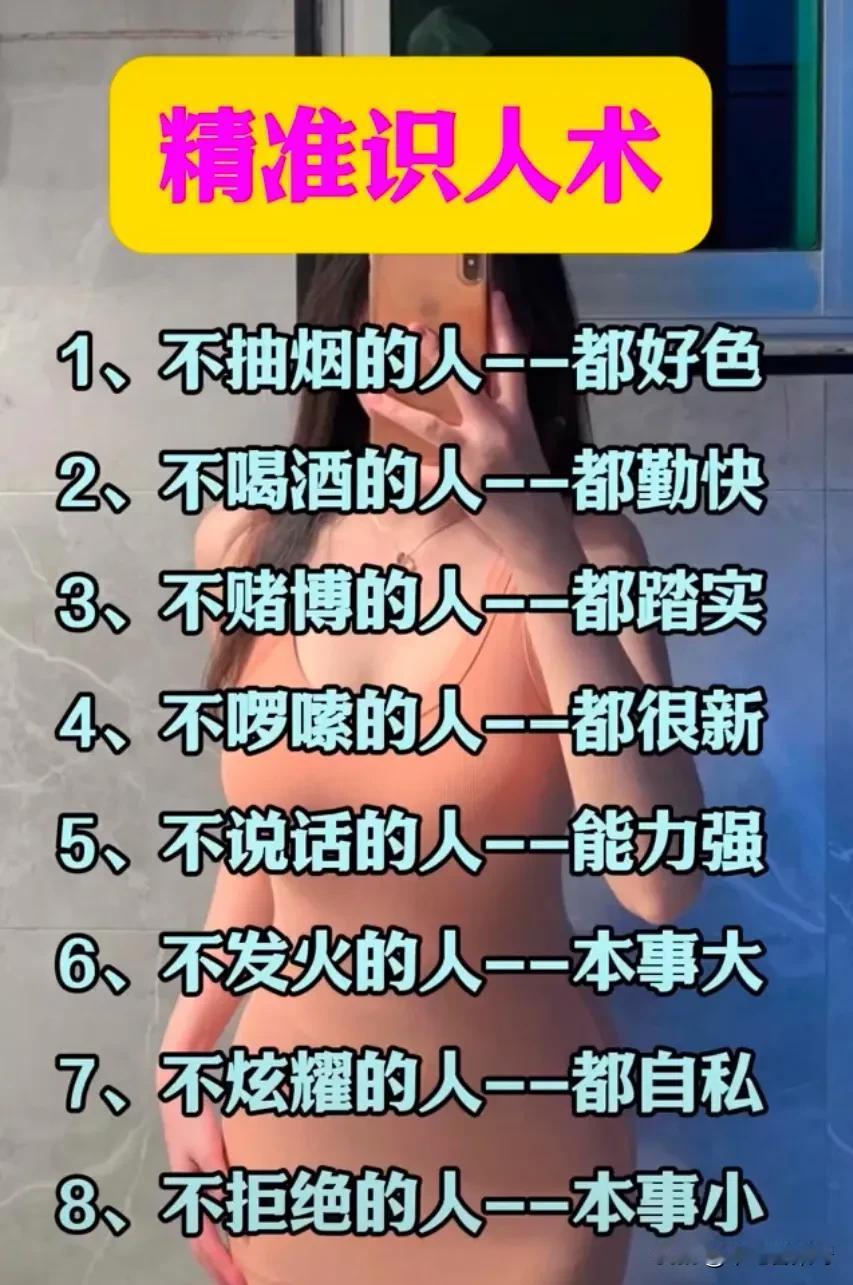


其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