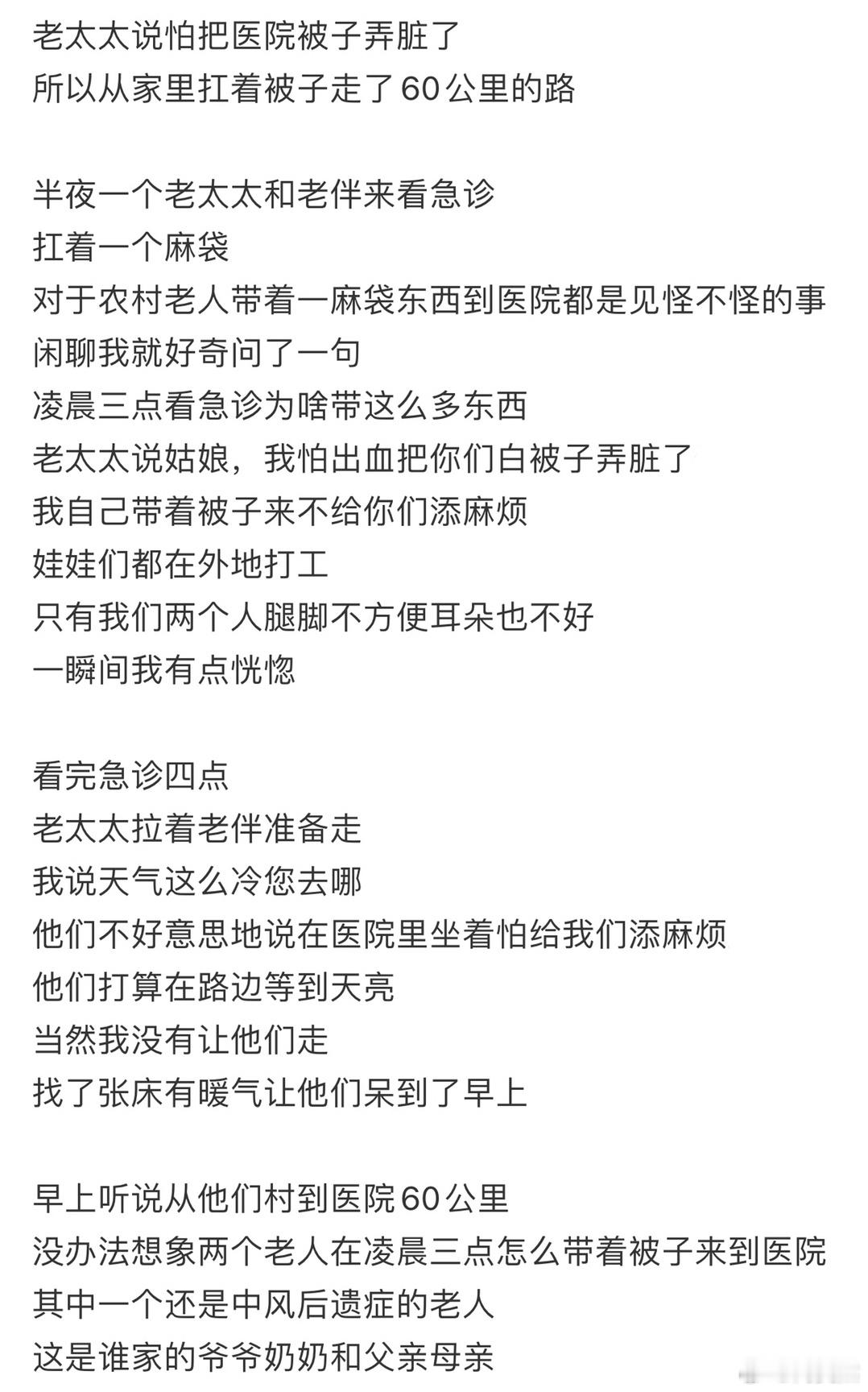"抢救室!让开!有人中毒了!"
十六岁的我刚从卫校毕业,第一次独自照顾住院的大伯和隔壁床一个素不相识的病人。
谁能想到,那个被我毫无顾忌地搀扶、照料的普通病人,竟然是一位能够改变我命运的县长。

"抢救室!让开!有人中毒了!"
1978年的夏天,一声急促的呼喊撕裂了区医院的宁静。消毒水的气味中,担架飞快地从眼前掠过,上面躺着的是我的大伯,一个壮实的庄稼汉,此刻却面色铁青,嘴角不停地冒着白沫。
一个小时前,大伯还在地里打药。前两天连降暴雨,虫害严重,大伯这个犟脾气又上来了,明明我大嫂劝他歇会,他偏要顶着烈日和大风,非把最后一亩地的农药打完。
"血压特别低,心跳特别快!大伯都快不行了!"护士急切的声音从抢救室传出。
"小杨!快进来帮忙!"熟悉的声音传来,是我实习时的带教老师张医生。
我深吸一口气,跟着冲进抢救室。十六岁的我刚从卫校毕业,还在等待工作分配。此刻,所有课本上的急救知识,都变成了血淋淋的考验。
"什么农药?剂量多少?"张医生一边布置护士准备洗胃,一边问我。
"是打地虫的农药,大伯兑得有点浓。"
抢救室里一片紧张。张医生忙着给大伯洗胃,我在一边帮忙。大伯呼吸特别困难,戴着氧气罩,整个人难受得直哆嗦。
不知过了多久,大伯总算缓过来了。我瘫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白大褂已经被汗水浸透。抢救室外,大伯母和堂哥们焦急地围过来。
"没事了,但需要住院观察。"我强装镇定。
张医生帮忙安排了普通病房,走廊尽头的206,一间条件稍好的双人间。病房里还空着一张床,倒也清净。
"你们都回去吧。"我对大伯母他们说,"地里的活不能耽误,我在这守着就行。"
大伯母迟疑了一下:"可你......"
"大伯母,我学医的,懂这些。有什么事我马上找张医生。"
送走家人,夜色渐深。输液器里的液体一滴一滴落下,大伯的呼吸终于平稳了。我趴在床边的小桌上打盹,忽然听见大伯在说话。
"杨娃......"
"大伯,咋醒这么早?难受不?"
"没事,就是看你这样,心里过意不去......"
"说这些做啥。您好好养着,我去给张医生说一声。"
夜里,我我得时不时看看他的情况。走廊的灯光透过输液瓶,在墙上投下微弱的光斑。这是我第一次独立照顾病人,每个细节都不敢马虎。
天亮时分,我正给大伯换新的输液瓶,就听见门口传来脚步声。
"老张,这间还有床位没?"
"206吗?里面还空一张床......"
2、门被推开,一个中年男人被护士搀扶着走了进来。他的脸色发白,额头沁出细密的汗珠。
"就是急性肠胃炎,闹肚子闹的,吊两天水就好了。"张医生跟在后面。
"麻烦医生了。"男人的声音有些虚弱,但还带着客气。我注意到他说话时的语气和神态,不太像我们这个偏僻山区的人。
新来的病人姓王,是外地来出差的。光是这一点就让人觉得新鲜——在我们这个小县城,见到外地人可不多见。
"小杨,麻烦你照看一下王叔。"张医生拍拍我的肩。
我点点头。这时大伯已经好多了,能自己坐起来喝水。我帮王叔挂上药水,见他西装裤还规规矩矩扎着裤线,就搬了个小板凳给他垫脚,看着就跟咱们农村人不一样。
"你是这里的护士?"王叔问。
"不是,我刚卫校毕业。"我一边把药水调慢点,一边回答,"大伯是我亲戚,我来照顾他。"
"卫校毕业?"王叔眼睛一亮,"今年分配了没有?"
"还没有。"我笑笑,"可能会分到乡卫生院吧。"
王叔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他看人的眼神特别,不像个普通病人。我这乡下小子,竟然有点儿发怵,可又说不上来为啥。
午后,大伯要上厕所。我帮他把针先拔了,扶着他慢慢走。回来时,王叔也想去方便。
"我帮您吧。"我自然地走过去。
王叔有些不好意思:"怪麻烦你的......"
"王叔,这都是应该的。"我一边扶着他,一边说,"您看,我这不是还没分配工作嘛,就当提前实习了。"
接下来的一天里,我忙着照顾两位病人。大伯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好,王叔的胃肠炎也在慢慢好转。
让我没想到的是,王叔话挺多,而且说起话来很有意思。他经常和我聊起外面的世界,说起大城市的医院,说起现代化的医疗设备。
"小杨啊,你知道吗,医学这个行业,最讲究与时俱进。"王叔一边打点滴,一边说,"你现在是中专学历,以后有机会一定要继续读书。"
我心说,您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爹每年光超产钱就交了仨,能让我上个卫校就已经是村里第一个了。
"年轻人不要给自己设限。"王叔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现在是好时候,机会多着呢。"
听他这么说,我心里竟然真的升起一丝期待。这个看起来并不普通的病人,说话总是这么不一样。
3、第三天一早,大伯的情况已经完全稳定,医生宣布可以出院。大伯母来接时,一个劲地让我也回家休息。
看着还在打点滴的王叔一个人,我心里直发愁。
外地人,孤零零的,这要是有个啥事可咋整。索性我就再多待一天。

送走大伯一家,病房突然安静下来。王叔放下手中的报纸:"小杨,这几天真是麻烦你了。"
"王叔太客气了,照顾病人是我们学医的本分。"
"你这孩子,是块好料子。"王叔认真地说,"踏实,有责任心。"
我不好意思地笑笑:"可能是从小看我爹给人看病,耳濡目染的吧。"
"你爹是村医?"
"不是,就是个赤脚医生,帮乡亲们看些小病。"
"那你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能分配个好点的单位吧。"我老实回答,"最好是县医院,但那都是有关系的人才能进......"
话没说完,突然听见走廊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走廊里的谈话声越来越近,我听见有人喊着"县长"。
"王县长!王县长在这间吗?"
我愣住了。只觉得耳朵嗡的一声,脑子里一片空白。
王叔——不,是王县长,轻轻摆手:"小张啊,不是说了别来医院吗?"
门口探进来一个穿制服的司机:"县长,您这两天没去上班,大家都很担心......"
我的天老爷,这几天我可是啥都干了,扶他上厕所,帮他系裤带,还一口一个'王叔王叔'地叫,这下可闯大祸了..。
难怪他说话不像本地人,难怪眼神那么锐利,难怪对我的前程这样关心。
想到自己这几天毫无顾忌地又是扶又是搀,甚至还帮他系腰带,我脑子里嗡的一声,这几天的事一下子全明白了。
说不上是害臊还是害怕,就是腿肚子直打颤。一个县长,让我这么伺候了好几天...
"小杨,愣着干什么?送我一程?"王县长的声音打断我的思绪。
门口停着一辆崭新的2123吉普车。我战战兢兢地跟在后面,一路上大气都不敢出。
到了我家门口,王县长突然说:"你的工作分配,我会关注的。"
"王...王县长......"
"还叫王叔就行。"他的语气依然和往常一样温和,"记住我说的话,好好准备,该来的总会来。"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分配通知——县城城关医院。这是除了县人民医院外最好的医院。
村里人都说我运气好,我心里却怪不是滋味。
运气确实好,可这运气里头,装的是王县长看得起我这份心。
进了医院,我就是个地地道道的老杨牛,别人下班约饭,我就抱着书啃,整得连隔壁村相看的姑娘都杨了,办公室的躺椅就是我的床。
困了就去冷水房泼把凉水,饿了就啃个干馒头。
一想到王县长当初在病房里跟我说的话,就觉得浑身都有劲。
整整两年,我就这样熬着,终于拿到了大专文凭。
这天,我站在县政府门口,攥着文凭的手心全是汗。
两年来我从没找过王县长,就等着有了成绩再来。
门卫打量我半天,仔细登记后才放我进去。
见到王县长时,他的鬓角添了些白发,但精神矍铄。
看完我的文凭,他露出欣慰的笑容:"好小子,果然没让我失望。要不要去省医学院读个三年制本科?"
我一愣,这样的机会对我来说简直像做梦一样:"可是医院不会批准我脱产......"
"这个你不用管,回去等通知就是。"王县长的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
4、1994年秋天,我背着简单的行王,踏上了去省城的火车。
王县长帮我争取到了公费生的名额,还特意把我叫到办公室,嘱咐了几句。
"小杨啊,这一去就是三年,到了省城要好好学习。"他说这话时,目光中带着我熟悉的期许,"咱们县里正缺人才。"
省医学院的学习很苦,但我甘之如饴。
从中专到大专,再到本科,每一步都走得异常珍惜。
那些年,课本和手术刀就是我最好的伙伴。
过了几年,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回县人民医院。这一年,王县长已经调任到了市里。
记得报到那天,站在医院门口,想起当年在病房照顾李叔的日子,心里头五味杂陈。要不是他当年看得起我这个毛头小子,我现在指不定还在村卫生室打杂呢。。
那时的我,还只是个懵懂的卫校生,如今已经是正经的本科大夫了。

人生就是这样奇妙,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遇见谁,也不知道一个不经意的善举会带来怎样的转机。
后来,我也调到了市医院工作。
每逢周末,我都会去看看早已退休的王叔。有时帮他量量血压,有时就是坐着聊聊天。
这天,我又去王叔家。老人正坐在阳台上晒太阳,看到我来,笑着招招手。
"王叔,今天感觉怎么样?"我习惯性地拿出听诊器。
"老毛病了,不碍事。"他摆摆手,"倒是你,听说评上主治医师了?"
"嗯,上周的事。"
王叔欣慰地点点头:"好啊,真好。"
阳光透过纱帘洒在他花白的头发上,我忽然记起了十六岁那年的夏天。
那时的我,不过是个刚毕业的卫校生,而他,是一个偶然住院的病人。
谁能想到,这一晃,竟然过去了这么多年。
"王叔,"我放下听诊器,"那年要不是遇见您......"
"傻孩子,"他打断我的话,"是你自己够努力。这些年,我看着呢。"
我心里一热,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
这些年,每次看到王叔,我心里就暖烘烘的。
说来怪,明明是县长,可在我这儿,就真跟自家长辈似的,亲得很。
窗外,又是一个明媚的午后。
我想,这世间最美的风景,不是看到了什么,而是遇见了谁。
声明:
本文非新闻资讯内容!内容来源于互联网素材改编。
作者专属原创文章,无授权转载搬运行为一律追究到底!
部分图片非案件真实画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