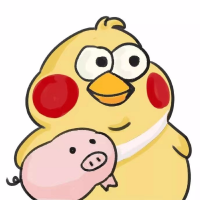我爹官至右相那年,梁王送我一个俊美的苗蛊死卫。
我心悦于他,多次为他的倾命相护感到动心。
只是我忘了,他终究只是个无情无爱的死卫。
后来朝廷群伐爹爹叛国,新皇下令诛我族群。
他是梁王身边最冰冷锋利的刀刃,手中沾染我家人的血。
我心灰意冷,命悬一线之时,却又见他慌乱抱着我。
“我有情于她,请您相救。”
1
天定元年,新皇登基,荆州知州姜方明受新皇提拔,官至右丞相。
此等光耀门楣之事传遍了荆州,家中大喜,祖母忻悦,让父亲将朝堂奖赏救济难民,与其共乐。
我那时已有两月之余未见过父亲,得知他回家的消息,便急匆匆跑去他的院落见他。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周行之。
他守在紧闭的房门外,身形挺拔削瘦,肤色如那时隆冬天大抔飘落的雪,面容清隽俊朗,神情淡漠,看着也不过少年郎的年纪。
我要进屋,他却阻拦着我。
父亲向来对我随和温善,府中规矩也少,我急着见爹爹,执意入屋。
下一刻,他竟面无表情拔剑,剑刃抵着我的脖颈,余光中那锋利剑刃上泛起的冷光,似乎毫不畏惧地要将我的肌肤划开。
青碧是与我一同长大的丫鬟,见状赶忙将我护在身后。
“好大胆的侍卫!剑竟敢指姜府大小姐!”
闻言,他只是不紧不慢放下手中的剑,冷声道。
“职责所在,谁来都一样。”
我差点被他气死,只能站在亭廊,挨着雪天的冻。
片刻,房门被推开。
我正想向父亲告状,却不料看见的是一个陌生男子。
他一袭青衣,装扮低调,可衣裳上繁杂精细的云纹却显现出别样的尊贵。
我猜想他是父亲的客人,便乖巧行礼,安静站在一旁。
楚礼认得我,便道。
“我方才听到了姜小姐的话,他是死卫,只执行命令,不明事理冲撞了姜小姐。”
头一次听到死卫二字,我好奇看向周行之,他垂首低眸,整个人毫无情绪地杵着,一言一行都得听从主子的命令,倒是真真切切应了死这个字。
“我罚他在雪地里跪几日,再将他送给姜小姐,以表歉意,如何?”
楚礼唇角噙着礼貌笑意。
话落,周行之便动身跪在了雪地中。
送我?
我怔愣住,将一个男人送我,我要他做何用?
刚想拒绝,便看到房中走出的父亲,他朝我使眼色,我立刻明白眼前不是可随意拒绝之人,只好点头应下,答谢。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梁王,新皇一母同胞的弟弟。
他递给我一块玉佩,有了它,周行之便会无条件听我差遣。
我不明梁王为何要送我一个死卫,父亲动身前去送他,院落中只剩我和周行之。
这样大的雪,就算武力高强,哪能挨过几日之时呢?
我让他起来。
他跪坐在苍茫雪地中,语调平淡:“奴犯了错,应该受罚。”
我一时语塞,便问他:“你犯了什么错?”
他愈加垂首,道:“冲撞主子。”
我叹气:“可我现在让你起来。”
他充耳不闻。
我还未见过如此死板固执之人,便拿出那块玉佩,冲他道:“诺,我现在命令你,起来。”
他的眼睫上也落了雪,毫无生气的白笼罩着他,只是抬眸一眼,眸光聚在我手中的玉佩上一瞬后,他便照做起身。
周行之高出我许多,还未扫净身上的雪,来到我身前时带着凛冽的寒冬冷意。
我看着他清隽的眉眼,感慨他长睫如羽翼,漂亮得养眼,不禁心生愉悦之感。
“你现在是我的侍卫,那就得听我的命令。”
他看着我。
我说:“第二个命令,以后不可自称为奴。”
2
我问过父亲,梁王为何要送我死卫,直觉告诉我不仅仅是冲撞之事的补救那样简单。
问了许久,我才知,父亲得去京城当官,不久后我们姜家便要搬去京城。
还有,梁王向新皇讨要我做他的王妃。
得知消息那刻,我如五雷轰顶,久久道不出一言半语。
我尚未至及笄之年,婚嫁之事不知要远到哪里去,何况要嫁给一个陌生人,我自是百般不愿。
那时窗棂被风雪敲打,砰砰作响,父亲静坐房中,眉眼低垂。
我红着眼,问:“一定要我嫁给他吗?”
父亲第一次对我的祈求回应沉默,那时我看不出他的无力,对他的不作为心生怨恨。
我跑到房中嚎啕大哭,将屋中瓷器都摔碎。
祖母与母亲来,我视而不见。
平时与我相处甚好的几个下人来宽慰我,一一被我赶出了房中。
我顶着哭肿的眼坐在窗边,一眼就看到站在院落树下抱剑而立的周行之。
唯有我拿着那块玉佩发令,他才会有所作为。
其他时间,他都像个局外人,事不关己,淡漠站在一旁。
他是梁王送给我的,我讨厌梁王,自然也对他心烦。
那天青碧给我送信,城南顾娘子的婆婆恶疾缠身,请我前去医治。
我自幼学医,常跟着医馆师傅去各地替人诊病。
祖母生病之时,我苦寻药方上一味药材不得,还是顾娘子帮了我。
这个人情,我定是会还的。
我收拾东西,急匆匆欲往外赶之时,瞧见跟上的周行之。
顿时烦躁之意涌上心头,我皱眉斥责。
“不用你跟着。”
周行之面对我突如其来的怒意,神色没什么变化,只是朝后退了半步。
“奴……”
他常这么自称惯了,说出口后想起我的命令,又连忙改口。
“我得保护小姐。”
我在这里活了十几年,每一条街巷都了如指掌,荆州民风淳朴,姜家向来乐善好施,从未得罪过人,哪会有这样多危害安全之事?
懒得与他多言,我冷声命令。
“不准跟着我。”
他闻言不语。
我起步走向院落之外,穿过亭廊之时,余光瞧见周行之又回了那棵树下,正欲放下手中的剑,似想要坐下休息。
“周行之。”
我喊他。
他回头看过来,青光照着他半边眉眼,乌发在穿堂风中轻扬,如此之姿,应是一个意气风发的马缰少年郎才对,怎么会是一个死卫。
那刻,我就是不想让他如意,便吩咐。
“你跟着我,帮我拎箱子。”
我让他放下手中的剑,安心拎着药箱助我医人。
他没有犹豫,只是松开剑柄那刻,我恍惚看到他蹙眉,极轻极短暂的一瞬。
似是不愿。
3
顾娘子的婆婆患了风寒,我替她施了几针,回府时记起少给了一味独活。
正欲返回时,见周行之驻足望着某处,随后便被慌张的声音喊住。
“姜芙大小姐!救救...救救我!”
是个蓬头垢面的老乞丐。
他半躺在逼仄的巷子口,似乎是路上瞧见我的身影,仓皇费了极大力气爬出来,仍旧大喘着气。
腿疾不能行,小腿上皲裂的伤口因为无药可用,已然生了疮。
我还未迈步走向那边,便察觉周行之垂眸看我。
他的眼神中,隐喻着某种期盼。
我愣了一下,探究他的神情许久,好奇地问他:“你想我救他?”
他眸光停滞一下,眼睫低垂,点了点头。
这倒是新奇,平时冰冷寡言、拔剑打打杀杀的人也会想着救别人。
我故作沉思。
“也并非不可,但我帮了你,你怎么报答我?”
他垂眸,那神情莫名显出几分局促,半晌道出句。
“你吃杏子糕吗?京城的杏子糕。”
听到京城二字,我便又觉得无趣。
“不吃。”
“算你欠我个人情。”
我蹲在药箱前,找出一包药材,递给周行之。
“帮我送给顾娘子。”
他的目光仍停留在气息奄奄的乞丐身上,很快无言接过我手中的东西,应声后离开。
我擦拭着翻找出的银针,看着周行之的背影,想起楚礼同我说的。
周行之是苗蛊死卫。
苗蛊死卫,幼时身体里便被下了蛊虫,在死卫营里日复一日地训练,直到被人买走的那一天。
而那块能使唤他的玉佩中,有操纵他身体里子蛊的母蛊。
若违背命令,他将身受蛊虫啃食撕咬之苦,毫无喘息之时,直至死去。
这样的死卫,大多都无情无爱。
当真无情无爱?
若没有情,又怎会不愿放下手中的剑,抑或怜悯世间的苦。
“谢谢姜大小姐。”
老乞丐感激不已。
我替他清理好疮口,笑道:“你唤我姜芙便好。”
“我也是实在疼得厉害,冬天太冷,没办法只好找您了。”
“没关系,这个扎针敷药便能好。”
银针尚未扎完,我听到身后陌生的声音。
“阿芙。”
除了家里人,几乎不会有人这样喊我。
那声音僵冷,又故作柔和。
我回头看去,心却凉了半截。
来的人是楚礼。
待彻底看清我救治之人的模样后,楚礼的神色便又冷了几分,那掩藏不住的嫌恶被他倨傲的神情覆盖。
他将人带到了一处院落,审问似的落座屋檐之下。
老乞丐被人按压在苔藓地上,浑身战栗不敢发声。
我不明楚礼为何动怒,只好跪下。
“阿芙,你贵为未来的梁王妃,这双手,不该碰这样的人。”
他微勾唇角,语气森寒。
我虽想反驳,却也知晓眼前之人得罪不起,便垂首道:“姜芙知错。”
“这双腿烂成这样,似乎也没什么治疗的必要。”
楚礼眸光轻扫匍匐于地的老乞丐,轻笑看我。
“不如砍了吧?”
我脊背瞬时一僵,赶忙抬手求情。
“今日之行是姜芙失礼,他只是求医心切,还请梁王高抬贵手。”
对于我的请求,楚礼似乎不为所动,只是淡言轻语。
“阿芙,女子行医,本就有辱名节。”
“你贵为荆州知州独女,你的教养和礼节就该告诉你,这样卑贱之人不可近你的身。”
“知州和知州夫人,可是从未教导过你?”
他的话便如刀子,生生剐开我的脸皮。
从小到大,我尚未受过如此羞辱。
何况字字句句,针对着我的父母。
那一刻,我不再避着他的视线,挺直脊背抬首,一字一句道。
“自我幼时学医,父母和师长对我的教导皆是,医者行针,不分尊卑。”
“如若梁王觉着我为民行医坏了未来梁王妃的名声,大可退婚。”
一颗心在我胸腔中猛跳,我却不后悔自己说出这样的话。
直到,沉默被楚礼的发笑声打破。
我只听他喃喃自语道。
“姜家……可真让我刮目相看。”
随后,刀子划破颈喉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我的衣袂被老乞丐的血染红。
“……”
楚礼带着人离开,只留下我和一具佝偻的尸体。
我僵硬跪在原地,直到发红眼眶装不下隐忍的泪水。
耳边有脚步声。
我迟缓回头,见周行之给那具尸体盖上了粗布。
那粗布下蜿蜒流出的血迹,触目惊心。
我苍白着唇,始终道不出“对不起”三字。
4
老乞丐悄无声息死在冬天,死在我替他治腿疾那日。
那日回家,父亲重重责罚了我,下令没收府中所有行医书籍和工具,并且不准我以后再施针救人。
我跪在祠堂中,对他的话感到陌生。
“您现在要我与从小您教导我的背道而驰,我如何做得到?”
我哭红了眼,却只能换来他严词厉色。
父亲罚我在祠堂跪两日,禁食一日。
母亲泣声求情,父亲仍旧不为所动。
我从未觉得溺爱我的父亲这般苛责于我,就好像是那趟京城之行,将他换了个人似的。
那时隆冬,夜里霜寒,挟风裹雪冲撞窗棂,祠堂紧闭的大门也被吹开。
脊背那几层薄衣被风雪吹湿,我僵着身子跪在祖宗的牌位面前,身子被吹得难受,却毫无力气起身关门。
没过一会,有人来将那门关上。
步履很轻,应是我脑袋有些沉重,没听到那脚步声,直到余光中显现一抹晃动的墨色衣袍,我才发觉身旁站着一个人。
他先将手中的剑放下,顺势蹲在我身旁。
“我将他的尸体埋在了城西,给他换了新袄,棺材里还垫了层被子,冬天他不会冷。”
周行之的声音很轻很淡,又像跟我汇报似的那般刻板。
我没吩咐他做这些,但也庆幸他做了这些。
悔意压着我的心头,我艰难喘着气,无论我怎么想,始终没法消弭它一分一毫。
“是我害死了他。”
周行之拆着手中的一包油纸包裹的东西,缓声道:“不怪你。”
我鼻尖一酸,眼泪顺流而下。
如若……如若我不顶撞梁王……
“姜芙,你没错。”
“医者仁心,行针不分卑贱。”
我眼泪朦胧看去,周行之低着头,眼睫落下阴影一片,随着烛光轻晃。
“死卫为了保命,不会放下手中的剑,如若你想,亦可握紧手中的银针。”
他将拆开的那包杏子糕递到我面前,透亮的眼眸里映着跃动烛火,看到我的泪,他愣了一瞬。
我回神,赶忙偏头抬手拭泪。
“这是我在城里找的杏子糕,味道应该大差不差,吃一点垫肚子吧。”
我接过那糕点,拿起一块咬了口,甜腻在唇齿间蔓延。
身上似乎也没那么冷,那样疼了。
吃东西的空暇之余,我才后知后觉忆起他方才唤我什么。
我朝他看去,这才发现他欲言又止地盯望着我。
短暂地对视几秒,他垂首避开。
“方才出言不逊,冒犯了小姐。”
我摇头。
借着烛火,我能将他看得十分清楚。
周行之比许多贵家公子都生得好看,就像画本里的谪仙,身段也好看。
“你以后不用唤我小姐,姜芙就好。”
我停了一下,才道:“阿芙也行。”
5
“江南水灾,朝廷发放的赈灾粮和各州的救济粮马上就抵达荆州关口,关口南面府邸已经清扫好,可作运输灾粮队伍的落脚点。”
“江南之地外族虎视眈眈,眼下重振任务繁重,稍有差池疆土必失啊。”
“姜大人,荆州也为江南水灾集捐了不少物资,可北面一带瘟疫霍乱不堪,朝廷任务要我们援助北面,这可如何再跟民众开口?”
春来之际,雨便淹了江南。
恰逢北面霍乱,荆州再无力援助,父亲苦愁不已。
春季一过,整个姜家便要迁去京城,荆州民众便会迎来新任知州。
父亲将姜家坐落荆州几十年的宅田全部卖去,又遣散了家中所有奴仆,每人给了一笔银两,其余的换来物资援助北面霍乱。
祖母与母亲虽不舍,却还是肯定了父亲的做法,常同我说:“你父亲是个好官。”
我当然也这么觉得。
那时与父亲下令禁止行医已过两月之久,我想着父亲气应已消去,便去请求同行救援北面霍乱。
“不可!你将入京嫁于梁王,既要成皇室之人,行医之事便不可再做!”
我厌恶极了梁王,也不喜京城那样的地方。
“你当真要我一辈子待在京城?做那既不贤能也不良善之人的妻子?”
父亲当即扇了我一巴掌,那一掌,是我生平从未遭受过。
“姜芙!以后不可再出此言!”
“你也最好断了行医的念想!”
那一掌不重,却让我对父亲生出了怨恨。
父亲已然官至丞相,为何还左右不了我的婚事?
“皇上旨意,不是你父亲能撼动的。”
周行之作为我的贴身侍卫,跟随我几月有余,像是我肚子里的蛔虫似的,即使我不言,他也能猜透我在想什么。
“那他……皇上为何要乱点鸳鸯谱?也没问过我想不想嫁。”
我气冲冲地踩捻着落地的初春落花,紧接着生出一个念头。
周行之想我嫁给梁王吗?
我还未问出口,他便劝我。
“小姐还是遵旨为好。”
那时凉意的春风都吹不散我胸腔中的愤懑和失落。
我咬牙问:“我嫁给梁王,你就没有不舍吗?”
周行之静默看着我,过一会才答:“我只要小姐安全便好。”
我不该跟一个死卫谈情爱,因为他们本就无情无爱,只会执行命令。
可我觉得周行之不一样,他有情。
我想起那块玉佩,可以命令周行之的玉佩。
一气之下,我砸了那块玉。
我赶忙去查,书上说,母蛊死去,子蛊的承载体会陷入昏迷,醒来后便如同正常人那般。
可周行之没有反应,他也不知我砸了那块玉。
我那时才意识到,梁王送我的那块玉中,没有周行之身上蛊虫的母蛊。
楚礼在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