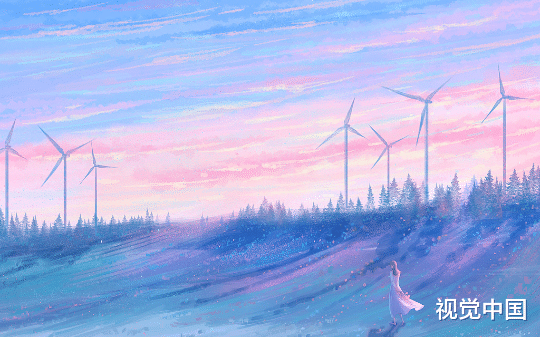和薄斯言分开的第三个月,他空降成了我的领导。
公司年会,我被组长拉去敬酒。
男人装作不熟,垂眸拒绝:「最近在备孕,酒就不喝了。」
后来,转场去酒吧。
薄斯言当着众人的面,将装醉的我揽腰抱起。
男人气极反笑:「周暖,你就不能哄哄我?」
01
「周周,你就说咱薄总这脸绝不绝?」
同事用手肘撞了下我的手臂,示意我往边上瞧。
此刻男人正斜靠在沙发上,偏头听旁人讲话。
许是不喜被开玩笑,薄斯言微微皱眉,面露不耐。
抬眸喝酒间,两人的目光猝不及防地撞上。
连带着心跳都乱了一拍。
我避开视线,下意识地往同事身后躲了躲。
「怎么了?」
摇摇头,我低声回道:「低血糖吧,头有点晕。」
同事顺势递给我一大块蛋糕,「是不是空腹喝酒了,你先垫垫肚子。」
回宁市这么久,我怎么也没想到再遇薄斯言会是在公司组织的部门聚餐上。
耳边的音乐逐渐大声,我埋头吃着菜。
一口一口,直至光盘。
「部门联谊秒变迎新会,真是无趣。」
「办公室恋情,真有人敢谈?」
「甜不甜不说,分手了还得见面,才是真的尴尬。」
我扯了扯唇角,没有说话。
下一秒,身旁的同事弯着眼睛凑近。
「周周你说,我去追那空降的帅哥,能有机会吗?」
喝酒的手一顿,我支着脑袋回她:「同公司……你真不觉得像太监宫女对食吗?」
话音未落,耳边传来哄笑声。
「周暖,看不出来哎,还是资深甄学者一枚。」
这话不知被谁传到了隔壁桌,就连喝酒的薄斯言都抬眼看了过来。
我有些绝望地闭了闭眼。
刚刚就不应该多嘴。
02
酒过三巡,包厢的门被人推开。
女人一身高定,踩着高跟鞋偏头探了进来。
目光瞥过我时有片刻的停顿。
随即唇角轻扯,带着几分轻蔑。
我认得她。
毕业时,薄斯言家里给找的联姻对象。
哈佛高材生,正儿八经的豪门千金。
他妈妈说过两人青梅竹马,天生一对。
「你好,我找薄斯言。」
女人侧身进来,顺滑的黑色长发别在耳后,露出小巧精致的耳坠。
整个人看上去像个气质温柔的大姐姐。
「薄总,找你的。」
刚刚还说要追薄斯言的同事像是突然泄了气,「我就知道,帅哥最不缺的就是美女朋友了。」
「没事,万一帅哥想吃小青菜清口,你还是有机会的。」
说罢,桌上众人笑作一团。
女人淡淡收回视线,走向隔壁。
「您就是咱们薄总的女朋友啊。」
沈悦轻轻一笑,「未婚妻。」
「郎才女貌。」
「薄总真是好福气。」
薄斯言身边的人自觉让开位置,「嫂子,你就坐我这儿。」
身边不少同事,举杯吹捧。
也不知道谁先起的头,莫名其妙地敬起酒来。
为了合群,我也灌下满满一杯酒。
半晌,拿起身后的包,狼狈起身。
「我去趟洗手间。」
同事立刻放下手里的筷子,有些担忧地抬头:「要我陪你吗?」
「不用。」
推门时,听见女人柔柔开口。
「阿言,咱们该回家了。」
02
身体不舒服是真,不想看见两人浓情蜜意也是真。
我晕得厉害。
在走廊里缓了好久,才慢悠悠摸到了洗手间。
几捧凉水泼到脸上,顿时清醒了大半。
镜中的女人发丝凌乱,双眼通红。
因为长期加班,本就熬夜过度的脸,此时更像是死了三天有余般苍白。
我闭了闭眼,回想起刚刚的画面,突然有些心累。
过了会儿,洗手间又挤进来两个人。
我拿着包往边上让了让,对方却没有再往前。
落锁声在身后响起。
通过面镜子,我看到身后的女人面目狰狞。
「原来你就是周暖。」
她的美甲勾起我的发尾,「长得确实漂亮。」
「谢谢。」
我拿起包,就打算离开。
下一秒,沈悦冲过来捏住了我的下巴。
力道很大,我被强逼得倒退了好几步。
想要挥手去挡,却还是晚了一步。
缓慢地抬起被打偏的脸,指甲划破肌肤,火辣辣的疼。
「周暖,京市还是宁市,你都玩不过我。」
她偏头示意另一个女生将我按住,用手机壳拍着我的脸:「你一个妈不要爹不爱的东西,要拿什么和我比?」
沈悦冷冷收回手,轻哼出声。
「周暖,你怎么老是阴魂不散啊!」
「我出国那会儿,一个没看住,薄斯言就叫你勾住了。」
「怎么,还想再体验一次做三的快乐?」
我仰头看去,同她对视:「舔了这么多年还没舔上呢?」
沈悦的脸上出现一瞬间的慌乱,随即是掩盖不住的怒意。
「要不是你,我们早结婚了。」
嗤笑一声,我反手将身后的女人拖倒。
……
等到从厕所出来时,聚餐早已散场。
空荡荡的走廊里只有几个打扫卫生的工作人员。
03
教训人的事情,沈悦很熟练,专门挑看不见的地方下手。
但好在我反应快,除去最开始那一巴掌,两人也被踢得不清。
卸了所有力气,我垂着脑袋往电梯口走去。
身上又疼又累,只想赶紧回家睡觉。
许是没有看路的缘故,一头扎进了男人怀里。
薄斯言低头看着我的发顶,倏地开口:「你就这么不想见我,躲到现在才出来?」
我捏紧了包带,失焦的目光顺着指尖缓缓落在掌心的那粒醒酒药。
「我们……」
男人淡淡开口:「不用你提醒,我知道我们分手了,你就当我放不下。」
未出口的话哽在喉间,我瞥见薄斯言头也不回地进了电梯。
掌心的醒酒药还沾着外头雨水的湿气。
短短几月未见,他好像变了很多。
药片顺着舌根滑进,我的喉头有些发涩。
瞬间,这股难受的感觉开始蔓延到四肢。
犹豫再三,我还是张嘴喊他:「薄斯言。」
电梯门打开,薄斯言依旧站在里面。
薄薄的单眼皮上挑,散漫又疏离。
他真的生得极好。
哪怕仅瞥见半个下巴,也勾得人心痒。
难怪会惹这么多人喜欢。
「最近在公司里,别说我们认识。」
男人脸色微微一变,眸色很暗,怒气在眼底翻涌。
「为什么?」
「公司的人容易说闲话,我可不想被别人当下饭菜。」
对面的男人稍一点头,目光从我的脸上挪开,颇有几分咬牙切齿的意味。
「行,周暖,你真行。」
好不容易强压住的情绪,又一次涌了上来。
围巾的布料挡住大半张脸,我默默走到电梯的角落,努力将自己的存在感降到最低。
男人按了楼层,不冷不淡地开口:「我送你回家?」
我的心咯噔一声,连忙拒绝,「不要。」
「嗯。」
这次,他没有再说什么。
发散的思绪被拉回,神色恢复自然。
似是闲聊,他又开口问道:「得有两个月了吧,觉得公司怎么样?」
我舔了舔干涩的唇,却不知道要说什么。
想来想去,就憋出两个字:「挺好。」
电梯到了,我目送他进了停车场。
后知后觉,自己刚刚忘了按楼层。
04
昨天在聚会上的放纵,导致我的炎症更严重了。
见热度依旧没有下降的趋势,只好打车去了趟医院。
医生怀疑是甲流,给开了抽血的单子。
等报告的期间,瞥见部门的小群炸开了锅。
【刚刚薄总来我们部门干什么,有人看见吗?】
【没有啊,我刚刚在厕所摸鱼。】
【哦,听到他把沈经理叫出去了,好像是说婚假什么的。】
看到这儿,我的心咯噔一下。
但很快,又冷静了下来。
五分钟后,报告出来了。
细菌感染导致的发烧,需要输液。
我看了眼时间,又向人事补了半天假。
流感季,输液大厅里挤满了人。
我拿着刚取的药,到窗口排队扎针。
后面是一家三口。
女孩病恹恹地窝在爸爸怀里,「讨厌生病。」
「乖宝宝,打完针就好啦,昂~」
余光瞥见女孩黏糊糊地缠着妈妈,心生羡慕。
要是爸爸没出轨,妈妈也没离开。
我是不是也可以……
十岁那年,妈妈发现爸爸出轨,他的私生子就比我小三个月。
女人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婚。
我哭着求她带走我。
她却说:「暖暖,错误的决定要及时止损,爱自己才是终生浪漫的开始。」
她走了,带走了所有属于她的东西,却唯独留下了我。
长大后,我才意识到原来她口中的那个错误……是我。
继母对我并不差,她只是更爱自己的孩子。
就因为偷拿了桌上的二十块钱,我被爸爸拿着衣架满院子抽。
泪眼朦胧间,我看见了被打弯的铁丝。
男人红着脸、瞪着眼:「白眼狼,你和你妈一样自私。」
可他却忘了那天是我的生日。
我拿走的那二十块钱,买回来也不过是块巴掌大的蛋糕。
从小我就被继母告知,家里的一切资源都属于弟弟。
弟弟想要什么,爸爸就会给他买。
而我想要的东西,只能靠自己争。
05
大一那年的寒假,我高铁转公交,奔波七个小时到了家。
推门进去,三个人正围着圆桌吃晚饭。
「你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
男人夹菜的手微微停顿,「可能是手机静音了吧。」
下一秒,电话铃声在耳边响起,他的脸上却没有半分被戳穿的窘迫。
继母笑着圆场,「哎呦,肯定饿了吧,快洗洗手来吃饭。」
桌上咕嘟冒泡的清汤火锅,好像都在嘲笑我的天真。
我冷笑着往房间走去。
推开门却发现,那件小屋子早已被改造成了杂货间。
「一个姑娘家家的,跑到京市这么远的地方念书。一年到头也回不了几趟家,那房间空着也是空着。」
「那我睡哪儿?」
男人随意指指阳台的走廊,「这儿给你支个行军床,铺两层软垫子,不比房间差。」
「那阳台都没帘子,一女生怎么睡啊?把我的房间给她好了。」
继母伸手轻拍了下男生,「吃你的饭,搬来搬去也不嫌烦。」
看着默不作声的父亲,我连夜定了返程的车票。
哪能不恨?
从妈妈丢下我的那日,我就知道自己再也没有家了。
这个世界上,只剩自己。
我虚荣物质、尖酸刻薄、敏感自卑、自私自利。
可是,你哪能要求一簇生长在阴暗角落的野草明媚大方?
下一秒,护士小姐姐一针扎下来,直接就给我疼清醒了。
我拎着吊瓶不断往里走,找了个相对安静的角落坐着。
06
再醒来时,发现自己靠在别人的肩膀上。
「不好意思。」
男人带着耳机和口罩,睡得很熟。
看样子,估计是没听见。
我闭了嘴,小心翼翼地将贴着他的腿往外挪。
「换了最后一袋,刚刚见你不舒服,给调慢了速度。」
听到熟悉的语气,我猛地抬起头。
坐在我边上的这人,不是薄斯言,还能是谁?
给我一种两人从未分开过的错觉。
喉头干涩,我吞了吞口水,说话的声音有些哑。
「谢谢。」
男人先是有些愣神,随机挑了挑眉。
一声轻笑从唇瓣溢出,他毫不遮掩地盯着我看:「周暖,你真不知道我来宁市做什么?」
他的眼神过于直白,我紧张到后背都沁出了层薄汗。
【截断点】
这算什么?
知道我们没可能,还来招惹我做什么。
睫毛颤了颤,我强逼自己从他脸上挪开视线。
随后,我听到身旁很轻地叹了声。
「走了。」
下一秒,掌心被强硬地塞进来盒退烧贴。
我的目光下意识地追着他的背影往外走。
未喊出口的名字,就这样卡在喉头。
吐也不是,咽也不是。
他的跟前站着个女人,和薄斯言带着同款的黑色一次性口罩。
虽看不见五官,但瞧这身形。
应该就是沈悦。
女人双手抱胸,满脸的不耐。
似是等了薄斯言很久,此时正发脾气:「你瞎啊,那女孩和我完全两个风格,这都能认错?」
男人吊儿郎当地靠过去,从鼻腔里发出一声嗯。
见他这般敷衍,女人挥拳作势要打。
「薄斯言,除了我,谁还能受得了你这狗脾气!」
07
攥着退烧贴的手一紧,我自嘲地勾了勾唇。
人就只是体恤员工,乱想啥呢。
还记得,薄斯言也曾对我说过这种话。
【为什么不回消息?】
【粥粥,你这算不算对我冷暴力。】
【不准有下次了。】
【除了我,谁还能受得了你这脾气。】
……
我和他是在大创组队时认识的。
虽不在同个组,两个项目却被安排在同间办公室。
说来好笑。
整个学生时代,我都坚定地以为他是个渣男。
毕竟,我们的初次见面并不愉快。
那天我早早到了师生交流中心写BP,享受着一个人独占整层楼的宁静。
结果没到五分钟吧,门外突然闪进来个人。
他好像不知道自己的蓝牙断开了。
带着耳机,却外放音乐。
强鼓点的重低音,咚咚咚砸在耳后。
男生皮肤白皙、长得很帅,比例也好。
就是……好吵。
我就这样直勾勾地盯着他,试图用眼神唤起他的良知。
但很显然,我高估了自己,也低估了他的理解能力。
现场这么多座位,他偏偏要坐在我的对面,手机还正正好摆在两张桌子的交界处。
我很少用聒噪来形容一首音乐。
可除此之外,我找不出比它更合适的形容词来。
「同学,你能把歌关了吗?」
实在憋不住,我停下了打字的手。
好家伙。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一个人能如此快地变红。
当然,物理意义上的。
从耳根到脖子,噌一下全都被染上了粉色。
「抱歉。」
他手忙脚乱地停了音乐,却像是突然蔫了。
08
男生拽过卫衣帽子,将整个脑袋都给罩在里面,仅仅露出一对好看的眸子。
只不过,按手机屏幕的指尖一直没停。
我猜他肯定是在和朋友蛐蛐我。
大概又过了半小时吧,他突然拿着支笔走到我的跟前。
「学姐,我的笔坏了,你能借我一支吗?」
余光瞥见那支被暴力折弯的水笔,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
当然,我也没戳穿他。
只是从眼前的笔筒里随便抽了支递给他。
临走前,他又喊住了我。
「学姐,不好意思啊,我还没用完。要不加个微信,等你下次过来了,我再还你好吗?」
我挑了挑眉,「不用,笔是办公室的,你用完直接放这就行了。」
后来听组员提起,我才知道他就是那个在表白墙天天被捞的学弟。
没几天吧,他也不知道从哪里要来了我的微信,坚持不懈地加了几次。
不过,我都没同意。
再后来,我保研本校。
研究生时,替导师监考,又撞见了薄斯言。
巧合得有些过分,这次不加不行了。
他比我家楼上那个三岁的小邻居还要吵,一天能喊二十几遍的学姐。
我给他回一条,他就能还我五条。
约着吃了几顿饭,又正巧赶上我学业压力大的时候。
牵手、接吻、确立关系。
该做的,不该做的。
在那几年全都做了。
再后来毕业,他留京市,我回宁市。
他母亲的约谈,未婚妻的恐吓。
实在坚持不住了,我才正式提出了分手。
当然,他没同意。
只是说分开一段时间给我喘息的空间。
也是那会儿,我从共友口中知道他是东基集团的太子爷。
朋友笑着问我,「你后不后悔?」
「后悔什么?」
「差点你就能嫁进豪门,实现阶级跨越了。」
「不。」
人总是要和握不住的东西说再见。
薄斯言的起点,是我奋斗一辈子也无法达到的终点。
有些人注定没有以后,到此为止才是最好的结果。
可以说,我是个极度自私的人。
同样,我过得一塌糊涂的人生,没有任何可以承担风险的能力。
原以为分手后,我能重新回到那个刀枪不入的自己。
却没想到,这一切都只是徒劳,走不出来的始终是我。
舍不得删的照片,反复查看的聊天记录……
好不容易缓了点,他却又出现了。
这一下让我所有的努力付之东流。
09
从医院出来时,天已经完全暗了。
又赶上晚高峰,等了十几分钟也没等到接单。
无奈,我点了取消。
紧了紧脖子上的围巾,准备去最近的公交站。
额前热度依旧没退,此时又吹了风,整张脸都在发烫。
我偏头在包里一顿翻找,扯出那盒被攥得有些发皱的退烧贴。
再抬头,看见薄斯言半倚着公交站牌。
他按灭烟蒂,漫不经心地垂着头。
眼中出现一点波动,我扭头想躲。
「周暖,你跑什么?」
胸前横过只大手,一把将我箍进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