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失踪后,镇上多了道名菜「活叫驴」。
在驴子活着时,割开皮浇烫水,汁肉鲜嫩,叫声勾魂。
爹让我日日养驴,却从不让我靠近烫驴的铁台。
说是怨气太重,怕伤着我。
直到我意外发现,死掉的驴都没舌头。
那么声音究竟是从哪儿来的……
1、
破旧的饭馆,熙熙攘攘挤满人,连根筷子掉落地上都得竖着站。
「老谢!能不能上,大伙馋不住了!」
话音刚落,一阵异香袭来。
在此起彼伏的吞口水声中,爹抬着绑好的驴上台了。
可我总觉得那不像驴,哪有驴肤若凝脂,凹凸有致的。

「驴腿三斤!」
「腩肉两斤半!」
这些人只要念过一次,我都能记住,抄录给爹。
他接过单子,手起刀落一块驴皮就被掀开,露出鲜红嫩肉。
这时的驴还不会叫。
直到大哥将滚烫的热水,「嗞啦」一下浇在裸露的肉上。
它就会被烫得四肢乱颤,发出的却是娇喘的呻吟。
似勾魂的海妖般,勾得周围男人气喘如牛。
「小玲!发什么楞,给大伙上肉!」
大哥出声叫我,我连忙过去端盘子。
滚烫的热水顺着铁台流下,台上的驴子已经死了。
它是被活活烫死的。
伸手接到盘子时,爹一驴鞭抽在我手上,瞬间皮开肉绽,鲜血直流。
「左脚越过栅栏了,不长记性的蠢东西。」
烫驴的铁台周围有圈栅栏。
我爹说驴死得惨,怨气重,女娃子受不住,从不允许我接近半分。
「掉地上的驴肉别浪费,捡起来吃了。」
我吃驴肉会吐,但爹看我眼泪打转也没半分心软,铁了心罚我。
那肉太厚,中间没烫透,血水丝丝外冒。
我一咬牙,闭上眼睛抓起肉就往嘴里塞。
关键时大哥拉住我「爹,小玲今天也累了,这块晚些我烤了,给你老下酒。」
爹冷哼着转过头,他放过我了。
大哥递给我杯热茶「别往心里去,爹是为你好,喝了去后院休息会。」
去后院的路上一头小驴撞到了我。
它朝着的方向正是热闹的大堂,我捞起它。
日日养驴的我,一眼就看出,它母亲就是刚被烫死的那头驴。
我哼着歌安抚怀里的它。
回头看,月夜下,肉馆泛着冷光。
十年前这里不过是个已经倒闭的饭馆,爹也不卖驴肉。
但自从我娘失踪后,爹重新开了馆子。
生意爆火,只卖「活叫驴」。
2、
第二天起床,我就失声了。
喉咙里面干痒难耐,像有东西般。
我在后院正用手薅着嗓子眼,转头看见大哥满脸疑惑地看我。
看我无法说话,他噗嗤笑了出来「来,吃了这个就好了。」
他手掌中有颗晶莹剔透的东西。
我捏起来往嘴里一丢,熟悉的香味从口腔里散开。
那些被烫死的驴,身上也是这个味。
「活叫驴」每周做一次,做菜前几天,选中的驴会被圈养到红房子里。
里面日夜散发这诡异的香气。
爹不让我进,但我偷看过,他们正在用黄色的浆液抹驴。
没一会,我的嗓子确实好了。
「大哥,这是什么呀?」
他神秘地凑近我耳朵「虫卵。」
我脸色一变就要吐出来。
他连忙说「我开玩笑的,这是味药材,要连吃一个月才能好。」
我盯着大哥眼睛「哥,打小你就对我好,你不会骗我对吧?」
娘失踪后,是大哥一手带大我。
如果没有他, 我或许早就死在爹某次的殴打中。
大哥灿烂地笑着「当然,我对娘发过誓,要照顾好你。」
说完大哥就跟着爹出门,我留下收拾昨晚的残局。
铁台上驴的骨架已经被抬走。
说来也奇怪,我跟爹一起埋过骨架,那些驴嘴里都空空如也,没有舌头。
没有舌头,怎么来的声音。
收拾着碗碟中零星肉沫,一声呼唤打断我思绪。
「给我点剩下的肉沫子吧,我给你好多钱!」
转身瞥见门口的陈瞎子。
他是人牙子。
镇上大多人的老婆都是他拐来的,也包括我娘。
「我不要钱,爹不喜欢你,你走吧。」
他眼冒绿毛地看向碗里「那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觉得值,就把手里那碗肉沫子给我。」
陈瞎子是镇上出了名的百事晓,我生性好奇,被勾起了兴趣。
看我没拒绝,他凑近我「我拐来的姑娘,最后她们都被你爹剁碎混在粮里,喂了驴。」
我眉头一抽,谁家驴吃肉啊。
转身就要走,他却抢过我的碗跑了。
第二天,陈瞎子死了。

3、
鲜血染红了整条街。
从喉咙延伸而下至肚皮的刀口,贯彻陈瞎子。
他整个人被剖开,大咧咧晾着。
肠子七零八落纠缠着,被一只野狗叼住,用力扯断。
我怀里抱着小驴「月月,我们回家吧。」
跑回家,正好撞到王二狗来家里。
他用铁锁链拴着一个女人,递给了我爹。
她也是被拐卖来的,她们生不出孩子后就只剩被玩弄到死。
经常会有人送来给爹,可以抵上几顿饭钱。
也有一些家里差钱的,干脆就再将人卖回给人牙子。
她们身上完好的器官,就是最后可以榨干的价值。
「小玲!烧水去。」
爹出声命令我,他嫌脏这些女人脏,都是要洗干净再快活的。
我放下小驴不敢耽搁,慢了就是一顿鞭子。
可我还是遭了秧。
「死丫头,几天没收拾,手脚都慢了。」
我正要解释,他大脚重重揣在我背后。
额头重重磕在灶台上,一会血就模糊了视线。
「爹,原谅我,我马上就弄好。」
看着我颤抖求饶的样子,他还是不解气,抓过尖刀直接划破我的脸「跟你那晦气娘长得真像,求饶的样子
更像,破点相好。」
爹满意地走了。
他深深的恶意令我如坠冰窟,在他眼里,我和圈里的驴有什么区别?
都是能随意割开皮肉的畜牲罢了。
最后还是大哥,将我从柴火房捞出来。
他心疼地擦去我伤口污渍,紧紧抱住我。
「没事了,小玲,我找到你了,没事了。」
说罢,他从包里拿出上次给我吃的那晶莹剔透的「药」。
「哥,我不想吃,这东西和驴身上一个味道。」
「小玲,那些驴之所以能勾得街坊邻居魂都丢了,就靠这个药,吃了你的脸才能好。」
看着他坚定的眼神,我闭上眼,面无表情地吞下。
心里却已死灰一片。
大哥也在骗我。
这东西不是药,就是虫卵。

4、
第二天睡醒,我脸上的伤口只剩一道粉色的痕迹。
皮肤嫩得跟可以掐出水一样,连平坦的胸部,都开始有了起伏。
我拿过一根针挑破指尖,血液滴落,细长的白色虫子在其中扭动。
轻含住渗血的指尖,从第一次大哥喂我吃,我就知道那是虫卵。
每一次,我都会问大哥「能不能不吃?」
我得到的答案都是「乖,大哥不会害你。」
我已经给过大哥机会了。
今天是烫驴的日子,和往日一般馆子里早早开始上客人。
但不同的是,平常只能吃边角料的李叔,今天将会分得最好的那块肉。
在我刻意安排下,今日进馆的人比平日多。
「小玲,怎么回事?那边几个,不在我和爹邀请名单内。」
我低下头轻晃大哥袖子「哥,平日里他们对我照顾有加,今天我想还他们个人情。
你放心,我保证驴肉够,但...」
大哥无奈地摇头,最后掐了下我鼻尖「放心,我会跟爹说,是我叫多了。」
我开心地扑进大哥怀里,勾起了嘴角。
盛宴随着美妙的呻吟开场,只是今日的食客们,有些兴致索然。
「今天的驴肉总感觉差点味。」
「确实,没以前那感觉了。」
趁爹安抚着大伙,我钻去角落,将一盘极好的驴腱放到李叔面前。
「吃了就快去吧,以后每周我都会给你一块。」
得到我承诺的李叔顿时喜笑颜开,抓起渗血的驴肉大快朵颐。
李叔离开后没一会,镇上传来响锣声。
「着火了!着火了!快来人救火!」
我探出头问「哪儿着火了?」
「后面那条街!」
那条街是居住最集中的地方,馆子里吃饭的好多户都住那。
馆子里的大伙闻言手中筷子一顿,立马转头就跑。
爹和大哥也随着大家一起去救火。
饭馆做的是熟人生意,大家有困难时,爹总是要帮一把的。
剩下的人自然也跟着走了
等馆子中的人都散去,我走进爹从不让我越过的栅栏。
铁台上的驴早被挖成了肉窟窿,却还在用力喘息着。
它也是我亲手养大的,我还记得给它取的名。
伸手蒙住它的眼睛,手起刀落,结束它的痛苦。
将它从铁台上推开。
我拿出一根细铁丝,顺着铁台摸索,直到摸到个小孔。
有天半夜我被惊醒,看到饭馆大堂亮着。
爹就这般,拿着根细铁丝打开了铁台。
我回忆着爹的动作对着小孔弯曲铁丝,「咔」的一声,烫驴的铁台像盖子般,弹了起来。
下面是黝黑的洞口。
我伸头往里看去。
剪了舌头的驴当然不会叫了。
叫的是我那失踪的娘。
是被滚烫热水反复浇淋、十年不见天日的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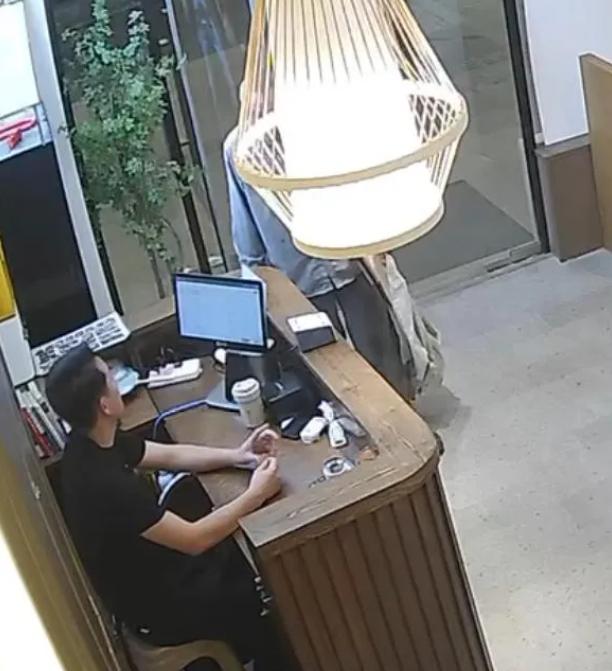




有点扯了,天天开水烫,还能活10年
请问你的金条要怎么分
快意恩仇,好书!
没有舌头不能发出声音?又不是没有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