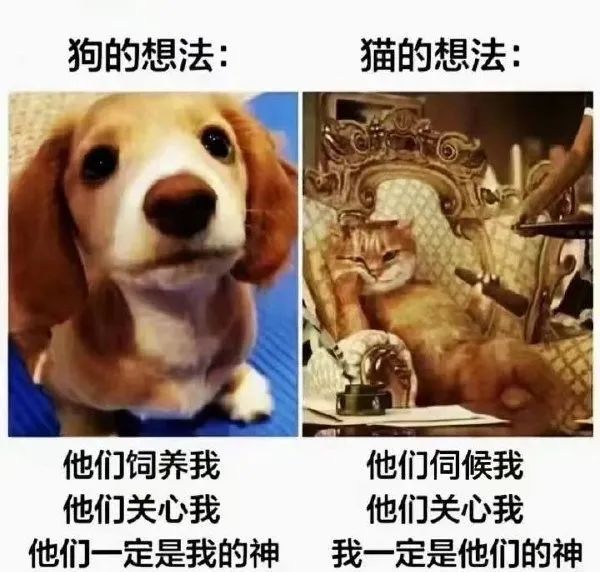我爸是全村的活神仙。
可我知道他不干好事,专门做让人断子绝孙的生意。
男人进了我爸的看诊室,暴躁的性格能立马变得温顺。
女人进了我爸的看诊室,直接从蓬头垢面的大妈变成妙龄女郎。
我爸更是有一个不收钱的规矩。
来找我爸看病的,必须要拿自己身上一块肉来换。
可即便这样,来我家看诊的人依旧络绎不绝。
我不明白我爸明明是神医,为什么不去行医救人,偏偏要做伤天害理的事。
直到我也从身上拿下一块肉给他。
我才明白他的良苦用心。
1
「我不管,你今天要是不给我排上队,就别想回家!」
眼前恶狠狠地拦住我的,不是村霸恶霸,而是跟我从小到大的好朋友。
他被家人训斥的时候,我出面调和。
我被家人打的时候,他挡在我身前,一声不吭的挨了几鞭子。
我从未见过他如此凶狠的对我。
这一切只是因为他想拿到我爸看诊的号码牌。
「我做不到。」
我不想帮他,因为我知道我爸药里加了让人绝育的东西。
我不想让我的好朋友也受到迫害。
我知道他们家为了逼他来看诊,使用了各种办法,软的不行用硬的,硬的不行用软的。
如果再没有拿到看诊的号码牌,以他父亲的性格,定然把他打得生不如死。
我苦口婆心的劝,「别人追求的那些,不过是身外之物,况且这个世上根本没有完美,我爸有没有修仙的本领,我还不知道吗?」
「你觉得去找我爸开个药,就可以让你长寿,就可以让你荣光繁华?」
「即便真的有这样的东西,我爸为什么不留着自己用?」
我点到为止。
作为他的好朋友,我算是仁至义尽了。
大壮怒吼道,「我有什么办法?人人都要找你爸看诊,谁不看谁就落后,落后是要挨打的。」
他一点也没说假话。
从前个月起,大壮就是一瘸一拐的走路。
整张脸写着疲惫和痛苦。
可我咬死不松口,大壮拿我没办法,揍我又下不了手,只能眼含热泪的离开了。
若是他真的知道,我偷偷把他的名额又往后排了排。
估计会恨透我。
可我即便让他恨我,也不愿他抱憾终身。
大壮曾跟我说过希望有朝一日,能和儿女们一起在农田里嬉笑玩乐,尝遍山中野果。
我绝不能害他。
回到家,我准备在用这一招。
结果我爸已经根据他的病情,已经开始调理配方了。
我故意打翻了给大壮煎的药。
我爸这次并没有像以往那样暴揍我一顿,反而冷静的警告我,「刘咪,你以为的对他好,却并非是真正的为他好。」
我听不懂他的意思。
也不愿意听懂。
隔壁的齐爷爷来找过我爸后,一直到老死都没人送终,包括村头的沈嬢嬢,村尾的刘叔叔更是独居老人。
膝下无儿无女也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这些偏偏都是在大家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迫发生。
甚至只要有家长点头,我爸就会同意给他看诊。
全然没有问过孩子的意见。
我不认为孩子年纪小就该是理由,所有的选择都应该自己做主。
没有人能代替他做选择。
我不服。
更不认可我爸不要病人的钱,只用病人身上的一块肉做酬金。
我千方百计的拦着大壮来我家,可没有想到,他以一种我完全想不到的方式彻底离开了我。
他被人打死了。
所有原因,都指向他没有及时来我爸这里看诊。
我一度怀疑,我爸是不是用了什么法术,可以把全村人的脑子洗的干干净净。
我气得把家里家具砸了个稀巴烂,「爸,你明明是个医生,可你为什么要做伤天害理的事?」
我爸冷静道,「难道不是因为你害了自己朋友,如果他当时来我这里看诊了,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到底是我病了?还是这里所有人病了?
我爸是什么神仙吗?
有预判的能力?
我愣了许久。
想到我家以前很穷的时候,我爸穿着破棉袄天天给人上门问诊。
不知何时,我爸不出门了。
家里更是冰箱洗衣机天天换,就差整个房子都焕然一新。
现在想来应该是从,我爸开始在药里加上一块绝育药粉开始。
自从加了这块药粉后,我们家的生意就络绎不绝。
男人来了,在暴躁的性格也变得温顺起来。
女人来了,直接从蓬头垢面的大妈一跃成为妙龄女郎。
后来不管有病没病,谁都想要挂挂号开点药。
最后直接变成一票难求。
甚至有的家长还鼓动自己的子女来看诊。
一来二去找我爸看诊的成了一个潮流,如果谁家没来反倒成了一个不可饶恕的事情。
大壮也是稀里糊涂丧命。
反倒让人找到机会说上两句。
我带了一点大壮喜欢小鱼来坟墓,有时我在想,如果当初我没有偷偷换掉他的号码牌,会不会结局就不同了。
哪晓得我供台上的小鱼被打翻。
小翠直接站到了供台上,「你还有没有良心?这种货色你也供他?」
2
我听不懂她的意思。
不过在旁边人的闲言碎语下,我听出了所以然来。
他们在说大壮为人不端,是渣男,各种强迫其他女性。
这次也是因为他对一个女孩下手,结果被女孩家人发现了,失手打死了他。
从一开始就是他的错。
所以双方协商之下,谁也没有追究谁的责任。
这个说话,我一点都不信。
大壮比我大三岁,从小也比我懂事,就是因为太乖了,所以经常被打得浑身是血也不吭声。
我一口咬定,「这中间绝对不会有什么误会,这种事他干不出来。」
小翠哽咽道,「怎么干不出来?他连自己家人都敢打,怎么干不出来?」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大家在颠倒黑白。
而这一切都是从我爸开始药里加上绝育药粉开始的。
他们开始失去同理心,失去最基本的准则。
于是我回家之后偷偷躲在我爸的看诊台下面。
我倒是想看看我爸用什么手段,把这些人治疗的服服帖帖。
我爸一进来先是穿上了全套的卫生服饰,又仔仔细细的把手术台周边认认真真的消毒,直到把每一把刀具都擦得反光,这才开始今天的手术。
男孩的妈妈在门口千方百计的嘱咐着。
而躺在手术室的男孩,不断地在流泪,嘴里喊着,「不要!」
我趴在看诊台下,撩开帘子,只能看见我爸拿手术刀的样子。
还未看仔细看,就已经结束了。
男孩的妈妈哭着说谢谢,刚要拿出钱来,就被我爸推了回去。
他拿着从男孩身上取下的一块肉,得意道,「我只要这个。」
我吓得捂住口鼻,不敢发出一点声音,就在这时,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腿。
我爸似笑非笑,「该你了!」
再次醒来,我依旧躺在坟墓一角。
这个梦太过真实,真实到我似乎亲眼见过。
可明明从小到大,我爸对我的好,只多不少。
妈妈在很小的时候就跟着其他男人跑了,我爸一手把我拉扯大,当时家里穷,可每赚得一笔钱,我爸总会给我改善一下伙食。
我想知道真相。
想知道我爸为什么不让我沾手学医。
我故意将今天的排号顺序打断。
有些村民后来的,却先去看了诊,有些村民最先来的,却等了十天半个月。
大伙聚集在门口你一句我一句的抱怨着。
「人家医馆的帮手那么娴熟负责,哪里像刘家这样,养着一个白吃饭的,整天什么事都做不了。」
「就是,连号码牌都能够搞错,还能做什么事?」
「一共就这点事,还做不到真是可笑!」
我知道他们在说我。
我也希望他们说我,
只有这样我才能进我爸的看诊所,所有的真相才能就此展开。
我在门外敲门,我爸刚一打开,门就顺手被他带上。
就连一点偷溜进去的时间都没有给我。
等我爸安抚好所有的病人后,又重新开始问诊。
直到病人全部走了之后。
我爸给了我一巴掌,「有些真相是你看不到的,也不必知道。」
「要不是你多管闲事,大壮能死吗?他如果早点来我这里,也不会有今天的结局!」
「你尽管去大街上看看,有多少人穷困潦倒?有多少人暴尸荒野?」
「马上就到冬季了,又要死大批大批我们的同胞,你没有看到?」
提到生死,我就想到大壮。
天气寒冷是老天的事,我们管不了。
可人为调制绝育药,却是天理难容。
这次我砸了他的药台,毁了他的药材,直到我摔碎了一口大缸。
里面一个个小肉块流出……
我整个人都傻了,胃里一阵阵的翻着恶心。
可不知为何,我这样的场景竟觉得有些熟悉。
我爸气得直哆嗦,「你给老子滚!滚!」
我从惊恐中迅速调整过来,不服道,「我现在就告发你的恶行!」
一开始我爸在药里加绝育药的事,我闭口不谈。
就是怕村民知道后,把我和我爸赶出去。
可如今我爸逐渐疯魔。
他们的家人只是希望他们的过得好点,可没想到,最后却是用这种方式。
每个从我家的出来的人都带着泪。
我绝不能看到我爸在堕落下去。
可到了帽子叔叔的地方,他们却用扫帚把我赶了出去,「出去!出去!一会儿院里来检查,看到你我们都要完蛋!」
3
我连话都没说完,他们就断定我是在胡闹。
不光把我赶出去。
就连我待过的地方,他们都用消毒水和杀虫剂反复清理。
活像我是什么很晦气的人一样。
被赶出来后,天已经全黑了。
眼前一辆急速驶来的快车,飞出一个绳索,短短三秒就捞走一个人。
快车调转车头,突然向我而来。
我猛地一激灵,岔开腿就跑,可跟在后面的是车。
如今就算是插翅也难逃。
身后的绳子快速绑在我身上,还未来得及叫唤,我整个人已经被带上了车。
我被丢上车的时候,正好有几双手将我接住。
大家面面相聚,互相知道对方都逃不过此劫,每个人的脸上都是藏不住的恐惧。
「这辆车每晚都会抓我们这些小流浪,逃过这劫,逃不过那劫。」
他们有的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好地方,可有的身上白白净净的一片,不像是小流浪。
可想而知这些坏人,抓到谁,谁就要死。
我试图观察周围,发现整个车厢里,除了人空空如也。
连接车门的铁栏杆又硬又粗,绝非他们几个凡胎能够搞定的。
车辆进入一个小巷后,便是深深的黑暗。
在这里伸手不见五指。
这里哪怕疯狂喊叫,都没有一丝回音传过来。
我不信邪,用牙齿咬着车上的铁皮,试图挖出一个洞来逃生。
结果同伴指着另一个朋友的牙齿。
上下的几颗大牙全掉,一张嘴看上去像深不见底的黑洞。
「别想了,这些方法我们都用过,我们逃不出去的。」
我心里一下子泄了气,可又不得不装作还有办法的样子,「等我想到办法,一定可以出去的。」
想起离家出走的时候,我信誓旦旦地说,一定要还所有村民的一个真相。
结果现在连自己都救不了,还想当救世主。
可不知为何,在这暗无天日的车厢里,我似乎想起了什么,犹如我曾亲生经历过一般。
车停了。
我们所有人被拖下了车。
我被包裹在各色各样的尖叫声和惨叫声中。
「现在做哪个?还是一起来,直接上麻药!」
另外有个声音立马制止了他,「不行!太多了,麻药的用量分布不均,很容易导致有的用多了会的痴呆,用少了会被痛醒。」
我冷不丁一惊。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可我并不敢往那边想。
可打碎的药瓶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里面一块块的小肉成了堆。
按照我爸平均每天要看诊四个人。
那么多的量,仅仅靠每天问诊,也不足十分之一。
我越想越觉得害怕。
直到我旁边的同伴被抓走,我一爪子抓到那人手上,那人暴怒,立马用放开同伴抓住我的颈脖。
我不并非不怕,而是我想知道。
里面的那个人究竟是不是我最爱的人。
突然间一阵眩晕,我的眼前逐渐模糊,哪怕有人把我的舌头拉出来,我都没有反抗。
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面前。
他全副武装着,可护目镜下的一双眼睛格外透亮。
看着他手上的刀缓缓落下,我微张着嘴,「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