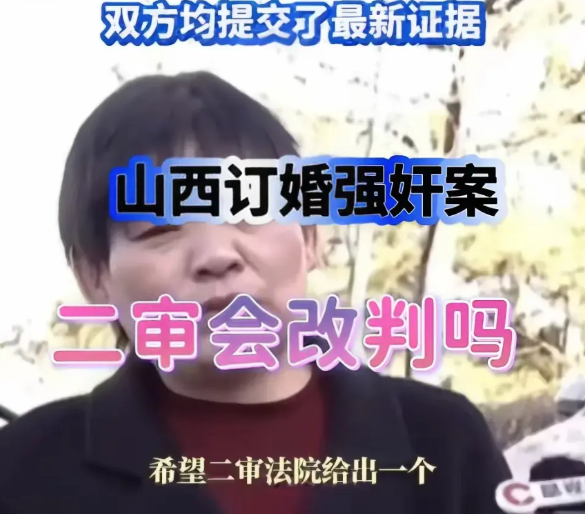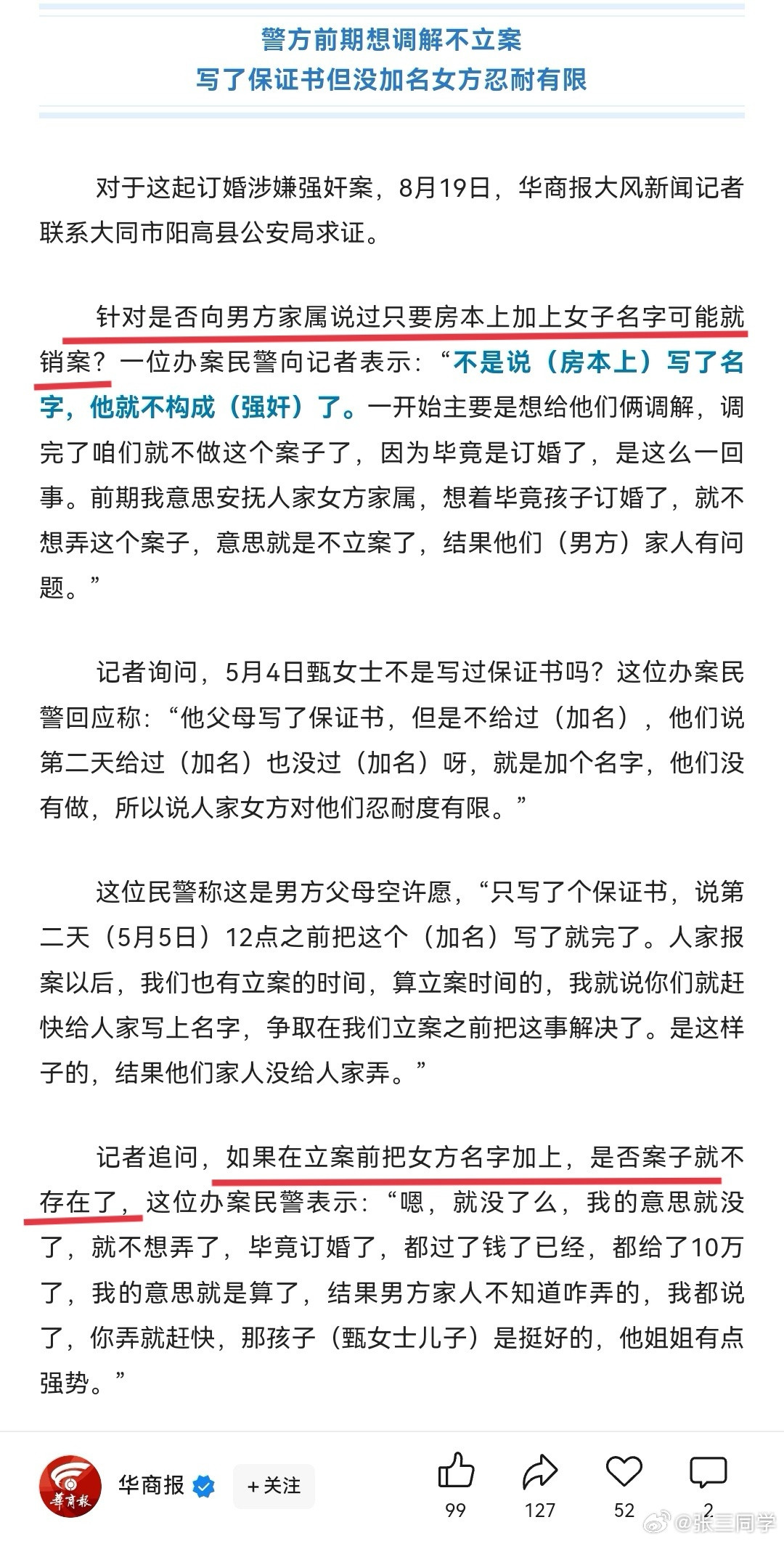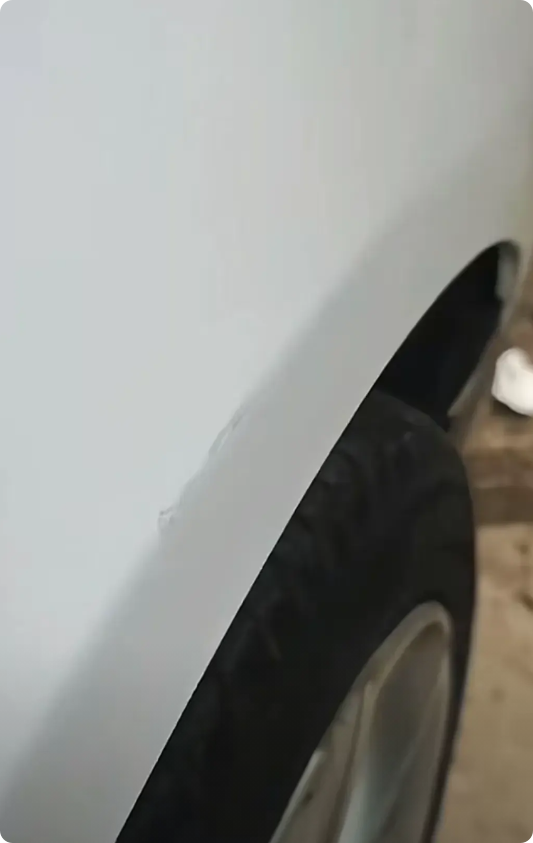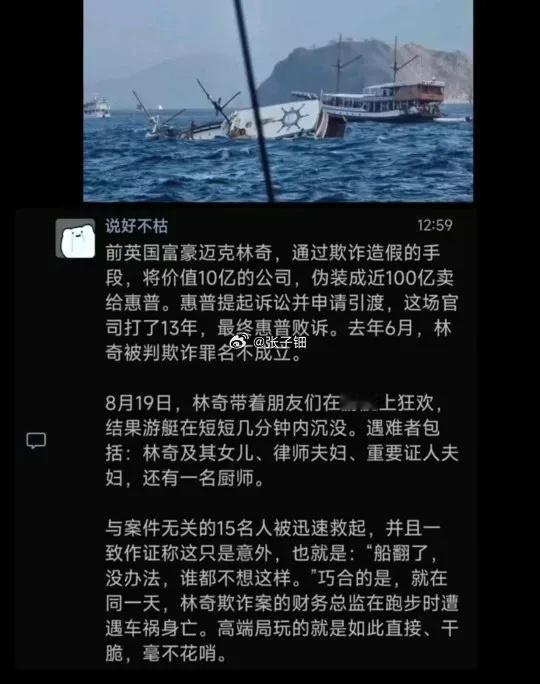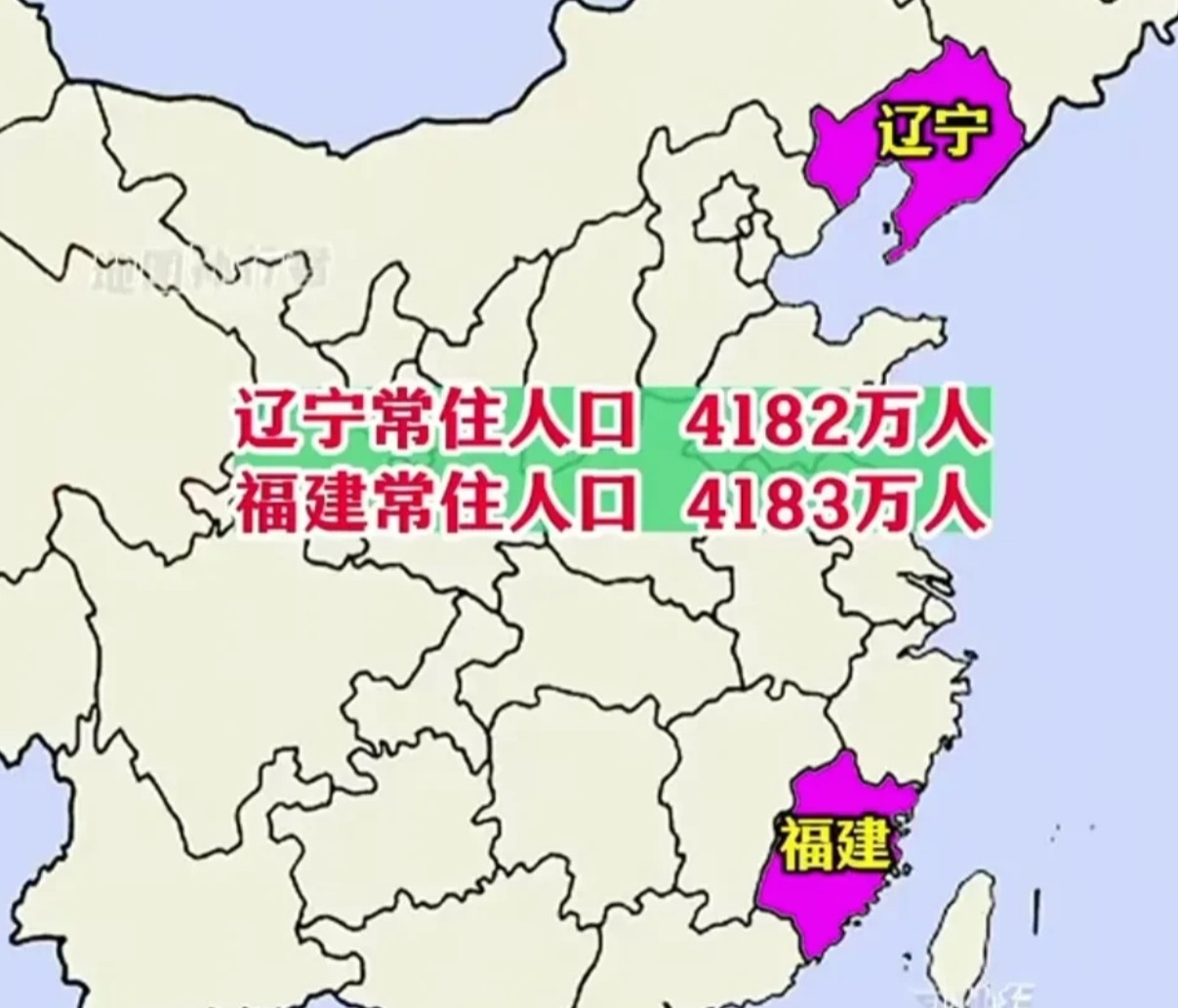辽宁,一男子因母亲与一商贩起争执,竟深夜驾车遮挡车牌,捡拾石块砸向商贩。石块意外击中货架反弹,致某路人手部擦伤。警方以"殴打他人"对男子作出拘留5日+罚款200元顶格处罚,但监控显示商贩毫发无损,路人事后签署谅解书。男子不服,坚称"只想吓唬人",将警方告上法庭。经过审理,一审和二审法院的结果发生戏剧性反转。这场"飞石袭人"案暴露出执法裁量权与司法审查的激烈碰撞——当一块石头同时牵动"故意伤害"与"无心之失"的边界,机械执法与实质正义该如何抉择?
(案例来源:裁判文书网)
2024年6月18日,某市场内,张明(化名)的母亲李芳(化名)与商贩李强(化名)因摊位问题发生争执。
当晚,张明陪同母亲前往派出所调解未果。次日凌晨,这场普通的民事纠纷却因当事人的过激行为演变为治安案件。
据监控显示,张明在送母亲回家后,驾车行至三新路时故意遮挡车牌,随后从路边捡起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
当车辆行至人民街与三新路交叉口西南角时,张明突然摇下车窗,将石块掷向正在路边行走的李强。
石块击中木质货架后反弹,意外砸中路人高娟(化名)右手。经法医鉴定,高娟仅造成轻微表皮擦伤,李强则未受任何身体损伤。
派出所接警后,办案民警调取了沿途监控录像,对涉案三人及目击者进行询问。
张明在笔录中坚称"只是想吓唬李强",但监控视频清晰显示其遮挡车牌、捡拾石块、瞄准投掷的全过程。
8月7日,警方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对张明作出行政拘留5日并处罚款200元的决定。
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张明与高娟达成和解协议,高娟书面表示不追究责任。
但警方认为,张明的行为存在主观故意,不适用调解程序,仍维持原处罚决定。
张明遂提起行政诉讼,主张其行为应认定为"情节轻微",仅需罚款处理。
在庭审中,张明提出如下主张:
其一,石块系因撞击货架反弹误伤高娟,无直接伤害李强的故意;
其二,张明已与直接受害人高娟达成调解协议并履行完毕;
其三,张明符合《辽宁省裁量标准》"未造成伤害后果"的情节轻微情形。
警方则坚称处罚合理合法,提出如下抗辩:
其一,监控视频证明张明存在"遮挡车牌-捡拾石块-瞄准投掷"的完整行为链;
其二,石块虽未直接击中李强,但具有明显攻击指向性;
其三,调解协议仅针对高娟,不适用于存在主观恶性的治安案件。
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1、张明投掷石块行为该如何定性?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将"殴打他人"与"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并列表述,前者侧重行为方式的不法性,后者强调损害结果的违法性。
本案中,张明实施"遮挡车牌—捡拾石块—瞄准投掷"的行为链,其蓄意制造危险状态的特征明显:选择硬度较高的石块、在交通要道实施、针对特定对象投掷,均超出一般情绪宣泄的合理限度。
监控显示张明投掷前有明确瞄准动作,且石块飞行轨迹与李强站位存在直接关联性,足以认定其至少具有间接故意。即存在一定违法性。
2、张明的行为是否符合情节较轻情形?
《辽宁省公安机关行政处罚裁量权细化标准》第四十二条第五项将"未造成伤害后果"列为情节较轻情形,但该条款的适用需结合行为整体进行实质判断,而非机械对照结果要件。
警方主张张明行为具有预谋性(遮挡车牌、准备工具),故排除"情节较轻"的适用。结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量罚应综合主客观因素,但不得将不同维度的要素混同评价。本案中,张明虽有预谋表现,但实际损害结果轻微,且未造成社会秩序严重混乱,符合"情节较轻"的核心特征。
同时,高娟伤情经鉴定为表皮擦伤,李强无实质损害,损害结果显著轻微;另一方面,张明积极赔偿并获得部分受害人谅解,社会关系得到局部修复。
警方未充分考量上述减责因素,径行选择拘留并处罚款的顶格处罚,违反比例原则中"最小侵害"要求。
3、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创设的调解制度具有双重功能:既是对当事人处分权的尊重,亦是对社会关系修复的司法倡导。
本案中,高娟的单方谅解仅对其自身权益产生约束力,不能当然及于其他受害人。本案中李强作为主要冲突相对方未予谅解,但张明攻击行为实际未对其造成损害,此时高娟的谅解对整体社会危害性的降低具有证明价值。
警方以"存在主观恶性"否定调解适用,混淆了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的价值取向。
本案张明行为虽具一定预谋性,但实际危害结果轻微,且已履行部分赔偿义务,符合"民间纠纷"的本质特征(特定主体间非对抗性矛盾)。行政机关僵化理解"情节较轻"要件,实质上架空了调解制度的适用空间。
最终,二审法院撤销了一审判决,并判决撤销对张明的处罚决定。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