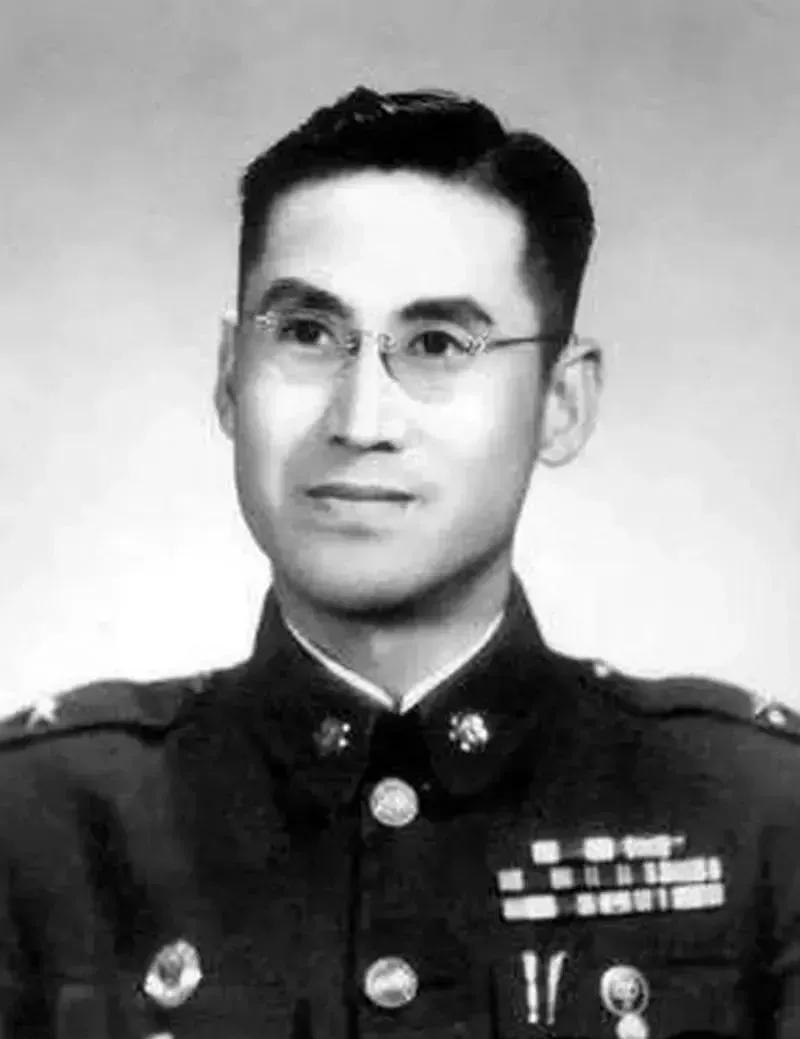1976年,女知青范红梅得到了回城的名额,她却将名额让给了男友,男友信誓旦旦地保证:“安顿好了,我就来接你!”可是,男友回城后却音信全无…… 1979年,随着知青大返城的浪潮,曾经声势浩大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正式结束。在那些曾经充满活力的农场里,随着大部分知青的离开,原本热闹非凡的场面逐渐消失,留下的只是空旷的田野和寂静的宿舍。拖拉机停在田间,已没有人来操作,学校也没有了老师授课。知青食堂里曾经的饭桌上布满了尘土,墙角处的蜘蛛网也显得格外显眼。原本象征希望的地方,逐渐变得荒凉,往日的热闹不复存在。 尽管大多数知青都离开了,但仍有少部分知青选择留下。这些人大多是因为他们目前的工作较为稳定,或者在政府机关、银行、邮局等单位工作,他们不确定回到城市后是否能找到更好的机会,因而选择继续留在农场。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知青因为与当地青年结婚,依照当时的政策,若不希望造成两地分居,将不予办理回城手续。不过,他们可以为孩子办理落户。 对于知青群体来说,情况复杂。一方面有那些希望回城的知青,他们不愿意继续在农场生活,认为自己在城市能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知青已经在当地找到了归属,安定下来。这种“几家欢乐,几家愁”的情形,反映出知青们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心态和选择。 在这些情绪的背后,有一个名叫范红梅的女知青的故事。1976年,她获得了回城的机会,但她却将这个机会让给了自己的男友,男友承诺说:“安顿好一切,我就来接你。”然而,当男友回到城市后,却再也没有与她联系,音信全无。 一九八六年深秋的一个清晨,范红梅正在县城的家里收拾屋子,邮递员送来一封信。信封上的字迹陌生,寄信人是一个叫小宋的年轻姑娘。她在信中说,自己是宋建国的女儿,父亲已经因病去世,临终前让她来传达一声"对不起"。 这封信,让范红梅的思绪不由得回到了十五年前。一九七一年,正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十八岁的范红梅响应号召,从上海来到了这片土地。那时的农村生活虽然艰苦,但范红梅很快就适应了下来。白天在田间劳动,晚上就着煤油灯看书,日子过得充实而平静。 在那个年代,农村的文化生活十分匮乏。范红梅和其他几个文艺青年商量着要办一个文艺演出。正是在筹备演出的过程中,她认识了宋建国。宋建国是江苏人,在大队负责文化宣传工作。他学识渊博,说话做事都带着城市知识分子特有的气质,在排练节目时常常能提出独到的见解。 两个来自大城市的年轻人,在乡村的天地间慢慢熟络起来。休息时一起朗诵诗歌,劳动时并肩耕种庄稼。渐渐地,他们发现彼此有着相似的理想和追求。范红梅欣赏宋建国的才华,宋建国也被范红梅的知性与坚韧所打动。 一九七六年初春,一个意外的消息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大队领导找到范红梅,告诉她因为表现优秀,组织决定批准她回城。这本是范红梅期待已久的好消息,可当她看到宋建国黯淡的眼神时,内心却犹豫了。她却将名额让给了男友,男友信誓旦旦地保证:“安顿好了,我就来接你!”可是,男友回城后却音信全无…… 1978年春天,国家放宽了知青返回城市的条件,尤其是考虑到健康问题和家庭困难,允许符合条件的知青回城。特别是独生子女可以直接回城,而多子女家庭中,有子女在农村的,也可以选择一个回城。虽然符合条件的知青人数并不多,但政策松动的信号无疑使得回城成为了可能。因此,许多知青开始寻找各种途径来实现这一目标,其中,办病退成为了最直接的方式。 有些知青在干农活期间曾经受过伤,为了能够回到城市,他们带着骨折的片子找医生。虽然医生知道他们早已痊愈,但由于这些知青有强烈的回城意愿,最终医生无奈同意了他们的病退申请。除了这种通过“特殊情况”获得批准的做法之外,还有一些知青为了病退采取了极端的方式。例如,他们会故意伤害自己,像是将火柴头刮下来吞下。这些火柴含有红磷,吃下后会造成严重的胃部损伤,目的就是为了能获得病退的资格。虽然这种行为非常危险,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它成为了某些知青回城的“捷径”。 除了采取极端手段的知青外,还有一些人则从自身的小问题入手,将问题无限放大,以期通过这样的方法获得病退。例如,有一个体格健壮的知青,几乎没有什么健康问题,但为了回城,他开始强调自己小时候尿床的问题,并通过医生的建议将这一问题提升为“遗尿症”,最终成功获得了病退的资格。 对于那些急于离开农村或兵团,却找不到其他途径的知识青年来说,病退成为了一条既快速又无奈的选择。正如云南兵团的卫生员周良宗所说,病退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抛弃”,它的背后不仅是对现实困境的无奈,更是一种希望通过回城来改变命运的尝试。 然而,病退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美好前景,许多病退回城的知青生活十分困苦。他们虽然回到了城市,却往往面临着医疗费用和生活费无法负担的问题,且很难找到工作。最终,许多回城的知青只能依靠街头的劳动服务站寻找短期工作,加入了待业青年和打短工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