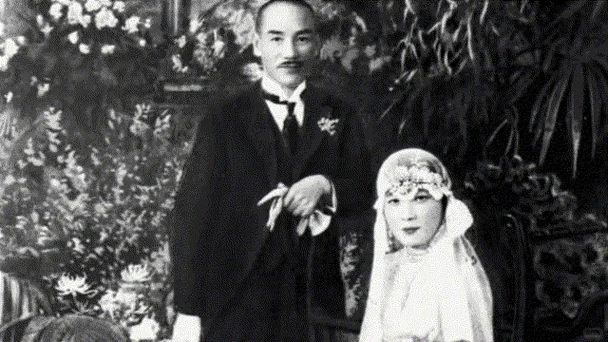许崇智被日军抓后,连写三份绝命书。很快家属被通知去接人。其子女推来灵车,不料许却走了出来。 1941年12月,日军进占香港之后,来不及逃港的许崇智很快就被日军抓进了香港大酒店。外界疯传日军会逼迫许任伪职。为了表明心志,许崇智连写了三份绝命书,以表明自己绝不失节。 许崇智抱了必死的决心,让人奇怪的是,开始的几天,根本没人来找他,日军仿佛忘了许崇智一般,这也让许崇智也很纳闷,不知日军葫芦里卖什么药。 这天,许崇智的老同学,日军在香港头目的矶谷廉介来到酒店要了一间大厅,便派人去请许崇智。许崇智得知是矶谷要见他,并不敢意外,他甚至已经猜到了矶谷要和他谈什么,无非是叫他出任伪职。其从容应对,一身旧西服,敞开内衣领,来到大厅。 矶谷一见,连忙起身相迎,伸出右手。许崇智一见矶谷那种仿佛以胜利者自居的洋洋自得神情,就产生一种反感。于是他也伸出右手,当矶谷正准备握手时,他突然把手朝自己的右额边轻轻一扬,似打招呼非打招呼。 矶谷颇为尴尬,很不自然地微微一笑,然后将右手改为让坐的姿势,请许在沙发上坐下。许崇智脸上毫无表情,仍然站着。矶谷使劲拉着许的有手摇了摇,然后把他按倒在沙发上。嘴里连说:“老同学,老同学,这是何必呢?多年不见了,今天相见,应该高兴才是。” 许崇智说:“我曾与你是同学、朋友,但你们侵略我们,也就谈不上同学、朋友,只能是敌人。你说我现在不是你的阶下囚,又有何其他可言呢?” 矶谷连忙说:“不,我们很快就会放你。你是个将才,蒋原来也只是你的手下,可现在却只给你一个虚职,简直太不像话。作为老同学我为你感到可惜,我已经请示了东京,要委你到南京去,汪手下的军队都是你的。” 许崇智按捺不住激动的情绪,不由地站了起来并且提高声调说:“我是绝对不会去南京的,我们过去是同学,现在是敌对双方。我现在还是个囚犯,你们要如何处置就处置吧。” 说完,许崇智昂然挺胸,离开大厅扬长而去。矶谷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无言以对。在场的人大惊失色。矶谷在香港大酒店与许崇智话不投机,一怒之下,他彻底抛开所渭老同学的感情,给东京发了电报,添油加醋的要求枪毙许崇智。 就在那次谈话的3日之后,许崇智在港的妻、子女等10余人得到通知,全部来到了香港大酒店前。一会儿,许崇智由几名日军押着,出现在酒店二楼大阳台上。此举是让他与亲属遥相会见,以表最后离别之情。 据说,这一安排是示矶谷特意做的,由此体现他们的“人道”。许崇智开始并不知道日军的意图,当他在阳台上举目环顾时,突然看到马路对面一群熟悉的面孔。许崇智立刻意识到这也许是一场永别。 于是他举起了右手,朝他们摆了摆,尽量显示出无所谓的样子。他特地表现出挺胸昂首的姿态,面带微笑,大有慷慨赴死的从容。 此时,马路对面的家属们已是抱头痛哭,悲伤不已。几个子女边招手,一边鸣咽,其情悲惨之极。来往市民也为之驻足,纷纷抬头仰望酒店二楼。知情者皆唏意不已,不知情者不断探寻原委。一会儿,人越来越多,以致人头攒动,交通为之堵塞。 在香港大酒店阳台与家人见面后,许崇智音讯全无。其家人知道其凶多吉少,整日在悲切、伤感中度过,以为许即将被枪毙。两天后,他们却又意外的接到要家属们到香港大酒店“接人”的通知。 家属们伤心之极,都准备披麻戴孝,并雇好了灵车准备迎接许崇智的灵柩。在港的亲戚、朋友也接到了通知,他们都赶来等候在酒店大门外。大家心情沉痛,彼此打个招呼后就什么话都没有了整个气氛悲怆、肃然。 闻讯赶来的记者纷纷抢占位置,将镜头对准大门,调好焦距,以便随时抢拍镜头。扎着黑布的灵车当时十分醒目,已有不少人对准它拍了好多照片。 大约一个小时后,众人正翘首引颈使劲向酒店大门里张望之际,却见一位脸色苍瘦、憔悴、面容倦息、年近花甲的人,拄着拐杖从门口慢慢出来。他面带笑容,频频点头,向周围的人打招呼。“许崇智出来了!”不知谁喊了一声。 正处在悲伤情绪中的家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他们确信许崇智仍然活着并正向他们走来时,不禁大喜过望。儿女们不顾一切,推开了拥挤的人群冲上前去紧紧拉住父亲的手。 好事的人群依旧很拥挤。有人嚷道:“不是枪毙了吗?这是怎么回事?转眼之间悲剧变成喜剧。有记者要探究原委,拼命挤上前现场采访许崇智。 许崇智略带微笑,显得神秘地说:“实在对不起,我很疲倦,需要休息,无可奉告。”很快许崇智在家人和亲朋的簇拥下走出酒店。 好不容易回到家,许崇智才详细地向家人说:“都是矶谷导演的一场闹剧,他为泄忿,故意如此安排以整我。至于为什么要放我,连我也说不清。也许他还有同学之情,也许认为再关我也没有什么意义,反正我是不会就任伪职,于是他落个人情。” 以后许崇智闲居香港,靠儿子经营公司的收入维持生计,后来又避居澳门。在79岁的时候,许崇智突惠心肌梗塞。这位曾经名震遐迩的一代骁将,在香港天后庙道其子的公寓里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