惭愧,一个毕业30多年的哲学系学生都写不岀来![泪奔][泪奔][泪奔] 刀郞在其演唱会用四川话说了如下一段开场白: 成渝铁路,沱江河,资中火车站,这三个意象几乎占据了我所有的少年梦,这三者就很象音乐的期望、挫折与实现,那个时候就觉得很对映,有一种梦想置身于现实的高度叠合的状态,那时候唯一阻碍自己的就是这条河,迈过这条河,踏上铁道,就能抵达人生的车站,奔向自由,逃离平庸。 到后来慢慢发现,这段音乐的诠释,更像一个生命的隐喻,期待和实现是一个“能指”,而挫折是“所指”,这个结构搭建了我与自己、与他人、与外物的关系。就像不能单一地去看待音乐,因为音乐一头在现实,另一头在理想,它是结构的、空间关系的。我们所有的实现并不是唯一圆满正确的实现,是有漏的、残缺的。我们满意的结果往往都是通过大脑完形而得到的。所以当我迈过了这条河之后,去到的每一处地方,攀登到人生经历的每一个节点,就会发现,生活是无法参与的,你甚至连一个观察者都做不到,你是一个局外人。 就像这次回到资中,就会发现记忆存在的偏差。这种偏差是历时的,也是共时的,有时间的原因,也有场域的原因,既有当时年少认知的错陋,也有现实期待对记忆的塑形。 从我期待走出去,从与母体割裂的那一刻,那些我们普遍认为美好的、圆满的,全都变成了空洞的、焦虑的、孤独的。漂泊瓦解了曾经让我感到母体赋予温暖的归属,并逐渐遗失那些原初的记忆。每到一处,对我来说都是各个充满隐喻的符号。我获得的、我必须承受的,都包含在他浩瀚的文本之中。 我无法掌控生活,踏入别处以后,仿佛只有创作这件事,能成为生活的介质,而我只能用此作为媒介参与生活,所以音乐对我而言的那种媒介作用在与自己的沟通中最为明显吧。从最早开始的感官式的与世界交付所投射的内心的冲动与宣泄,到后来理念式的由内心向外寻找空间和时间的思考。我把材料、形式、根源、概念变成我与自性交付的仪式、语言、模型、行为因素,以此来探索边界,寻求自由。所以我希望我的所有创作是一个“见而不识、识而不义”的探索未知的过程,它不会因为熟悉或者陌生,而对此过程产生障碍。 我想这会是我以后创作需要的一个向度,这样的作品不是传达某种特定的思想观念和美学理想的载体。他们是我对事物实在或者世界的塑形,在这种赋形中,实在的世界就会被构建出来的表象所截获。所以在别处的空间里,作品解释了我和空间的关系,也可以说这种关系描述了我存在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的作品是不受我掌控的。当面对听众时,他们会自己给自己阐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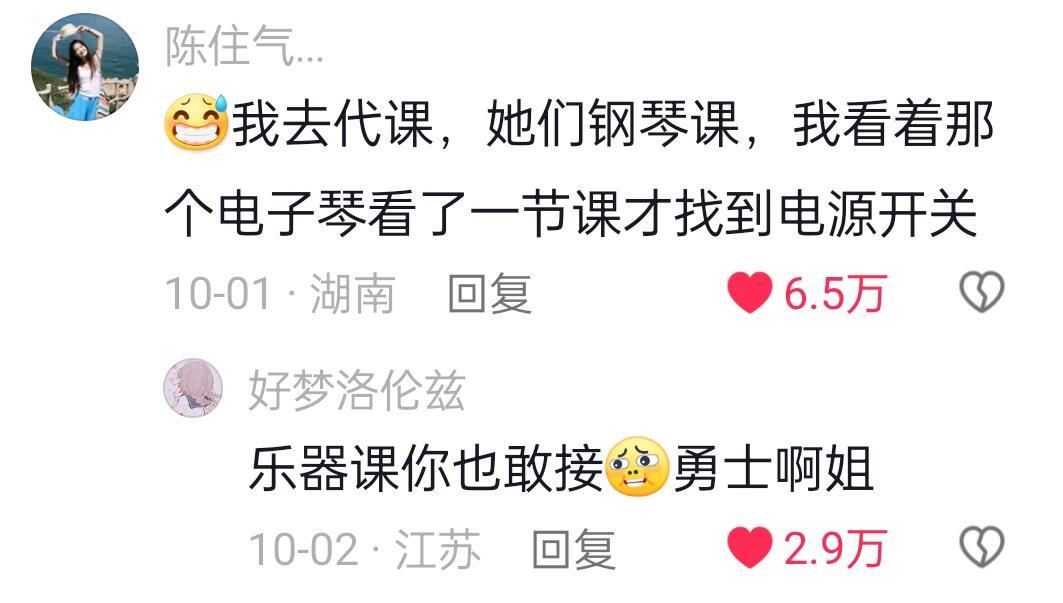






刀郎老师是个孤单的人,他只是需要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