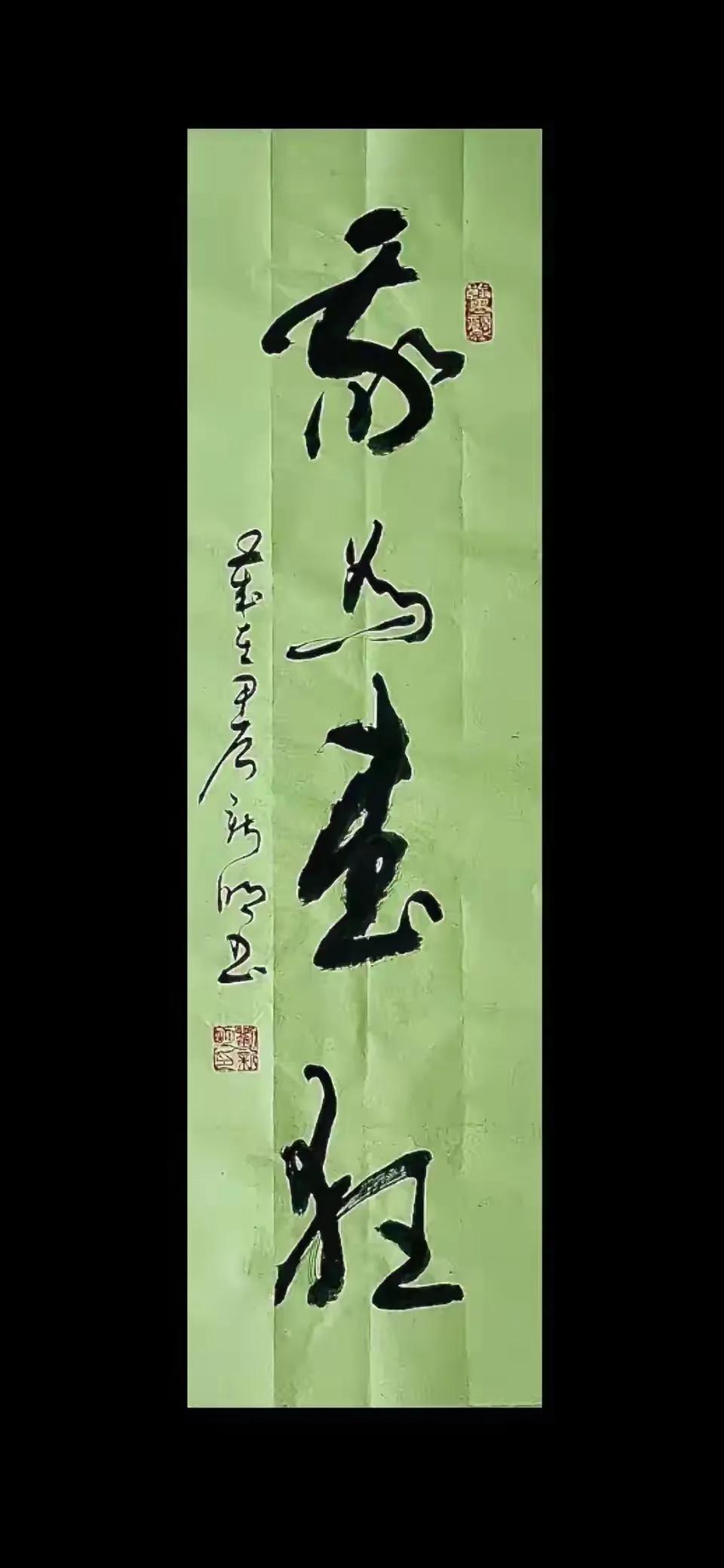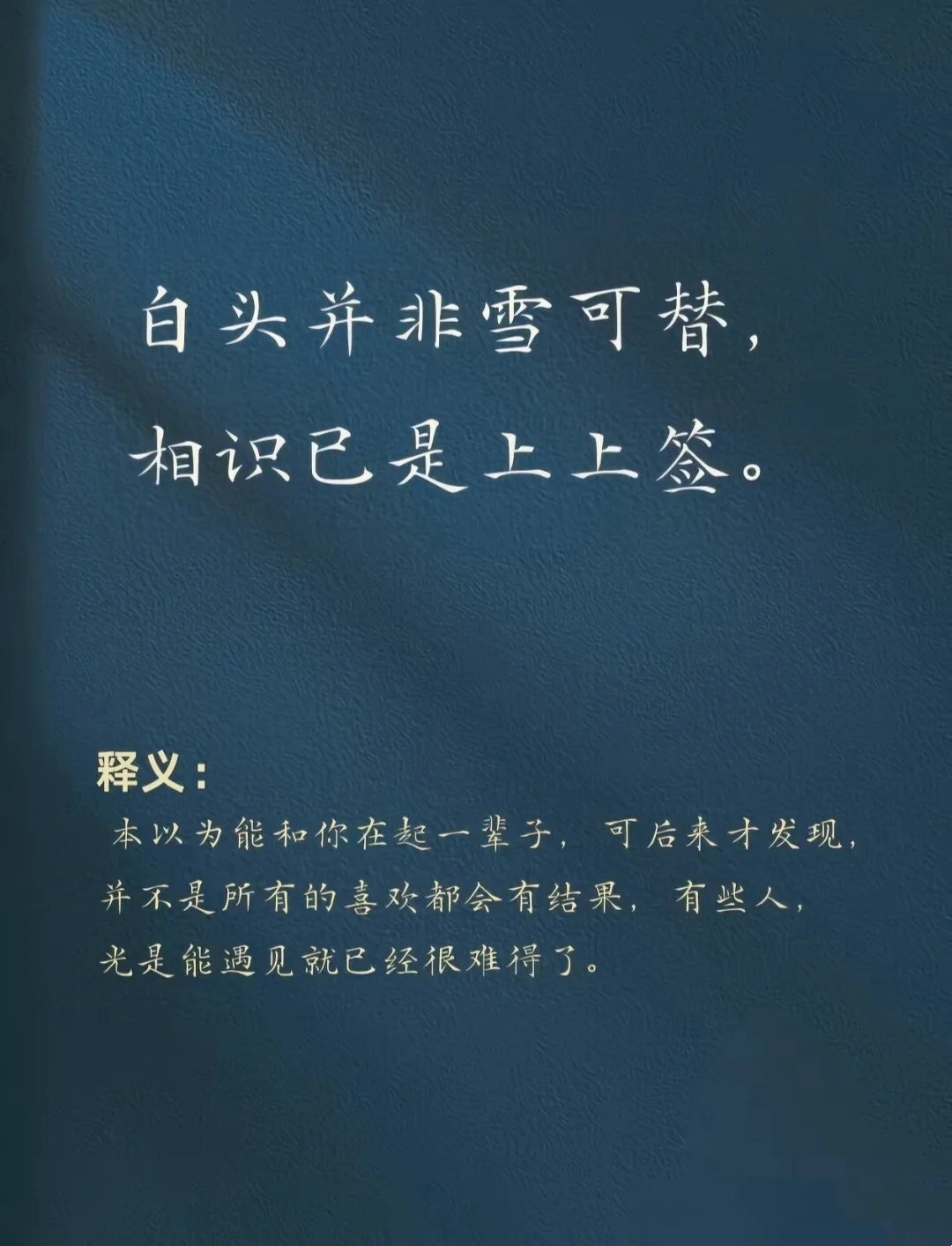文案: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建康城里的郎君如星,谢韶音便是众星所捧之月。
只是这轮月亮从未想过,身为陈郡谢氏之后、太傅之女,自己有朝一日竟会下嫁李勖这样的寒门武将。听闻此人能征善战,有万夫莫敌之勇,腰间一柄环首刀杀人如麻。
新婚之夜,看着那高大威重的男子一步步踏进洞房,韶音攥着帕子的手出了一层潮汗,话却说得掷地有声:
“我已向阿父禀明,效法古人之礼,与足下试婚三月。若是三月之后,你我二人不能情谐,当一拍两散,离绝各过!”
李勖长眉微挑,“怎么试?”
帝晚年时,曾与太子戏语,“美人计真乃天下第一阳谋。’
太子思想起从前偷看过的那些信件,忍不住腹诽:那不还是因为你乐意!
良夜中宵,皇后仪态万方而来,眼角眉梢犹是当年月色。
李勖看着她,仿佛又回到了几十年前。早在乌衣巷口绮霞漫天的那个傍晚,她移开遮面的纨扇,向他投来宿命般的一瞥,这一生一世便已注定。

片段:李勖行至萧墙,迎面便见一团轻盈的云霞朝着自己飞奔而来,那挺翘的鼻尖几乎贴到他胸膛方才堪堪止住步子,一抬头便用一双眼睛亮晶晶地看着自己,喜孜孜道:“你回来啦!”
一脸的眉飞色舞,像是做了什么天大的好事,迫不及待等着他夸奖一般。
李勖平静地看着她,“你跟我进屋,我有事问你。”
他今日因赵勇和刁扬到访检阅换上了一身戎装,归来前卸去了外面一层甲衣,内里仍是一身玄色绑腿劲装,头上顶着一只漆纱笼冠,足蹬一双赤色马皮战靴,腰间紧紧束着条虎头革带,其上铁碌寒光闪闪,上别着一把乌沉沉的环首长刀。
本就生得雄武,这副打扮又在雄武之外添了几分腾腾杀气,再加上说话时面无表情,整个人看起来便是十分地气势迫人。
韶音上翘的嘴角缓缓落了下去,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与他拉开了一个比较安全的距离。
这个男子前几天刚信誓旦旦地说过,无论她做了什么,他都永远不会伤害她韶音瞄着他宽阔的肩背和两条壮硕笔直的长腿,只希望这人说话算话。
二人一前一后走入内庭,谢候和四娘早就躲进了厢房,双双躲在屋里扒着门缝往外偷看。李勖进屋先是屏退了阿筠阿雀和一干侍女,随后卸下佩刀挂在墙上,继而一抖衣袍、脱鞋上榻,身姿挺拔跪坐其上,眸光肃然凝视着韶音,一副“你过来,咱们好好谈谈”的模样。
这副样子不由令韶音想起了谢太傅。
她十二岁那年,先帝曾亲临谢府为谢太傅贺寿。好巧不巧,韶音前些日子进了一趟宫,在姨母王皇后也就是如今的王太后处听了一耳朵先帝宠幸郗美人冷落姨母的二三事,出于义愤,便偷偷在寿宴所用的酒水里掺了些三十九郎的童子尿,继而乖巧地走上堂,跪地为姨父陛下献酒。
宁康帝当时的表情十分精彩,韶音现在想起来还忍不住想乐。事后谢太傅大发雷霆,关起门来审问她时就是李勖此刻这副表情。
韶音想到这里不自觉地撅起了嘴巴,磨蹭了一会儿,还是坐到了李勖的对面,“你生气啦?
李勖那张面无表情的面孔蓦地发出一声哼笑,好像是在嘲讽她,原来你也知道我生气了!
“说说吧,怎么回事?”你不都知道了么,就那么回事呗。
韶音说到这儿又想起了赵化吉屁股上的字,一个憋不住噗嗤乐出声儿来,“我早就跟你说过,那厮是个好色之徒,看我的眼神一直不怀好意,就该狠狠打他五十军棍!你偏说不能因为一个眼神定人家的罪,这回好了,人证物证俱在,一齐送到你面前,还给你省了事呢!”
若不是谢候将赵化吉缺勤之事讲给她听,她还想不出这么妙的主意,那田舍猥人命中注定遭此一劫,要怪只能怪他自己不检点,调戏民女在先,肖想阿嫂在后,五十军棍都便宜了他!
韶音咬着唇忍笑,李勖依旧眉目凝肃,沉声道:“他为何会将巨光剑盗来还你?
“那自然是因为我神机妙算!此僚既胆小怕事又极为好色,我看透了他的德性,自然有办法教他乖乖听我的话。”
韶音得意地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讲了个七七八八,待说到刁云和赵洪凯那两个军候差点还手的时候,这才发现李勖的脸
色已经沉得极为难看了。
....我不是得理不饶人,实在是他
们有错在先,你想想,若非我及时制止,那女侍会有何等遭遇还未可知,我不过是抽了他们一下而已,这也不算过分吧?”
她被他这眼神看得有些心虚,说到此处又急急道:“你可是还欠我一个条件呢,李将军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想必绝不会食言!我要你不许因为此事与我生气,也不许责怪于我!对了,你看——”
韶音说着举起自己的左腕,露出一圈醒目的乌紫,委屈巴巴道:“我都负伤了,赵化吉那厮力气好大,若不是蒙汗药的效及时发作,只怕我的骨头都折了,现在还痛得不行,你就别再怪我了。
话落便将胳膊肘撂在案上,双手托腮,耷拉着眉眼,无辜地看着李勖。这是她对付谢太傅的杀手锏,谢太傅就是再生气,一见到爱女如此乖巧又委屈的模样,那一腔怒火也只能哑火,末了化成一声无奈的叹息,“唉!你如今也越发大了,不再是小孩子了,往后可莫要再如此顽劣,得时刻记着你是陈郡谢氏的女郎,记住了么?”
“呜呜鸣,记住了,阿父真好,韶音知错了,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
这般对话自谢夫人过世就反复在父女间上演,韶音知错就改、下次还犯,年年如此,直到出嫁。如今,这对话换汤不换药,不过是对象从谢太傅换成了李勖。
不过,李勖的反应与谢太傅不尽相同。他并未叹口气,再语重心长地说一番大道理,而是沉着脸——一把捉住了她的腕子。
说是捉,是因为他动作突然,令韶音意想不到,直到纤细的腕子已被他的大手握住,她方后知后觉地红了脸。
“你干什么呀?”韶音往回抽手。
“别动!”李勖的语气忽然加重,吓得她真的不敢再动了。
李勖一手把着她的手腕,另一只手握住她的手掌,上下轻轻晃动,“疼么?”不疼。”
韶音有点发呆。李勖又握着她的手左右摇了摇,“现在呢?”
“有一点。”
他那两道浓郁的剑眉微皱,抬眸看她,“可有冷热交替敷过?”“回来就敷了,先是阿筠用帕子包着冰块敷了一阵,后来阿雀又用草药包炙了一阵,已经没什么事了。”
许是离得太近的缘故,韶音被他身上的气息灼得脸颊发烫,声音不由自主地低了,亦问亦答,倒真像是个做错事的小孩子了。
“晚上睡前再敷一阵,明日我请温嫂过来给你瞧瞧,这几日一定好生注意着,切莫再练习舞剑了。
李勖的口气不算温和,也谈不上严厉,有点像是命令,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意思。
还是头一次有人用这般口吻对韶音说话,不是谢太傅那般哄着,也不是王九郎那般戏谑着,更不是一众建康郎君那般讨好地捧着……这令她觉得有点新鲜,有点不好意思,还有点不服气:他凭什么这么说话?
李勖瞧她楞椤地看着自己,以为她是在担心自己的伤,遂缓和了语气道:“应该没有伤到骨头,不会耽误你日后跳舞抚琴。温嫂的医术很好,军中伤兵断骨中箭都是她治好的,教她过来看看,你放心。”
“那.….你不生气了?”
李勖的眉目在她的注视中缓缓舒展开来,“不是生气,是担心,你懂么?京口民风悍勇,不比建康百姓知文懂礼。尤其是底层百姓和兵卒,正因不知轻重因此便无所畏惧,管你是不是谢氏女郎,真犯起浑来,一时不知轻重伤了你,就算事后惩罚也于事无补,岂不悔之晚矣?
受你鞭打的二人,其中一个叫刁云,乃是刁氏旁支。刁氏与赵氏都是本地豪族,素来与你们王谢几家士族不睦,他既已下跪磕头,却又遭你鞭打颜面,岂有不怒之理?幸好刁云也是一曲军侯,还算知晓些分寸,赵化吉又及时阻拦,你方才躲过一难。你自己说,换你是我,能不担心么?”
他说的这些,韶音从未想过。士庶之别,实自天隔。韶音出身谢氏,母亲又是王氏女,这样的出身,即便是司马氏的公主也要稍逊一筹,遑论庶民?从小到大,韶音实是不懂“畏惧”二字的含义,也不懂得什么叫收敛和分寸。
可李勖却说,越是低到尘埃里的这些田舍之人,越是无知者无畏,他们本已活得艰难,那些兵痞也是靠着卖命才能养活一家老小,对这样的人而言,万事莫大于一死,身份的差异并不足以令他们任由呼喝,真要是惹急了,大不了与人拼命。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正是这个道理。
韶音其实已经被他说服了,可是心里还是觉得不舒服,因便嘟囔道:“我在建康和会稽时就自在得很,怎么到这里就不行了?他们不管我是不是谢氏女郎,也不管我是不是李勖之妻吗?”
说着便将自己的手抽了回来,鼓着脸生起了闷气。
李勖不由轻笑,温声道:“若非李某还有几分薄面,你以为自己还能全身而退?”韶音哼地瞪了他一眼,嘴巴撅得更高了。
李勖摇摇头,起身进了内室,待出来时,手中已多了一只颜色泛白的旧布袋子。撂在案上,打开来看,却是满满一袋子钱。
“你这是....
韶音惊讶地看着他,便见他探手入怀,从中取出几样熟悉之物递了过来。欸?这不是我的么?”那金雀钗、金丝臂钏和一对翡翠耳环
正是她和四娘上街那日当出去的,此刻已完好无损、一样不缺地躺在了李勖手掌之中。韶音有些惊喜地看向李勖。
他已不复方才的沉稳严肃模样,面上竟是现出了一丝局促,微微侧过脸去,道:“我这些年的积蓄都在此处了,虽是不多,养家糊口还算够用。你往后若需用钱,直接取用便是,莫要再抵自己的首饰了。”
韶音嘴角忍不住向上弯起,从他掌心里一一拾起那几只失而复得之物,再看那只旧旧的钱袋子,心里便是一暖,嘴上却道:“原不过是些小玩意罢了,我多得很,没放在心上的。”
李勖点点头,重新坐回了她的对面,忽然又伸手过来,轻轻握住了她的小手。
韶音浑身一颤,只见他神色郑重地看着自己的眼睛,缓缓道:“我知道,这些于你而言都算不了什么。你下嫁于我本已委屈,我便不能教你再受委屈。方才说的那番话,也是将道理讲与你听,并不是教你处处忍气吞声。李勖之妻,或许在富贵上比不得世家宗妇,可内外行走、说话行事,自可随心而为,不必看任何人的脸色。我已拨了几个护卫给你,往后出去带上他们,也好教我放心。”
这夜的韶音出奇地安静。隔着一扇薄薄的屏风,李勖能听到她浅浅的呼吸声和翻身时的窸窣声,显然,她还没睡着,只是反常地沉默着,不知在想些什么。
韶音的确在想着心事,她在琢磨李勖那两次握手。第一次握着她的手,应该是出于关心,想看看她腕上的伤势如何;第二次么便与第一次有那么一点不一样。
他说话便说话,干嘛要握着她的手说呢?她当时被他握得身子一颤,好像是有什么东西自指尖麻酥酥地流淌过来,直流到她的心尖上,那感觉既新奇又令人害怕,好像是就要失去了控制一般。王九郎也握过她的手。
她从小就喜欢粘着他,他总是烦得要命,又怕舅父和舅母责骂,就只能不情不愿地牵起她的小手,带着她去秦淮河上的画舫里听小曲吃菱角糕,或是去燕子矶西边的澄园里折梅花。
长大以后,他们两个一见面就吵架,已成了斗鸡对鹌鹑,再也没有了幼时那般的牵手。只有打闹急了忍不住互相动手时,他才会用力捉住她的腕子,紧紧地攥着,令她无法抽出手去掐他、拧他,只能愤怒地往他脸上吐口水。
九郎那双手是书画双绝、琴笛俱精的手,生得修长而白晳,无一处瑕疵,胜过这世上最好的羊脂美玉。韶音因为天长日久地习舞剑,指根和指腹已磨出了一层薄薄的茧子,看起来柔软,摸上去其实很有筋骨。
他便因此而嘲笑她,“阿纨这双手比男人的还粗糙,哪个好郎君见了还肯要你?若是将来嫁不出去,不如收拾收拾包裹,直接搬到我家来给我做糟糠好了。”
韶音当时气得要命,“你想得美,想娶我的人从乌衣巷排到了建康宫,我就算嫁司马德明也不嫁你!
王微之听后大笑,捏着她的脸蛋道:“还当真了,你想嫁我还不想娶呢!”
回忆里王微之的手细腻温润,熟悉得便如韶音自己的手一般,与那双手相握,并没有今天这样的奇异感觉。
韶音忍不住用自己的右手握住了左手,摩挲了一会儿,依旧没有那股一瞬间麻酥酥的感觉。
“李勖。”
“睡不着么?”
屏风那边的男子几乎与她同时出声。听她唤他,他很快又道:“嗯,怎么了?”
韶音在半空里捏了一个兰花手型,借着一点微弱的月光端详着,“傍晚那会儿,你为何要握我的手呀?”
那头的男子默了一瞬,过了一会儿才回答道:“你是我妻,我握你的手是天经地义之事。”
他的声音很平淡,听不出什么情绪。韶音被他这个回答弄得有些兴味索然,莫名地不太高兴。想想又道:“假如我当时没有说要用了那个条件,你也不会对我发火的,对么?”
“嗯,不会。”
“那……我想收回那句话,不想用那个条件了,你继续欠着我,行么?”
“行”韶音这回觉得好受多了,调整了一个舒服的姿势准备睡下。
却听李勖忽然问道:“赵化吉身上的字是你刺的么?”
韶音阖上的眼复又睁开,嗤了一声道:“他的脸我都不想碰,更何况是屁股?那是冬郎刺的,回来之后用皂角洗了好几次手呢!你好端端的为何想起问这个?”
“没什么,只是随便问问”,李勖轻声道,“往后再遇上这种事要与我说,不可再像今日这般鲁莽了。”
第二日上午,李勖刚出门不久,便有一辆小驴车吱悠悠地停在了李府门口,从中下来一位方圆脸的中年妇人,头上包着方蓝地白花的细葛帕子,身上斜挎着个竹编的药箱,观之神情爽朗,眉眼之间颇有几分英气,正是温衡之妻孟氏,因随军为医,大家都亲切地唤她一声温嫂。韶音得了门房通传,赶紧领着阿筠阿雀两个到门口迎人。
温嫂揖礼后细细打量韶音,笑道:“又见夫人了,不知这些日子夫人在京口可还住得习惯?”
韶音方才便觉得这笑容可亲的妇人似是在哪里见过,听她这么一说顿时想起来了,这不就是迎亲那日指挥李府马车前来接人的妇人么?
那日她心中凄凉,萦绕着满腔的离愁忧惧,并没有多少心思留意那些迎亲之人。温嫂走在最前,看样子似乎与李勖颇为熟稔,言谈举止亦没有寻常村妇的扭捏,反倒是十分爽快利落,因就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韶音原先还以为她是李家哪房的姻亲,这会儿才知道此人竟是个医女,并非寻常的后宅妇人。
她素来钦佩有本事的人,尤其是像她师父那样有本事的妇人,因就对这位温嫂也高看了三分,当即便笑呵呵道:“劳温嫂记挂,已经习惯许多了。我这腕子不过是一点小伤,这么一早惊动你跑一趟,真是过意不去。”
温嫂顿时笑道:“李将军之命哪敢不从?只怕是夫人少了一根发丝,将军也心疼得不行呢!
韶音被她这句话打趣得有些害臊,从脖子到耳尖都蒙上了一层虾粉色。温嫂看她这副模样,忍着笑没有再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