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郁在《解密》拍摄现场的调光台和监视器前(受访者提供/图)
采访前,曹郁的助理特意发来一则提醒:“曹老师的职位是电影摄影指导、摄影师,不是摄像师哈,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称谓”对曹郁非常重要,他对此的介意有时会显得苛刻。“摄影指导这样的名字,是全世界电影摄影师工作了数十年,经过新浪潮运动和新好莱坞的推动,在上世纪70年代才真正确立的角色,非常不易。”
摄影指导是Director of Photography(DP)的中译名,亦可作摄影导演,是导演的联合创作者,是将影片呈现出来的关键角色:将文本变成视觉景观。DP需要兼具技术能力和艺术感觉,他们创造了每个影片独特的气质。

《可可西里》(2004)
曹郁的电影生涯始于2002年孟京辉的《像鸡毛一样飞》,两年后他就凭借陆川导演的《可可西里》获得了金马奖最佳摄影,至今仍是金马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摄影师——那年他30岁,感觉自己开始走入正轨了,有点明白电影摄影是怎么回事了。2009年,曹郁再次与陆川合作,凭借庄重又灵动、肃杀又诗意的影像风格,战争题材影片《南京!南京!》在国内外电影节展中收获了数个摄影奖项。
但此后,曹郁一度陷入低谷,连拍四部都不满意,拍不出自己独特的东西。那时候他才知道,原来不是每一部电影都能让摄影师找到感觉,他得珍惜那些“有感觉”的电影。
2015年,曹郁接到王家卫监制的电影《摆渡人》的邀约。那是一段艰难的工作时光,但他从王家卫那里受益颇多,突破瓶颈,逐渐蜕变成一个更职业、掌握了更多技术和更多解决方法、能与不同导演合作的摄影指导。

《摆渡人》(2016)
次年,陈凯歌邀请曹郁加盟《妖猫传》。曹郁在其中实践了更丰富的摄影、布光方式,并对中式影像美学做出了新的探索:瑰丽奇诡的盛唐想象和青绿山水的色彩质感,呈现在柔和还带着些透明感的画面中。这部作品为他赢得了金鸡奖最佳摄影。
近年来,曹郁先后担任了《无问西东》《八佰》《1921》和《解密》的摄影师,他还是高口碑文艺片《脐带》的监制和摄影指导。其中《八佰》是亚洲首部全片使用IMAX摄影机拍摄的影片,《解密》亦是全片IMAX摄制,但《脐带》是小成本制作,曹郁很久没拍过这么穷的戏:《八佰》一场戏能用2000台灯,《脐带》一共只有12个灯。
2024年8月,陈思诚导演的《解密》上映,有褒有贬,也有共识:摄影及视效的水准一流,曹郁也自信这是《八佰》之后,中国电影工业质量最高的作品。“顶级大片是说工业化程度很高,而不是说挣钱最多。顶级大片意味着所有主创都得在一个水平线上,画面的质量是由摄影、美术、CG和剪辑共同决定的,哪块差了都会影响观感。”
而小成本影片《脐带》也表达了曹郁对电影工业化的态度。故事不复杂,讲的是小儿子带着患有阿兹海默症的母亲重返草原,寻找记忆中的家。由于每个环节都由专业人士协助作者表达,影片的镜头语言准确,画面兼具情感与美感,蒙古草原不是明信片式的蓝天白云,而有了一种飘忽不定的诗意。
曹郁总在强调影片是团队的成果。无论是创作分享课,还是朋友圈的转发,他或是要求在结尾展示全部幕后工作者的名单,或是点名感谢灯光、工程、DIT(数字成像)等等环节的伙伴。
电影自诞生来,就是一门以技术为支撑的艺术,是团队创作。所谓“电影工业美学”,其核心要义是电影技术美学,即美学通过电影技术来实现,电影技术服务于电影美学。而工业化的核心是分工化、专业化、流程化、标准化和规模化,水准差距往往不取决于硬件设备,更重要的掣肘因素是观念的滞后和技术思路的狭窄。《流浪地球》的导演郭帆曾多次提到,由于没有工业化基础支撑,国内的创作者只能单打独斗地摸着石头过河。而好莱坞许多中小成本电影,却能依靠美国甚至全球分工成熟的电影工业体系,提高各环节的专业水准。

《南京!南京!》(2009)
曹郁第一次触摸工业化是拍摄《南京!南京!》时,其中战争场面的呈现非常复杂,需要多个环节协作完成,也需要电影工业化的知识。此后,他深度参与、见证了中国电影的工业化进程,感受到技术给创作者以自由,也不由得感慨这个进程还是太慢:“我们现在用的摄影机和灯光,跟国外的没有太大的差别,但通过同一个机器拍下来,仍然有很多画面质感那么的差。这其实是使用工业产品的鉴赏能力和创造能力跟不上设备的迭代。”
采访伊始,曹郁从衣服兜、书包前口袋、后口袋掏出三种烟。他说这是为采访准备的,保证自己能在接下来三小时的交谈中保持高度专注。这三种烟的口味不同,他最爱“南京”,但抽多了嗓子疼,就得换味道淡些的烤烟或是凉烟,用来麻痹喉咙。
片场不能抽烟,曹郁每次都要大费周章找个能抽烟的区域,比如在看监视器的帐篷里。在他的描述中,摄影指导确实是一项需要大脑高速运转、在规定的时间和空间中给出各种解法的工作。他们承担着事关成败的压力,一刻不得松懈或走神,宛如带队打仗,指挥失误就可能失去威信。

《无人驾驶》(2010)
在我们的采访中,曹郁也保持了高度专注。他不惮于谈论曾经的失败,坦率又富有感情地讲述了自己的职业经历和对摄影技术、电影工业化的理解,流露出他对电影的热爱。以下是他的讲述:
就算拍不出我的样子,我也能完成影片需要的样子我第一次受到挺大打击就是拍张杨导演的《无人驾驶》(2010),找不到感觉。以至于我现在看到张杨都挺不好意思的,觉得人挺信任我,但我没给他拍好。
张杨找我的时候,我刚跟陆川凭《南京!南京!》得了一堆奖,信心特别足,没想到瓶颈期来得这么快,怎么就不行了呢?一方面是我当时技术不够好,有想法也不一定能达到;另一方面就是我不太能真正理解故事的情感,可能我想法都是错的。
我自小就生活很单纯,在大院里长大,父母都是搞文字工作的,妈妈是记者,爸爸是编剧。上的普通高中,然后考到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我在学校里绝对是好学生,班上第一名,北京市三好学生、优秀毕业生。
就我一直是平顺、单一的生活,对张杨剧本里那种复杂的男女关系,不仅是没有经历过,也没法想象,整个就卡住了。
我想了很多方法,技术上也特别严格地去处理,但出来结果就是不满意。我当时想对胶片做减冲,让画面反差更低,细节更多。从技术上看,我是成功的。但我后来觉得,《无人驾驶》根本不需要这个风格,它不需要那么柔和的画面,它需要的是一个概念、一个强烈的情绪才能把多线条的故事撞击在一起。技术上越减显(保持更多的细节和色彩),画面的情绪就越平淡。像我现在讲课老说摄影的形式感要和剧作完全吻合,我那时候就没做完全吻合,就是两张皮的感觉。

《妖猫传》(2017)
那几年我拍了四部戏都不太成功,很焦虑,也很害怕,害怕自己再也拍不好了。拍完《可可西里》,我希望自己未来拍摄的题材都能跟我的内心产生共鸣,我能创造出更有力的影像,到了拍《南京!南京!》时,我常感到自己有一种摄影师的本能,很多决定都是靠本能作出的选择。但之后我连着失去内心的感觉,就找不到方向了。
那段时间我也没什么活儿,或者说我也不想接什么活儿,没什么希望解决我的困境。2015年,我突然就接到《摆渡人》的邀约。这部电影争议很大,但我非常感激这个项目,对我极为重要。
王家卫是我见到的第一个电影大师,我特别特别喜欢他的《春光乍泄》《东邪西毒》和《花样年华》。我到现在最想拍的片子还是《春光乍泄》那样的,工业水准高,但又是非常好的艺术电影。
王家卫很敏锐,我刚进组拍了几天,他就说:“咱俩的拍摄方式不一样,你喜欢从宏观看问题,我喜欢从微观去观察,你总是有种渐离感。”后来赶上整个剧组停工改剧本,改了半个多月,王家卫就天天找我吃饭,把我给吓得啊。我当时也特别受挫,我特别喜欢王家卫,他的电影那么有情感,又那么诗意,但我觉得我可能永远都拍不了这么好。
王家卫问我为什么不能投入到这个戏里,我说我确实不能对这个剧本感同身受。他真的给了我很多很多的耐心,老说,你肯定是可以的,你到底卡在哪里了呢?我们一起来解决。他特别想了解我,跟我聊我的家人啊,聊音乐啊,聊我以前拍过的片子啊,试图让我们达到心灵上的共振。我到现在想起这些都觉得很温暖,很感动。
他教给了我一个真正的技术,就是怎么去拍演员的表演。王家卫其实特别古典主义,特别讲究戏剧化和很强的塑造感。以前我没有塑造演员的感觉,可能演员都是和我差不多年纪、差不多经历的人,或者像《可可西里》,演员都是普通人。我习惯先塑造场景,再看演员的效果是怎么样的。如果整体氛围是很棒的,我对演员的塑造就没有那么细致。但王家卫恰好相反,天天都要我拍演员的脸。这部戏跟我以往拍摄的题材不一样,不是盗猎或者打仗,是在很正常的生活中,要拍出人的故事和情感,就需要镜头有很强的戏剧感和塑造能力。
就那一回,我真正明白过来,电影最重要的是讲故事和塑造人,画面是为了情节和人。这说起来很简单,其实上学时候就学过,但真的之前没有体会到。直到《摆渡人》,才突然捅破了窗户纸,想明白了。
《摆渡人》是最不像我风格的电影,我变成了另外一个摄影师。我当时压力很大,经常洗完澡随便穿件衣服,站在浴室里一边抽烟一边听崔健,就想我怎么还能做自己呢?但拍完之后,我突然释然,我下一部片子可以不这么拍,我还是曹郁。
可我已经变成了一个更职业的摄影师,我做到了就算拍不出我的样子,我也能完成影片需要的样子。而我之前失败的四部戏,或许正因为换了我不擅长的风格、内容,我就不知道怎么去塑造画面了。说白了,还是技术上差点意思,我只能按照一个方式去拍才行,那就很有局限性。作为一个职业摄影师,我要能去学习爱上一个故事,爱上一些角色,要能读懂不同导演,并且用画面表达出来。
拍《摆渡人》的经历太重要了。摄影机的调度与戏剧性、剧本语言的配合,我在这部戏才被点明白。没有这部戏,也就拍不了后面所有的戏。

《八佰》(2020)
一旦想做些冒险,就要承担更多的风险《摆渡人》之后我就进组了《妖猫传》,那是我第一次用上调光台来打灯光。调光台在每个剧场都会有,有点像调音台,有好多推子,用推子控制光线变化。调光台给了我自由,再也不用命令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人去调光,都能自己直接控制。
哪怕我在片场已经工作了快二十年,命令很多人去干一件事我都会有一点心理压力。没有调光台的时候,将几十个灯调红一点或者蓝一点,就需要加色纸。色纸是很厚一叠,各种颜色分得很细,要是加错了,就得再加一遍。现场的工作人员要爬梯子去加色纸,人家加一次就要问一下行不行,如果我很犹豫,可能所有人都要盯着我。最可怕的是这色纸加都加了,我说“真不好意思,还是给摘了吧”,所有人又要爬梯子给摘了。
电影是工业生产,时间就是钱。我们在现场就是带队打仗,要是打错了,说不该打那个要打这个,所有人就要说“你这是什么啊”,就没威信了。摄影指导就是又要准,要很稳,又要奇,要出奇制胜,又要冒险又不能出错。像拍《八佰》八个月,摄影指导是任何一天,任何一个场景都不能出错,你想这多大压力啊。
我这种有些内耗的心理压力可能是早年在北影厂留下的。我毕业后分到北影厂做摄影师,现场负责管灯光的师傅叫“灯爷”,灯爷每天一开始就会问,灯是放这儿么?我说就放这儿。如果过会儿说,师傅您能再往前挪一米么?师傅就要带点语气地说,刚不是问你了么,怎么回事儿?
我们这些年轻摄影师真是被吓大的。所以看到电子调光台的一瞬间,我觉得太自由了,就像在搞一场巨大的舞台演出,能随心所欲控制光线,甚至做出即兴的光线,想象力得到了无限拓展。对调光台的使用延续到《八佰》《解密》,成为我的一个创作标签。
还有一个技术迭代也给了我自由,就是数字摄影。以前拍完《南京!南京!》,柯达公司让我去给他们做个数字摄影的广告,我还拒绝,说我们不妥协,我们就要用胶片拍,现在真是啪啪打脸,我现在都是数字拍摄。
我非常喜欢胶片,我到现在也觉得数字摄影机在中低亮度的厚度感不够,拍出来的人物很薄,没有胶片浑厚的质感。
但我不喜欢胶片冲印的过程,一方面是冲印效果我作为摄影师没法完全控制,要看师傅心情,另一方面是我觉得洗印厂对画面效果有很多主观的判断。
拍《可可西里》的时候,我们攒几天的胶片就派一个人背去西宁机场,飞回北京送到电影洗印厂。冲印后,我们会拿到一个像医院检查单的回执,写着曝光正常、胶片没有划伤等。但最可怕的是,洗印厂可能给一张单子说这个镜头曝光不足。我说我要艺术效果,他说不行,用机器看你这就是曝光不足。这是我最害怕的,因为洗印厂会在技术上告诉你要补拍,如果不补拍,就会直接在底片上打个孔。胶片曝光如果控制不好有可能拍成全白或者全黑,那就更可怕了,洗印厂会直接给你打电话,告诉你这里有张事故通知单。
1997年,我进北影厂时,进的是摄影车间。我们的头叫车间主任,那说白了我们就是车间工人。我们工作有严格标准,不能有误差,这种从苏联学来的管理方法当然也有合理性,但也给了人很大压力。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电影在第五代之前,多数看起来都很像,因为摄影师一旦想做些冒险,就要承担更多的风险。
我所学习的胶片摄影,学的就是如何使用测光表控制曝光。我又有好学生的习性,学得很认真。这样能把人训练成一个艺术工作者,但不可能把人培养成艺术家。我到现在都记得在洗印厂看冲出来的样片的紧张:胶片是没有声音的,现场只有放映机转动的哒哒声。前面坐了一排老师傅,都给年轻的张艺谋、年轻的陈凯歌冲过胶片。他们一边看一边说,“哎哟喂,就这曝光,还电影学院毕业的呢!”“哎呀,这个焦又虚了,没办法,年轻摄影师就是爱虚焦点。”我的天,我真的压力狂大,感觉浑身都在被戳。
我很快就意识到这很残酷。如果达不到这些规范、标准,就是不专业,但如果一直在这个规范里面做,就没生命力了,被箍死了。我太窒息了,非常想超越这些标准。拍《南京!南京!》的时候,我已经在试图超越那些属于胶片的规矩了,只是我水平还不够,不够高明地超越这些标准。
但没多久我用上了数字摄影机,终于不用再看冲印师傅的脸色了,我也不需要在胶片调光的过程中做出妥协了。别人喜欢不喜欢,我也不是很在意,我要这么拍就这么拍,我就能精准地拍成我想要的样子。我也自学了数字调光,能够自己控制色调了,要黄就黄,要红就红,拍不好我就认了,但我不会有遗憾了。

《脐带》(2022)
魔术师我所知道的最早在电影拍摄中使用调光台的是意大利摄影师维托里奥·斯托拉罗,《现代启示录》和《末代皇帝》的摄影师。
1989年,我读初二,看到了《末代皇帝》,我觉得天啊,太神奇了,那里面的故宫跟我看过的完全不一样。我买了好几次故宫的门票,去看电影里出现过的场景,比如太和殿。开场小皇帝被叫去宫里那场戏,那个光太神秘了,让人着迷,我不知道为什么太和殿变成了那样一种气氛。我意识到我眼睛看到的黑,没有电影里那么黑,我看到的黄昏,也没有电影里那么暖。
我爸给我弄来一个纪录片带子,讲的是《末代皇帝》的拍摄。我爸跟我讲,电影摄影师能创造气氛,能改变色彩改变光,让你熟悉的东西变得很陌生,变得更美,我就觉得电影摄影师太了不起了,这是魔术师。我说我也想当电影摄影师,我家就给我借了一个松下的摄像机,用的是“大1/2”录像带,总共只能拍十分钟,因为电池已经老化了。
我现在回看那些带子,那些飘动的云朵和落日,还有剪影,和我现在的风格已经有点像。
二十岁那几年,没什么事,就天天在家看片,买了一堆盗版碟。盗版碟给我造成了好多错误观念啊!最大的误导是盗版碟压缩视频信号后,我不能正确判断怎么控制亮部,最亮和最黑部分的细节,我看不到。有段时间,我一直以为艺术电影就要拍得特别黑,比如我看《风吹麦浪》,那都黑成鬼了。我觉得,就得这么干!结果那段时间,我老听到别人跟我说,曹郁你能拍亮一点吗?
等我能看到正版时,我才知道那些暗部是有层次的。这干扰我挺长时间的。当然这也不能都怪碟,也是自己能力不够,就算知道要拍得亮一点,也控制不了。
我到大学时再看《末代皇帝》,还是有不少镜头没法理解,琢磨了好多年。比如婉容和川岛芳子在屋内说话那场戏,那个光特别美,特别有质感,婉容和光浑然一体。我完全知道这是打出来的光,但又没有打光的感觉,不像很多电影,光直接拽在脸上了。特别朴素但又很有细节的光,就是我在《解密》中追求的效果。
我直到这几年才真正解决打光的疑问,这其实就是个技术分寸的问题,比如灯的距离、角度、透过的介质、通过什么区域渐变等等,这是一环扣一环的,哪个环节错了都打不出这个效果。
其实大家用的摄影器材差不多,甚至80年代全世界的胶片也就五六种,《末代皇帝》的胶片也不比别的电影更高明。所以说到底,还是美学的差异,再玄一点,这是哲学问题,什么是虚假?什么是真实?什么是真实的光感?我不要真实得平淡,怎么才能在真实和戏剧性之间取得平衡?
像罗杰·狄金斯(《肖申克的救赎》《银翼杀手2049》《冰血暴》《朗读者》等片的摄影指导)前两年拍的《光影帝国》,假装很写实,很准确,但却很诗意,他那个劲儿使得就跟打太极似的。有个镜头,约会失败的女孩一个人在屋子里,那个画面真是无声胜有声,又有情感储备,又有技术,又有哲学感。拍出这样的画面,真的不是技术问题。任何摄影师,你让他重复一次,绝对都能拍出来,但问题是他知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要拍成这样。作为一个同行,看到这样的画面真是又嫉妒又享受啊,就觉得哎呀要是更多人能看懂这种美就好了。也会觉得罗杰·狄金斯就是明灯啊,他七十多岁了还这么富有创造力,让我也觉得电影摄影能干一辈子。

《解密》(2024)
用到今天为止所有的经历来拍现在这部电影我现在的拍摄基本都是在做减法:当我对技术能运用自如,就会逐渐让拍摄变得更简单,只要合适就行。
《八佰》和《解密》都是用IMAX数字摄影机拍的。这机器到现在,全球也只有六十多台左右,只能租。我第一次拿到这个机器时特别惊讶,简单地说,用IMAX拍广角不会变形,它的空间感和眼睛看到的是一样的。一般情况,我们在照相机或者手机里看到的图像,都比眼睛实际看到的立体感短一些,薄一些,更容易变形。《八佰》是史诗风格,特别需要广角镜头把所有人和景都拍进去,但我现在又特别喜欢怼着人脸拍,要塑造人脸,那能够不变形,空间感又很浑厚,只有IMAX摄影机做得最好。其实《八佰》是把《南京!南京!》里的靠近感,把《可可西里》里的广阔背景,以及《妖猫传》里对于人物的肖像式塑造,三合一了。
《八佰》是真实事件,但我要当作史诗来拍,诗意地写实。《解密》则不一样,其中有很多梦境,影片要在梦境和现实之间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因此我决定从一开始就要在真实的基础上渗透出梦的异样感,把现实部分带有梦境感地去拍,然后把梦境按现实去拍,使整部电影都犹如一个完整又真实的梦。
“真实”或者说写实这件事对我来说特别重要。我想要让观众相信眼前看到的这个银幕世界是自然存在的,即使这个世界极不正常。我希望观众能在两三个小时里,始终沉浸在这个假定的电影世界里。
我最喜欢的一部作品是《脐带》,那是我在《可可西里》之后,第二次真正全部在大自然里拍电影,再次感觉到上天的恩赐:上天给你什么,你才能拍到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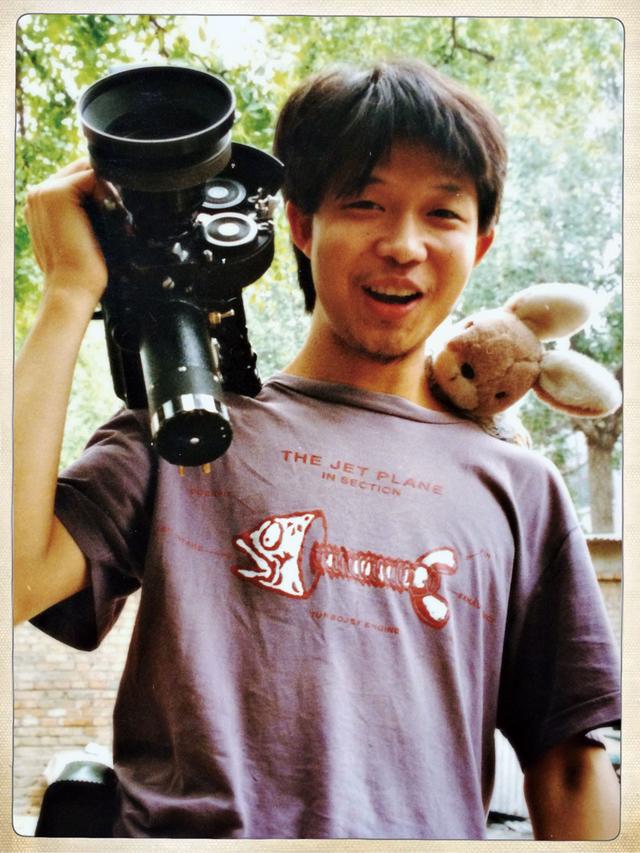
大学时期的曹郁(受访者提供/图)
正因如此,虽然我们提前想了很多框架性结构,但真的到了那一瞬间,机器怎么移动,光亮一点还是暗一点,都是凭着内心本能作出的选择,不是经过计算产生的。同时有很多机遇是大自然给予的,该怎么抓住机遇,是感性决定的。
我1974年生的,今年50岁了。可以说我现在拍的电影是我50年人生积累的展现,是人生的积累帮助我在拍摄的瞬间作出决定,其中包含了我对剧本的判断、对人的情感的判断、对生活的理解以及技术手段的运用,最重要的是对现场本能的感觉,所以可以说我是用一辈子到今天为止所有的经历来拍现在这部电影,也可以说我现在拍的电影就是我过去所有手段的集合。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杨楠
责编 杨静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