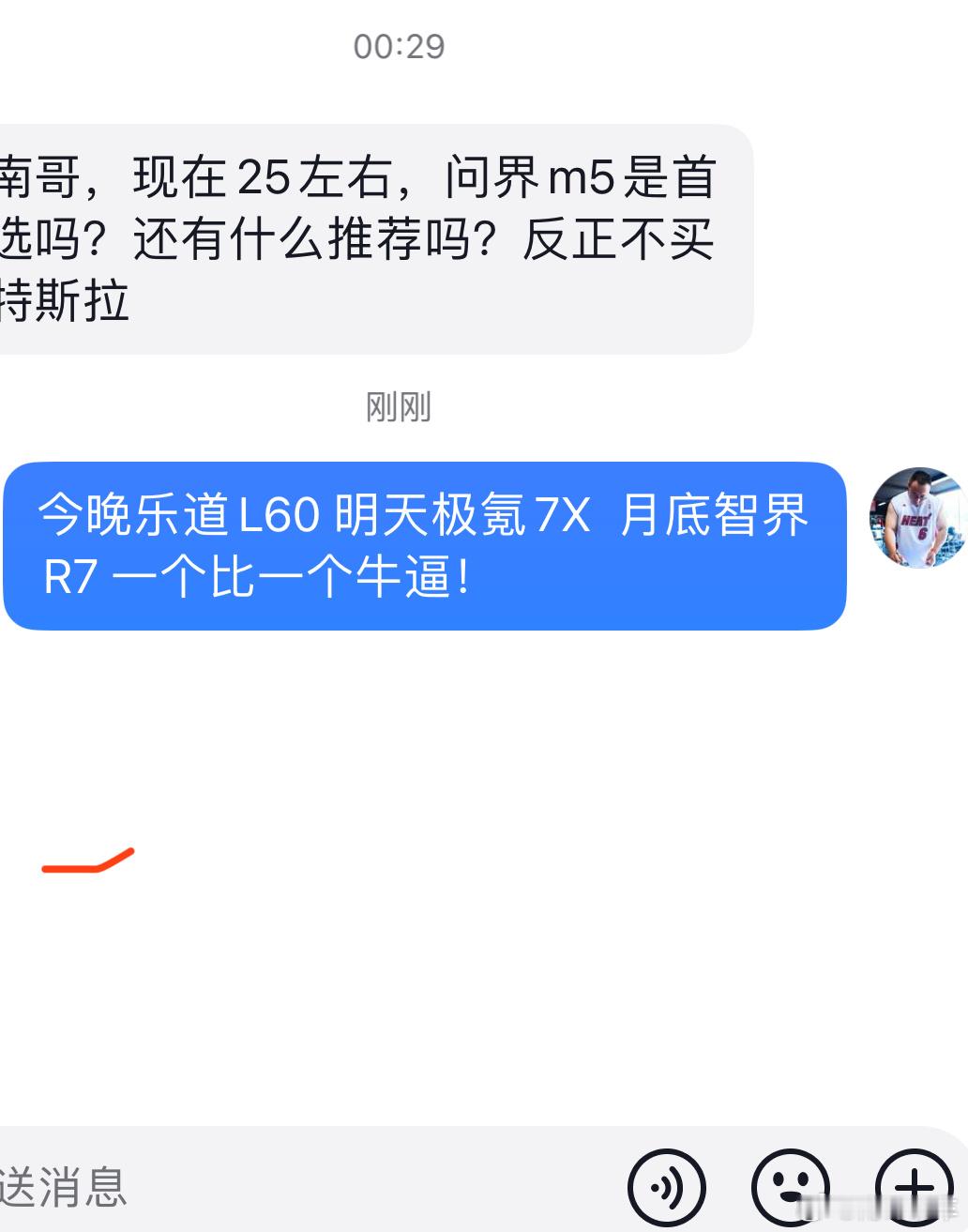怎么样让周边的好人多一些?郭德纲在相声段子中,曾说过一句话:你成功了,周围就全是好人了。这话乍听感觉很庸俗,但仔细品味,发现又很符合现实。
1975年,在极度苦难的时候,我去向家中富裕的三叔家借粮,却被堵在门外,连屋都没能进去,还备受嘲讽。可当我后来提干回家探亲时,他却笑盈盈提着礼物上门。让人不禁感叹,人心的善变与复杂。

我叫徐平,1959年出生在陕南的一个农村。村外一条文川河流过,河的两岸就是大片的耕地。
我的父亲这一辈共有三个兄弟,父亲居中排行二。
小时候,我很纳闷,为啥堂哥堂弟,都能到爷爷奶奶那边去吃饭,而父母却从不允许我们兄弟过去。
后来我渐渐长大,才得知,父亲并不受爷爷奶奶待见。即使我们兄弟上门去吃,大概率也是一口都要不到。
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父亲有些口吃,一紧张说话就会结巴。
村里人都叫他“徐结巴”,久而久之,竟然没人再叫他的本名了。
就连生产队干部,通知开会时,都直呼他为“徐结巴”,仿佛结巴一词,成了他的代名词。
我说话比较迟,别人两岁就能说出完整句子了。而我到了三岁,都还只会一个词、一个词往外蹦。
一直到我上小学前,我都被村里小孩叫“小结巴”。
直到我上学后,说话也流畅了起来。加上老师严禁同学之间互相起外号,我的这个“小结巴”之名才慢慢消散而去。
父亲因为这个毛病,从小就不受爷爷奶奶待见,结婚后就分了家。
连我们家住的泥草房,都是父母后来亲自动手修建的。
因为爷奶嫌弃,村里人讥笑,我们家和别家来往也不多。
遇到欺负和不公平的事,也没人帮忙说话,成了村里的边缘户。
父亲心里也不服气,只能将希望寄托在我们这一代身上。
我是家里学历最高的,上完了高中。原本以为凭借高中学历,能回队里干个记分员、会计或者学校老师的活计,但这些抢手岗位,根本轮不到我们这种人家。
每当我在生产队挥汗如雨,干着农活时,周围就传来了阵阵奚落声。
“徐结巴真的是有毛病!砸锅卖铁供儿子上高中,有啥用?还不是下地干活!”
“是啊,没想到那人不但嘴笨,脑壳也不好用。家里穷得叮当响,有那功夫还不如把房子收拾下。”
我在一旁听到这些话,不禁握起了拳头。

1975年冬天,母亲生了一场大病,身体十分虚弱。
医生说要补充营养,吃点好的,可家里连点细粮都没有,更何谈其他好的了。
我无奈之下,只能去比较富裕家的三叔借点细粮,拿回来给母亲改善伙食。
三叔和爷爷奶奶住一起,他从小就很受宠,爷爷奶奶偏心他,为此大伯家和他家关系也很一般。
三妈娘家那边条件不错,还给了三叔一辆二手自行车。三叔很是得意,经常骑着自行车招摇过市。
当我敲开门后,三叔看到是我,脸色便沉了下来。
站门外,我难以启齿地说了母亲生病,想要借点白面的事。
三叔还未说话,三妈的咆哮声就从屋里传了出来。“徐建明,你死哪去了?家里都穷得要饭吃了,你有那个本事帮别人吗?”
“别人都有钱供娃读书,你就别操那份闲心了。”
这番话深深刺痛了我的心,我红着眼眶看着三叔,想听听他怎么说。
三叔面不改色,打着官腔道:“平娃,你三妈话说得不好听,但道理是没错的。当时我就劝你爸,供你们读啥书啊?出来还不是一样出大力!可他那人就是犟……”
我没有等他说完,快步离开了小院。
可没有白面,母亲的身体咋办?我走了十里路,两个多小时到了外婆家。
最后我从外公外婆那边借了2斤白面,2斤大米,5斤苞谷面。
更让我感动的是,怀孕的小舅妈还给了我五个鸡蛋。
我流着眼泪,背着粮食走回了家。
这一幕,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当中,哪怕后来被人环绕的时候,我也能冷静那些人趋炎附势的,那些是真心为你好的。
这种日子过了两年,1976年冬天,命运的转机来了。
得知征兵消息到了公社后,我第一时间跑到大队的民兵连长那边去报名。
结果他虽然写了我的名字,但压根就没往上报。
等我看到村里同龄人去体检了,却没有通知我,我才得知被耍了。
我跑到民兵连长那去闹,他却信誓旦旦地说:“你不满18岁,有啥资格去当兵啊!”
我不忿,这理由根本就说服不了人。我怼了他一句,“你家余杰前年去当兵,有17岁吗?”
说完我拔腿就跑,剩下民兵连长在那里跳脚大骂。

我一气跑到了公社,找到了武装部王干事。
他往年来我们生产队搞过征兵宣传,我帮他写过标语,算是有点香火情。
王干事很同情我的遭遇,带我去见了武装部长,在那里我遇到了接兵的李炳林副连长。
李炳林首长,让我原地做了几个动作,跟我聊了会,得知我还是高中毕业时,他更感兴趣了。
于是他当即决定,让我五天后去区医院进行复查。如果身体没问题,这兵他要定了。
五天后,我早早赶去了区医院,见到了带队来的民兵连长。
他脸黑得锅底一般,看我一副很不善的样子。
我没有放在心上,李连长都说了,只要身体合格,这兵我当定了。现在你还能阻拦我吗?
经历了忐忑的体检,万幸我身体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有些偏瘦,营养不良而已。
李首长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说道:“好小子,去了部队敞开了吃,好好练,身体能练起来的。”
感受到领导的拳拳关心,我忍不住红了眼眶,重重点了点头。
1976年12月15日,告别了家乡亲人,我一路向北,终于抵达了内蒙古包头城郊的一处营房。
当兵不易,我也将部队看成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不敢有丝毫懈怠。
可我的身体条件不是太好,力量和速度都差了许多,我只能在态度上弥补,追求量变引起质变。
教官演练的每个动作,我都力争做到完美复刻,哪怕是晚上休息时,我都在默默加练。
这些都被李炳林首长看在眼里,他此时在当新兵连连长。
他后来跟我说,当时我就看出你小子不一般,有股子狠劲。
最终三个月的新兵训练,我的表现得到了认可。最后李连长强势决定,哪里都不去,到连队给他当文书去。
对于新兵而言,这可算是一步登天了。我心中惶恐,连忙推辞自己能力不够,无法胜任。
李连长眼睛一鼓,“你别废话,我可是将牛皮吹出去了。回去后跟我去见连长和指导员,这事最终还得他们首肯。你小子可别给我掉链子,不然我扒了你的皮……”
李连长的话说得粗鲁,但对我的爱护和重视溢于言表。
我也没有给他掉链子,经受住了连长和指导员的考核,以新兵身份当上了连队的文书。
文书岗位事务繁杂,方方面面的事都得考虑到。我知道自己初来乍到,就得了高位,肯定会引起老兵们的不满。
所以我的姿态放得很低,对那些老资格前辈很尊重。时间久了,大家都觉得我为人谦虚,做事严谨,也认可了我的工作。
时间一晃而过,1979年底,我被推荐到师教导队参加培训,这也是战士提干的最后一次机会。
1980年4月,我从教导队培训归来,成功提干为排长。
想想当初为了当兵,我也是豁出去了,到如今能够提干,身穿四个兜,我对部队充满了感激。几位首长的看重和提拔,更是助推我走到了这一步,他们都是我人生中的贵人。

1980年8月份,我回家探亲,让我也真正看懂了何为人情世故。
我提干的消息,父母捂得严严实实,从未跟别人说起过。
但等到我回家,这事就藏不住了。村里人跟我热情地打着招呼,纷纷邀请我上门去坐坐。
我打着哈哈,敷衍着周围的恭贺声。
几年过去,我已不再是当初的愣头青。
回家吃饭时,家里来的人更多,以往和我家不亲近,甚至发生过口角的人都来了。
没人再叫父亲“徐结巴”的外号了,大辈的叫大名,小辈们则叫起了“叔”“伯”。
曾经门都不让我进的三叔也来了,三妈没好意思上门。
三叔拿着一瓶酒,讪笑道我为徐家争光了,晚上一定要喝酒好好庆祝一番。
按我以往的脾气,我肯定要将三叔赶出去。最亲的人往往伤害最深,当初借粮的那一幕,我恐怕一辈子都难以忘记。
但看到父亲意气风发的样子,仿佛几十年受到的委屈一朝被洗刷,我也默许了。
也是,我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快意恩仇,但父母却不能。他们还要生活在村里,还得面对这些人情世故。
晚上人都走了,父亲却叮嘱我,“平娃,你明天去看看武装部的王干事,还有你外公外婆那边,你能有今天,可多亏了人家。”
“你外公那边你也得抽空去一下,我知道当年你受了委屈,如今你有出息了,可不能忘了人家的好。有些人有些事,应付就行了。但有些人,有些情,咱可得记一辈子!”
听完父亲的话,我很欣慰,也很佩服。虽然他没有多少文化,嘴巴也不利索,但心里还是很清楚的。
他没有被突如其来的追捧冲昏头脑,以后我在部队干,就彻底无后顾之忧了。
我去拜访了王干事,向他表示了感谢。又去外公外婆家住了两天,他们看到我出息了,两位老人也是激动地抹着眼泪,连连感叹终于熬出来了。
看得出来,他们是由衷地为我高兴,为我们家走出困境而高兴。相比较其他人的前倨后恭,这种真情才是值得一辈子去维护的。
我一直在部队干到了1999年,在40岁的时候,以正团职转业回了老家公安系统。

从小的经历告诉我,当一个人有一定的地位后,身边总会围着一圈人,嘴里说着好话,手上提着礼物。
但一定要擦亮眼睛,保持清醒,不要沉醉于别人的吹捧中。为人重情重义没有错,但也要看是否是真心,是否值得。
素材/徐平 撰文/老刘(本文采用第一人称叙述,部分细节有文学处理,请理性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