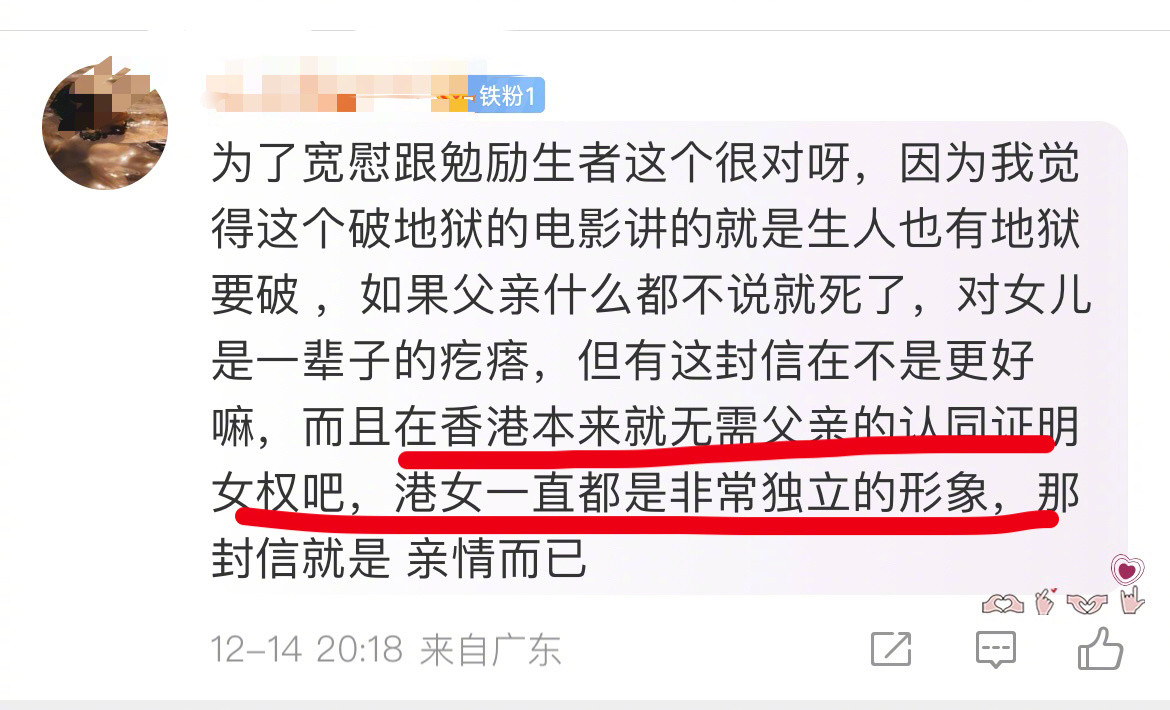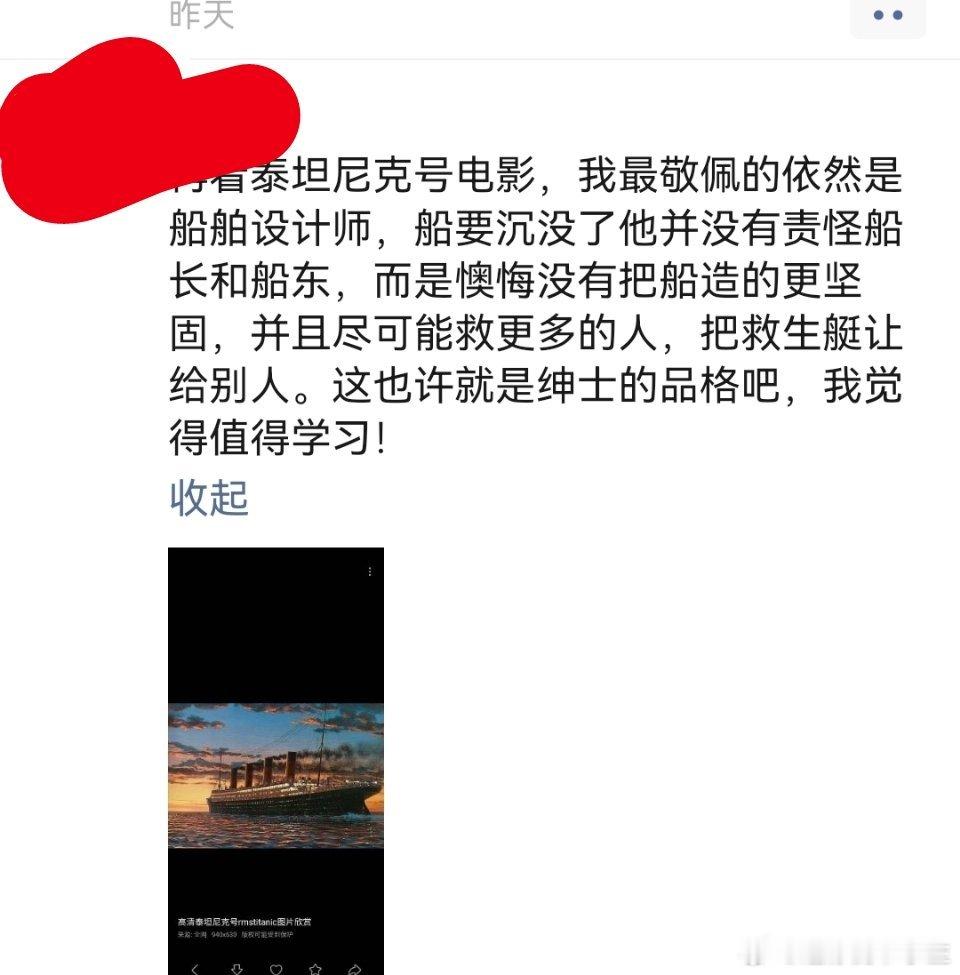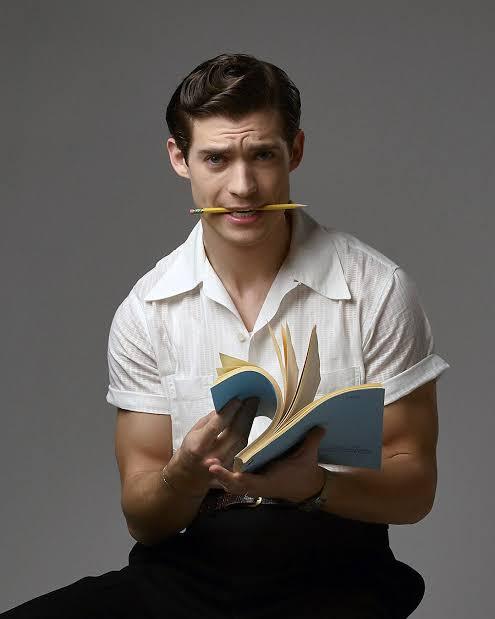先解释电影名:“破地狱”是葬礼仪式,源自佛教《目连救母》的故事。目连为佛陀徒弟,以神通(比特异功能更厉害的超能力)及孝道闻名。

而“超度亡灵”的核心理念,与电影中的人物在“他人即地狱”的生活中挣扎,活人也需要被超渡相互呼应。
片中多次提到的祖师爷,则展现了香港深厚的黄大仙道教体系信仰,将黄大仙信仰融入喃呒师的角色设定中,借着新一代的年轻人视角,思索并怀疑从小耳濡目染的宗教其意义与仪式之必要性。

《破·地狱》在香港上映已经一月有余,便以现象级之姿打破香港华语电影史上最高票房,赢过同为黄子华所主演的《毒舌大状》。
其中,因许冠文、黄子华而入场看戏的影迷不少,而这也是港产电影近年少见的一片荣景。

亚洲电影经常出现的一种叙事方法,是借着传统礼俗、科仪来照见家庭困境,以及由此迸裂出的个人难题;透过这样以小见大的观看,折射当今社会之现况,又或是更进一步地处理长久积累于社会的历史创伤。
因此,“创伤”也成为亚洲电影经常处理的命题,如马来西亚电影《富都青年》以一对非法移工兄弟档,借导演自身经验之延伸,拍出中下阶层生活困境;同为马来西亚作品的《五月雪》则是将中国古代窦娥作引子,以古喻今重现冤假错案。

而香港电影亦于近年交出几部佳作,如《七月返归》以都市传说成功引起香港观众共鸣,电影本意则为探讨当今香港社会所面对的真假虚实,以及人究竟该保守生活,或是选择探明真相一路?而以爱情故事包装的《幻爱》所欲指涉的电影意识及女性观刻画也是一绝。
如此的人间困境,有着多种层次。
而《破·地狱》从最能体现“困境”的大疫之年,借由生者视角出发,主角道生从为生者筹备婚礼的婚礼顾问,转行成为帮死者筹办葬礼的丧仪经纪人,他接手葬仪公司长生店,由此串起另一主角文哥一家人的故事。

《破·地狱》之所以引起关注,源于其深入探索香港独特的宗教信仰与文化,特别是殡葬仪式与道教的紧密结合。
透过“破地狱”仪式将这些元素与一段家庭故事的交织,唤醒深植于香港民众日常生活中的道教、佛教及传统民间信仰,使得这部作品不仅仅是宗教题材电影。
更是香港文化和精神层面的呈现,同时更触动人性与情感的深层探讨。

《破·地狱》不仅探讨生死哲学,更深刻描绘了人物关系的纠葛。
观众或许能超脱剧情文本,从另一个角度与香港当前的社会背景相互连结。
在疫情后,香港的各行业经济萧条,红勘地区殡葬业与繁华红馆紧邻,此一地理与社会的对比折射出极端的对立。
正如电影中呈现的亡者与生者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

《破·地狱》的叙事线十分简单,甚至可以说这是一场道生的“英雄旅程”。
电影前半段,讲述道生为保住婚礼公司,抵押房产做贷款,因此在接手长生店后想出各式方法想多赚些“死人钱”,期间碰上几组来委托举办葬礼的死者亲属,逐渐改变原先对丧葬礼俗的态度;
后半段则由道生与文哥的相濡以沫为转折,借文哥之死达到电影高潮。
再以道生为文哥(遗体)化妆沐浴,于葬礼上与其他喃呒师傅起争执,只为让文哥的女儿能在父亲葬礼上跳“破地狱”作结。

《破·地狱》的第一场戏与最后一场戏,皆以尖锐的唢呐声揭序,喃呒师傅诵念经文,步罡踏斗,绕着火盆为亡者开路,行破地狱之仪。
更旨在渡化生者面死之哀,其后的施食与炼度才为真正渡化亡者之意。
因此,喃呒师傅悬抛于空中的桃木剑或许更像是生者之思,如目莲以思念踏破地狱救母,而喃呒师傅所执之白幡与红幡,前者代表亡者,后者代表先祖,除了渡化家属欲救之魂,更望惠及众生孤魂与现世的一众生者。

当破地狱成为一众人的疗愈,导演陈茂贤在片中不同情节以金句点明其本意,如“活人怎么可以被超渡呢?活人也需要破地狱的,活着也有很多地狱。”
便完整地点明了他拍的《破·地狱》并不是为了亡者,而是为了生人。
也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视道生一角便是陈茂贤思想之延伸,陈茂贤曾于专访中提及,起初《破·地狱》是想做成喜剧的,但在疫情期间碰上许多死亡,电影才逐渐往现在的方向发展。

不过可惜的是,电影以每20分钟设计一场戏剧冲突(高潮),搭配整个交响乐团从旁伴奏的悲壮配乐,再搭配满满金句,几乎塞满了整部片子。
没有一丝留白的节奏,更没有让观众从角色的行动开始进行自我思辨的空间。
甚至在几场回忆戏里,除了搭配角色口白、回忆画面之外,也同样塞入满溢的配乐,实在有点过份用力。

而针对角色的刻画也仅仅只是蜻蜓点水。
道生多年下来并未与女友结婚,在女友怀孕时亦表明孩子的出世并非其自由选择,那么又何必让孩子来人间受苦受难?
电影并未描述道生在成为葬仪顾问之前(或者更早)所遇的创伤经验,仅仅在文哥葬礼结束之后带出了道生似乎由死向生,愿意接受“只要能来到世间,皆是一场难得”的想法,最后带着女友开车行向城市(象征着世界)的意象作结。

道生一角于片中的最大作用在带领文哥打破传统观念,并借传统科仪疗愈生者,可对于其自身的创并未多作补述,或许是在金句与配乐之外,观众较难感到共鸣之处。
来到片中的文哥一家人,已经娶妻生子的志斌面对父亲传承下来的喃呒师傅一职,一方面排斥这个自幼就面临的没有选择权力,且希望能让自己的儿子脱离红磡、脱离喃呒师傅的工作,另一方面,又深知自己的行为或许是对父亲的背叛。
夹在两个家庭(原生家庭与自组家庭)之间的他,在医院长廊上的那一场戏,朱柏康实在演得极好,但于其后便未有着墨,实在可惜。

另外,卫诗雅所饰演的文哥女儿、文玥一角,则是个救护员,日日面对由生向死之过渡。
自小便视父亲为偶像,或许比哥哥更勤于练功、更有才能继承喃呒师傅之职,却因其生理女性身份而被拒于门外。
若是本片能进行更深度的刻画,相信将是最精彩的一条故事线。

片中不仅探讨了宗教仪式,也揭示出香港殡葬业的现实面。
黄子华所饰演的道生一角,接管了名为文明殡仪的长生店,揭露以往鲜少在银幕上揭露的殡葬业幕后,呈现了各个殡葬环节。
更罕见地至香港东华义庄场景,义庄历史背景能追溯至香港开埠初期严峻环境下的殡葬环境,其不仅是遗体临时存放的地方,更是社会低阶层、无人照顾亡者的最后归宿。
而这样的环境搬到电影中,成为尸体是否需要遵循传统安葬方式来处理的疑问发生地,更反映出传统与现代在拉锯之间,皆欲寻求超脱的矛盾。

我印象最深的一场戏是《破?地狱》最后一段,文哥的自白就是以葬礼(现在)、文哥回忆(过去)及文玥的人生发展(未来)相互交替组织建立的。
这种现在、过去、未来的三角时空永恒回路,不停建造人物立体且可变的性格。
电影中人物性格就是经堆积来表达。以文哥为例,从心软仗义帮助道生处理尸体,到表达对已逝太太的情深;再到最后一段,文哥显示自己勇敢突破的一面。

电影结尾,引用白居易《自觉二首》中的诗句“置心为止水,视身如浮云。抖擞垢秽衣,度脱生死轮。”表达了超越生死、解脱烦忧的佛教思想。诗句中的“止水”与“浮云”象征内心的平静与对生死无常的豁达态度,对于活人来说,期许能借仪式疗愈伤痛;而“抖擞垢秽衣,度脱生死轮”则象征洗涤心灵、解脱生死束缚,与仪式中亡者的超渡过程相契合,深化解脱与超越主题。
影片最后的那场破地狱科仪,道生与众人争吵的说教意味实在过分严重,而在兄妹俩开始舞起破地狱时,画外音却突兀地切入文哥朗诵写给文玥的身后信,并且切换至几场父女俩的回忆画面,使得观众无法真正地将目光看向正在被破地狱疗愈的兄妹俩,亦无法借着这样的再观看达到导演所欲完成的渡化众生之意。

这或许是整部片最大的败笔,如果这场戏能够完全地专注于科仪本身,以及两兄妹之间的对戏,或许会更好。


《破·地狱》旨在各个层面上都要“破”,除了道生、文哥各自的转念与自我和解之外,整场破地狱,也是在为文哥的家人以及银幕外的我们、进行一场解除生之执念的创伤疗愈。而即使在许多人物刻画上稍显苍白,许多情节也都过分煽情。




但至少是近年来在商业制作上完成度最高的港产电影,且能再见许冠文+黄子华合框在大银幕上的身影,亦属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