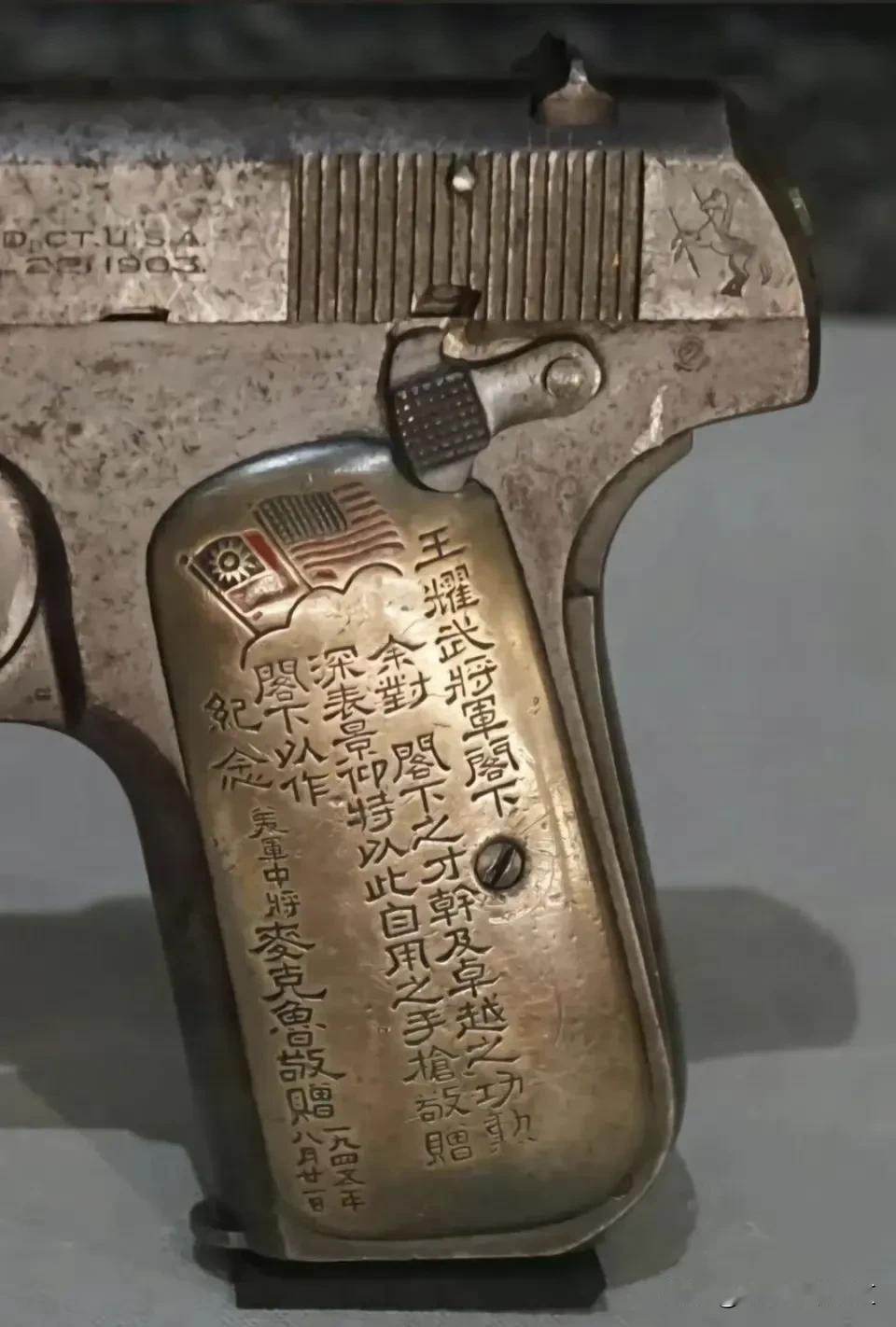简介:
庚子之乱,及笄之年。
慈禧老佛爷亲赐的姻缘,成亲路上,京都大乱,血染的凤冠霞帔流亡。生死之隙,那个挡在她面前的人,那双琥珀色的眸子…
她府上也有一位琥珀眸色的洋先生,教她洋文算术天文地理,亦教尽她一身学识和应世做人。
相像的眸子,截然不同的皮囊。
…
大清将亡,挽清未挽。

精选片段:
如果早一百年前,我陪你打战,陪你流放,把命交到你手上。
——记
时间追溯到一百多年前。是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
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八国联军侵华,老佛爷西狩,等等。动国之根本,牵一整个朝代及一整个朝代下所有人的命格。
当然,包括她。
这一年,她刚到及笄。
铺设了红毡的御道,沿街绸缎搭起的彩架挂满了大红宫灯,颇为壮观的迎亲队伍从东堂子胡同的地安门再次启程出发,绕半城,到城北的另一座府邸。
观亲的人群熙涌,人声鼎沸,鼓声震天。轿里的人一身金丝大红凤冠霞帔,手握玉如意和苹果,端坐,脸上一片祥静。她的心思似把这一切都屏除在外。
“这京城里少有人见过清格格,传闻也少得很,可依我看,这清格格的才情样貌定是不输孝哲毅皇后及其他王公贵女。”
“是啊,这次的联姻可谓是门当户对,佳偶天成。一个将门之后,一个状元之女。”
“差矣差矣,观其姑侄姊妹,哪一个不比清格格嫁得好?”
“…”
……
轿里的人嘴角似噙笑。这场太后授旨,阿妈额娘属意的姻亲,其实她也是情愿的。
爱新觉罗氏和阿鲁特氏。
她脑间一遍遍过着出阁前额娘嘱咐她的话,以及待会行大礼的礼数规矩。行程过半,她手心攥出了汗。她也是紧张的。突地喜轿颠簸,一下踉跄,她手中的苹果脱落,滚至轿外。
她心也骤停。
那一下俯身抬眸间,她看到轿外,人影迭乱。
她想,她该是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
轿子倾斜摇晃,最后狠狠砸在地上。她是被跌出轿外的。旗头松落大半,从阿玛那,她多少知道点时局。
她抬手,索性将旗头拔去。
瞬时,盘至顶头的发乌泱泱地全散落。
在这一片大红的世界里,她第一次见识到了,什么叫做,兵荒马乱。
是,真的乱。
她心里立刻有了决定,卸去了多余累赘的外喜卦,冲进流乱的人群里,跟着逃命。
也许真的是她那一身红太过扎眼,以至于真的还有人在流亡途中伫足回头瞥这一眼。很多年后记者追踪采访,有人回忆说,真正的倾国倾城是怎样谁也没见识过,可清格格那一眼,当真是,一见不忘。
关于太后赐婚的旨意,下达是在光绪二十六年的年初。那天的院落飘起了鹅毛般的雪。崇绮府一众人齐齐地跪满内堂。着,五月后大婚。
针线女红厨艺等等一系列我认为为人妻该会的事,都是在那五月里匆匆学就的。
出嫁的红喜盖头遮去所有视线,周遭围住了人。我听到他们唤我,清儿,格格。听得最分明地,还是廉宏侄儿的那声‘挽挽’。
伤情之余,大抵觉得人生从未如此圆满。
可这圆满似乎也就止在这。
义和拳、清兵、各国公使、洋援兵等等多方势力盘踞冲突,那场动乱猝防不及。就是迎亲路上,我被冲散流亡途中。
一身喜服拖累,我跑不开太远。情急权衡之下,我躲进了一方破矮房屋。
有人马逼近,在我想到下一步脱身之策前,一声枪响,房屋坍塌,我被掩埋废墟之下。
这一塌一埋,幸,也不幸。
我不知道多久后转醒,目所能及,瞧不到一点光亮。一动,牵得全身疼。
之前的记忆悉数涌来,然后又慢慢地开始意识涣散。
我闻到了血腥味,以及死亡逼仄的气息。我只要顺其,我便可能永远这个姿势,永远地被掩埋在这。
不,不行。我要出去。阿玛,额娘…还有…
我拳头一点点收紧,再松怔,抬手一点一点拔落发髻上惟一的珠钗。然后朝四周探了探。敲击的声音是辨得出的,大部分地方都堵得严实,只有一处,或许留有虚缝。
我屏住全身的气力,猛地只朝那一处。
滚石的声音,我心里暗松一口气。刺进眼睛里的太阳,有瞬恍如失了明。
我手探着外面,凭着知觉一点一点往外挪。也许是我动静早就引来了外界注意,反正当我耗尽周身气力爬出时,看到的第一眼世界,就是被诸多的洋士兵团团围住。
再之后,前方让出一道口,一个长官模样的人,凌迟般地抬起手。他手上的枪口,正对我额头。
原来,横竖都逃不过,横竖都是死。
我累得阖上眼。心里盘桓的惟一念头就是,如何才能活下去。
那一声枪响太突兀。再然后,是更突兀的‘咣噹’声。我没死。那一眼睁开,晃得我…又再闭回去。刀光剑影,我看到被子弹打凹了的剑,以及上方那只棱骨分明的手。再往上,琥珀色的眼睛,及张很好看的脸。
这是我人生里遇到的第三双琥珀色的眼睛。也是他,成了我日后生命里最重要的人。
光绪十一年五月(1885),吏部尚书崇绮的侧福晋诞下一女。七日后崇绮为其取名,挽清。
阿鲁特·挽清。
侧福晋难产,大夫拼尽全力才保母女均安。侧福晋产后心思郁结,没捱过几日,终是在小格格的满月日,撒手人寰了。
此后小格格便交由大福晋瓜尔佳氏抚养。这之后的很长年岁里,她一直以为,瓜尔佳氏就是生她养她的亲额娘。
据府里的下人说,格格小时候生性极顽劣。虽是女儿身,却是十足的男儿性情。大概与大人老年得女有关,宠溺很,所幸并不太骄纵。约莫四岁半的时候,生了场大病。请动了半个京城的名医,还未有效。最后是京郊的一位女住持出手,才将格格救回。作为诊金,住持向吏部大人要了小格格,名曰委其修行。格格跟了她三年,唤她一声师父。她擅医术擅卜卦。可那三年她从没见她给谁占过卦。她跟着她,最多算是师承医道。
住持当年要带走小格格,格格的阿玛自是不肯的。一番下来,住持给格格算上这一卦。卦上说,格格此生,只怕命途多舛矣。
时间调拨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这一年,我十三岁。
转变得像是一个姑娘家,好像就是这一年。
这天,我立在桌案前写大字,抬眸低首间,看到窗外院落的杏花瓣又落了几落。
不多一会,我听到有人唤,挽挽姑姑。
这府邸里正儿八经叫我姑姑的有好些个,可这前缀加上挽挽的,便只有廉宏一个。
我大哥葆初的第四子,论辈分他叫我一声姑姑,可年龄上还是他稍大些。
我当下写好最后一笔,立即飞奔了出去。到廉宏近身前,腿上一个用劲,双手准确无误地钳在他手臂上。双脚腾空而起,整个人引体向上。这是我做惯了的动作,早些年同他一道练箭,师傅说,可练臂力。
廉宏大概也是拿我这个姑姑无奈得很,笑笑,任由。
我的兄弟姊妹大多在我出生前就已嫁娶婚配,惟独大哥葆初的几个子女年龄倒还与我相仿些。在这几个侄子侄女里,就属廉宏与我最为亲厚。
我房中的桌案几乎在最显目的位置,进屋来一眼就能看到。此番廉宏走近,仔细看了几看,道,字里行间越发有阿玛和玛法的韵味了。
我的阿玛即廉宏的玛法崇绮是这大清国的第一位旗人状元,才情自不必说,这书法丹青更是了得。这些年辞官在家,更是投身醉心于此。自我习字以来便日日跟在阿玛身边,少说练了也有四五年光景。是不是完全得他老人家真谛不敢说,拿去唬唬市面上的人倒也是还可以的。
“对了,今日阿玛从玛法那回来,据说是谈到挽挽你了。玛法寻思着,是不是该给姑姑你定一门亲事。”
“哦?有这等事,玛法可说属意哪家的公子了?”
廉宏盯着我没说话,半晌,“来得路上我想了数种你会有的反应,抗拒,娇羞。惟独没想你会如此直白问出来。”
“你何时见你姑姑娇羞过。况未定的事,我干嘛抗拒。早些知道阿玛的想法,保不准我还能从中自己做主呢!”
“听姑姑这说法,心中可是有中意的男子了?”
“你小子这是故意诓我的话呀!”
“我做你这中间人甚是辛苦,挽挽姑姑总该给些彩头。”
“你说便说,不说便罢了。我让落络去你阿玛那牵了赤乘来,这会该到了,我去山上小住几日。”
“又去你那半个娘亲那…”
落络是打小就跟在我身边的婢女,而那‘赤乘’是千里难觅的良驹,虽一直养在葆初那处,这些年下来,倒越发像我的坐骑。
廉宏说得‘半个娘亲’是有典故的。当年我突被师父带走,岂止是阿玛不肯,我更不肯。大哭大闹,后来想想实是小孩子心性。三年后我被送回,临别时,我竟偷偷抹了眼泪,第一次生出自己都说不明白的情绪来。师父见状,安慰我道,‘只是小别,你若想,便可时时来我这小住几日’。阿玛见状,也发了话,‘一日为师,自是终身为父’。我听不进安慰,只抓住最后二字,“师父是女的,怎么可以为父。”在场的人大抵都是愣了一愣,笑了一笑的。师父她老人家率先反应过来,“那便作你半个娘亲罢。”
师父的寺院外植了一排木槿,有好几次我来都恰时花期。说起我来的时点都是有迹可循的。师父每小半月都要出一次义诊,我便每每都赶在这时候,以带帮点小忙。
此次我早来一日,师父正在院落翻晒药材。我两步作一步,上前一道。
她老人家不抬首也知是我,温温开了口,“我给你炖了药膳,你先趁热喝了吧。”
师父这个人性子不冷不热,对人说不上是好是坏。可对我,我总觉得是要与别人,不一样些。
师父在的这座寺庙,加上她及别的师太,以及旁支的女弟子,统共也不过八、九人。人不多,是以每次义诊人都是抽去大多半的,只留一两个人看守寺庙。
会诊病的便留以诊病,不会的,便抄抄药方,抓抓配药什么的。而我,从当年那个抓配药的小丫头已然褪换成,半个大夫。
师父准许了,瞧些小病还是可以的。
“老大爷,您这并非是咳嗽之症,而是体内寒毒太盛所致。我先给您开几味药,去去寒…”
…
“小儿热症,配连翘,防风,甘草,山栀子各等分,捣末,每服二钱,水一中盏。煎七分,去滓服温。”
…
义诊一天下来若天色还有早的话,我们便会在当地镇上用了晚膳。今天便是这么个情况。
我与师父习惯坐与一桌。饭菜上来时,师父问,粗茶淡饭,可还吃得惯。
我略一愣,“师父讲笑。”
“听你那侄子说,这京城里凡是美味,就没有你没吃过的。”
我赔笑,“是贪吃了些。”
“我们家修容可不止贪吃呢,也贪色得很。”
修容是当年我拜师时师父给我取得法号,是以一直这么叫。
我与师父说话邻座的师太不知怎地留心听了去,还搭了腔。此番我嘴边的笑是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
师太一:修容你当年可是调戏了个琥珀色眼眸的俏洋公子,可还记得?
师太二;不过那小公子的模样生得真是好,也难怪小修容情不自禁…
师太三:…
实在冤枉紧了,当年那个委实称不上调戏。当年我才多大,撑死了就是有些个好奇心。那个时候也是出好义诊在用晚膳。我生平第一次瞧见一双有别于我们的眼睛,还讲了我听不懂的话。那时我大约是魔障了,一步步蹒跚走到人家跟前,‘哥哥,你能听懂我说话吗’?
事后想想忒丢人,此刻再赔笑,“师太们真是好记性,好像是有这么一桩事…”
深夜,崇绮书房。
崇绮的眉间似锁非锁,走道福晋瓜尔佳氏端了一盅汤,过来。
“夜深了,大人。妾身送了盅汤来。大人若是饿了,正好垫一垫肚子。”
“福晋有心了。”
瓜尔佳氏把汤放置桌头,盛了小碗出来,“大人最近睡得较平日都晚些,可是为清儿的事忧心?”
崇绮捋了捋胡子,“不尽是。”
沉吟半晌,又道,“不过说到清儿,这几日我一直想着,咱们是不是好给她定门亲事。”
“大人心中可是已有人选?”
“我与徐桐徐大人相交相知多年,与他结成亲家就不错。可惜那徐大公子长清儿太多,又已娶正妻。清儿此番万不好再嫁过去。”
“是可惜了些,”稍一顿,“尚有几个亲王之子未娶妻,清儿嫁过去也不算委屈。”
“你知道罢,清儿自出生起我觉得对她不住。加之多年前她师父的那一卦…如今时局正乱,我护佑不了她一世,夫家这件事便马虎不得。纵看她姊妹几个,此番我不想她嫁得太好,又不愿她嫁得太差,福晋可明白?”
“其实大人也不必太过忧虑,清儿这样没几个人能欺侮了去。清儿的夫婿…您觉得恭亲王奕嫡孙溥伟如何,妾身听说他不日将承袭王爵,是个有勇有谋的人,做夫婿想来是不错的。”
崇绮好一会没接话,“恭亲王府那近日风头盛得很,我之前也是想过,只是现下我…”
“那大人是与我想到一处了,想到一处便就好办。我与那些福晋们总算有些交情,这几日我便去走动走动,探探她们的口实,看看能不能再摸摸那些世家公子的秉性来。”
“如此最好,只是有劳…”
“大人,”瓜尔佳氏出声打断,“你我夫妻之间用不着这样的言语,况,清儿也是我的女儿。”
义诊结束我便径直回了府。如今这京城里各方势力盘踞,着实不太太平。我一路快马加鞭,小心得很。
我让落络把赤乘安顿好,自己则先步回院子。远远地看到那片杏花树下,立着个月牙色的少年,清朗得很。
“你上次拿我夫家来调侃我,我却是忘了该拿你婆家来堵你。想来你应该比我更早定下一门亲事才是。我这个做长辈的,也可给你做主了。”
廉宏本就在这等我,此番听到我声音,也只是,笑笑。
作为小辈的他,倒一直很让着我。
不多一会,有几个婢女轮番端了吃食上来,远远地闻着那味,整个人都舒心开来。
“今日我路过那信远斋,又想着挽挽你今个回来,便给顺手匀了来。”
这信远斋的甜点最是有名,尤其是这萨其马和糖葫芦。糖葫芦的火候极难掌控,信远斋这一道工序做得尤为好。糖衣外还裹了碎核桃和瓜子仁。萨其马也不马虎,外面点缀着冬瓜做得金银条,看着怡人,口感也尤其好。
“你小子有心了,不枉姑姑平时那么疼你。”
“疼这个字眼用得不错,不过挽挽,你是不是把这主宾顺序颠倒了?”
这话我也是笑笑,不说话。
“你出去这几日,有件事你肯定不知。府里来了位洋先生,听说是从鸦片那国来的,给我们授洋文,还有…”
“算术。”这洋先生我早有耳闻,早年我修行回来便说要请,请了这么多年也没个踪影,现下,“消息确实吗?”
“确实呀,阿玛都见过了,玛法也发话了,说我们这些个没成家没出嫁的,想来的便都可以过来听听。”
“你玛法这般,倒是开明得很。”
“挽挽,你说这洋文和算术好是不好玩?”
我摊了几摊手,“总不会比那满蒙汉文更无聊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