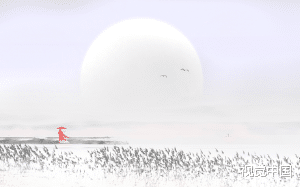十三岁这年,我爹救了个商人,却因为救他惨遭灭门。
商人让我跟他走,认我做干女儿。
我问他家中有几个孩子。
“两个。”
我心想:我也要让你也尝尝失去亲人的滋味。
可后来机会摆在眼前时却下不去手了。
1
临睡前,我又看了一眼枕头旁的木雕像。
那是明日要送给阿娘的生辰礼。
阿娘一直想要生个弟弟,把这个送子观音给她,她定然会很欣喜。
阿娘一高兴说不定就会同意我跟着阿爹走镖。
我越想越美,一翻身,吓得跳了起来。
窗外隐约亮着好多火把,还有喊杀声。
来不及穿鞋,我推门跑出去,一把撞在我娘怀里。
“外头来了强盗,快点躲好别出来。”
强盗?这山里山外谁不知道我爹是武状元是镖头,哪个强盗敢来我家?
我回屋穿了鞋提上流星鞭正要出去帮忙,就见我爹架着个人冲进院门,他浑身是血,用身子顶住门催我们快点进屋藏好别出来。
我这才知道来的不是普通的强盗,是专门劫财的山匪,他们冲着我爹救下的人而来,那人是个富商,身上带着上百两的货银。
激战一夜,我爹杀了三个跳进院子里的山匪。
天刚微亮他便打开院门叫我陪着富商去衙门报官。
“快去快回,等你回来一起给你娘过生辰。”
阿爹眼底发青,却还冲我眨眨眼,我知道他一定也准备了礼物给阿娘,他也想哄阿娘高兴好同意我跟着走镖。
我点头,带着胳膊缠着纱布的富商抄近路去了衙门。
县令震惊,立刻发了海捕文书,还叫上捕快随我们一道回来收敛山匪尸体。
离得好远,就见院门敞开着,一股淡淡的血腥气随风飘过来。
我心里咯噔一下,撒开退就往家跑,一进院子就见我爹横躺在地上,身上被戳了五六个血洞,身下血汪汪的一片。
我娘倒在厢房门口,胸口上插着一把刀,上面有一个大大的陈字,手里还紧攥着我雕的那个观音小像。
她一定是替我收拾床铺时看到了这个礼物,拿在手里正欢喜地把玩,没想到昨晚的山匪杀回来报复……
我跪在阿娘尸体旁失声痛哭。
为什么?明明我爹救了人做了好事,为什么好人没有好报?为什么他们都死了?今日本来是我娘的生辰却因为我爹的善举变成了她的祭日。
富商站在院子里眼眶通红不知所措,他也没想到山匪竟会跑回来报复,我猜他也很内疚。
可若昨晚我爹没有开门,没有把他救进来,我家今日便不会招来灭门之祸,此刻我一家三口正欢欢喜喜庆祝阿娘的生辰。
裴县令派人安葬了我爹娘,我收拾他俩遗物时才发现我娘已经有了身孕,她做了好几件婴孩的衣服,浅蓝、青色,我猜这一胎定是个男孩。
我把那个送子观音放在了阿娘身旁,还有她给弟弟做的那些衣裳,一起放在了棺材里陪她。
棺木入土,裴县令问我想要去投奔哪个亲戚,他遣人送我。
“跟我回家吧,我欠你爹娘一条命,日后定然像亲生的一般疼你,一定会比对亲闺女还疼……”
富商踌躇着看向我,眼里满是内疚。
我问他家中有几个孩子。
“两个。”
我点头同意,心想:我也要让你也尝尝失去亲人的滋味。
2
富商姓廖,名谦,竟还是个举人。
我跟着他一路水路陆路辗转回到江州,见到了他的妻子跟两个女儿。
大女儿廖菁与我同岁,小女儿廖蓉还不到四岁。她手里抱着个绢人娃娃往我怀里塞,“姐姐,一起玩。”
我从不爱玩娃娃,只喜欢舞刀弄枪,便摸出流星鞭一鞭子甩出去劈裂了青石砖。
廖蓉吓得哇哇大哭,我却看着她笑。
“胆小鬼,怪不得坏人来了你只敢往屋里躲。”
廖谦脸红到耳根,抱起廖蓉从怀里掏出块七巧板,“等蓉姐大了再跟穆槿姐姐学武艺强身好不好?”
廖菁见我吓哭妹妹很不高兴,可摄于他爹的威压又不敢当面跟我翻脸,我看她那一脸吃瘪的样子心里畅快极了。
廖谦的妻子夏元娘亲自下厨备了丰盛的洗尘宴,她领我换了衣裳,牵着我坐在上座。
“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大女儿,也是我们全家的恩人。”
我知道廖谦提前写了信回家,但是我并不领情,他们待我再好也不能换回我爹娘,他们这辈子都欠我的。
廖谦、夏元娘齐齐举杯敬我,我端起杯子直接浇在地上。“先敬我爹娘。”
二人大囧,立刻也学着我的样子把酒浇在地上,感谢我爹娘。
“他们听不见的。”
我不咸不淡来了一句,立刻让整个席面都静了下来。
他们都不敢动筷,只有廖蓉饿急了伸手去拿最近的莲子糕,被她娘拍了下手哇哇地哭。
一场欢欢喜喜的宴席被我搅得不欢而散。
我很开心。
夏元娘亲自安排我在离她最近的厢房住下,她给我做了很多四季新衣,全都是比照着廖菁的尺寸做的,大小很合身,但我却不喜欢。
“我平时习武,穿不惯裙子。”
夏元娘一拍脑门,“瞧我,忘了这茬,你先将就穿着,明日我便叫人抓紧裁制新衣。”
我没说话,坐在床上发愣。
“可是这被褥不舒服么?”
“不是,我想阿娘了……”
夏元娘愣住,旋即红了眼圈,走过来一把搂住我。
我来廖府第一晚,夏元娘陪我一起睡哄我入梦。
她会看星象,给我讲牛郎织女的故事,我说“从前我阿娘也给我讲过。”她便闭了嘴,只是陪着我,直到我实在扛不住困意沉沉睡着。
转天早上吃饭,我见夏元娘眼皮红肿像个桃子正要讥讽她装什么伤心难过,廖菁牵着廖蓉瞪我,“阿娘平日都是陪我跟妹妹一起睡,昨晚听你喊爹娘哭了整整一晚上……”
我看向夏元娘,她赶紧拿帕子遮脸。
我又看桌上的早饭,江州在江南,他们却特意做了并州特有的刀削面跟羊汤,还烙了一张葱油饼。
我端过刀削面大口吃了,可吃着吃着眼泪又不争气流下来。
夏元娘赶忙问我是不是太烫了。
“我就是想起来我娘会在面里放醋。”
廖菁急了,一拍桌子跟我瞪眼,“你爹救了我爹,我们廖家是欠你一条命,可救人的不是你呀,你凭什么在这儿糟蹋我爹娘,难道你爹当初救下我爹为的就是让别人觉得亏欠他一辈子么?”
“放肆!”
啪!
廖谦急匆匆走进来,扬手给了廖菁一个耳光,怒斥她没有礼数。
“我怎么教出你这么个不知感恩的逆子,她跟你一般大,突然没了爹娘,心里难过抱怨委屈愤恨都是人之常情,你换位想想,若你如她这般,你又能做的如何?”
3
廖菁被打没有哭,我却哭了。
廖谦一句话说出了我心里的憋屈跟不甘,这些日子糊在我心口的那层纸终于被他捅破,憋在我心里的那股子怨恨一股脑儿冲了出来。
我对着廖菁大喊,“你知不知道我有多羡慕你,你至少还有爹爹打你,我现在想让我爹爹打我都不能了!”
我哭着跑出屋子一路往前,也不知道是哪儿就凭着一股子劲一直跑,直到跑到花园假山里躲起来,确定他们都找不到我才停下来。
所有人都出来找我,我听见他们喊我名字,但是我就是不想出来。我不想待在这个地方,不想看着他们一家其乐融融。
我不想让他们可怜我照顾我,我只是想让他们都正常些。
他们不知道家人之间的爱不会刻意表现出来,他们越是对我好,我就越觉得自己是个外人,是多出来的那一个。
轰隆隆,头顶响起了闷雷。
夏日的江南,雨说下就下,我往假山里面躲,没想到竟然发现了一只奄奄一息的小狗。
我把它藏进怀里冲出雨幕,朝着急着找我浑身淋湿的夏元娘挥手,“快,快给它找个大夫。”
廖谦找了只刚下崽的母狗,小狗吃饱奶依偎在大狗身下睡得很香。
我把这窝狗养在房里,给小狗起名叫小蘑菇。看着它肚子吃得鼓鼓的能到处乱跑,便觉自己没那么孤单了。
可夏元娘因为那日淋了雨染了风寒躺在床上好多天。
我悄悄去看她,听见她叫廖菁跟我赔罪。
“你爹说得对,穆槿她只是个孩子,我们对她好不是因为觉得亏欠,而是因为感激……阿娘哭是因为把她当成家人,你看到家人伤心难过你会怎么做?你好好想想,若是你跟蓉姐去了外人家里做客,她跟你哭着说想娘了,你会对她拍桌子瞪眼睛骂她不懂事么?”
廖菁垂下头什么都没说。
夏元娘病好以后,廖谦又接着出发了,临走时我也去送他,不过我没有跟着她们一起而是躲在大门后面偷偷看他上了马车。
他对我很好,特意请了女先生在家叫我念书,每日还会问我功课,嘱我随时可以去书房打扰他。
他还请了师傅教我练剑,更是让管家教我看账。
廖谦说自己无子继承家业,但他觉得我可以。
我觉得他还会有儿子的,毕竟他还不到三十岁。可是有人等不及,这人就是廖谦他娘刘氏。
刘氏原本并不住廖府,她跟大儿子廖县令住一起。
可是廖县令三年任满调任,这次要去岭南。岭南湿热路途遥远且多瘴气,廖县令便把刘氏送了过来。
她来的第一天就请了大夫来给夏元娘看诊。
“虽说我已经有了长子长孙,可是谦儿家大业大怎么说也得有个儿子继承家业才是。你嫁过来十几年了,又不肯替他纳妾,谦儿整日在外奔波,一年回不来几日。”
“若是明年开春前你还怀不上,那我老婆子就要做主纳上两房姨娘好叫我儿后继有人……”
刘氏还夺了夏元娘的掌家权,说是叫她好好将养身子早日生个儿子。
夏元娘好歹也是当家主母,刘氏一来就下了她脸面,把她架空,还逼她生子,搞得府里就连下人都敢怠慢她。
4
那天我肚子饿想去厨房要碗面,还没进去就听见哭声。
廖菁抱着廖蓉站在院子里,对面的婆子叉着腰,“燕窝是要留给老夫人的,夫人要吃自去找老夫人要去,为难我们这些下人做什么。”
夏元娘身子不好,从我进府就知道她每日要吃一碗燕窝,没想到刘氏竟把这个也给停了。
“我娘虽然现在不管家了,但她也是主子,吃穿用度没有我爹的话谁说的也不行!”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这些欺下媚上的东西们背地里是怎么编排议论我娘的,告诉你,今个儿你就是没有燕窝也得给我现买去,我就守在这儿等着。拿不出来你就给我卷铺盖走人!”
“搁这儿吓唬谁呢,有本事你去找老夫人闹去,或者生个哥儿出来,别说燕窝了就是灵芝也能做。”
廖菁气得浑身都在抖,怀里的廖蓉哭得更厉害。
我卷起袖子走过去直接甩了个巴掌在那婆子脸上。啪的一声脆响,惊得廖蓉立刻止了哭。
“干爹临走许我看账,你刚才既说连灵芝都有那我便要拿了账本去库房里对对,若是有灵芝便罢,若是没有,便治你个信口胡诌欺瞒主子的罪。”
这婆子是跟着刘氏过来的,没刘氏授意她绝不敢这么跟主子说话。
刘氏料定夏元娘不会因为一碗燕窝去跟她这个婆婆撕破脸,只能忍气吞下,而孩子是小辈,更不敢去找祖母分辨。
刘氏借一碗燕窝让整个廖府下人都看清风向,日后随便什么人便都能欺负夏元娘。气死了夏元娘,刘氏便能稳坐主母位置,替长子长孙多捞些油水。
我原本以为刘氏只是想替廖谦纳妾延续香火,没想到账本上越来越多的账目对不上,我便意识到刘氏来府的目的并不是要个孙子那么简单。
听见我要进库房那婆子立刻就慌了。
赶紧进屋拿了碗燕窝捧着递给廖菁,“奴才记错了,燕窝是有的。”
“只今日有还是日日有?”
我挡住廖蓉伸过来的小手,沉着脸问。
那婆子犯了难,一时支吾着说不出。
我冷笑一声,指着她嗓门洪亮:“干爹说廖府最看重规矩二字,不论是御下还是治家,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你今日先是顶撞了主子后又欺瞒胡沁,我这就修书一封与干爹,看看是找人牙子发卖了你还是打上四十板子丢出府去。”
廖菁也听出来我这话是说给刘氏听的,她管家本就没经过廖谦同意,如今又擅自停了儿媳份例,还偷拿钱财贴补长子,这若是传扬出去别说她的脸不要了,就连那位远在岭南的廖县令也怕要被人参一本不修私德。
“日日有,日日有……”
婆子扑通跪地,一边抽着自己嘴巴一边磕头赔罪。
半个时辰后,厨房换回了从前的管事嬷嬷。
过了没两天,我房里多了一窝小兔子。
我知道是廖菁送给我的。
我没要,给她还了回去。
“兔子吃草太臭,我已经养了小蘑菇……”
小蘑菇已经能屁颠屁颠跟在我身后了,我到哪儿它就跟到哪儿,吃饱就爱窝在我腿上睡大觉。
廖蓉很喜欢小蘑菇,问我能不能借她玩会儿,我本想说不行,可是廖蓉一把抱住我大腿,哈喇子都滴我裤子上了。
她很高兴,抱着小蘑菇咯咯地笑,又亲又蹭占了一身狗毛。
晚上,廖蓉起了高热,身上红红的疹子一片连着一片,叫人看了直起鸡皮疙瘩。而且,她小脸还憋得通红,呼吸特别沉重。
5
大夫瞧了半天看不出是什么毛病,我抱着小蘑菇凑上来,他顿时眼睛一亮。
“狗毛,二小姐是狗毛过敏……”
几针下去廖蓉终于呼吸平缓,脸色也逐渐恢复如常,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我抱着小蘑菇悄悄退出来却被赶来的刘氏一把拦着,“杀了这只狗,日后再有人赶在府中养狗也一并打死丢出去。”
我盯着她牙咬得咯咯响。
夏元娘护我,说我也不是有心的,从前府里也养狗,并不曾见廖蓉发作。
“是啊,我跟妹妹一直都养着一窝兔子,也没见她对兔毛过敏……”
刘氏眼睛一瞪沉下脸,“怎么?你们一个个的都要忤逆尊长不成?为了只畜生竟然连亲人的命都不顾了吗?”
我抱着小蘑菇心想着大不了我就回家去不在廖家待了,也不能叫刘氏杀了它。手就摸到滑滑的粉末,就像是滑石粉。
我低头一闻,它身上果然有滑石粉的味道。
我记得夏元娘说过,廖蓉对这东西过敏,府里绝不会有这类东西。
我赶紧把狗抱给大夫,他摸了摸又闻了闻,转过身又替廖蓉把了脉,“确实,滑石粉为利水渗湿药,古书上有记载有人会对其过敏。”
“可是府上早已明确禁止这东西,偏巧这东西竟出现在狗身上而非兔子身上……”
我看向刘氏,“不如就请老夫人搜一搜我房里,看看是不是我有心要害蓉姐?”
她既然有心要栽赃我,那必然还会有后招,我猜滑石粉一定被藏在我房里某个地方。
我话还没说完,廖菁就捏着一个小白瓷瓶跑了进来,“阿娘找到了,在穆槿衣柜里,女儿这几日都跟她同吃同睡,不曾见她身上痒要用这东西,一定是有人要陷害她故意抹在狗身上。”
“穆槿是我女儿,若是有谁要栽赃陷害她我第一个不容。”
夏元娘走过来,揽着我肩膀,廖菁也紧紧牵着我手,她俩一左一右夹着我,温热的体温通过轻薄的布料传过来,热乎乎的。
刘氏撂下一句出了事你们可别后悔就气哄哄走了。
我跟廖菁给小蘑菇洗澡的时候,我问她为何会相信我。
“你前几日刚替娘出头就出了事,自然是我祖母要收拾你。”
“那你就没想过我会恨你们,会害了你们?”
“想过,”廖菁放下手里的毛巾抬头看向我,“可我若把你当成亲姐妹便不会这么想了。”
我是廖家唯一的外人,出了事自然第一个会想到是我干的。刘氏便是利用了这事。
但她没料到夏元娘廖菁把我当作亲人,亲人间是不会疑心的。
我没说话,垂下头给小蘑菇搓洗,夏日空气湿热让人胸口觉得发闷。
转天我把账册上所有对不上的地方抄录了一遍,给廖谦去了封信。
信刚寄出没几日,县衙竟然来人请我去。
夏元娘正绣花,听见管家回禀一失神被针戳破了指头,沁出一滴血珠落在正绣的木槿花上,淡粉的花瓣染成了红色。
廖菁不放心,非要跟我一起去。
6
县衙后堂我见到了裴县令,没想到他竟调来了江州。
他新来上任,县里的耆老请他宣化民风,他便想到了我。让我讲一讲我爹舍己为人救下廖谦的全程。
我其实是不愿意再回忆的。
但是裴县令帮我安葬了父母,今日又同着这么多人,我不好驳他面子,何况他也是好心。
我一开口眼泪就跟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止不住,“那日正是我娘生辰……”
裴县令眼圈红了,他打断我的话,“抱歉了各位,是在下想得不周,穆槿小小年纪失怙,我实在不该逼她再回忆一遍。”
我摇头,“让我讲完。”
我爹舍己救人是大义,我该让他的事迹广为传扬。
我一口气哽咽着讲完,廖菁已经哭成泪人,堂上众人也纷纷抹眼泪,许久,一片沉默中有位老人拄着拐杖颤巍巍站起身朝我鞠了个躬。
“如此高义实乃吾辈之楷模,老朽提议为穆壮士及家人建一座祠堂。”
“应该的,应该的。”
“还要请穆小姐进县学读书,她读书习字才好将其父事迹传颂下去。”
“对对,我出钱给穆壮士立传。”
“那我出钱资助穆小姐读书。”
“那我便给穆小姐备份丰厚的嫁妆……”
裴县令也没料到众人反应如此强烈,他赶紧叫书记一一记下,替我挨个谢过,又亲自送走每个人。
这些人回去后在各自家族祠堂里训诫族人口口相传,很快,我爹的事迹就传遍江州。
我成了忠义之士的遗孤,得到了所有人的尊重跟照顾。
众人筹资在并州老家盖了祠堂,还筹集了一百两悬赏山匪人头。
之前裴墨发了海捕文书倒贴二十两银子悬赏,可是山匪一回山就如同泥牛入海,县衙兵力有限不可能入山剿匪,这事便不了了之了。
“我来江州的时候交代了继任的县令,若有动静会立刻来告。”
裴墨从袖里掏出本账册,“这是江州各家商户及耆老里正自发捐募的钱款,一共一百二十两……”
来县衙一趟回忆自家被灭门经过竟能有这么大的反应和收获,我始料未及。
“嗯,应该是一百五十八两,若是再算上城郊那片水田跟城东的宅子,折合……”我在心里估算了下价,“大约有不到四百两,三百八十两吧。”
城郊水田不算上好,但近几年收成不赖。
城东宅子一进三间外加一个院子跟柴房、灶间,虽然临街但是后门通河交通方便,按照那坊市今年春日成交的一间规格类似的宅院价格估算,二百两绰绰有余。
裴墨俯视着我,随即嘴角扬起,“想来日后你定能立足这世间,我也能安心了。”
我揣好账册,告诉裴墨自己在廖家这一个来月学到的东西,“我想等干爹回来跟着他一起走南闯北学经商,熟悉风土人情,日后还是要继承我爹衣钵,重建镖局。”
他夸我有志向,但又担忧我是个女儿身行走江湖多有不便。
我摆手,“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
裴墨伸手摸摸我脑袋,“木兰,穆槿,愿你朝开永不落。”
7
有了裴墨撑腰,刘氏收敛很多。
我转去了县学读书,成了那里第一个女学生。
先生很照顾我,同窗也多敬让,我学得很快,除了毛笔字写得不大好看,其他功课都跟得上,尤其是算学,表现得尤为突出。
八月里黄河决堤,无数灾民南下。江州也来了不少灾民。
我找到裴墨,把之前募捐的一百五十八两银子全部拿出来赈济灾民。
“开粥棚只能赈济一时,我想开间布坊,租给灾民纺纱织布的机器跟原料,成品卖给商户,他们挣了钱抽出三分抵扣租金,还清租金机器便是他们的,挣的钱都是自己的。”
裴墨眼睛一亮,提笔写下我这法子上报朝廷,很快得到批复在整个江州先行实验。
夏元娘也很支持我,她拿出自己的体己银子买了各色绣线免费发给灾民,有手巧的在布匹上绣了宝相花、云海纹样拿到布庄一匹布能卖翻倍。
裴墨也拿出府衙的钱贷给灾民在山上种果树,山下种菜。江南气候好,等再过两三个月便会有一波收成,灾民们口袋里有了钱度过今年寒冬不成问题。
八月十五的时候,黄河堤坝得到加固,很多灾民北迁回了故地,但江州的灾民大多选择留下。
果树发了芽,菜园子绿油油,卖布挣的钱足够过冬。
江州这次实验很成功,朝廷决定推广到全国。
裴墨亲手把一百五十八两还给我,还多了把匕首。
“留着防身。”
我笑,“有裴大人给我撑腰哪个敢欺负我?”
他又摸我头,“那便留着做嫁妆。”
中秋节前廖谦终于归家,还带回来好多缫丝。
正好因为水灾我们笼络了一群手艺不错的灾民,这些丝抵押给他们纺绸不仅省了雇工的钱,织出布匹的质量也有保障。
特别是夏元娘当初免费资助的那些巧手的绣娘,她们都愿意来廖家帮工,开不开工钱都无所谓,她们只想报恩。
廖谦跟夏元娘又商量着要开间成衣坊,夫妻间恩爱互助羡煞旁人。
刘氏塞给廖谦好几个小妾,可要么被他配给府里没成亲的下人,要么送进夏元娘房里成了侍女,气得刘氏砸了不少茶盏。
中秋廖府办宴,还特意请了裴墨,他给我跟廖菁、廖蓉都带了礼物,给她俩的是小猫跟磨喝乐,给我的却是毛笔。
我不大乐意,“大人是讥笑我字写的丑么?”
他一愣,随即反应过来,“对对,夫子跟我说你门门功课都很好,唯独这字实在是需要多多练习啊……”
“又不考状元,”我气得把笔塞给他,“本来这次还要邀请大人入股,现在想想还是算了。”
廖谦听见,笑着看过来问我想开店?
我看了眼夏元娘,她冲我点点头。
我深吸一口气,说出了我的想法。
“我想开一家兽舍。”
我老家在北方,来江州我才发现这边很多人家把猫、狗当玩物豢养,还舍得给它们花银子购置食物、笼舍跟玩具。
这若是做成生意必然会大赚一笔。
我正要喊过蓉姐拿她当示例说明开一家兽舍会吸引多少幼童来花钱,一回头却发现蓉姐不见了。
8
我跑出花厅,到处都找不到廖蓉还有带她的丫鬟,我发现小蘑菇也不见了。我猛然间想起小蘑菇常爱去花园水榭,赶紧追过去。
廖家后花园有一池莲花,中间修了座水榭以桥相连。
水榭上的红灯笼倒映在水面上,我看清蓉姐正蹲在水池边逗弄着小蘑菇,身边没有一个下人。
我赶紧跑过去一把抱起蓉姐,“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裴大人送了小猫给你……”
“小狸奴么?哈哈,太好了,小蘑菇有伴儿了……”
她搂着我脖子咯咯笑,丝毫不知道若是再往前半步或是脚底一滑便会跌入莲池,永远沉在里面。
等我们回到花厅,看蓉姐的丫鬟敏儿才急匆匆跑过来,说自己刚刚不舒服叫其他人看着孩子。
我没说话也没把蓉姐给她,整场宴席我都一直把蓉姐抱在腿上,直到她吃饱喝足要跟小猫去玩儿,我才把她交给廖菁。
廖谦继续问我兽舍的事,我心情烦闷,掏出提前写好的计划书给他看,裴墨凑过来,看着看着眼睛都冒光。
廖谦也点头,夸我写得详细,“过完年穆槿便跟我去经商吧,爹觉得你是个好苗子。”
我送裴墨出府的时候他掏出一个十两的银锭给我,“这是我的本金,等着你分红给我哦。”
我心里只顾想着廖蓉的事,脱口而出,“大人可知前任知县为何会被调去岭南?”
江南富庶,岭南虽物产丰富终究气候炎热路途遥远,廖知县被调去莫非有什么原因。
裴墨一愣,随即也想明白其中关节。
“官场上的事我不是很清楚,不过廖谦是举人出身,听说当年还连中两元,至于他最终为何弃文从商就不得而知了。”
廖谦弃文从商?
那是否与他哥哥有关?为什么刘氏如此偏袒?我明明去信告知了他账目的事,为何他没有反应?任由刘氏把持着廖家钱财用度呢?
我摇摇头,觉得一时间有太多事情想不明白,转身要走。
裴墨拦住我,“若遇难事,随时寻我。”
我心里烦躁,点点头匆匆离去。
等蓉姐睡了,我找到廖菁跟她把晚上的事说了,我叫她不要打草惊蛇,暗地里找个信得过的下人盯住蓉姐身边人,看看她到底想干什么。
我用那一百多两银子做本钱,租了间门面,进了些猫狗还有猫窝狗窝小鱼干肉干,我甚至还准备了小猫小狗穿的衣裳,一连几日都忙着铺子的事准备开业。
哪知,蓉姐出事了。
她跑到后厨去要小鱼干,被热油烫到,幸好之前廖菁叫自己的侍女跟着,这才没伤到要害,只是胳膊烫了一点皮。
夏元娘对待下人一向宽容,她只想罚敏儿半年月俸,但我不同意。
我喊了廖谦来,从怀里掏出一张赌场的票据递给他。
“敏儿哥哥好赌,两个月输了近二百两银子,他只有这一个妹妹,父母早亡,乡下的地早就卖了。敏儿月俸二两银子,就算她不吃不喝也不可能攒够二百两。”
敏儿一听扑通跪倒,不等廖谦拷问自己就都说了。
9
两个月前,刘氏来到廖府,买通了敏儿,叫她在照顾蓉姐的时候不那么用心。
“老夫人跟前的嬷嬷说小孩子调皮,难免会出点什么意外……”
“到时候蓉姐出了事,干娘身子弱本就受不住,说不定就一病不起,廖府便再没人能跟老夫人抗衡。我本就是个外人,到时候随便把我打发了或者使计陷害我,府里便再没人监督着账目,任由她把府里东西都搬空了给您哥哥……”
前头我拦着刘氏,后面又有裴墨给我撑腰,她无计可施,便想到了这么一条毒计。
手心手背都是肉,曾经我想不明白刘氏为什么会偏心大儿子。后来我问了廖菁才知道。
廖谦本来也是能考中进士为官的,可是那年北方戎国犯边,皇帝不仅不敢开战还杀了戍边的大将求和。
廖谦对皇帝很失望,觉得自己没必要“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遂弃文从商,选了士农工商最末一等。
但刘氏认为当官可以光宗耀祖,兄弟之间还能互相帮衬,她认为商人低贱,一直对小儿子的决定耿耿于怀。这次大儿子被放逐到岭南,她心中的恨意无处发泄,才有了那些举动。
我在府里找不到线索,只能借开铺子在外面搜罗证据。
廖谦叫人拿来敏儿的身契,撕了。
“欠的赌债我会叫人还上,但从今往后你与廖府再无关系。”
廖谦拿回了管家权,还给夏元娘。
他与刘氏谈了一晚上,转日刘氏搬去了庄子上。
我后来问过裴墨,“你为什么还要做官?这样的皇帝有什么可效忠的?”
“做官不是为了皇帝而是为了百姓。我若不为官,便会有其他人,若这人是个狗官便有一方百姓遭了殃,我虽官小但能护住一方百姓。”
我想想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
“你要是皇帝就好了……”
他吓得赶紧捂我嘴,“我死不要紧,你可还有家人呢。”
是啊,我如今有家人了,不能乱说话了。
“那你呢?你的家人呢?”
跟裴墨相处久了,我才发现自己对他的事一无所知。
“跟你一样,我也是个孤儿。”
“所以你才格外照顾我?”
他看着我,眸光里有亮亮的东西,然后点了点头。
我大手啪的一下拍在他肩上,“放心,我也拿你当家人,我给你养老。”
他呛了一口,好半天才缓过来,“多谢。”
秋去冬来,一转眼入了年关,我惊讶地发现江州没有下雪。而且也没有糖葫芦卖。
夏元娘怀孕了,等到来年夏天廖家便会多一个孩子,我希望那是个男孩。
我经营的兽舍生意也很红火,每天我在县学跟铺子之间来回奔波,时间根本不够用。
廖菁常带廖蓉来铺子帮忙,我发现她很擅长招徕生意,那些客人听她讲完总会买一只猫儿或狗儿,有的还让她帮忙取个名字,再买上些动物粮食回去。
我鼓动她入了股。
廖蓉则是现成的招牌,她抱着狸奴往大堂中间一坐,来来往往的人瞧见她跟猫儿玩得开心的样子就会进来。
我让她也入了股,分红就是小鱼干。
裴墨有时也会来,他会帮我给猫狗喂粮铲屎遛狗还有分装小鱼干跟肉干。
他问我过完年是不是就要跟着廖谦离开江州了。
“放心,我打算把铺子交给廖菁,她会从廖家带个人过来帮忙。”
裴墨眸子一暗,问我最近可还在练剑。
“诶,你送我的匕首可好使呢,护住干爹没问题的,不过你说你个文人怎么会有把剑呢?”
他忽然凑过来压低声音说:“我其实是专门……”
正好街上有人放炮,他说的话我也没听清,后来来了客人买猫,这一打岔我也便忘了再问。
10
嘉熙四年,我在江州跟没血缘的亲人一起过了年。
夏元娘挺着肚子送了我好几方帕子,每个上面都绣了木槿花。
廖谦送我间铺子,正好拿它卖糖葫芦。
廖菁亲手给小蘑菇做了件大红开档棉袄,廖蓉用狸奴的毛弄了个毛球说是狗都爱抛球,可小蘑菇一闻是狸奴的味道,说啥都不去捡。
我没空准备礼物,就学着当地人的样子给他们每人都包了个大红包,大家都很高兴,唯独廖蓉不开心,“能换成小鱼干么?”
我拿着红包去给裴墨拜年。
砖红的炮仗皮铺满街道,踩上去软软的,大红灯笼映着走亲访友人们的笑脸,每个人看着都喜气洋洋。
裴墨说他要回并州处理些遗留的公务,顺便送我回去祭拜父母。
老家的祠堂修得很好也维护得很好,看得出裴墨费心了。
我很感激他,提出要陪他回他老家拜祭他父母。
他很惊讶。
他家在边关,很远的耀州,一去一回至少两个月。
我只好拉着他一同朝北方跪拜磕头,算是拜祭过他父母了。
那天,我俩住在了我家老宅里,裴墨很高兴,跟我讲了很多他小时候的事。
他家很穷,爹妈为了供他读书操劳至死,他考中进士回来才发现他们都已不在人世,陡然生出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凉感,一度觉得自己很不孝。
“那时我整日都活在愧疚里,也不愿去赴任,我对爹娘都没有尽孝,又何谈对百姓对皇帝尽忠尽职呢。”
是他村里的邻居让他改变了想法。
“他们找到我,说我要去做个好官,我爹娘拼了命就是为了能让我做个好官,我不该辜负他们。”
裴墨十八岁为官,很年轻又出身贫寒,他本可以入赘为婿靠着岳丈在朝中拼出一片天地,但他拒绝了。
“官位小有小的好处,我这个人不会那些逢迎之事,偏安一隅造福百姓挺好的……”
我抬头仔细打量他,细长的丹凤眼,白皙面皮,高挺的鼻梁,就是瘦弱了些,按理他若肯当个驸马也是绰绰有余。
他被我看得红了耳根,“你这么瞧着我作甚,我可是你长辈。”
我扑哧笑了,大九岁也叫长辈,你还真指望我给你养老呢。
不过刚刚我都跟他拜过父母了,认他做哥哥倒是可以。
我刚提议他就翻脸了,“不行不行,我是官身,你还有干爹娘,怎么也得问过他们……”
切,瞧不起谁呢,等我挣了大钱也捐个官做做。
北方戎国又蠢蠢欲动,朝廷要凑一大笔钱送过去。可国库被皇帝折腾得空了,他便想了个法子,卖官。
一说到这个,裴墨气得邦的一声把酒杯墩在桌上,“如此儿戏,岂能如此儿戏。”
听说杀我爹娘的山匪拿着杀人放火的钱捐了个武将,打戎国打不过,镇压农民起义倒是杀了不少人。
裴墨越说越气,咕咚咕咚提起酒杯就灌,一壶酒下肚竟然趴桌上睡着了。
我拉不动他,只好给他盖了棉被,躺在他旁边睡着了。
转天天还没大亮,我就闻见一股香味,肉包子跟菜粥的香味。
我恍惚了,以为阿娘回来了,来不及穿鞋就推门跑了出去,一头撞在裴墨怀里。
“是我阿娘回来了么?我闻见她做的早饭味儿了……”
裴墨眼圈红了,一把抱起我往屋里走,“下雪了,你穿这么少出来还光个脚丫冻病了我怎么给廖老爷他们交代?”
我不听,只挣扎着要跑去灶间看看是不是阿娘回来了。
他湿了眼角,告诉我是他见我昨晚上没睡好早起给我做的早饭。
“许是你梦见爹娘了,喊了他们一晚上……怪我,不该带你回来,哪怕找家客栈也好。”
我再也忍不住,扑到他怀里大哭。
我以为自己释怀了,其实并没有。
11
出了正月我跟着廖谦出发。
一家人都来送我们。
“学什么不重要,累了就赶紧回来。”
“姐姐记得给蓉儿带只小狐狸回来,要白色的哦。”
“你那铺子二楼空着也是空着,我打算收拾出来叫客人随意摸猫狗,一个时辰十个铜板,若是看上哪个便直接买回去……”
我带了小蘑菇随行,走到城门口时裴墨提着个笼子气喘吁吁追上来。
“这鸽子能千里传书……记得给我写信……路上注意安全。”
我接过鸽子拍拍腰间的匕首,“放心吧放心,春暖花开我们就回来了。”
裴墨眼尾红了,他站在城门口默默注视着我们的马车,直到成了个小黑点消失在视野里。
廖谦问我是否在并州定亲。
“没有啊,干爹为啥这么问?”
“过完年你也十三了,该是考虑的年纪了,你觉得裴大人如何啊?”
我一口气差点儿没上来,脸憋得通红。
“他是长辈啊,不不,我一直拿他当大哥……”
廖谦不说话只是笑,还摇头晃脑地说什么当局者迷,不识庐山真面目什么的。
我恼了,拿出地图来看,这一路我们要北上出关去戎国买上好的皮货跟马匹再南下京城卖掉,粗略一算要走四千多里路。
等我们回去夏元娘都生了。
越往北走越冷,官道上的人也越少。
我看我们这一路的行程途经耀州便问廖谦能不能顺道去看看裴墨父母。
“应该的。”
裴墨家的老房子还在,不过年久失修,房顶都漏了,土垒成的墙壁也塌了,院子里的荒草比我还高。
廖谦付了村里人银子叫他们帮着修缮房子,说等我们回程再来。
戎国刚收了我朝的岁贡,此刻边关安宁得很。我们收货交易十分顺利,空出来的时间廖谦亲自带我去了草原,从戎国人手里买了只雪白的小狐狸。
不过这东西骚气得很,虽然很怕小蘑菇可成天都惦记着笼子里那只鸽子。
廖谦说我就是那只鸽子,裴墨就是那只骚气的狐狸。
胡说,我明明是小蘑菇。
我们从戎国出来已经是四月下了,裴墨的老房子修好了,用红砖新砌的房子结实又好看,我给他写了信,还画了一幅老房子的画。
一路南下进了京城,廖谦带我去看了几间铺子,还同掌柜伙计们介绍了我。
“这是我大丫头槿姐,虚岁十五了,再过几年这京城的生意就交给她打理了。”
我大惊。
京城一家铺子少说得值个上千两,廖谦这就要交给我了?!
廖谦说着就叫人拿出张羊皮,负手站在一旁听老掌柜给我讲如何挑选如何储存,京城里近几年价格销路又是如何。
我听着,一一用心记下,末了拿了账本来看。
“去年价格高其他商户必然会大量购进,供大于求价格也自然会降下来,我们可以找巧手的绣娘做成成衣等到来年最冷的时候卖给要北上出关的客人。”
老掌柜听了频频点头,廖谦则大笑,“我没说错吧,这孩子无师自通,天生就是做买卖的好料。”
我们在京城修整了几日,我用自己挣的钱给一家人买了礼物,还给裴墨买了根束发的白玉簪子。
归心似箭,我们选了水路回去,走大运河,再有半个月便能抵达江州。
六月的夏夜有些闷热,我写完给裴墨的最后一封信跑到船板上透气,远远地瞧见有一艘小船正往我们这艘大船上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