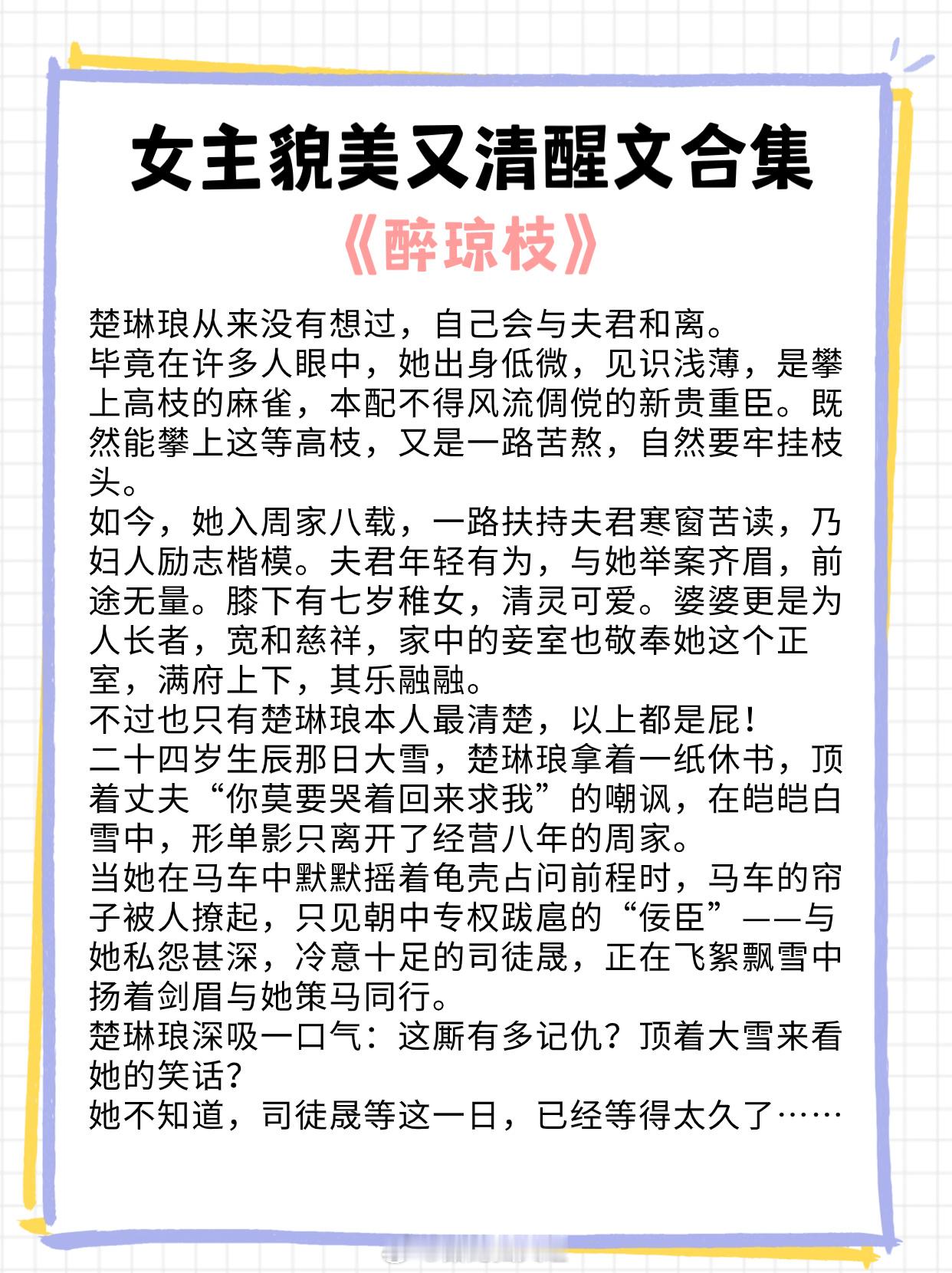文案:
顾景阳十六岁出家,做了道士。三十二岁承嗣,做了皇帝。三十六岁遇见谢华琅,还俗,娶了她。
我道自己六根清净,直到遇见我的枝枝。她坏了我的道心,也乱了我的情肠。
枝枝说:陛下他总是假正经,明明就是喜欢我,嘴上却不肯认

片段:缱绻而温柔的吻结束,他们仍旧彼此相拥。“枝枝。”顾景阳在她耳畔低声道:“你是故意的。”
谢华琅莞尔一笑,道:“就是故意的,怎么啦?”
顾景阳同她略微拉开一点距离,环住她腰身,垂眼看她。
他素来雅正,连语气都是敛和的,然而到了此刻,神情中居然有了几分咬牙切齿的意味:“你还知道回来!”
“道长,其实我可想你了,一点也不比你想我少。”
谢华琅轻摇他手臂,道:“可你呢?明明心里在乎我,惦记我,嘴上却什么不肯说,跟苦瓜成精似的,成日里板着脸,我可受不了。”
顾景阳又好气又好笑,抬手掐住她下颌,道:“你说谁苦瓜成精?”
“谁成天板着脸装正经,那我就说谁,”谢华琅才不怕他,眼波微荡,似喜似嗔:“道长,我可不惯你这些毛病,以后要是再这样,我再不来找你了。”
顾景阳目光含笑,丰神如玉,轻轻道:“你敢。”
“你看我敢不敢。”谢华琅理直气壮道:“我心里中意你,巴巴的往这儿跑,你会看不出来?我从小到大,什么都吃,就是不吃亏,喜欢你三分,你起码得还我六分,这才叫礼尚往来。”
“枝枝,”顾景阳失笑道:“你这叫高利贷,不叫礼尚往来。”
谢华琅抬眼看他,语气娇蛮:“有本事你别贷呀。”
顾景阳目光柔和,垂首到她耳边去,轻轻道:“没本事,甘拜下风。”“道长,我当你是木头脑袋,永远都不知道开窍呢。”
谢华琅听得莞尔,明媚流转间,顾盼神飞,伸臂搂住他脖颈,撒娇道:“拿了我的耳铛,可就是我的人了。”
“哪有你这么霸道的?”顾景阳道:“你去买一盒点心,连摆点心的案台,带做点心的锅,统统都要带走吗?”
“不止呢,”谢华琅气势汹汹道:“做点心的厨娘我都要带走。”
她还正当年少,尚是最鲜艳夺目的时候,一腔孤勇,尽数交付,这样的情意,怎么会有人不动容?
顾景阳定定看她半晌,终于低头,轻轻亲吻她的唇。
“好,”他温柔道:“都是你的。”
谢华琅坐在栏杆上,笑盈盈的看着他,忽然开口,语气中有些娇嗔的埋怨:“道长,都怪你,我好容易摘的花,现在都掉了。
顾景阳微觉怔神,低头去看,才见她方才捏在手中赏玩的那朵茉莉已经落到了地上,便含笑道:“我再去为你摘一朵便是。
谢华琅抬腿,轻轻踢他一下,娇声催促:“那还不快去。
那几株茉莉极其繁密,枝叶繁茂,洁白的花朵点缀在绿叶之间,人近前去,便嗅得清香扑鼻。
顾景阳抬头细望,摘下一朵半开的茉莉,返身回去,簪在了她发间。谢华琅抬手轻抚,低问道:“好不好看?”
她原就生的美,往日里喜着艳色,更加华美绝丽,今日淡妆素衣,却令人觉得清新雅致,颇有些清水出芙蓉的意味在,同那朵茉莉花也极相衬。
顾景阳垂首看了半晌,却没说好看与否,只低声道“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这句诗的前边,其实还有两句。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至于他所说的那两句,却是洞房花烛之后,翌日清晨,新妇起身梳妆之后,问夫婿妆面如何。
“道长,你学坏了,”谢华琅歪着头看他,轻笑道:“换了以前的你,才不会说这种话。”
顾景阳却定了心,握住她手,低柔道:“枝枝,我还俗娶你,可好?”
谢华琅抬眼看他,轻轻道:“你说真的?”
顾景阳专注的望着她:“我从来不骗谢华琅垂下眼睫,少见的有些羞赧,唇边弯起的弧度,却暴露了她此刻心绪。
伸臂揽住他脖颈,她低声道:“九郎抱我进去,别在这儿说。”顾景阳亦是轻笑,将她拦腰抱起,转身进了观中。
衡嘉先前被打发走,自然知道陛下是哪儿不高兴了。
说到底,不过是气谢家女郎往扬州去玩儿,却不吭声,即便回来,带给他的礼物也不是独一份罢了。
他往房中去,将那礼盒搁下,再回后堂,却不见陛下人影,在周遭转了几圈,正待往前边去寻,却见陛下怀中抱着谢家女郎,神态缱绻,迎面而来。
衡嘉心中既惊讶,又觉理所应当,忙不迭低下头,不敢再看,见陛下一路进了后堂,极有眼色的上前,将房门掩上了。
顾景阳抱着怀中人落座,却没有松开的意思,反倒将她抱得更紧。惯来端肃自持的人,倘若真遇上了乱心之人,将那阀门打开,情绪倾泻而出此怕也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或许他的枝枝,便是命中注定来降服他的那个人。
“枝枝,”顾景阳低声问道:“做我的妻子,好不好?”
谢华琅伏在他怀里,手指有一搭没一搭的抚弄他胡须,闻声抬眼,望向他明亮的眸子,低声道:“九郎,你知道我的身份吗?”
顾景阳道:“知道。”
“那你得先等等,”谢华琅仔细思忖后,道:“我要先同阿娘通个气,再去同我阿爹说。”
顾景阳道:“不需要那么麻烦。”
“要的。”谢华琅认真道:“我不想叫他们伤心,我们的事于他们而言,也有些突然,所以有些事情,得先铺垫着说了才行。”
“好,”顾景阳心中明了,笑道:“只要你高兴。”谢华琅见他应得这样痛快,再思及他此前那副闷葫芦模样,颇有些拨开云雾见青天:“这趟扬州,去的真是值了。”
望着他清冷俊秀的面庞,她越看越爱,凑过去重重亲了一口,又道:“道长,你家中还有什么亲誉?”
顾景阳搂住她,轻轻道:“我是长子,底下还有弟妹,不过都已经成家了。”
“是吗,”谢华琅点点头,又道:“高堂呢?”
顾景阳道:“父亲早已过世,母亲体弱,一直静卧养病。”
谢华琅听得有些奇怪,顿了顿,方才道:“既然是长子,便该承继家业,怎么会出家呢?”
这便要从太宗时期,说到先帝时期,乃至于皇族之中的种种纠葛了。顾景阳一时之间,却不知该从何说起,沉吟片刻,道:“这便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了……...”
谢华琅见他如此,倒是有些难处,不必开口,倒没有继续追问,伸手过去,手指掩住他唇:“好了,你若为难,便不必讲了。
顾景阳定定望着她,忽然道:“枝枝,你不怕吗?”
谢华琅道:“怕什么?”
“母亲卧病,我却出家在此,未免有些奇怪,”顾景阳低声道:“这样一个人,值得你委身相事吗?”
“我不知道你家中发生过什么,就没办法妄下决断,我所得出的结论,皆是我双眼所见,双耳所听,”谢华琅平视着他,坦然道:“我见到的九郎,是皎皎君子,风光霁月。”
她第一次见他,便同他说了自己名讳,他若有意,必然能知道自己是谁,倘若真有攀附之心,何必屡屡退避?
自己略微说了句露骨些的话,他居然脸红了,每每举止亲近,也会有礼的避开,唯恐被人觉得轻浮失仪。品性端方,雅正至此,她又何必相疑?顾景阳久久的望着她,到最后,忽然笑了。
他伸手去勾了勾她鼻梁,低叹道:“真是在劫难逃。”
谢华琅哼道:“那也是桃花劫。”
顾景阳闻言失笑,抱紧了她,却未曾言语,谢华琅伏在他怀里,抬手轻抚他面颊,这一室的安谧之中,竟生出几分天长地久的静好意味来。
门虽合着,窗扉却半开,扑簌簌的声响传来,却是先前那只牡丹鹦鹉飞来了。
月余不见,它竟还认得谢华琅,振翅飞到她肩头上落下,又一次哑声道:“好漂亮!嘎,好漂亮!”
顾景阳瞥它一眼,道:“走开。”那牡丹鹦鹉扭头看他,脖颈灵巧的弯了一弯,在翅膀上啄了啄,叫道:“走开,嘎,走开!”
谢华琅忍俊不禁,伸手摸了摸这只漂亮至极的鹦鹉,道:“它叫什么名字?”
顾景阳道:“它叫鹦鹉。”
谢华琅笑的花枝乱颤:“我说真的,九郎别闹。”
顾景阳扶住她肩,道:“没给它起名字,一直就叫鹦鹉。”
他们说话的时候,那只牡丹鹦鹉黑亮如豆的眼珠便在乱转,忽然一探头,叼起谢华琅发间那朵茉莉,振翅飞走了。
“哎!”谢华琅赶忙坐直身,唤道:“那个不能拿!”
那牡丹鹦鹉却没理她,也没回头,她闷闷的歪回去,抱怨道:“你看它。”
顾景阳道:“晚上不给它东西吃。”“算啦,”谢华琅倒不至于同一只鹦鹉斤斤计较,含笑道:“待会儿你再给我摘一朵便是。”
顾景阳应道:“好。”
内室中那架瑶琴仍摆放原地,谢华琅抬眼瞥见,忽然想起此前二人合奏之事来。
“道长,”她直起身,道:“我们再合奏一曲吧。”
顾景阳侧目望她,道:“好。”
谢华琅抚琴,顾景阳弄箫,目光交聚,不需要言谈,便心领神会,琴声婉转,箫声悠扬,相辅相成,珠联璧合。
衡嘉守在室外,不觉听得入神,禁军统领武宁不知何时来了,低声问道:“听说谢家女郎来了?”
衡嘉低声道:“若非如此,陛下哪有这样好的兴致?”
武宁是武将,对乐理不甚了解,听了半晌,不明就里道:“合奏的是什么?”
“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长相思兮长相忆,短相思兮无穷极。”衡嘉答道:“是长相思。”陛下近来心情转好,连月来为此战战兢兢的朝臣们,总算是松了口气。天威难测,倘若君主阴晴不定,朝臣们的日子也难过。
昔年郑后当政时,曾以种种缘由,扑杀重臣逾十人,宗亲更是数不胜数,前车之鉴,难怪他们为此提心吊胆。
谢允官居门下省给事中,掌驳正政令,校订功过,正逢门下省将去岁官员迁贬诸事统计出来,因为此事原就由他主理,侍中裴凛便令他将这份奏表送往太极殿去,倘若皇帝垂询,也可应答。谢允自无不应。
衡嘉往偏殿去沏茶,捧着往前殿去时,正遇上身着绯袍,丰神俊朗的谢家长子,停下脚步,笑问道:“给事中安?”
谢允同他向来没有交际,毕竟宰辅之子结交内侍,无疑会惹人猜忌,见衡嘉如此,倒不失礼,向他颔首,道:“内侍监。”衡嘉与他并肩而行,又道:“给事中是来拜见陛下的吗?”
谢允轻轻应了声“是”。
朝臣不好结交内侍,内侍其实也一样,故而衡嘉只问了那一句,便停了口,到前殿门前去时,方才道:“给事中稍待,奴婢先去通传。”
谢允客气道:“有劳。”
顾景阳端坐椅上,正翻阅案上奏疏,便见衡嘉上前奉茶,道:“陛下,门下省给事中谢允求见。”
顾景阳手中御笔一停,道:“他怎么来了?”
有郎官在侧,闻言恭声提醒:“陛下,去岁天下五品以上官员迁贬诸事统计,便是交由谢给事中负责的。”“原来如此。”顾景阳将笔搁下,道:
“宣他进来吧。”
谢允还很年轻,丰神俊朗,气度敛和,更多是肖似谢偃,而枝枝鲜艳娇妩,俏皮灵动,面容则更像母亲,可即便如此,仍旧能从眉眼之中,察觉出他们兄妹二人的相似之处。
顾景阳的神情不觉柔和了些,内侍呈上奏表,他翻开细阅,轻轻道:“坐吧。”
谢允应声,另有内侍搬了矮凳来,他便垂眼落座,静待皇帝垂问。
奏表很长,有数十页之多,顾景阳静静翻阅,内殿中自然无人做声,唯有纸张翻起的声音,不时响起。
现下正是五月,天气已经有些热了,内殿的窗扇洞开,有和风伴着鸟鸣声,依稀传入耳中,谢允坐的久了,再听殿外鸟鸣声,下意识侧目往窗外看,再回过头时,目光扫过东侧架上摆放的那柄剑时,眸光一颤,忽然顿住了。
那柄剑名唤太阿,乃是皇帝随身的天子剑。
谢允先前也曾在皇帝身边做过郎官,后来才调任门下省,自然识得这柄剑,只是那时候,剑柄上尚且没有现在佩的这枚玉坠。
他打量了几眼,总觉得这枚玉坠有些眼熟。
...倒像是枝枝几年前过生辰时,外祖父专程送的那枚,连玉坠下的穗子都一模一样。
若只是玉坠,相似也便罢了,可连底下穗子都一样,便由不得人不多想了枝枝的玉坠,怎么会在陛下这儿,还被佩到太阿剑上了?难道……..
饶是谢允素来端和,骤然发现此事,也是心中骇然,面上变色。顾景阳将那奏表翻了大半,方才停下,唤道:“谢卿。”
谢允心中惊骇,尚未回神,一时竟未应答,郎官微觉诧异,低声提醒道:“给事中,给事中?”
谢允回过神来,便见皇帝正垂眼望着自己,背上生汗,心中凛然,忙道:“臣在。”
顾景阳见他盯着那权玉坠出神,也能猜度几分,淡淡一笑,道:“朕有些不明之处,要你细讲。”
谢允道:“陛下请问。”
这一问一答,几番往复,便是大半个时辰过去,谢允应对自如,心中却愈发躁动不安,见皇帝不再问了,方才松一口气,低头饮茶。
陛下与枝枝,当真是那种关系吗?怎么也不曾听她提过?
淑嘉是陛下嫡亲外甥女,倘若他们成了,自己岂不是要管妹妹叫舅母?还有,上月枝枝往扬州去玩,而陛下作色,也是自上月开始,难道竟同枝枝有关?对了,几位宰辅之中,似乎只有阿爹没被陛下训斥…….
谢允心中乱糟糟的,似喜似忧,五味俱全。
顾景阳将奏表细细翻阅完,已经临近午膳时分,便打发郎官们退下,又勉励谢允几句。
后者满心复杂,却听不进耳中,犹疑片刻,终于踌躇道:“陛下请恕臣冒味…….”
顾景阳淡淡道:“怎么?”
“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讲: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
谢允道:“臣先前曾为陛下郎官,也曾见过太阿剑,可那时候,上边似乎还不见珠饰,陛下说不必为外物所束缚,如今怎“是心上人送的。”顾景阳微露笑意,神态轻和:“朕若不佩,她见了,要发脾气的。”
二房里的谢莹即将出嫁,谢华琅同这堂姐感情深厚,又因她喜爱兰花,便打算亲自绣一张丝帕相赠,这日傍晚,一朵秀逸兰花将将绣完,却听女婢入内回禀,说是郎君来了。
谢府中所说的“郎君”,只有长兄谢允一人,而其余的郎君们,皆会以“二郎”“三郎”相称。
谢华琅听得有些奇怪。
较之庶兄庶姐,她同几个嫡亲兄弟,自然格外亲厚些,然而彼此年岁渐长,总要避讳,唯有最小的弟弟谢玮时不时来找她,上边两个兄长若有话说,多半是在母亲院中,又或者是书房,如今日这般直接过来的,倒很少见。
左右打量一圈,见没什么扎眼的,她方才道:“请哥哥进来吧。”
谢允离开太极殿后,在门下省枯坐了一下午,心神不宁,猜量种种,既忧心胞妹,又忧心谢家来日如何,归府之后,便先往谢华琅院中寻她。
“哥哥怎么过来了?”谢华琅亲自为他斟茶,奇怪道:“可是有事寻我?”
谢允打发女婢退下,再抬眼打量面前美貌鲜艳的幼妹,心中百感交集,半晌,方才道:“枝枝,你十三岁生辰那年,外祖父送你的玉坠哪儿去了?”
谢华琅不意他会这么问,神情微滞,偷眼打量哥哥一眼,试探着道:“我一时也想不起来了。哥哥怎么忽然问起这个来了?’
谢允见她如此神态,便知此事为真,轻叹口气,道:“因为我在别人处见到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