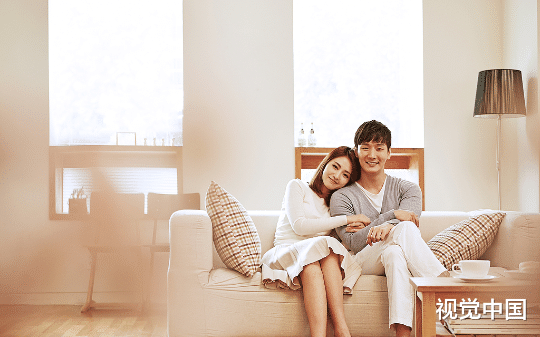《闻春声》
作者:长青长白

简介:
【木讷结巴糙汉VS风情泼辣寡妇】
在媒婆的撺掇下,大姑娘姚春娘带着嫁妆远嫁到了梨水村张家。
怎料成亲当晚,病秧子丈夫便两眼一闭蹬了腿,姚春娘还没醒过神来,一夜间就成了梨水村最年轻的寡妇。
小寡妇隔壁邻居姓齐,齐家上有老下有小,中间一个年轻力壮的结巴撑家,叫齐声。
齐声寡言少语,三天憋不出一句话,平日和姚春娘碰了面,闷头连个招呼都不打。
但时间久了,村里不知怎么渐渐传出闲话,说张家的小寡妇和齐家的结巴搞在一起了。
精彩节选:
正月二十五,早上天刚亮,姚春娘还裹着被子在床上梦周公,隔壁就传来了叮咚咣当的声音。
她一脸怨气地撑坐起身,眯着睁不开的眼从窗角望出去,看见隔壁院坝里的身影后,不情不愿地从床上爬了起来。
她穿上今年才给自己做的厚棉衣,伴随着扰人的刨木声烧开热水洗了把脸,打开大门,把还冒着热气的洗脸水泼在了空荡荡的院子里。
哗啦一声,半盆水浇湿了一大片坝子,多少带着点起床气。
隔壁和她家紧挨着的院坪里,一个正埋头刨木做棺的身高体壮的男人听见这声音,直腰抬头,沉默地看向了她。
那是一张年轻端正的脸,浓眉黑目,在这犄角旮旯的十里八村,长得是一顶一的俊。
这人叫齐声,是个远近闻名的木匠,姚春娘嫁到梨水村前就听过他的名字。
但不是因为他长得好,而是因为他是个结巴。
一个做棺材的结巴。
昨夜下了场不大不小的阴雨,奇冷的天,哈口气都能结团白雾,偏齐声穿得薄,一件黑灰色的薄里子,挡不住半点寒气。
眼下时辰早,天还没亮透,雾蒙蒙的天看着似隔了层暗纱。齐声手里拿着把刨子,臂上袖子挽了几折,人高马大地站在半成型的棺材前,实在有些瘆人。
姚春娘运气不好,嫁过来的当天晚上新婚丈夫就一脚蹬了天,棺材也是齐声帮忙做的。
她还记得那天守灵守了半夜,五更天听见门外传来敲打声,昏头昏脑出门一看,就撞见他大早上蹲在棺材里钉钉子。
姚春娘本就怕鬼,当时天黑,她只模糊看见棺材里一个蹲着的背影,冷不丁吓了一大跳,如同见了鬼,大叫一声猛冲回了门,吓得发了两天的烧。
做法事的八字先生一通算,说她亡夫生怨,她被鬼缠上了身,神神秘秘让她喝了黑乎乎发苦的符水,姚春娘这才退了烧。
如今姚春娘习惯了齐声做棺材,已经不觉得害怕,反倒用力瞪了他一眼,显然是不满他一大早扰了她清梦。
她畏寒,大半张脸都裹在厚棉衣领里,就一双水灵灵的眼露在外面。瞪完她又像是觉得自己不占理,也没说别的,扭头进门忙活去了。
如今她一个人住,要做的事可多着呢。
姚春娘和齐声两家房子建得近,房贴着房,中间一条一尺宽的小沟排水,也没立道篱笆作界,不知道的,还以为两家往上数三辈是亲兄弟。
但实际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
姚春娘是从柳河村嫁过来的梨水村张家,两家为什么把房子比肩建在一起她刚开始也不清楚,后来去河边浣衣,听村里人说两家祖爷那辈当年看上了同一块地,谁也不肯让,这家在中间建墙那家隔日就拆,好似让一寸都是吃了天大的亏,两家置气才把房子建成现在这样。
到了齐声这一辈,与张家隔阂已消,相处还算融洽,隔院墙也就没建。
姚春娘刚嫁过来时还挺高兴,觉得有家离得近的邻居是件好事,遇上什么事儿的话互帮互助来往方便,哪知道隔壁住的是别人口中的齐木匠。
齐声性子闷,平日里见了面一声不吭,做木工时动静却大,吵得很,偏偏挺会做人,弄得姚春娘想骂他两句都觉得自己不占理。
大早上做棺材这事怪不得齐声,一年到头,年前年后是天最寒的时候,今冬又落了场雪,前不久村里接连走了两个老人,两家人都找他做的棺材。
人等着下葬,棺材要得急,他得抓紧时间。
齐声也知道自己做事吵,过年时还送了姚春娘两块肥瘦适中的腊肉和几节灌得饱满的香肠,还是已经熏好了的。
姚春娘本来不爱吃熏腊肠,但齐声家灌的肠咸香味好,冷水入锅煮得半熟,再切成小方肉丁倒热锅里一炒,连油都不用放,红油已经滋滋冒,拌饭好吃得要命。
拿人手短,吃人嘴软。姚春娘收了礼,饱了口福,如今除了蹬他一眼,也不好说什么。
午时,姚春娘给自己包了顿馅满皮薄的饺子,外边的声音总算消停了片刻。
吃完饭收拾了灶台,她抓了两把前天晚上刚炒的南瓜子放衣兜里,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嗑。
她小时身子骨弱,干不得重活,她娘便教会她一门绣花的好手艺,她学得精,以往在家时便常缝制些床被衣裳卖给街上的何记衣铺,补贴家用。
如今成了寡妇,买这要钱,买那要钱,更晓得赚钱之重。年刚过,地里不忙,她便成天到晚地坐在屋里缝厚棉被。
天冷,赶快做好了拿出去,收价也比往常高一些。
针线活废眼,盯久了眼睛酸胀得很,见中午出了太阳,她便晒着暖和的太阳磕了半把南瓜子,没一会儿,脚下就堆了一堆散乱的壳。
院坝里泼的水已经干了,她抬头瞅了眼挡光的檐角,又提着小板凳坐到了坝子中间晒。齐声吃完饭走出门,就看见她坐在那悠哉悠哉嗑瓜子。
她皮肤白皙,暖烘烘的太阳一晒,像头裹了棉服的大白菌菇蹲在那儿。齐声看了一眼就挪开了视线,也没有要打个招呼的意思,走到快完工的棺材前,拿起刨子继续打磨。
顺滑的刨木声响起,姚春娘听见声扭头看他,他还是穿的早上那件衣裳,姚春娘耸肩抖了下,看一眼都觉得冷。
齐声动作利落,握着刨子一推,黄白的刨花一卷卷掉在他脚边,风一吹到处乱飞。
姚春娘瞌睡醒了,起床气消了,也不觉得这声音烦人了。她从兜里掏出一把南瓜子,远远伸手递向他:“齐声,吃炒南瓜子吗?”
齐声手上动作没停,头也不抬,只摇了摇头。
他话少,大多时候能不出声就不出声,背地里姚春娘还听见有人叫他齐哑巴。
姚春娘嫁来张家也才三个月,和齐声拢共没接触过几回,眼下跟他说话见他看都不看自己一眼,才算知道他齐哑巴的别号不算白来。
她把南瓜子揣回兜里,继续一个人慢吞吞地磕,腹诽道:闷葫芦,不吃就不吃。
正月二十六,宜嫁娶,忌出行。
大清早,姚春娘仍是被齐声的木活声吵醒了,她顶着瞌睡爬起来,拖着昏昏欲睡的身体烧水洗脸,再将洗脸水哗一声倒在院坝里,还是气鼓鼓瞪了齐声一眼。
齐声已经习惯,这回连头都没抬,见她起了,默默放下了手里的刨子,改拿了把更吵人的锯子。
午后,姚春娘又抓了两把南瓜子坐在门口悠闲望天,齐声也还是在做别人之前定下的棺材。
昨天那口棺已经做完,傍晚来了几个男人把棺抬走了,今日这一坝子的木料还是刚从山里砍来的杉木,透着一股好闻的新木味。
不过今日和昨日有些不同,今日有人登门拜访,但拜的不是姚春娘的家门,而是齐声。
远远地,还没见着人,姚春娘就听见了李媒婆洪亮高昂的声音。
李媒婆叫李清田,个矮体圆,一脸和蔼的福气相。她奔走各乡邻里,靠一张巧嘴说成了不少男女姻缘,好坏不论,也算声名远播。
姚春娘当初便是由李媒婆搭桥才远嫁给张青山。
柳河村男丁少得奇怪,跟受了咒似的,姚春娘两个叔一个爹,三家七个孩子,就一个带把的儿,姚春娘还是家中独女。她远嫁梨水村就是因柳河村找不到同龄的男人,那些个男人要么年纪大了死了媳妇儿拖着几个嗷嗷待哺的孩子等后娘,要么年纪小得毛都没长齐。
以前姚春娘她爹何成明总觉得自己女儿模样生得好,得好好相看相看,这一相,仅有的几个适龄的小伙子一眨眼就都成了家,剩下姚春娘成了十里八乡的老姑娘。
眼见女儿年纪越拖越大,何成明总算开始急了,只好放宽了眼,把女儿往外嫁,但家里就一个女儿,又舍不得嫁太远,挑挑拣拣看上了梨水村的张家。
何成明性子实在 ,就是看上张家有几亩良田,张青山还念过几年书,性子也顺。他头上就一个老母,一家子都是和善的人,万不会因姚春娘年纪大了点瞧不起她。
张家的情况都是李媒婆亲口到姚春娘家告诉何成明的,何成明这辈子不识几个大字,自己的名字都画不像,唯独喜欢读书人,他一听张家的情况,觉得很合心意,托人私底下打听过一番,没发觉什么问题,很快就和李媒婆定下了姚春娘的婚事。
可惜这门亲结得不善,定下婚事的当天,张青山的娘王春华一高兴,出门喝了几口酒,回家路上就栽河里淹死了,第二天尸体浮了才被人发现。
张青山倒的的确确是个识理得体的读书人,并没因此迁怒姚春娘,仍旧按数给足了彩礼,一年后迎姚春娘过了门。
可天不遂人愿,哪想在大喜之日张青山又犯马上疯,一脚踩进了阎王殿。
姚春娘苦不堪言,年纪轻轻背上一个扫把星的名号,她越想越不对,后来四处一打听,才知道这李媒婆以前一句真一句假骗了她多少,就连她爹想方设法找到的打听张家情况的那人,也都是李媒婆提前一步打过招呼请吃了酒的。
是以此刻撞见李媒婆打她家门前过,姚春娘实在挤不出好脸色,她嗑着瓜子,从鼻子里不满地哼了声。
正卖力锯木的齐声听见响,以为她嫌自己吵,默默放下锯子,换了把声小的凿子,哪想敲了两下,又听姚春娘心烦地哼哼了一声。
他停下动作,抬头看她,这才见姚春娘压根没往他这看,而是皱眉瞥着打院门前过的几人。
他一个结巴,平时并不和旁人聊闲,不了解姚春娘和李清田之间有什么恩怨。不过他也不在意,见姚春娘不是在烦他,又把锯子捞起来,继续忙他手里的活。
李清田今日穿了身大红衣裳,过年似的喜庆,她笑眯眯地揣着手,身后领着两个拎着满手鸡鸭鱼鹅的瘦巴男人。
看样子,又是要给哪家的姑娘说亲。
她乐呵呵地对身后两个男人道:“快点快点,前面就是了。”
这两天夜夜下雨,路上积水未干,路泥泞得厉害,一脚踩下去湿得打滑,鞋底子全是泥。
姚春娘家门口的小石板不知道被谁搬走了,眼下陷了个小水坑,李清田打她门前过时,看了那坑一眼,也不晓得是腿短跨不过去还是怎么,抬着一脚泥就踩上了姚春娘扫得干干净净的院子。
姚春娘见此不乐意了,她吐了嘴里的瓜子壳,眉头一竖就想骂人,但见那两个男人提着的绑了红绸的鸡鸭,想了想便给忍了。
这边有个说法是媒婆说媒淌不得水,否则要坏喜气。
姚春娘以前不信这些,但她嫁来张家的路上停了轿,嫁来后丈夫便死了,如今多多少少有些避讳。她不喜欢李媒婆,但也不想坏了别人的姻缘。
不想姚春娘没出声,那李清田反倒变本加厉起来,脚脖子一歪,竟是把一脚烂黄泥刮在了她坝子边上,还跺脚抖了抖。
后一个瘦巴的男人有样学样,也踩着姚春娘家的坝子走,两人一来二去,将那院子口弄得一团糟,跟野猪滚过似的。
走在最后的那男人也跟着抬起了脚,可姚春娘忍不下去了,她抄起门口堆着的木柴块就用力扔了过去。
木头在院坝滚了几圈,那还没落脚的男人听见声一抬头,恰对上姚春娘怒气冲冲的视线。
“敢踩我就打折你的腿!”
几人闻声扭过头,这才瞧见屋檐下坐着个脸色难看的姚春娘。
李清田今日有正事,没空瞎扯,忙瞥过眼当没看见,最后那男人倒是冲姚春娘讪笑了声,悬着的脚转了个向,没敢往她家的院子里落,往前直接跨过了水凼。
姚春娘皱着眉,冲几人的背影嘀咕骂了句:“两坏东西。”
李清田今日的确是上门给人说亲,但让姚春娘没想到的是,李清田过了她家后没再往前走,而是停在了齐声院子门前。
说来齐声年纪已经不小,村里像他这么大的男人孩子都能遍地跑了,独独没见他和什么女人有过来往,有人说亲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但叫姚春娘意外的是,李清田今日是带了礼来的。她气没消,但忍不住好奇,扭头看起戏来。
李清田领两男人往齐声院子门口一站,突然懂起礼来,那双沾泥的脏鞋站得远远的,挨都没挨着齐声家的院坝边。
她让身后的男人把手里的东西放进齐声家院口,笑眯眯对他道:“齐声,这些是蒋家托我带来的。”
她弯腰提起地上的鲢鱼,手指勾着鱼嘴里的稻草绳把鱼来回转动着给齐声看:“你瞅瞅,这鱼多肥多嫩。今早费了好一番功夫才钓上来,趁还鲜,忙叫我给你送过来,你扔水盆里,或许还能喘口气,晚上煮了吃刚好。”
姚春娘坐在门口,听见这话颇有些惊讶,连手里的瓜子都忘记嗑了。
因为这番话她太熟悉不过,当初李清田就是这么拎着张家的东西到她家说的媒。
不过没带这么多礼,只有一条鱼一只鸡,也是夸那鱼肥嫩难得,说张青山一早上街买的,托她送过来。合着原来是雷打不动的套话。
姚春娘诧异地看了眼那地上扑棱的鸡鸭,又抬眼看向抿着唇沉默不言的齐声,突然回过味来。
敢情李清田今日上门给齐声说亲,不是要他娶妻,而是要他入赘啊。
蒋姓在村里不多见,就一户人家,一家四口,在街上开了家面馆。面馆生意兴旺,姚春娘赶集时还上他家吃过面。
蒋家一双儿女,大姑娘蒋招娣,二儿子蒋兴旺。今日李清田上门,想来便是给蒋招娣说亲。
蒋招娣自小在面馆里帮工,大家都叫一声蒋大姑娘,但真要说起来,蒋招娣已经不是姑娘,因她成过一次亲。
蒋招娣和姚春娘的经历有些说不出的相像,蒋招娣出嫁半年,原本康健无恙的丈夫身上突然开始长脓疮,请了医吃了药,药膏抹了一层又一层,却怎么也不见好。
蒋招娣婆婆死得早,公公不是个好相处的人,丈夫又是个没主意的软骨头,日子过得实在不舒心。三个人挤在一处住,三天两头吵架。
丈夫患疮,蒋招娣自然忙前忙后地伺候,吃药看病的钱都是她从嫁妆里拿的。
可她那公公见自己的心肝独苗苗一天天地躺在床上喊痛,忧心气急之下,竟然怨起蒋招娣是个扫把星,嫁来不到一年就将他的好儿子活生生克成这副惨状。
她那公公不是个省心的主,私底下还请八字先生算了一通,这一算竟算出蒋招娣和他一家子犯冲,原本只克他儿子的蒋招娣,猛然间竟成了他一家的丧门星。
这下可不得了,她那公公骂起蒋招娣来是更不留情面,什么腌臢话都说得出口,叫人听了心寒。
更可气的是蒋招娣的丈夫,夹在中间也不敢劝那不敢说,听见他爹骂自己媳妇竟然一声不吭地装死,心安理得地用着蒋招娣的嫁妆吃药看病。
蒋招娣脾气也大,被骂了几天,收拾东西就回了娘家,果决地断了这桩婚事。
听人说,她回娘家那天都走到路口了,还在和她那公公破口对骂。
蒋招娣一张嘴利得很,她公公骂她克夫,她扭头就说他儿子一副死人薄命相,娶谁都得早年亡命,气得她那公公喘不上来气,差点倒地上昏过去。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蒋招娣一回娘家,她那丈夫的病竟当真慢慢痊愈了,这下她在村里可算是坐实了克夫的名头。
如今蒋招娣回了娘家面馆继续帮工,听说不想再嫁,打算找个男人入赘,因此暗地里相看了不少人家。
按理说,以蒋招娣的条件,再寻一门好人家并不难,没必要找一个齐声这样的上托老下托小、连话都说不顺的结巴。
姚春娘估计着蒋大姑娘这是看上了齐声木匠的身份。
做棺材的积阴福,命硬,十里八村的人信这个,如果是个哑巴更好。有个说法是:哑巴做寿棺,亡人殿前难开口,告不了阴状,损不了活人的气运。那做棺材的人捂了死人的嘴,命那就不是一般的硬了。
齐声不是个哑巴,但就那一天到晚不吱声的样,和哑巴也没多大区别,想来是个命硬福重的,所以暗地里想找他入赘的人不少。
听说顺河而下的十里村里有个天生不太聪明的姑娘,她家也请媒婆找过齐声,想着拉他进了门,自己姑娘的痴症说不定慢慢就好了。
入赘是件大事,在村里,男人要是入赘得给人戳一辈子脊梁骨,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齐声从来没答应过谁。
可若不入赘,谁又愿意嫁给他这样半天闷不出一句话的男人呢?
其实齐声除了家里一大一小需要照顾,外加结巴这点缺陷,其他地方没一点不如人。他身强体壮,长得周正,做木工也还算赚钱,是个能干的。蒋招娣若拉他入赘,一年半载后生个大胖儿女,那克夫的名声自然就不攻而破。
姚春娘坐在凳子上一边嗑瓜子一边胡思乱想,那边齐声面对李清田却没想那么多,他看也没看一眼院子里的鸡鸭鱼鹅,少见的开了口:“拿、拿回去。”
他声低,话也说得慢,但语气倒是坚决,说完头一垂,继续心无旁骛地干手里的活,连请李清田进门坐坐的意思都没有。
李清田显然提前打听过他家情况,见齐声拒绝也不着急,不紧不慢地劝道:“哎哟,拿回去干啥,你留着吃呗,蒋姑娘专门让我送来的,人家家大业大,几只鸡鸭而已,不打紧,不打紧。”
齐声不吭声,拿起锯子就开始锯木头。
锯木声刺耳,显然是在赶人走,可他低估了李清田死缠烂打的能力。李清田吃了闭门羹也不气,清了清喉咙,提高了声,继续笑眯眯地道:“哎哟,齐声啊,蒋家是真心看上你了,听说今年还打算再开一家面馆,专门留给蒋大姑娘和未来女婿……”
她说着说着,扬起的木屑飞进嘴里,她皱着脸往后退了一步,呸了几口,换了个方向站着。“蒋家还打算买块地给蒋大姑娘建一新房,她家给我透了底,你过去了,可以把你奶奶和唐安丫头一起带上,也不用像现在这样一个人担着一家子。蒋家面馆你知道的,哪次赶集不是坐满了人,蒋姑娘你肯定也见到过,到时候你和蒋姑娘互相扶持,来年生个胖小子,一家人和和美美,多好,是不是?”
这番话说得周全,姚春娘听着都有点心动。齐声一家三口,上有个双眼失明的奶奶,下有个在读书的妹妹,他平日做饭干活,又当孙子又当爹,有时做完木工还得上地里挥锄。姚春娘嫁到梨水村已有一段时间,但几乎没见他休息过。如果他和蒋姑娘成了亲,说不定两人日子当真过得安逸些。
可齐声还是一声不吭,只摇头表示拒绝。
齐声不知道李清田有多难缠,李清田显然也不清楚齐声性子有多倔,不过她倒是不慌不忙,想来有所准备。
李清田将手拢进袖子,做好长谈的阵势,苦口婆心地道:“齐声啊,你就是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唐安丫头想想吧,你对妹妹好,大家伙都看在眼里,可你终究是个男人,女孩子家心思细,很多事宁愿憋在心里都不好和你开口,丫头是个姑娘,需要一个当姐做娘的在前面领着路。再者说,等以后你奶奶年纪再上去点,一旦有个三长两短,你顾得了老的就顾不了小的,那又怎么办,总不能那时候再干着急是不是?”
这话说得就难听了,几乎是字字句句往齐声肺管子上戳。
这是姚春娘第一回见媒婆劝男人入赘,和劝女人嫁人也没什么区别,先好言好语说上几句,对方不听劝话里就开始夹枪带棒,半点不留情面,只等着人松口。
明明吐的话难听,表面上还要摆张笑脸,好像是诚心实意为了你好,实际也就只为了那点儿媒人费。
不说别的,蒋大姑娘和前夫家那点子事李清田是一个字没提,齐声本就不爱和人聊闲天,说不定这闷葫芦压根就不清楚蒋大姑娘的情况。
姚春娘当初就是被李清田这张能说会道的嘴给骗了,深受其害。眼下她见齐声不说话,担心他稀里糊涂就答应了李清田,想也没想就开口扬声截断了李清田的话:“齐声,唐奶奶身体好着呢,你别听她说,你好好想清楚,这是大事,可千万别胡乱答应。”
几人想是都没料到姚春娘会插这么一句嘴,纷纷扭头看了过来。
齐声也有些惊讶,他抬头看她,依旧不说话,姚春娘以为她没听清楚,重复道:“我说你考虑清楚,不要随便嫁人,如果到时候后悔了,天底下可没有后悔药吃。”
她说得诚恳,“嫁人”两个字是又响又亮,想是生怕齐声没反应过来李清田是来劝他入赘的。
齐声知她好意,冲她点了下头,意思是他知道了。
李清田见状,气得胸脯起伏,恶狠狠瞪了姚春娘一眼,姚春娘也不甘示弱,拿起瓜子壳隔着老远的距离作势朝她脸上扔。
李清田没理会她,忙在齐声面前找补道:“这入赘哪里是嫁人,这不胡扯呢吗,入赘和嫁人那能一样吗,再者说,就是嫁给蒋大姑娘,也吃不了亏啊,蒋大姑娘多好的人啊是不是。”
齐声突然听起话来,不过听的不是李清田的,而是姚春娘的,他拎起地上的礼递给李媒婆身后那两人:“拿、拿回去吧。”
那两男人收了李清田的钱,只顾跟她跑趟腿,似个木头杵子似的也不帮李清田说句话。齐声把东西给他们,他们伸手就接了,巴不得早点回去,把钱拿到手就算了事。
眼见姚春娘短短两句话就要把事情搅黄,李清田没办法,着急之下,一股脑将底都给透了:“蒋大姑娘是成过一次亲,村里那些碎嘴子说她克夫,不过这反过来说明蒋姑娘命重啊,一般人承受不起这浑厚的福气,你运气好,这才找上你……”
齐声是一个字没听进去,他擦了擦额上的汗,摆摆手,也不再看她一眼:“走、走吧。”
李清田气得直拍大腿:“哎,齐声,你,唉!”
媒没说成,白跑一趟,还得踩泥淌水地提着几只扑棱瞎叫唤的禽畜还回蒋家,李清田是郁闷得脸都青了。
来时有多高兴,此刻她那老脸就垮得有多难看,而对坏了她事的姚春娘自然更没什么好脸色。
姚春娘倒是笑得格外开心,她自认劝住齐声算做了件好事,又把李清田气了一顿,可谓双喜临门。
李清田吃了一肚子气,见坐在屋檐下的姚春娘磕着瓜子春光满面,忍了又忍,实在没忍住,对着姚春娘就呸了一声,骂道:“扫把星小寡妇,谁遇见你谁倒霉。”
姚春娘一嫁过来就死了丈夫这事本就是她心存芥蒂,如今听见李清田当她面喊她扫把星,表情立马就变了,她“腾”一下站起来:“你说什么?”
李清田憋着火气正愁没处撒,见姚春娘还了嘴,索性在她家院子边站定,阴阳怪气道:“哟,怎么,我说错了?这一家子人难道不是你克死的,喊你一句扫把星难不成喊错了?”
姚春娘也不甘示弱,她把南瓜子往兜里一揣,冲着李清田骂道:“半截入土的人可就是不一样,嘴皮子上下一碰,张嘴就是鬼话,看来是习惯了骗人姻缘,害人不浅,你做什么媒婆,你做害人精算了。”
她俩说吵就吵,眨眼的工夫火气就冲上了天,跟着李清田来的那两男人见这一时半会儿也停不下来,颇有兴味地蹲在一边看戏。
齐声也停了活,他看看姚春娘,又看了看李清田,看表情似乎是想劝架,但唇枪舌战之间,他一个结巴,哪里插得进话。
李清田一手叉腰,一手指着自己的鼻子不可置信道:“我是害人精?你可真会说笑,那怎么不见我家婆婆掉河里淹死,也不见我男人一命呜呼。”
她拖长腔调怪声怪气地“哎哟”了一声:“张家好端端的一户人家,一读圣贤书的儿子,一能干的娘,自从和你攀上关系就开始死人,一家子如今死绝了,谁是害人精谁自个儿心里清楚。”
李清田这嘴利得像把刀子,字字句句往人伤处戳。
姚春娘不是块石头,被人当面说她害死了张家一家子人,她心里不可能一点儿不难受。她冷笑一声:“这亲可是你牵的线,你做的媒,你还好意思拿这说事?”
李清田做媒婆,平日这家来那家去,本就得是个嘴皮子利索不要脸的,见姚春娘耳根子都气红了,她说得越发来劲:“我有什么不好意思,又不是我嫁给了张家,又不是我克死了人,是你姚春娘克死的!”
姚春娘反驳道:“人人都知道他娘是自己喝酒淹死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李清田不依不饶:“怎么没关系,王嫂子就是因为定了你做儿媳妇才上街去喝的那几口夺命酒!没有你,人家当天压根不会过那条河,事到如今,人已经走了,你想起来把自己摘出来做窦娥了,晚了!你如今住张家的房子种张家的地,张家的害人精这称号,你就老老实实背到死吧。”
姚春娘年纪轻轻,和人吵过的架一只手都数得过来,哪里是身经百战的李清田的对手。李清田还游刃有余,她已经气得手抖。
可姚春娘天生是个不肯白受欺负的主,她怒道:“老不死的!你胡说八道!王春华本就酗酒,定下谁做儿媳妇儿她都要贪那二两酒,她爱酒这事儿你上我家说亲的时候就该说清楚,遮遮掩掩地瞒我这么久,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李媒婆做媒,自然清楚各家各户是个什么状况,王春华爱那两口酒的事不是个秘密,可王春华已经没了,她当然是咬死不认:“酗什么酒?谁爱喝酒了,你看见她喝酒了!还是王嫂子的魂回来找你和你说的?”
她皱眉“呸”了姚春娘一声:“还找我算账?你坏我的事我还没找你算账呢,你自己过不好还拦着人家齐声上蒋家过好日子,你什么居心!”
李清田说着说着,若有所思回过头望了齐声一眼,又打量了一番姚春娘一身棉衣也遮不住的俏身段。
她不知道误会了什么,面露鄙夷,意有所指道:“都说寡妇门前是非多,我看啊,某些人没两年估计就忍不住学周寡妇一样四处勾搭男人。”
姚春娘嫁来梨水村前,周梅梅是村里唯一的寡妇,四十多岁,性子尤其泼辣,夜里爬她墙的男人比老鼠还多,一些个管不住枕头边男人的女人恨她得很。
听说十多年前还有女人带着兄弟打上过门去,结果被周梅梅一个人举着粪勺赶了出来,从此再没有人敢去找她麻烦,只好睁大了眼盯着自己家不老实的男人。
周寡妇一个人过得可怜,但做的事也招人恨,无论哪个男人往她门前过,不管有妻没家,她都要耍嘴皮子招惹几句,不是个好货色。
李清田把姚春娘比作周梅梅,这话实在有些阴毒。
可吵架本就是哪句阴毒提哪句,她说起这一茬,紧接着是喋喋不休,字眼越来越难听:“小寡妇一个人守空床不好睡哦,这要是耐不住寂寞,啧啧……”
姚春娘骂又骂不过,又气得不行,左右看了看,似想找条扫帚把李清田这臭嘴给打一顿。
齐声还不知道李清田是在说他和姚春娘的闲话,他见姚春娘捡了木柴又抓矮凳,最后又嫌不趁手似的全部扔下,偏头往他这一堆工具看了过去。
他眼看着姚春娘,手上动作倒快,两下把身边的锯子锤子凿子划拉到跟前来了,像是怕姚春娘抢过去让李清田血溅当场。
果不其然,姚春娘眼睛看着他这儿就不挪了,腿一抬就走了过来,齐声顾不得避嫌,伸手拦她:“别、别动……”
他“手”字还没说出口,就被姚春娘一把挥开了手。怒急之下人哪里听得进劝,她端起他手边一小盆子刷在木头上的桐油,转身就冲着还在乱骂的李清田冲了过去。
齐声下意识去拉她,但想起李清田骂她的那些话,迟疑了一下,又松开了。
他这厢没拦住,李清田可就开始慌了,她见姚春娘端着盆朝她过来,一边着急忙慌地往后退一边颤着手指她:“你、你,你想干什么!”
“你不是很能骂吗,继续骂呀!”
跟着她来的两个男人拎着鸡鸭鱼鹅也忙躲得远远的,生怕祸及自己。
李清田慌张下没看清路,一脚踩进了之前姚春娘院前的水凼里,险些摔了个跟头。
姚春娘趁此两步走过去,手一扬,就把盆里的桐油朝李清田泼了过去。
李清田尖叫一声,立马扭着肥胖的身子往前躲,躲了大半,但半边身子还是遭了殃。
她咬牙切齿想骂回去,但见姚春娘手一抬,盆里竟还剩半盆没泼完,再顾不得别的,只好尥蹶子开溜。
姚春娘端盆冲着她慌急跑远的背影“呸”道:“晦气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