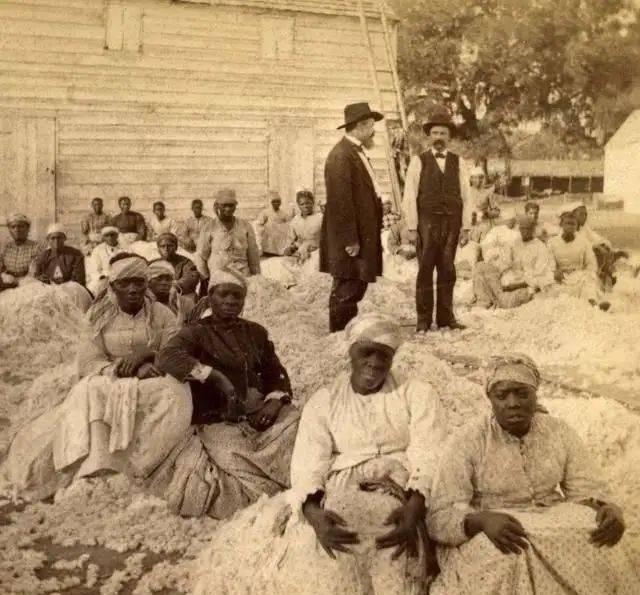本文来源:《法国大革命补论》,(英)埃德蒙·柏克(Burke, E.)著,冯克利译。节选自《致一位国民议会成员的信》。转自公众号 经典摘读。
《致一位国民议会成员的信》的收信人是弗朗索瓦-路易-蒂博·德·曼诺维尔。开头一段提到了曼诺维尔对柏克《法国大革命反思录》一书的回应(Corr.Copeland6:pp.162-169),柏克表示感谢,但并未理会他的大部分批评。
1791年1月写这封信时,柏克对现代的革命思想及其自我辩解的方式,已经有了深入的理解:暴行是由它的敌人激起的“过激行为”;不能用对待其他人一样的伦理标准对待革命的鼓吹者,因为他们毕竟是出于极为良好的动机;不能用当前的现实苦难,去质疑革命者对光明未来的向往。柏克明确认为,这场革命事业是国际性的,必须用武力加以对抗。不久之后,他对于为此目的而形成的欧洲联盟的迟疑和内讧深感失望。
这篇文字能够闻名于世,是因为它讨论了让-雅克·卢梭;它引人注目,还因为它反对卢梭的著作,尤其是《爱弥儿》中有关教育和情感的新模式。柏克最迟于1759年就开始阅读卢梭,当时他在《年鉴》中评论过《致达朗贝先生的信》,提到了书中的两章。1762年他又评论过《爱弥儿》。至于卢梭本人,1766年1月至1767年5月他的英国行,尤其是他与东道主大卫·休谟的争执,得到了广泛报道,让英国人对他的虚荣和忘恩负义印象深刻。
从这封信和《新辉格党致老辉格党的申诉书》中,可以看到柏克是站在古人一边,他赞成古典的教育和情感模式,反对启蒙运动。
先生:
我荣幸地收到了您在去年11月17日的来信。除了一些例外,您在信中对我就法国事态所写的信表示赞许。我接受任何包含着指教的赞赏,这要比泛泛的、无条件的赞扬更让我高兴。那种赞扬只能让我们虚荣心膨胀;而指教能鼓励我们,有助于我们在前进的路上有所改进。
......
国民议会奉行的准则与此截然相反。它建议年轻人学习大胆的道德试验家。人人都知道,他们的领袖之间有很大分歧,但是他们与卢梭最为相似。事实上,他们都与他相似。他们把他的血输入自己头脑、自己的作派之中。他们研究他、思考他,只要能从白天作恶、晚上放荡的生活中分身,他们总是会翻阅他。卢梭是他们的神圣教义。他毕生都是他们的波利克里托斯式教义,是他们标准的完美形象。巴黎的铸造厂,正在把他们的穷人的水壶、教堂的铜钟融化,为这个人、这位作家、作为作家和法国人的楷模赶造塑像。假如有位作家是伟大的几何学天才,即使他的所思所行在道德上极为恶劣,也可以为他塑像,他们推崇他,只是把他作为几何学家。然而,卢梭是个道德学家,不然他就什么都不是。因此,选出这位作家供人学习,其用心何在,人们不可能搞错。

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年6月28日—1778年7月2日)
他们的大问题是,要寻找某种代用品,取代过去一直用于规范人类意志和行为的所有原则。他们从那个人的思想中发现了有这种力量和品质的气质,要比过去的道德观好得多,适合他们的状态,更有利支持他们的权力,消灭他们的敌人。于是他们选定一个自私自利、弄风情的恶棍,用来取代朴素的义务。真正的谦卑,作为基 督 教信的基础,是所有真正美德的深厚而牢固的基础。但是,它践行起来很痛苦,表现起来很压抑,因此被他们彻底丢弃。他们的目的是把所有自然情感和社会情感变成过度的虚荣。稍有虚荣,而且是表现在小事上,倒也无关宏旨。倘若毫无节制,却是最大的罪恶,是所有罪恶中最丑陋的表现。它使人变成彻头彻尾的伪君子,毫无真诚可言,完全不值得信任。最好的品质受到毒化和扭曲,反而会产生最恶劣的作用。你们的贵族养着许多作家,像他们所崇拜的对象(例如伏尔泰等人)一样道德败坏,他们选择了卢梭,因为他们打算树为美德的那种奇怪的恶习,在他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我们在英国,也能感觉到这位虚荣哲学的大师和创立者。我几乎每天都有机会知道他发挥的作用,他使我毫不怀疑,影响他的心灵或引导他的理解力的原则,只有虚荣。他这种恶劣品质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同样是出于这种颠狂错乱的虚荣,这位被国民议会奉为苏格拉底的狂人,忍不住出版了一本疯狂的《忏悔录》,讲述他的颠狂的缺陷,试图赢得一种新名声,费力地炫耀阴暗而庸俗的恶行,我们知道,有时它还混杂着耀眼的才华。他看不清虚荣的性质,也不知道它什么都吃,从来不挑食,甚至喜欢谈论自己的缺陷和恶行,只要能令人惊奇、引人注目即可,而那是最不宜率真地公之于众的事情。这种能让虚荣变成虚伪的恶习和堕落,使卢梭所记录的生活,不需要用美德、用哪怕是一次良好的举止偶尔装点一下。他选择了把这种生活呈现于人类的眼前。他以粗野的轻蔑态度,把这种生活呈现在他的造物主面前,他只将其作为挑衅的对象。你们的国民议会知道榜样要比格言强大得多,所以选择了这个人(从他本人的记录看不到一样美德)作为模范人物。他们为他竖起第一座雕像。以他作为起点,开始了他们的荣誉和成名之旅。
你们的主子把这种新发明的美德奉为教义,这让他们的道德英雄为表达自己的普世之爱,不断消耗着他的花言巧语,他的心无法守住一丝寻常的父母之爱。怀有对全人类的爱,却对与他有交往的每一个人缺少同情,构成了那种新哲学的特点。他们这位虚荣的大英雄,坚持反社会的独立精神,拒绝对普通劳动的公平出价,否定富人给予天才、给授受双方都带来荣誉的捐赠;然后把他的清贫作为犯罪的借口。他向与他几乎毫无关系的人释放柔情,然后他抛弃已让自己腻烦的恋情,把子女送进育婴堂,就像扔掉垃圾类便一样,没有一丝痛苦。熊尚且能呵护和养育自己的幼崽,但熊不是哲学家。虚荣从颠覆我们的自然感情找到自己的价值。有成千上万的人赞赏这位伤感的作家,而在他自己的家乡,却没有人知晓这位“深情”的父亲。
在这位哲学导师的“虚荣伦理学”的指导下,他们试图在法国重建人间的道德法典。政治家,你们现在的统治者,靠弄虚作假蒙骗世人生存,正是这种做法,使那个人离开他的住处,登上一个舞台,装扮成矫揉造作的角色,涂满作戏的油彩,供人们在烛光中观赏,隔着适当的距离细心地品味。虚荣极易在我们中间、在所有国家流行对于让法国人更趋完善来说,按这套学说进行教育似乎不是绝对必要的。但是显而易见,目前的反叛是它顺理成章的产物,而反叛也在每天喂养着它。
如果国民议会推荐的这套制度是虚假的演戏,那是因为他们的政府系统有同样的特点。两者可谓一拍即合。要想理解它们,我们必把立法者的政策和道德风尚联系在一起。你们务实的哲学家事事都有一套理论,思想有着明智的起点。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排在第一的合乎自然的道德因素。与之针锋相对,他们把一个铁石心肠的下流父亲树为表率,他有博爱之心,爱全人类,却恨自己的亲人。你们主子否定这种天然的义务关系,视之为自由的对立面,它没有社会契约的基础;不受人们权利的约束;因为不言而喻,这种关系不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在子女一方肯定不是,在父母一方也未必总是。
他们通过推崇卢梭而宣扬的第二种关系,其神圣性仅次于父亲。古代的思想家认为,教师是头脑冷静、值得尊敬的人,与父权并列。黑暗时代的道德学家 preceptorem sancti voluere parentis esse loco,【0Filiola tua te delectari laetor et probari tibi gropyyv quauk'v esse TЙv TpÃG TÃ Tékva : etenimsi haec non est, nulla potest homini esse ad hominem naturae adjunctio: qua sublata vitae societa!tolletur. Valete Patron [ Rousseau ] et tui condiscipuli! [ L'Assemblée Nationale. ] Cic, Ep. ad Atticum.(“我很高兴看到你为小女儿而开心,对子女的爱能让你心满意足。因为假如不是这样,人与人之间就没有任何自然的纽带了。取消了它,也就毁灭了社会生活。”)Cicero, Letters to Aticus 7.2(Loeb Classical Library),——柏克原注。最后一句是柏克自己加上的:“向大师(卢梭)和您的弟子们(国民议会)致敬!”——译者注[拉丁文:“他们让教师占据了父母的位置。”Juvenal,sauires 7:pp.209-210.]——编者注】与此不同,他们教导世人说,在这个光明的时代,教师应当成为勇士。他们系统地腐蚀很容易腐败的一群人(有一段时间在你们中间不断壮大的害群之马),一群鲁莽、暴躁的文人,为他们指派的角色,不是承担起适当、严肃、朴实无华的义务,而是卖弄小聪明,他们快乐、年轻气盛、趾高气扬,衣服上挂满饰物。他们号召法国的新一代心仪于冒险和运气,竭力将他们的情感吸引到教师一边,背叛最值得敬畏的家庭信任,教唆他们的女学生行为不端。他们教导人们说,那些勾引几乎还在父母怀抱中的处女的人,他们家里可以放心地接纳:合法接任丈夫位置的人,他甚至能充当其荣誉的卫士,而那个位置是被年轻文人抢先占领过的,他不会为此询问法律或良心是否允许。
可见,他们打破了父母和子女、丈夫和妻子等所有的家庭关系,通过这种教师败坏道德风气,他们也败坏了品位。虽然人们通常认为,品位在道德品质中处于较为次要的位置,但是在调节生活中并非不重要。品位不是能把邪恶变成美德的力量,但是它用愉悦的规劝鼓励美德,消除恶行。卢梭是个笔力强健、精力充沛的作家,他把任何意义上的品位都置诸脑后。你们的主子以他为师,认为一切优雅的表现都有贵族制的特点。过去的时代使我们本能的嗜好变得优雅和高贵,将其提升到它似乎达不到的层次,但是这个时代气数已尽。通过卢梭,你们的主子决意毁灭这些贵族的偏见。被称为爱的激情有着十分普遍而强大的影响;支配着各种娱乐活动,事实上占据着塑造性格的大部分生活内容,形成能够培养同情心、激发想象力的方式和原则,对于每个社会的道德至关重要。你们的统治者很清楚这一点,为了改变你们的风俗以适应他们的政治,他们发现最好用的莫过于卢梭的思想。他们通过他教导人们模仿哲学家的作派,也就是说,他们教导法国人不讲风度的爱、没有青春之美和绅士精神的爱,而这种爱即便算不上美德,也能把生活装点得更美好。他们把这种激情,天然地与优雅和风尚相结合的激情拒之门外,为年轻人灌输一种下流、酸腐、阴暗、粗野、淫荡而又卖弄的混合物,一种形而上学的思辨和最粗俗的风流好色混杂在一起的东西。这就是从他们的著名哲学家、他的谄媚的哲学名著《新爱洛伊丝》中发现的激情。
阻挡这些轻浮教师的篱笆倒掉后,你们家庭不再受得体而有益的偏见的保护,离可怕的腐败便只有一步之遥了。国民议会的统治者大有希望看到,舞蹈教师、提琴手、美发师和男侍从以及诸如此类的活跃公民,会让法国家庭的女子成为他们可以轻松到手的猎物。这些人会进入你们的家庭,那里的气氛让他们不再见外,通过正常或反常的关系,与你们融为一体。他们利用法律,使这些人成了与您平等的人。他们接受卢梭式的情感,让这些人成了您的对手。这些伟大的立法者以这种方式,完成了他们的平等计划,在可靠的基础上确立了他们的人权。
我可以有把握地说,卢梭的著作直接导致了这种可耻的恶果。我时常纳闷,他在欧洲大陆为何比在我国更受推崇,有更多的追随者这种不寻常的差别,语言的魅力可能起了一定作用。我们确实承认,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感受到,这位作家有一种闪光、活泼、热情的风格,同时我们也发现,他行文松散,东拉西扯,说不上是最出色的文风;他的所有作品都矫揉造作,下笔铺张。他无所取舍,不分主次一般而言,他过于紧张,不善变通。我们无法信赖他的任何著作,然其中偶尔也有对人性相当不错的洞察。从整体上说,他的教义与真实的生活和风尚不相干,所以我们不能指望从中得出任何法律和行为准则,或者参照他的意见去强化和阐明任何事情。他的著作会让我们陷入古老的困境。
Cum ventum ad verum est sensus moresque repugnant,Atque ipsa utilitas justi prope mater et aequi. 【拉丁文:事物的真理、人的本能和习惯是受到排斥的,甚至效用也是如此,而后者才是真正的正义和公平之母。”见 Horace,Satires 1.3:pp.98-99.编者注】
也许大胆的思辨更易于被人接受,因为你们觉得这是新东西,而我们对它早就厌倦了。就像过去两代人一样,我们继续广泛阅读那些可靠的古代作家,我相信,这种现象较之现在的欧洲大陆要普遍得多。他们占据着我们的头脑,赋予我们另一种品味和作风;给我们带来的困扰,不会多于让我们对似是而非的道德观莞尔一笑。我并不认为这位作家彻底抛弃了正确的观念。在他的乖张表现中,必须承认他有时是讲道德的,而且是一种十分崇高的道德。但是,他的著作的总体精神和倾向是有害的,而且因为这种混合而更加有害。彻底堕落的情感与雄辩滔滔并无不相容之处;其思想(虽然堕落,但说不上面目狰狞)厌恶单纯的罪恶,避之唯恐不及。这些作家甚至能用美德去奉承恶行。
然而,我更为担忧的不是作家,而是国民议会借助于他颠倒道德观的学说。我承认,这让我几乎感到绝望,无法通过理性、荣誉或良知影响他们的追随者的思想。你们那些暴君的伟大目标,就是消灭法国的绅士。为此目的,他们用尽力气毁灭能使可敬的人变得强大或安全的关系。为了消灭这个阶层,他们败坏整个社会。不存在可以联合起来反对他们暴政的手段,他们利用这位“新爱洛伊丝”的虚假情感,颠覆了家庭内部的信任和忠诚原则,而正是这些原则构成了社会生活的纪律。他们鼓吹的原则,会让每个仆人认为,背叛主人即便不是义务,也是他的权利。按这些原则,每一个家庭的可敬的父亲,都丧失了避难所。Debet sua cuique domus esse perfugium tu tissimum,【拉丁文:每个人的家应当是他最安全的庇护所。——编者注】对这条法谚,你们的立法者先是予以谴责,然后加以废除。他们毁灭了家庭生活的宁静和安全,把家庭这个庇护所变成了阴暗的监狱,家之父只能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他的安全手段反而变成了对他的威胁。他在家里的处境比独守空房还要糟糕;自己的仆人和食客让他不放心,更有过于街头嗜杀成性、随时要他指明道路的暴民。
他们就这样毁灭了独立于政令和法规的良心的祭坛,这也正是他们的目的。你们的暴 君用恐怖进行统治,他们(暴 君们)很清楚敬畏上帝的人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们要通过他们的伏尔泰、他们的爱尔维修,以及这个无耻帮派的其他人,从人们的头脑中根除唯一能够产生真正勇气的敬畏。他们的目的是让他们的公民同胞变得无所忌惮,只害怕他们的调查委员会、他们的指路明灯。
一旦发现暗 杀有利于他们建立暴 政,这种做法就成了他们支持暴 政的重要手段。只要是反对他们的任何做法,或涉嫌反对他们的人就会赔上自己或妻儿的性命。这种无耻、残忍、懦夫的暗杀行为,他们厚颜无耻地称为“仁慈”。他们吹嘘说,他们篡权用的是恐怖而不是武力;几次及时的暗杀,便阻止了许多流血的战斗。不必怀疑,只要他们一看到机会,就会采取这种“仁慈”的行动。然而,他们试图用“仁慈”的暗杀政策避免战争罪恶,却导致了可怕的后果。假如他们不用有效的惩罚罪行去彻底否定这种做法或以此作为威胁手段,那么一位外国君主进人法国,便是来到了一个暗杀者的国家。文明的战争模式是行不通的,按现在的体制行动的法国人,也没有资格指望这种战争。他们的政策人所周知,就是暗杀每一个他们怀疑对他们的暴 政不满的公民,使所有公开的敌人丧失斗志,所以他们不寻求缓和敌意。所有的战争,而不是战役,都是军事处决。这会导致你们的报复行动,而每一次报复又会引起新的复仇。战争的一切恶行都将如脱缰野马。在巴黎成立的谋杀和野蛮学校,已经摧毁了使欧洲文明化的所有风尚和原则,也将毁掉过去使基 督 教世界鹤立鸡群的战争的文明模式。黄金时代正在降临!这就是你们国民议会里的维吉尔为他的皮利奥们唱出的颂歌。
在你们的政治、你们的文明、你们的道德风尚的这种形势下,你们怎么会受到任何自由辩论的伤害?有损失的人才会有警惕。对于合法的国王与受到践踏的宪法之间的关系,就它所导致的荒唐后果进行自由辩论,我曾经说过我有正当理由不为它所导致的恶果而担忧,这也适用于我为揭露强词夺理的篡权所造成的军队状态所做的辩护。现在掌权的暴 君们,并不需要证明他们每天都能感到的事情,即遵照他们的原则,不可能存在良好的军队。他们不需要有督察人员向他们提出摆脱军队、摆脱国王的政策,只要他们有条件采取这种措施即可。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年1月12日—1797年7月9日)
当下,为什么我们亟需去理解柏克与他的保守主义思想?只因柏克和他的思想,早已不仅仅只是一种政治智慧,更关乎文明本身的思想体系,其视野早已远远超出政治,在当下演变成重新理解世界、商业,甚至生活方式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审慎、自知、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智慧与美德,贯穿始终。后世诸多受柏克影响的思想家、政治家——丘吉尔、撒切尔夫人、里根等...都因汲取了柏克的保守主义智慧而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