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好笑,光听名字,我一直以为《不够善良的我们》和《我们与恶的距离》是同一赛道的剧,带着“袁湘琴要犯法了吗”的激动期待了老久。

毕竟台剧最大优点之一就在于它从不惮于给人性细细勾边,而律政戏又是王中王。
且卡司极强,履历上几乎没有一部我不爱看的。

所以当我猛虎扑食炫完前几集时,感受be like祺贵人奔着温太医查私通结果查出果郡王。
确实,没想到讲了这么个故事。
整体和《与恶》是搭不上什么边了,但对人的刻画,却也不可谓不精彩。
写这篇的时候,《不善》的豆瓣已从8.6飙至9.0,某书某博也都是“台剧已到下一level”的惊呼。

那我也先来个速评吧:
很喜欢《不善》,但next level嘛,有待商榷。
“没想到”的情绪其实带喜也带惊,咱今天就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先说喜。
我对《不善》的一大爱,在于它对女性嫉妒的绝妙刻画。
这也是整个故事的关键词。
双生花相爱相杀的故事见多了,但很难能见到一朵是“女强人”,一朵是“娃儿ta妈”的。
林依晨饰演的简庆芬同许玮甯饰演的Rebecca,曾为同事,爱上同一个男人何瑞之。
更准确的说,是简庆芬爱上Rebecca的男人何瑞之。
很老套的设定是不是?
按惯例,故事该从这开始,直到何同其中任一位的婚礼结束。
可《不善》的叙事角度不在此。
它将主线故事放在了数年后,何瑞之与简庆芬的婚后生活。

是的,“雌竞”已结束,但看“赢家”这一脸如丧考妣就知道,故事才刚起头。
理论上,此时的简庆芬应当是获得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一个不错的丈夫,一个不错的孩子,一个不错的居所。
可日子越平静,她的内心便越不平静:
太庸常了,太琐碎了,太反复了。
昨天、今天和明天,过得好像复制粘贴。

平静到她甚至感激起难缠的婆婆,刁钻在其次,总归为她的生活泛起一点涟漪。
她想要一个目标,一点刺激,所以又想起了“老仇人”Rebecca。

在社交软件的视奸下,简庆芬构建了Rebecca的生活,是“拥有一千八百万,每天都有新惊喜”的精彩。
然后夜夜在电脑屏幕泛出的蓝光前,咂摸着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写到这,我都觉得下面该给大伙儿讲一台台版《恶意》的戏才对。
但其实没有。
简庆芬什么都没做,也做不了什么,她只是暗自的醋意着,幻想着。

真正的生活嘛,就还是那样,在轨道里,在妯娌婆媳间。
只是会在手头日复一日的工作间隙幻视了Rebecca,然后被幻视中她的热烈刺痛,又渴望。
好无聊的“妒妇”是不是?但我偏就爱。
我知道以往影视热衷刻画的妒妇是什么样,扯头花,扇嘴巴,所有笔墨全用在外显的形态,恨不得一口气拍十部小时代,观众看个刺激,但也就看个刺激。
过段时间回想起来,就记住了倒红酒和一些贱来贱去的唇枪舌战。
原因是啥?想不起来。
你也不知道为啥就暴跳如雷,伤筋动骨了。
与其说这是在刻画嫉妒,倒不如说是想满足一种“吕子乔爱看女人打架”的奇观罢。
但《不善》里的妒意是浓在内,淡在外。
从简庆芬角度来说。
所有人都看得出她对Rebecca的牙酸,但从头至尾,她其实很少有称得上“斗”的动作。
那她如何展示妒意呢?通过不时在何瑞之面前做一些小俩口生活的“观察汇报”。
比如在Rebecca带鱼汤给住院的何妈被嫌弃后,简庆芬说:

比如在Rebecca升职加薪时,简庆芬对何瑞之说:

再比如,两人因何母分手,何瑞之于是不同妈妈讲话之后,简庆芬说:

有人说将讲这种话的简庆芬形容为绿茶,我倒不是很认同。
耍茶艺多是依靠编撰演绎的本领,编对方的蛮横,演自己的柔弱,这些简都没有。
她的确在讲事实,这些事实刺耳,不是因为虚伪,而是因为上帝视角的我们知道她心不净。
Rebecca与何瑞之的矛盾从不是简庆芬心机制造,硬说起来她还是莫名其妙被卷进来的那个人。
因为Rebecca和何瑞之都找不到人,她无奈前去帮衬,才有后续种种事发。

若换做何瑞之任一个其它朋友,被卷进小两口这些矛盾中,叹一句“你可要好好想想你俩适不适合结婚”,是不是就合理多了。

当然,我也并不是在说简庆芬于二人的关系破裂全然无责,我想说的是,大多数嫉妒并不会落地成撕头花,且,嫉妒的影响力也并不非要通过撕头花展现。
剧中对这个观点的阐释有点拗口,用了著名物理学思想实验:
薛定谔的猫。
这只猫在黑箱中本是既死又活的叠加态,而当有人打开黑箱,开始观测,则坍缩为了其中任一的形态。
所以观测本身,便改变了世界。

观测源于妒心,观测既是妒心。
观察汇报,就是简庆芬的嫉妒。
她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那些“斗”,至多只是在二人矛盾的关键处标红了一下,然后以“解决矛盾的方案”之姿一直萦绕,存在。

就足以成为二人感情破裂的最强催化剂。
但依旧,她不是根源,如果上述这段话让你觉得可怕,那不是简庆芬的可怕,那是嫉妒的可怕。
回到婚后时间线,简庆芬对Rebecca的互联网视奸,也同样如此。
哪怕内心已经嫉妒到幻视对方和自己男人激情doi了,简庆芬回过神来只是担心床单。

有人觉得这很不合常理,都妒到神志不清了,还不得上去撕扯一番。
甚至于回过神之前,她的表情不是怒,而是渴。

但这恰是《不善》对嫉妒刻画的绝佳之处。
它写出了“嫉妒”最核心最幽微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种情感:
不忍毁坏。
很多人对嫉妒的理解在于“因得不到所以想毁掉”,不能说错,但其实这只是嫉妒最坏的样态,且很容易产生误读,以为嫉妒的核心动因在于“得不到”。
其实不然。
嫉妒的核心,是“我想要”。
所谓的“毁掉”,不等同嫉妒,只是在“得不到”的极端愤怒下产生的变形举动。
大多数嫉妒走不到这一步,不是说不信人性之恶,而是不敢小觑人对“想得到”的欲望。
毁了,便真的什么都得不到了。

别陌生,这份信念也产于嫉妒之情,甚至于它才是嫉妒的根源,是嫉妒中关于“我想要”的那部分。
在两个女孩漫长的互相嫉妒中,“成为”的欲望,往往会战胜“毁灭”的欲望。
而这是真正的女性力量,一种超越父权定义的“妒妇”的力量,一种跳脱出父权“控制”“压迫”循环的力量。
这种成为,最终甚至会走向相互扶持。
不是因为很塑料的一句姐妹情深,而是因为深知“你必须前行,我才有方向。”
时代背景差异,简庆芬对Rebecca的嫉妒不大可能具有这种壮烈感,可本质却也是十分相似的。
很多人觉得若让简庆芬见到Rebecca真实状况,她便会小人得势,我实在有点无语。
她需要自己建构中的Rebecca,那是她的目标来的,她不会毁坏或过度攻击Rebecca,因为内心深处她明白,这只会让她的日子重归庸常。

目标与假想敌,一体两面。
同埃莱娜模仿莉拉走路一样,简庆芬也有意无意想追随Rebecca。
看到Rebecca纹身的照片,便也诞生刺青的念头。

看到Rebecca波浪卷,自己也去烫了个阿嬷头。

Rebecca的失意,注定意味着简庆芬的失重。
在简对Rebecca的嫉妒中,成为的部分,显然是高于毁灭的部分。
品味Rebecca的线上人生时,她的表情也是慕大于恨的。

这也是我为何无法讨厌简庆芬的原因。
她与Rebecca的故事很难用雌竞来概括,因雌竞是指完全丧失主体性的女性争夺男人,可简庆芬对Rebecca的嫉妒,却是一直带有主体性,且在不断增强的。
对应的,何瑞之反倒是比较工具化,客体化的那个。
让我们倒一下带,找找整部剧时间线的最初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契机?
才不是哪位与何瑞之的一见钟情嘞。
是简庆芬同Rebecca的撞衫。
同一件长裙,简是严严实实裹住腰身,贤德温婉地做一条长裙。
而Rebecca则是做风衣往身后一批,腰带背上一系,走起路都生风。

本不过是审美的差异,但简庆芬的感受是什么?
很糗。
这才是刺激到简庆芬宇宙大爆发的奇点,是后来所有故事的开端。
她与何瑞之的联系,也是从这里开始。

很多人误以为这句话,撞衫话题是工具,同何瑞之加深联系是目的,其实是完全相反。
“糗”才是这句话最深层的动因,而联络男人啥的,都不过是掩盖糗的手段。
衣服上输的,男人上我可以赢。
这其实不是想要“毁掉”Rebecca,而是当Rebecca的热烈严重冲击到简庆芬信奉多年的“恭俭让人生”时,她急于找东西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感。
何瑞之就是那个东西。
到底,她实在羡慕Rebecca。
无奈年轻时懵懂,明明想拥有Rebecca的主体感,却最后给男人戴上了裁判的高帽。

时过境迁,自欺欺人的幻觉散去,午夜梦回的还是那未尝到嘴的葡萄。
简庆芬在意何瑞之对Rebecca的念念不忘,与其说是因为爱何瑞之,倒不如说是“惊觉当初证明葡萄酸的工具人,好像撒了谎”。
也是这时,简庆芬意识到,她与Rebecca,本就是叠加态的同一人,没有Rebecca,便也不会有简庆芬。
她不会意识到自我的缺失,便极易在规训下模糊了这一生。
剧也给了许多明显的暗示,二者的撞衫、同月同日的生辰,都在揭示着这二人从不是水火不容,而是量子纠缠。

而当二人开始观测对方,当妒意开始流转。
各人便坍缩成了各人的宇宙。
可惜,任一个宇宙都是坍缩后的残缺,是自我的碎片,因而都充斥着浓厚的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简庆芬如此,Rebecca亦如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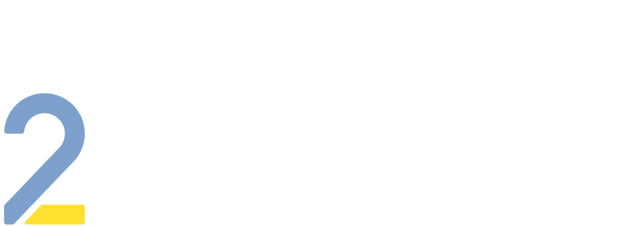
我知道此刻会有大女主热爱者出来喊停了。
独立自强的Rebecca,投身搞事业的Rebecca,能给自己买上一屋子华服,拥有六十多万台币存款,还没有踏入婚姻这个坟墓的大美女Rebecca,怎么会缺失自我呢?
就,怎么说。
国产大女主害人匪浅。
钱重要,但有钱就能解决世间一切问题,那是爹之逻辑。
觉得不婚便可不被父权社会剥夺人格,那是小觑父权,也是轻视女性困境。
所以,麻烦先不要急着替Rebecca喊不疼。

她明显疼,而她的疼痛核心,就是当今互联网口号女权时常会掩盖掉的那部分:
孤独。

Rebecca的孤独不单是“缺男人”,事实上她丧失了同任何他人建立深层关系的能力。
需知,我们强调独立,强调的不是遗世独立。
而是在与他者的关系间能保有自我的能力。
很简单的逻辑,若世上从无他者,那也无从谈起“自我”了。
Rebecca对他者的戒心与本能不信任,在遇到简庆芬之前,就已然有些病态的程度了。
在她同何瑞之的交往中,每一个糖点,她的脸上却只有害怕失去,觉得虚幻的忧心忡忡。
被表白如此:

被求婚也如此:


所以她明明在工作上是雄鹰一样的女人,卷生卷死,却在感情上没有一点坚定的姿态。
她对分离的焦虑已经大到有些下意识地寻求分离,好让自己脱离这个焦虑之中。
男朋友前脚求婚,她后脚便主动询问起对方妈妈的意见:在明知对方母亲很不喜欢自己的前提下。

而当听到对面传来简庆芬的声音时,她也不过是一脸“果然如此”的心灰意冷,甚至都已无力动怒。

所以她给领导当小三也好,做已婚男人的情妇也罢,皆不出于对何瑞之的报复。
更多的只是耐受不了孤独,又忧心过于沉重的离开,干脆将自己放在一段更为轻巧的关系间。

但就如同简庆芬得到何瑞之并不会更快乐,Rebecca也终将被这种掩耳盗铃刺伤。

她对简庆芬的羡妒,就在于简庆芬拥有同所有人真诚地建立联系的能力。
不要简单地理解成绿茶婊拥有男人缘,人家简庆芬可是真切拥有那种“对闺蜜的底线就是拥有知情权”闺蜜的人。

二人生日那场戏也足以看出,简庆芬的同事缘大大好于Rebecca。

也不难理解,毕竟她细腻到会夸前台的OOTD。

简庆芬也是Rebecca缺失的自我碎片。
当简幻视着Rebecca和小奶狗激情斯哈的时候,Rebecca却在梦中为丈夫孩子热炕头的画面落泪。


这一幕“庄周梦蝶”的设计还蛮让人唏嘘,做梦的是Rebecca,惊醒的是何瑞之。
不是唏嘘何与Rebecca的爱情,而是唏嘘世上又多了两个女人,被套进了红玫瑰与白玫瑰的模子。
何当然会有遗憾,不因贪,而因白红玫瑰本就该是一人,所以选谁都不会完整。
她们是被硬生生拆为了两个“半人”,一个封号“没人要的女强人”,一个封号“守在家的黄脸婆”。
被谁?不消多说罢。
大家也可以剧里寻寻去。


也不是我躲懒,实在是这个剧名起得不好。
是的,说完喜,我要来说“惊”的部分了。
上面的篇章看罢,所谓《不够善良的我们》究竟“不善”在何处,剧作又想给出怎样的理解,应该不大难懂了。
可我还是要说,这个剧名实在不是最优选。
抑或说,“职业女性”与“家庭妇女”的对照组,不是用来展演广义上的“人性幽微”的最佳素材。
因为“家庭”“事业”无法平衡的痛苦,早已是个公认的伪命题了。
这也是我说,此剧还不算台剧下一level的原因。
它的长处在于将那些困顿的情绪与其下的行为刻画地临摹般精准,但对这些精准,编剧想表达的上帝意志显然是“我们有些不善良,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话放在《第二十条》可以,但放这里,终觉不妥。
毕竟我们对所谓“平衡难题”的思考,早已跨越了审判女性自身的语境(哪怕这个审判是为了无罪释放)。
是谁让简庆芬视贤良淑德为正道,又是谁让Rebecca被划归“大龄女强人”不值得被爱。

这平衡题为何向来只对女,不对男?
当大家已经手握这个答案,其中的女性困境当然可以细细展现,但就绝对上升不到“善良与否”的价值判断上了。
倒不如叫《量子纠缠的我们》。
不过啦,区区剧名,瑕不掩瑜,也是我一家之言,大家看看罢。
曾经写《野蛮人入侵》的导演争议时我便聊过,只要将感受足够精准的刻画,便足够成为一部优秀的女性作品。
至于创作者觉醒到了哪一步,不重要,也不应该被苛责。
别忘了:
在平等到来之前,你我之命运,世间所有女性之命运。
谁又不与谁量子纠缠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