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年早于尼采,尼采直到晚年才邂逅了陀氏的作品,并称“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幸遇”。《罪与罚》中拉斯科尼科夫的梦境与尼采的结局并非全然是巧合,二者之共有的悲惨暗示了两人命运的某种交会。虽然尼采对陀氏的作品颇有赞誉,然而他们的哲学在根本上是背道而驰的。这一点我们接下来会讲到。
对于陀老,尼采这样说:“不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跟我的思想底流相反,我都会产生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来对他表示感谢。换句话说,我今天敬爱陀思妥耶夫斯基, 就如我对帕斯卡尔的敬爱。我所以要这样强调,是因为帕斯卡尔会曾给我 无限的启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唯一给我高深基督信仰理论的人。”

然而在阅读《罪与罚》的过程中,我们在偌大的篇幅中感受到了拉斯科尼科夫与尼采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尼采的超人哲学为我们所熟知,拉斯科尼科夫的形象变得更加饱满,却又蒙上了一层令人疑惑不解的面纱。《罪与罚》不间断的阅读串起了我整个暑假,也串成了一个问题:陀氏和尼采深层的隔膜,到底有无,若有,则如何在其书中体现出来?初遍通读,并未有所认识,但觉两人是属同一哲学流派的。然而仔细揣摩故事的架构,人物的心理,情节的安排,就会发现,尼采是怎样的忤逆了陀氏的信仰,又是怎样的逃脱了拉斯科尼科夫的心理命运和最终审判。
陀氏和尼采最本质的分歧,是在世界意志上,即有神论与无神论上。事出必有因,尼采之所以能“冒天下之大不韪”,高呼“上帝死了”,乃至成为后世存在主义者的思想来源,原因在十九世纪欧洲社会信仰的危机。陀氏可谓是一个卫道者,他敏锐而深刻地察觉到俄国人内心的矛盾、挣扎与冲突,并以一种悲悯之心再现了他们赎罪的痛苦和愉悦。学者王晓明这样评价道:
“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别能体会那种内心如同烈酒的俄国人:他们生命力很旺盛,欲望很强烈,但同时,他们的伦理感也非常强,这两者…本身就会冲突,又偏偏…特别需要上帝又没法相信上帝,内心冲突就更激烈。”
可陀氏到底还是让代表着广大迷茫的俄国民众的拉斯科尼科夫受到了教义的洗礼,从而重新达到了心灵的平衡,即所谓绝对价值。难怪尼采要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结交的罪犯们都比他好,因为他们比较有自尊心。尼采非常厌恶悔改和赎罪,他把这两件事称作“循环的蠢事”(罗素,《西方哲学史》,p348)。

西方哲学史(下卷)
8.8
[英]罗素 马元德 / 1997 / 商务印书馆
这一点我将会于后文中分析。罗素对这种分歧,多是站在陀氏这边,而批评尼采“轻视普遍的爱”。对于爱,《罪与罚》中的索尼娅展示了无与伦比的爱的能力,这是基督教对人内心的馈赠,罗素说“普遍的爱是关于这个世界我所希冀的一切事物的原动力”。然而在意志的问题上,罗素却开始偏袒尼采了,认为“某种高洁和自豪,甚至某种自以为是,都是最优良的品格中的要素;根源在于恐惧的美德没一件是大可赞赏的”,显然拉斯科尼科夫就在后者的行列。《罪与罚》中最终受摒弃的哲学,终究不是如许多网络写手所言,是与尼采的哲学殊途同归的。若真要说,不妨倒一下,是“同途殊归”的吧。
一、关于虚无
存在主义哲学家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人的存在先于存在意义的产生,人面临的,即是西西弗的处境。《罪与罚》描写了彼得堡的平民社会,数不尽的俄国人像《肖申克的救赎》中说的那样“忙着活”,然而仅仅是活着。在第二部中,拉斯科尼科夫在思考中,想起《巴黎圣母院》中的幻象:
“有一个被判死刑的人,在他被处决前一个钟头,说过活着想过,如果他不得不生活在一个高耸的悬崖上,在一块狭小得只有立足之地的崖面上,周围是无底的深渊、海洋、永恒的黑暗、永恒的孤独和永恒的狂风暴雨,如果他不得不站在那只有一俄尺大小的地方,站一辈子,站一千年,以至永远——这样活着,也比立刻死去要好!只要能活着,活着,活着!不管怎样活下去…”
这是一种病态的存活,是以生存为目的的生存。俄国人民在生活的重压下,开始怀疑上帝,信仰在贫困的啮咬中动摇,于是生活渐渐走向虚无,走向叔本华的生存意志说:叔氏意志的中心是生命意志或生存意志,为了活得好,生存得舒适,人才分化出并紧紧依靠理智。
然而尼采说道:
“你们称为世界的东西,应该首先由你们自己创造出来:你们的理性、你们的形象、你们的意志、你们的爱,都应该成为这种东西本身!真的,成为你们的天堂幸福,你们这些认知者!如果没有这种希望,你们要如何忍受生活呢,你们这些认知者?”
若言《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尼科夫以及卡捷琳娜等人是困在低地极力寻找上帝创造的法则,那么尼采则是站在山巅睥睨人生的虚无,从而发现一种活动的、不定的原则,并在奔流不息的意志洪流中创造一切。与叔本华的“生存意志”迥异,尼采意志的中心是“权力意志”,即寻找自身的意义,创造一种超越自身的新原则来指导自身。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尼采这样写道:“现在我命令你们丢失我,找到你们自己;只有当你们全部否定我的时候,我才会回到你们身边。”如此看来,拉斯科尼科夫“杀死一只虱子”的动机,未免显得太被动了些:面对人生的虚无,被动地寻找解决的出路;而尼采则更为主动地创造——这之间,便已多少个境界去矣。
二、关于身份
“那时是魔鬼拖我下水的,过后它就向我说明,我没有权利走那条路,因为我跟大家一样不过是一只虱子!它把我尽情的嘲弄了一番。”纵观全书,拉斯科尼科夫始终处于身份的漩涡之中,“伟大人物”和“渺小虱子”轮番对他的身份意识发起攻击,他在两者之间的痛苦徘徊也连接了全书的大部分内容。他心中不灭的“伟大人物论”,给出了一个相当模糊的形象,这个形象在尼采的处女作《悲剧的诞生》中似乎得到了共鸣,从而产生了一定的误解:
“雅利安观念中的特点却在于把积极的罪行当做普罗米修斯的真正德行这种崇高的见解。与此同时,它发现悲观悲剧的伦理根据就在于为人类的灾祸辩护,也为因此而蒙受的苦难辩护…当个人渴望融入太一时,当他试图摆脱个体化的界限而成为唯一的世界生灵本身时…他亵渎和受苦了。”
这一段凝练有力的陈述从对希腊的酒神美学的喋喋不休中脱颖而出,为其后继的作品及思想奠定了基石。
误解即产生于身份。《我不是药神》里有句话颇有内涵:“世上只有一种病:穷病。”在影片中固然指身体疾病,然而加之于《罪与罚》,却是认知上的疾病。整部小说,拉斯科尼科夫有将近一半时间处于疯癫状态,其原因即是贫穷与认知的深刻矛盾:拿破仑激励了他,使他产生不同材料的人的错觉,并认为其边界是模糊的。事实则并非如此,“天理”仍为不可忤逆的最高法则。
但是尼采的观点在《悲剧的诞生》,亦即其哲学之肇始便指出:超人并非真实存在,它只是一种趋势,一种目标,一种精神,一种理想,是一种极度超越自我的终极欲望,却不是世间任何一个实体,却在《悲剧的诞生》中体现为提坦诸神的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一般被认为是主观唯心哲学家的尼采,其思想也有一点客观唯心论的成分在:他否定上帝,却又用对超人的追求代替对上帝的膜拜。
如此明确而肯定的观点,却无法逃脱政治的利用:两次世界大战德国士兵经常在战壕里捧读的“圣经”就是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法西斯的元凶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公开声称是尼采的信徒,希特勒朝拜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尼采,两次朝拜尼采档案馆并亲自从私囊里拿钱向尼采档案馆捐款;墨索里尼致信给尼采的妹妹称:“尼采是他最喜爱和最崇拜的哲学家”,并为尼采档案馆捐款。1945年苏联红军占领魏玛,查封了尼采档案馆,宣布尼采的思想是“法西斯学说” 。尼采说,伟人因为被人误解方才成为伟人,他自身便是对此话最好的注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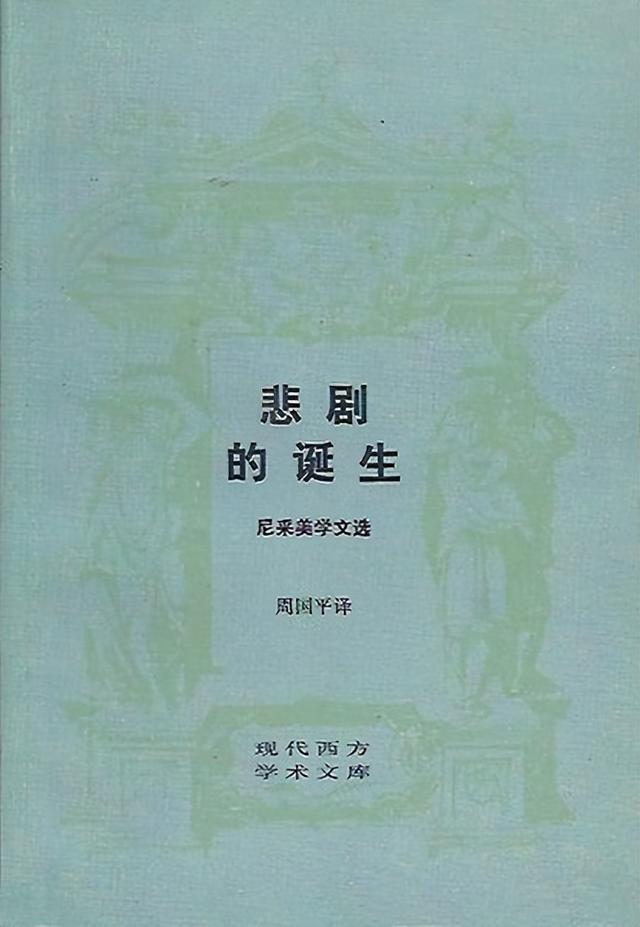
悲剧的诞生
8.9
[德] 尼采(Nietzsche,F.) / 1986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尼采是书斋里的哲学家,陀氏则是“悲惨世界”中的哲学家,陀氏在西伯利亚的流放,在临刑时极端的恐惧,让他经历到尼采无法经历的痛苦。因此陀氏会时时受“天理”的羁绊,而尼采如一只涉世未深的初生牛犊,真诚地挑战一切局限与束缚,而热情地歌颂强者,赞称他们“有较多的意志力量,较多的勇气,较多的权力冲动,较少的同情心,较少的温柔,较少的恐惧”。而陀氏则于生活的泥沼中发现平凡的痛苦,他们之间的分野从拉斯科尼科夫贫寒的出身就可见一斑,他不是强者,亦无较多的意志力量,因此只能成为陀氏的哀怜对象,而绝非尼采的歌颂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