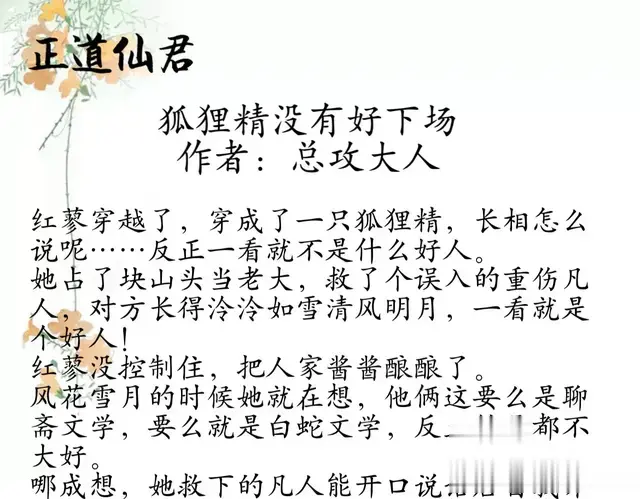原本,我和青梅竹马的沈行舟的婚期,定于四个月后。
可我却被一个女子拦在了长街之上,她声声哭诉,说自己已经身怀六甲,而她的夫君,正是我的未婚夫。
我气晕在了当场,所有人都准备看我的笑话。
后来,我让沈行舟成了笑话。
因为我转头便嫁给了他的死对头。
1
熙熙攘攘的长街上,百姓正拥挤着围观,一名身怀六甲的女子扑在沈府大公子怀里,紧紧拥住他,大声哭泣:“夫君,我和孩子找你找得好苦啊!”
这名寻上门来的女子,自称是在沈行舟游学江南时在一起的,与沈行舟在一起已一年有余。
而他二人旁边的马车里,躺着哭晕过去的我,他的未婚妻。
我和沈行舟虽算是一同长大,情份却并不深。
沈大人是我父亲的上司,但是家中产业不多,走动关系银钱消耗颇大。
所以一直想给儿子找一个家产丰厚的媳妇,好为以后的前途铺路。
沈行舟考中进士后,又看中我母亲经商积攒下的丰厚家底,让沈大人以我父亲上司的身份,恩威并施,为他定下与我家这门婚事。
我父亲迫不得已之下只得答应了这门亲事。
沈行舟意图用我家的钱,铺就他向上爬的路。
但沈行舟权钱双收的美梦,在这个看似平常的日子里,被千里寻来的外室打碎了。
贴身丫鬟晨儿正在我身边干嚎时,我母亲赶到了现场。
母亲冲到马车前,大声哭道:“我的女儿啊~沈公子刚考上进士,你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他落实了宠妾灭妻的行径,在官场上岂不是要被人唾弃啊!”
旁观的百姓议论声瞬间更大了,对着我们一行人指指点点,脸上满是看八卦的好奇神色。
听到母亲来了,我立马睁开眼,扶着晨儿从帘子中探出身子,泪流满面,喊道:“母亲!”
母亲走到马车前,一脸担忧地拉着我左看右看。
我把脸埋进母亲怀中,做足了楚楚可怜的模样:“母亲,我刚刚胸口好疼。”
沈行舟见我醒了,马上走到我跟前,急声说:“知画,你听我解释…”
不等他把话说完,那女子冲过来,大喊一声:“小姐!”
而后拖着沉重的身躯,楚楚可怜地在我面前跪了下来:“请小姐可怜可怜我和我腹中的孩儿吧,我怀着孕,四处乞讨,走了很长的路,才找到了沈公子。
我只求小姐给我和我腹中孩儿一个容身之处,日后在府上为奴为婢都可以。”
沈行舟十分心疼地扶起那名女子,向我求情:“盈盈她心地善良,性格软弱,不善与人相争。若她入府,只也会对你百般依顺。
知画,你可容得下她?”
薛盈盈闻言连忙看向沈行舟,泪眼婆娑:“夫君,我这一路上走来经历了十足磨难,就是为了带着孩儿与你团聚。夫君,不要抛下我和孩儿。”
围观的人正好整以暇地准备看我怎么答复。
母亲却替我先开口了:“只要一个容身之地,很简单。
我们顾府名下有好几处山庄,里面不缺衣食,也有大夫看顾。
这位姑娘可以挑一处去住。”
薛盈盈闻言急忙抱住顾行舟:“夫君,盈盈不想孩儿出生后没有父亲的陪伴。盈盈恳求能陪伴夫君左右。”
我假装伤心欲绝地看向沈行舟:“你纵容她当街闹开,把我置于何地?你让这满京的人如何看待我?”
沈行舟拥住薛盈盈,看着我正欲开口。
母亲已经不耐烦看这对男女的痴缠,冷冷地对沈行舟说:“沈公子,希望你好好斟酌如何处理这件事。
你父亲当初可是应允过不会委屈我们家知画的。
如若你做不到,我家就算是割肉刮骨,也会护好我家知画。”
说完,她登入马车中拥住我,吩咐驾车回府去了。
2
沈行舟作为新晋进士,初入官场,正被许多眼睛盯着。
本应该洁身自好、恪守礼节,但是却当众闹出外室气晕未婚妻的事,实在有伤风化、德行有亏。
眼看着事情在官场之中传播开来,危及沈行舟未来的升迁之路,沈府夫人连忙带了好些赔罪的礼品亲自上门道歉。
在我母亲和我面前,沈夫人信誓旦旦,已经好好管教了薛盈盈,在我和沈行舟大婚前,保证她不会再出现碍我的眼。
同时,又略有些强硬地表态:沈行舟年少有为,男子三妻四妾是常事。希望我以后作为当家夫人,要有容人之量,对于薛盈盈的事不要过多计较。
我心中嗤笑,既要我家的钱来给沈行舟铺路,又要我一心奉献不求回报,真是太贪了。
也是,毕竟我只是一个提供钱财的工具人,薛盈盈腹中的可是沈府的金贵血脉呢。
没过两日,在外游玩的郡主回来了。
她是我的手帕交,一向与我十分聊得来。
听闻这件事后,急匆匆来见了我:“我才出去游玩几个月,你怎的就定了亲?
那沈行舟绝非良人,定是宠妾灭妻之辈。
我替你入宫求陛下替你解除婚约!”
说着她就要走。
我连忙拉住了她:“当今陛下是个心软慈爱之人,我与沈行舟的婚约又是两家之间定下的,男子三妻四妾的,陛下也只会劝我忍耐。
陛下要下旨解除婚约不好师出无名,凉了沈家的心。
你且等等,届时可助我一臂之力。”
郡主问我的计划,我只说见机行事。
在沈行舟被嘲笑德行有亏的同时,我也成了京中的笑话。
身为顾府的千金大小姐,竟然被一个外室抢先怀上夫君的孩子,还被当街气晕,实在是一点当家主母的风范都没有。
明知道外面将我说得如此不堪,沈行舟还是冷了我四五天才姗姗来迟,他约了我在京中最大的酒楼中见面。
首饰衣裳在我面前一排排打开。
沈行舟让人托着一件衣服来到我面前:“知画,这件烟粉色的衣裳很衬你。
我特地为你挑选的。”
他看向我的一双眼睛里尽是情意绵绵:“盈盈她性格内向,我们成婚后只需在府上给她一个小院子,让她和孩儿在里面住着。
她轻易不会踏出院门,你一年也不会见她几面,你看怎么样?”
我看向沈行舟的眼里毫无感情:“性格内向的人会当街拦下我和你的马车,在众人面前哭嚎出你和她的往事?
况且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日后薛盈盈和我为了孩子争斗,你又该如何?”
沈行舟笑道:“盈盈性子温和,从来没和别人争抢过什么,你可以放心。”
我冷笑:“那我说把她送到山庄中养着,她为何争闹着不肯走?”
沈行舟:“她孕中情绪有起伏也是正常的。
知画,我知道,你一向都是宽和端庄的,娶你做正室夫人是不会错的。
此事你必然不会与她计较的,对吗?”
我本来是不想计较,我不想嫁给沈行舟,也不关心薛盈盈,但谁叫薛盈盈给我上眼药呢。
我眼光在衣服上逡巡了一阵,拎起了衣领,上面绣了一个小小的“盈”字。
3
我挑眉问沈行舟:“这也是沈公子特意为我绣上去的?”
沈行舟定眼一看,脸色瞬间涨红:“这衣裳是盈盈亲自做了向你赔罪的,她惯来习惯在绣花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一个没名没分的外室向我赔罪,未免太高看自己了。
我说:“我不是她的主母,她这样的赔罪实在不必。
她一直说只求一个安身之所,有这样的好手艺,却只甘愿四处乞讨路费,真是难得苦心啊。”
沈行舟不禁恼羞成怒:“顾知画,你也太斤斤计较了。
男子三妻四妾很正常,我还是新晋进士,前途光明。
更何况盈盈还怀了我的孩子。
我现在放下身段亲自向你赔罪,你还要怎样?”
我正欲说话,忽然听到楼下一阵喧哗。
晨儿进屋来,着急地说:“小姐,不好了。
那个薛盈盈跪在酒楼大门口,说要跪到你原谅她为止。
还引来了好多看热闹的人。”
这件酒楼位于京中最繁华的路段,看来薛盈盈是又想来一出逼宫大戏了。
我站起身准备下楼,沈行舟也要跟着。
我向晨儿使了个眼色。
晨儿领命,拦住沈行舟说:“沈公子请留步。
楼下那女子既然是来找我家小姐的,那就应我家小姐出面。
您今天是来赔罪的,跟着下去恐怕不太合适。”
沈行舟闻言思索了一下,还是留在包厢里了。
我穿过酒楼大堂,众人给我分开一条道。
薛盈盈跪在众人中间,额头已经磕出了血,殷红的血趁着素白的衣裙,显得格外楚楚可怜。
薛盈盈看我出来了,声音更大了些:“奴家给顾小姐赔罪,奴家给顾小姐赔罪。”
我问她:“你想如何?”
薛盈盈满脸的泪:“都是奴家的错。奴家不是故意要破坏你和沈公子之间的感情。
只是奴家生产在即,不想让孩子出生没有父亲的陪伴。
万望顾小姐能容许奴家陪在夫君身边,奴家不求恩宠,只求一个容身之地。”
我声音冷淡:“你说只求容身之地,我母亲说我们顾家的山庄有几处,皆是山清水秀,任你挑选,你为何不愿?
你说不争宠,自己非妻非妾,却一口一个夫君叫着。
不去求沈公子,却在最繁华的街上闹开,是想以悠悠众口来威逼我吗?”
薛盈盈连连磕头:“奴家并无此意。
只是顾小姐是夫君的未婚妻,夫君的后院之事往后定当是顾小姐做主。
奴家斗胆前来求一个恩典。
求顾小姐看在我腹中夫君亲骨肉的面子上,给他一个身份,让奴家留在府中为奴为婢吧。”
我说:“好。就算我答应你和你腹中孩儿入府。
但是,你要我给这孩子一个身份,这个孩子需得记在我名下,作为嫡长子女。
你只是个奴婢,往后不可再见他、在他面前谈及他的身世。你可愿意?”
薛盈盈愣住了。
她万万没想到我竟然会忽然同意她入府,还提出以这种方式接纳她的孩子。
围观的众人纷纷赞同我的话,一个大娘出声道:“姑娘,这顾小姐作为主母可真是宽容大度,一心为你肚子里的孩子谋前程。
你就答应了吧。”
应和的声音更多了:“就是啊,做庶子不如做沈公子的嫡长子,那可真是前途无量啊。”
“这个姑娘要是一心为肚子里的孩子着想,就该应允了。”
薛盈盈脸色越来越惨白,连连摇头:“不…我不要和孩子分开。”
4
我笑了:“姑娘真是贪心,富贵也要、夫君也要、孩子也要,说到底,你也没有自己说的那么清高,这孩子只是你向上爬的工具吧?”
“你!我腹中孩子可是沈家长子,宰相根苗!你怎能如此羞辱我!”薛盈盈脸色涨得通红,正要上前来拽我,不料却被裙子绊住,直直摔倒在地上。
鲜红的血色慢慢渗透了她的素色裙摆,薛盈盈脸上的神色痛苦起来:“我的孩子…”
沈行舟抱住薛盈盈,大喊:“快,送医馆!”
他又转头看向我,眸色凌厉:“盈盈她有孕在身,你何苦逞口舌之快?”
我捂住胸口流下两行清泪,喘着气说:“沈公子与这位姑娘相互维护,一致指责我,倒显得一心为她腹中孩儿的我像个外人了。
你放心,我会尽快让父亲母亲去你府上商议退婚一事。”
晨儿很识眼色地扶住我大喊道:“不好了,小姐心悸病又犯了!”
我适时地靠在晨儿怀里假装晕了过去。
很快,沈行舟纵容外室又把顾府小姐气到晕厥的事再次在京中传开了。
同时,传出来的还有薛盈盈生下了一个儿子的消息。
沈府现在上下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完全不把我这个明媒正聘的未婚妻放在心上。
我回府之后,父亲母亲开始为我遍寻名医。
那些大夫们往往是急匆匆地进了顾府的门,摇头叹气地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