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阅读此文前,诚邀您点击一下“关注”按钮,方便以后持续为您推送此类文章!!!点点关注,近我者富!!!
受到俄国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复调”与“对话”等理论的启发,克里斯蒂娃在《巴赫金:词语、对话和小说》、《封闭的文本》和《文本的结构化问题》首次提出互文性这一术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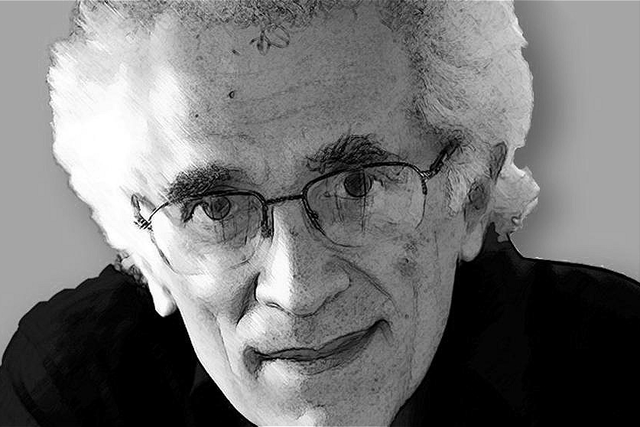
相较于语境观念理解文本局限于某一文本自身的内部语势和语脉,互文性概念把不同文本间的关系分析纳入进来,有助于突破单一孤立文本的共时性限制,从文本间性的视角展开对文本的分析解读。
“意象”则是古典文论中的概念,《周易·系辞》中有“圣人立象以尽意”的提法。意象在中国古典抒情文学中运用广泛,不过小说家也借由意象推进叙事,深化主题。
在晚期作品《故事新编》里,鲁迅仍然将意象叙事继承下来,并有新的发展。如武器意象在《奔月》中出现,同样又在《铸剑》等小说中出现,其它如黄昏意象、动物意象。
借由意象互文的视角能够帮助我们重新理解《故事新编》。意象互文大多呈现为自文本的互文,即《故事新编》八篇小说之间产生的交叉联动关系。

这种意象互文不仅增强了《故事新编》的叙事整体性,也彰显着鲁迅小说一以贯之的启蒙意味。
 铁屋空间意象
铁屋空间意象“铁屋子”式的空间意象自鲁迅提出以来,已经成为现代乡土文学的经典空间设置。无疑,“铁屋子”与启蒙想象密不可分。
启蒙话语为建构现代价值的进步性与正当性,便将矛头对准过去的历史文化空间,将其表述为压抑蒙昧,黑暗闭塞。
铁屋子空间意象的特征是狭小昏暗,封闭孤立,有时带有等级秩序的含义,有时也有着蒙昧麻痹的意味。

《补天》里的仙山:蒙昧学仙的的方士被困在奔流在海上的几座山上,浑浑噩噩地存在着。《理水》中的文化山、官场:麻木不仁的学者聚集在为洪水所围困的文化山;两位视察的大员回到京都大院,那里其实隔绝于民众,考察员们微醺之后,无聊且麻木地赏鉴木匣上的呈文。
一般读者往往忽略的是,前一空间场景中,母亲端坐床上,暗白的月影里,两眼发出光芒,而黑衣人在杉树林里出现时,后面远处有月亮出现;
黑衣人的眼光磷火一般,家庭屋内与杉树林的昏暗隔绝,都与月光以及作为眉间尺的启蒙者(母亲/黑色人)的目光同时出现,由此小说里昏暗的家与黑暗的杉树林都明显具有铁屋意味。
《出关》中的图书馆也承担着上述的空间功能:在孔子第一次问道离开,学生庚桑楚也出去后,老子又静下来,合了眼,图书馆寂静,孤立封闭的处所无疑可以算作是老子自我麻痹,以柔退走,徒作大言的讽刺与象喻;

作品后半部分的函谷关高踞峻坂之上,如同在峭壁间,俨然与世俗世界隔离的模样。关内大厅里巡警、书记、账房等一干人提示读者,这里同样是是庸众的世界,同样闷死滞浊。
《非攻》中宋国都城,对着聚集的十多个人,墨子的学生曹公子在南关街角大肆宣扬民气论;面对楚国来攻打的消息,整个都城百姓表现得非常麻木,被攻得习惯了,自认是活该受攻,竟并不觉得特别。
《起死》中庄子出现在,阴风怒号,鬼魂遍地的荒地,这里没有树木,遍地都是杂乱的蓬草。阴风习习,那些蓬头垢头,男女老少的鬼魂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至少在鲁迅的个人追忆当中,《故事新编》的写作计划重启是与四近无生人气的荒凉石屋所揭橥的厦门经验相关的。

熟悉鲁迅作品的读者,不难将四近无生人气的石屋与《呐喊·自序》里的闷死众人的“铁屋子”相关联,作于厦门时期的《奔月》与《铸剑》,不可避免浸透着鲁迅所体验到的现实与记忆的压逼,可以说整部《故事新编》都有着无生人气的意象暗示与氛围酿造。
 灾异空间意象
灾异空间意象在鲁迅作品中,灾异一方面指人事动乱,如兵灾;另一方面也指带有末世意味的场景,如《野草》中的地狱,独语者梦见自己在荒寒的野外,地狱的旁边。
《故事新编》当中,两种灾乱空间皆有所体现。相较于有实质性所指的铁屋空间意象,灾异空间意象在《故事新编》中,基本是以虚化的故事背景存在。
就人事治乱而言:《采薇》以殷周易代为背景,据传武王伐纣,牧野之战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铸剑》里国王善于猜疑,残忍嗜杀,荒淫无道,可想而知其治下国度之黑暗;
《出关》中老子走流沙,孔子遍览六经拜见七十二位主子,历史背景皆为春秋末年礼崩乐坏;《非攻》里墨子奔走宋国,目的是反对楚王的不义征战,宋国国界水灾和兵灾的痕迹到处存留,墨子走了三天,看不见大屋、大树、活泼的人和肥沃的田地。

就末世意味的灾异空间来说:《补天》发动战争的人触不周山,折天柱,绝地维后导致的天崩地塌;《奔月》当中后羿箭法过于巧妙,禽兽被射得遍地精光,从而仅剩乌鸦炸酱面可吃,暗含有末世意味;
八篇小说里对末世空间意象的营造共同凸显出鲁迅启蒙观念相对于《呐喊》《彷徨》的新变。《故事新编》中的灾乱空间意象,不同于《呐喊》《彷徨》时期鲁迅惯常构筑的铁屋子空间。
以《祝福》为例,读者当然不会忘怀小说中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所笼罩的鲁镇,同时也不应忽略被剩在四叔书房后,叙事者百无聊赖翻看《康熙字典》、《近思录集注》以及《四书衬》后所引发的“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的逃离冲动。
启蒙先驱者不再仅仅将无处不在的文化传统视为必须破毁根除的业障,而是试图赋予其正向意涵,并作为文明新生的必要前提接受下来。

启蒙者在《故事新编》里不再作为一个空作大言救救孩子的呐喊者,或者是隔岸观火像一匹受伤的狼的孤独者,而是成为积极的承担者、行动者。
就这个意义上讲,《故事新编》中的末世空间意象互文是鲁迅小说里对启蒙空间营建的拓展深化。
 仪规空间意象
仪规空间意象仪规的作用是引导人们进入必要的社会关系,它“并不只是给予人们一个文化传统中积淀下来的合适行为举止的标准”,还具有“个人创意的一面”。
不过这种开放性构造只面向权力拥有者,对于土俗世界的庸众则是僵化封闭的。所谓仪规空间在《故事新编》中,意指先驱者们或补天,或射日,或理水,或铸剑,或扶危。

凡此救世行为在小说结尾最终都免不了导向新的僵硬的权力秩序,小说叙事空间重新沦为毫无生气或充满悲哀的构图,其典型意象是京师、王城、都城。
《理水》的故事收束于大禹即位后京师的太平景况,大禹黑瘦赤足,衣着随便,逢旱路水路即坐车坐船,临山路泥路便坐轿坐橇,查山泽,导河川,勤勉务实,满脚底是栗子般的老茧,终成治水功业,可最后要妥协于传统近乎命定的仪规秩序。
小说结尾写到,大禹虽然吃喝不考究,但对于祭祀和法事非常认真对待;衣服虽然随便,但上朝和拜客时,穿著要漂亮得体。整个国度太平到百兽跳舞,凤凰齐飞,其背后是象征着文明秩序所积累的业障难以根除廓清。
都城、京师所象征的仪规秩序,在《非攻》中展现为墨子在宋国界被搜检两回,于南关遭逢大雨,想到城门下避雨,被巡兵赶开,淋得一身湿,俨然偌大都城,却无容身之所。仪规空间展示了现代启蒙命题与传统惯性在文明建构问题上复杂而辩证的吊诡关系。

《补天》里女娲用尽气力补天后,其结果上下是死灭以上的寂静。这固然可以看作救世者悲壮落幕的空间营造,同时也是世界又循环轮回成新的铁屋子的暗喻。
小说第三部分那些善于变化,精于做戏的伪士、虚无党,以及驱使方士寻仙访药的秦皇汉武们都在解构着启蒙图景,虚妄且令人看不到任何希望。
《故事新编》虽然没有直接承续《呐喊》《彷徨》的鲁镇、未庄,但前者所设置的空间意象背后却传达着一样丰富的启蒙意涵,并有所超越发展。
由此,本文意图探究同一类空间意象在《故事新编》不同文本之中为何会赋予其不同的意义。

事实上,作为鲁迅精心撰构的小说集《故事新编》,集内八部小说都或隐或显地书写着各种启蒙式空间意象,进而形成互文关系。
《故事新编》从第一篇《补天》到全部完成编成集子,耗费十三年,小说标题都是动宾结构,题材的一致性,每篇小说的编排顺序的刻意安排等等元素,无不告诉读者其整体性。
要言之,《故事新编》的整体性体现在文本内部的互文性,其中又以空间意象互文甚为突出。鲁迅在《故事新编》中形构启蒙空间时,不仅继承了自《呐喊》以来的“铁屋子”空间意象,同时又通过仪规型空间意象深化了这一意象构造。
同时又不再仅仅固守《呐喊》《彷徨》时期的封闭式的“铁屋子”所指代的被启蒙者蒙昧昏睡想象,而是借由灾异乱世空间的铺陈,开展出启蒙者的行动救世意味。

如果说前者还停留在启蒙与蒙昧的简单二元对立上,那么后者则显示出更复杂的“中间物”启蒙意识,展现出启蒙者短期内对彻底改变蒙昧混沌局面的不抱希望之心境,以及仍然为之付出不求回报的努力的承担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