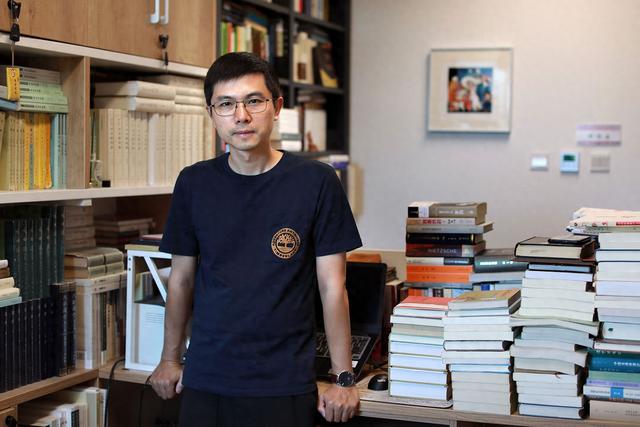
周思成在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办公室里(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图)
如果按当下时髦的MBTI人格分类,青年历史学者周思成属于典型的i人。他个性安静,喜欢独处,自我诊断为“社恐”患者。在清华园的办公室里,他一个人看书、思考、喝茶、写作。最近一两个月,他“密集地”参加了几场新书宣传活动,为自己的书(《王安石“强辩”考:十一世纪中国政治的常识与诡辩》,2024年6月)吆喝,更多是为圈内朋友的书捧场,精神很是“消耗”。“如果可以,最好是一场都不要有。”
2021年,他的历史非虚构作品《隳三都:蒙古灭金围城史》摘得首届文景历史写作奖的首奖,让这位一直默默深耕于冷僻、小众的蒙元史、军事史和民族史的青年学者,进入了普通文化大众的视野。
《隳三都》以蒙古灭金的三段围城之战为主线,讲述金王朝末年颠沛流离、节节败退的亡国史。该书首先在蒙元史学界、军事史爱好者中获得高赞,然后慢慢地溢出了“圈”。
其小说般的情节、丰富多元的史料、细腻动人的细节、生动的各色人物,逐渐吸引越来越多非战争史爱好者,甚至是我这般“最不可能的读者”——反感战争、对军事题材敬而远之的女性,北宋末年南逃的中原难民之后,一个从小听着南宋旧事、看着西湖边岳王庙里的秦桧夫妇跪像长大的原籍杭州人士。
《隳三都》的书写,让我第一次生发强烈愿望去突破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的、以中原-汉族为正统和中心的史观,去了解东亚大陆上那段宋、辽、西夏、金、蒙古多政权并存的民族大融合时代。
 崖山之前的悲剧史诗——在学术和写作之间
崖山之前的悲剧史诗——在学术和写作之间《隳三都》的书名源自春秋时期的历史事件——孔子在鲁国执政期间,遵周礼堕毁了有“三桓”之称的鲁国公族三家季孙、叔孙、孟孙私邑。该书中,“三都”指金朝时的中都(今北京)、南京(今河南开封,北宋时期称汴京)、蔡州三座城池。
书的灵感和构思,来自周思成多年读蒙元史、尤其是读金元之际史料时积攒于心头的诸多想法和感触。这些史料大多来自亡金的士大夫之手,他们记录下大量有关金朝的人和事,尤其是金灭亡之际的许多故人和往事:
有才具平庸而仍奋力苦撑败局的卫绍王、宣、哀三代帝王,中都被围时被迫和亲远嫁的金朝公主“小姐姐”,勇猛刚烈的传奇名将完颜陈和尚,还有知名文人刘祁、元好问和王若虚为自己在南京陷落时的历史“污点”辩解和彼此推脱责任的罗生门事件。以及在南京城破后,因蒙古人只要工匠不要百姓,很多百姓为活命假冒工匠,管事的人发现后帮着蒙混过关,再耐心教授他们营造的手艺……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曾有一段时间,周思成和家人一道在家中,人出不去,也进不来。沉浸在宛如围城的气氛中,听闻着各种荒诞离奇的事,他终于沉下心,全身心投入到这一部在心头盘恒许久的历史悲剧中。
在卷首君士坦丁堡被攻破的波斯语吟唱中,故事从金朝招待南宋使节的一场射弓宴拉开序幕——从公元1211到1234年间,大大小小的野战,三座苦苦防守、依次沦陷的金末都城,一个小高潮接着一个小高潮。战局动荡中,帝王、大臣、武将苦苦支撑,文人们在气节和求生欲之间“天人交战”,更多的百姓颠沛流离,命如蝼蚁。
“一般来说,纯正的专业学者写历史非虚构,行文里会有比较重的学院气。”历史作家刘勃评价,“但你在他的作品中能感受到他的专业功底,同时又有一种超脱于学院气之外的挥洒自如。”
刘勃的代表作是春秋战国题材的“历史三部曲”。作为国内最早的一批写手,他见证了历史非虚构写作从冷到热的兴起。
“周老师的语言特别好,是一种很纯正、很高级的文学语言。”他赞赏道,“而且,他使用的语言和他所写的对象之间有一种贴合。《隳三都》的文字本身就带有一种强烈的、毁灭属性的那种史诗感,他的语言很庄重,有那种沉郁顿挫的感觉。”
在《隳三都》之前,周思成的第一本历史非虚构作品是《大汗之怒:元朝征伐日本小史》。当时,他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读博,正写着有关蒙元帝国军事礼仪和军事法题材的博士论文(后出版为《规训、惩罚与征服》)。为了给自己透口气、“调剂一下”,他应一家出版机构之邀同时写了《大汗之怒》
《大汗之怒》讲述了发生在元朝初期的一段离奇却甚少被国内关注的历史——竞得蒙古帝国大汗之位的忽必烈在公元1274年和1281年两次出兵征讨日本,遭遇海上风暴受挫,最终无功而返。这催生了日本民族史上“神佛护国”神话的诞生,阻拦元军的风暴成为“二战“时期日本空军自杀式袭击特工队“神风敢死队”之名的由来。
《大汗之怒》出版后的反响,让他感受到小小的欢乐。“因为写论文太枯燥了,后来发现自己写的东西有人读、有读者喜欢,哪怕就一两个,对我来说也是挺大的鼓励了。”
“今天的学术已经高度专门化了。比如我发表一篇关于元代法律里某种刑罚或立法的论文,全国百余名元史研究者里,可能只有三四个对这个题目非常感兴趣的才会去读。可以说,我写论文多半是为这三四个人写的。”
更重要的是,让他找回了起初对历史学的热情,和面对历史记录里活生生的人与事时身为一个普通人的情感和心态,而不再只是一部论文生产机器——“一读到某个史料,自己就会想着是不是能榨出个C刊(论文),可以发到《某某研究》上。”

《隳三都》为周思成收获了来自学术同行的许多肯定和称赞,包括罗新、张帆这样的知名前辈和李硕这样的学术新星。另一方面,尽管在题材、领域和历史书写上有诸多创新甚至零的突破,它仍不能被归为“学术作品”——现实地说,不能为作者带来评职称、评奖、申请社科项目的好处。
在学术圈边缘多年,周思成一直由着自己的兴趣和节奏读书、做研究、写作。2021年左右调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后,他开始感受到身为“青椒”的压力。即使学校没有KPI的硬性要求,身处清北这样的国内顶尖高校,氛围是“自来卷”——“大家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彼此暗暗较着劲。”
“我现在必须认真面对这个问题了。”他坦白道——按照现行学术体制的规范,不断地去生产那种严格意义上的论文,“就是有很多注释、用很多材料,用一种更加理性、不带感情的语言去表述的论文。”“但是,我自己另一方面的追求,还是希望写有自己特色的历史,遵循我自己的历史研究之路。”
《隳三都》成功后,有不少友人和同好建议周思成在同类题材上继续发力,续写“崖山之后”的南宋灭亡史。但他兴趣寥寥,“我还是想尝试新的,不想自我重复。”2024年6月,他意外地出版了一本与过往专业领域不相干的“小书”——《王安石“强辩”考:十一世纪中国政治的常识与诡辩》。
无论是书名,所涉题材、领域,采用的解释框架和理论,还是长长的参考文献目录,都标示着这是一本合乎学术标准的的著作。但在学术之外,行文中一种极为克制、智性的冷幽默贯穿始终,让读者常常不禁莞尔,而后心头涌起难以名状的淡淡苦涩。
眼下,周思成在做一个新的写作尝试——把自己在清华开的一门法律史的课写成讲义,“也想写成一个类似于历史写作也好、历史非虚构也好的东西。”
“像他这样受过很好的学术训练、有很强的文字表达能力,还有自己独特问题意识的写作者是非常难得的。”资深出版人、北京行距文化创始人黄一琨说。因工作缘故,黄一琨接触过很多高校中青年文科学者,他们大多困在论文、职称和“非升即走”中,无力写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而一位出版了多部历史畅销书的作者,至今仍无法解决职称问题。
“我个人是希望像清北这样的高校,能给类似周思成这样的青年老师多一点空间。”

1281年,忽必烈第二次征讨日本,蒙古兵试图将夜袭兵船的日本武士赶下船(视觉中国/图)
边缘行走的“增上缘”周思成是湖南长沙人。他打小就是个书迷,常常踮着脚尖在父亲的书架上扒拉着书看。童年里最快乐的事之一是每个周末跟着父亲到老长沙的黄泥街去淘书。黄泥街当时是闻名全国的图书批发零售市场,一整条街密密麻麻都是小书店的门面。他在里头挑挑拣拣,看到感兴趣的就买下,然后高高兴兴捧着回家。那时,他喜欢读历史故事,还有亚历山大大帝、拿破仑的人物传记。
因为高考失利,他误打误撞去了中文系。读中文系,最大的收获在写作上——他读了大量文学作品,遇到了一些很喜欢的作家,黑塞、芥川龙之介、茨威格等。给他带来最强烈心灵震撼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夜自修时,他读着《卡拉马佐夫兄弟》里宗教大法官的段落,在座位上一个人偷偷流泪。“在那个年纪,那个成长阶段,正好遇到了那样一位作家,是一种缘分。”他感慨道。
毕业时,周思成已经想转向历史专业。他被保送进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主要做偏元代的古典文献研究。在文献阅读中,他逐渐喜欢上这个多族群、多语言、多宗教的北方民族统治时代。
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由北方民族建立的强大帝国,元代缺少传统中原王朝那样成熟、完整的历史记录体系,也没有一个高官士大夫群体留下日录、时政记等私人记录。“譬如,元代史书里一个像右丞相这样最高级别的行政官员,你不知道他从哪儿来,也不知道他怎么就没了——忽然从某年开始,他就在官方记录里消失了。”
“但它给你看历史的视角,不再只是汉人士大夫那种——乖乖地读好儒家经书,然后考上科举当大官,在朝堂上实现自己儒家抱负这样一群人的视角。它有各式各样的人的视角,比如蒙古人自己写的《元朝秘史》,在元之前从来没有草原游牧民以自己的视角、语言来写他们观察的这个世界是怎样的,社会关系是怎样的,婚姻是怎么样的,一个勇士应该是怎么样的。元之前的北魏、辽、金的历史,几乎都是中原史官帮他们写的。”
当成吉思汗一系的“黄金家族”东征西伐,横扫13世纪的欧亚大陆时,这个巨无霸帝国也裹挟进很多其他族群、信仰的人们。“比如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佛教徒,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人,譬如欧洲人马可波罗,他们都会留下很多记载来反映他们如何在这同一个时代生活和思考。”“这些记载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元代高层政治的史料缺乏,让这个时代更加丰富,或者说更加人性。”
2009年硕士毕业时,周思成没有读博,转而去中央编译局上班。一直待在学校里,他想到围墙外走一走。“当时对学问还很有热情,但对学院体系没有太多热情。”
在这家半学术性质的中央直属机构里,他主要的工作是参与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编译项目。此前,国内老版本的马恩全集还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苏联引进、根据俄文翻译的,而这套新全集则是直接根据两位思想家的德文、法文、英文等等的原著全面修订老版本。
在项目组里,他主要参与编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手稿部分,包括编译马克思本人亲自修订的法文版《资本论》。为了正确理解、把握原意,他阅读了大量古典政治经济学著作,包括李嘉图、斯密、萨伊、西斯蒙蒂等人的思想和学说。而马克思百科全书式的思想谱系和论著,也逼得他把欧洲史、19世纪到20世纪的哲学、社会科学多多少少都学习了一遍。
多学科领域的涉猎,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看待问题的角度和思考框架。中国史学长期以来主要的研究方法仍是走乾嘉学派的路子:注重考证,穷尽史料,辨析文献的来源、真伪和可靠程度,然后利用史料还原历史事件、制度。“但是,如果你接触了更多社会科学,你会得到很不一样的解读思路和灵感,更善于发现很多材料并不一定是它表面试图想说的那些。”

约1430年,战斗中的成吉思汗。法国国家图书馆藏(视觉中国/图)
这多少在他的《王安石“强辩”考》中有所体现。在书中,马克斯·韦伯的政治学,西方的心理学、精神分析方法等等,自然而然地融入了他的历史研究方法和框架里,没有如今一些“跨学科研究”里常见的嫁接西方理论的生拼硬凑感。
在主流学术圈边缘行走近十年,没有卡着点读博、做博后、进高校,让周思成重回象牙塔的道路多了曲折,却也有了很多意外所得,他用一个佛教词汇来定义之——“增上缘”。
周思成另一个令很多学界同行羡慕、佩服的独特技能点是语言上的独特天赋。
本科时,为了读自己喜欢的作家的原著,他自学了法、德、日、俄语;到研究生阶段,他又自学了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在中央编译局时,因为对蒙元历史发生了兴趣,他又自学了阿拉伯语、波斯语、蒙古语,接着是拉丁文、藏文、维吾尔文。
一个人在成年后如何能够学习、掌握十多门外语?
他认为这并非一个有关天分的问题,而是兴趣和缘分的问题——看你是不是真对一门语言背后的历史、文学世界感兴趣,以及愿不愿为之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其他成本,“许多更聪明的人是不愿意的。”
这为他打开了通往多个文明的大门,可以跟随14世纪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的脚踪探索神奇的中亚大陆,听着伊利汗国的宰相、学者拉施特用波斯文娓娓道来“黄金家族”的历史与天命……在《隳三都》里,为了寻找被迫远嫁和亲的金朝公主的下落,他在拉施特的《史集》里找到有关成吉思汗的“四皇后公主哈敦”的记载——“我们知道,她长得不美,但由于其父是伟大的君主,就使她获得身份,受人尊重。”
这些既是珍贵的史料,也让他感受到智性与艺术的双重愉悦。“像拉施特他本身就是很有文学修养的穆斯林文化精英,所以他会在他的史书里隔三差五来一段阿拉伯文的诗歌,或者引用几段《古兰经》、《圣训》里的内容。它们都会写得很像文学作品。”

王安石(视觉中国/图)
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辩论《王安石“强辩”考》是周思成读北宋政治史各种“边角料”时的所得。
这是一本风格独特的、非典型的学术著作。它以北宋改革家王安石的恶谥——“强辩”为题眼,以宋神宗时朝堂上的政治辩论为切入口,对变法派和反变法派的论争做剥洋葱式的分析,试图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北宋晚期看似活跃、开放、频繁的思想交流为何没能通向成功的政治变革。
一位青年学者评价说:“这本书体量不大,却有着四两拨千斤的构思。”
“它也许算一个准学术著作,不是那么很典型的学术书。”周思成说,“只要读者喜欢,不管他是研究宋史的学者,还是对历史本身感兴趣的,哪怕就是对王安石本人感兴趣的,他读完之后有一点收获,我觉得就挺好的。”
“他在这本书上是有一点野心的。”刘勃对周思成的自谦之词持保留态度。“他尝试对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重大问题——譬如就‘如何约束皇权’这个古代思想领域的核心命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解释,甚至有通贯整个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企图。”
在中央编译局上班时,周思成每天早上在地铁通勤要花上50分钟。这是他一天里精神状态比较好的时段,他不想浪费时间在刷手机上,但似乎也不适合读过于精深的书。于是他用来读《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这样的大部头史籍,每天读一到两卷。“在地铁上读文言文,是需要集中一点精力的,让你忘掉身边人的吵闹声,或是刷短视频的声音。同时,读编年体史书又不需要读每段都思维连贯,中间被打断、跳过去一两句,也没什么关系。”
七八年下来,他在地铁上把《资治通鉴》读了两遍,《通典》、《文献通考》各读了一遍。在读关于北宋最重要的史料之一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时,这位蒙元史学者感受到强烈的对比——相比元代高层政治稀少寥落的记载,北宋朝政治史史料空前丰富,“包括它的行政运作、信息流通等等各种的记载都保留下来,特别是担任宰执的高官们自己记录的君臣奏对、朝廷政事等。”
他最受触动的,是宋神宗时期施行变法后——主张变法的王安石、章惇、吕惠卿等人,反对变法的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等人,两派人物在朝堂内外有这么充分的见面、思想交锋的机会。每次读到王安石与其他大臣“吵架”,他都会写下一条粗略的读书札记。几年下来,有关王安石“强辩”和宋神宗“治术”的条目,是他写下札记最多的。
那时,周思成的个人兴趣已从军事史转向,开始对思想史好奇,因为“历史做到最后,还是要深入到那个时代里人们的心灵和情感”。在阅读萧公权、刘泽华等前辈写的政治思想史著作时,他也感到一些不满足——这些思想史大多是梳理、评价某位人物或某个学派在某篇文献里提出过什么不同于前人的思想学说,在思想史脉络里具有怎样的地位,譬如《管子》的思想、陈亮叶适的思想、李贽的思想……
“但是,我感兴趣的是中国几千年积淀下来这么多政治思想,譬如‘民本’、‘华夷’、‘天命’这些观念,到底对中国人的实际政治运作有什么影响:它们对当时的政治决策起了怎样的作用?那些皇帝、官员真是按照那些政治思想来行动的吗?还是说只是当作表层话语来论证他们自身已经设定好的目的?如果是事先设定好的,这些目的与他们所持的政治思想之间有什么关系?”
“熙宁变法”给他提供了一个观察宫廷政治决策过程的绝佳窗口——在这个中国历史上少见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黄金时代,皇帝走出内廷,直接与大臣们交流,角色宛如西方议会的议长,亲自主持不同派别之间的政治辩论。
在那个群星璀璨的历史年代,他也看到所谓的“北宋天团”——书生政治家群体的缺陷,以及这场政治论争走向动荡和失败的必然性。“他们的辩论看起来很激烈,其实政治辩论的思想水准并不太高。”
“像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这些人,他们都是很卓越的文学家、思想家,也是政治家。但是今天来看,他们的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真正面对挑战的时候,有很多心有余而力不足。”

司马光(视觉中国/图)
“党争”背后的思想资源和制度框架局限南方人物周刊:说到北宋,大家都会觉得很惋惜,出现了难得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的政治气象,尤其是神宗皇帝,很喜欢讲道理,也有走出内廷的自信,与其他时代的绝大多数皇帝不一样。他也鼓励大臣们通过政治辩论来定国策。两派精英也都有充分、热烈的辩论,尤其王安石是以“强辩”著称的。
但我们也看到,北宋政治最后陷入了严重的“党争”,新旧两党都缺少必要的宽容,一方得势后就把另一方打倒,反反复复好几回。如此充分的政治辩论为什么达不成共识,反而引向了这样的恶果?
周思成:今天,我们讲宋代政治史一般都会讲“党争”。我们常常把“党争”理解为不同利益集团或不同政策倾向之间的竞争,当然他们之间会有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譬如同年、同乡或是有婚姻关系。但在这些之外,在思想方面到底有没有一个更深的框架在困扰着他们,或者一个阻碍他们、使他们没有办法通过辩论交流来达成共识的深层次的机制呢?
我做了这样一个讨论的尝试,目前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结论。我自己倾向于认为:他们以历史为典据,喜欢旁征博引历史上的事件,用儒家那些道德化的话语来谈论政治,一些本来很好的思想资源,比如“民本”、对“天命”的敬畏等等,反而成了政治辩论中的游戏和工具。这个可能是君主专制制度下儒学本身的困境,或者多少反映了士大夫政治能支配的思想资源的局限。
如果在一个治平之世,一个不需要大动干戈搞改革的时期,它也许能够维持下去,有个惯性慢慢地往前走。一旦需要面对改革、战争这样的挑战,甚至需要它的政治(结构)本身、社会各个层面都要变革,能够为这样一个大动作提供的思想资源是很有限的,或者说能提供的只是一些浮在表面上的概念。这些概念谁都可以用来为自己谋利益。这就让他们不得不陷入这种分裂,一个没有结果、也很难达成思想共识的思想激荡之中。但是,他们找不出一个能够改变这种局面的观念思想上的突破。
南方人物周刊:我们可不可以说这场与改革相关的政治辩论来得太早了一些?如果参照西方的政治辩论和决策的话,英国的议会政治走了很漫长的路程。
周思成:因为议会本身也是在一个很复杂的历史情境里形成的,它是由贵族、教会、新兴资产阶级、商人这些跟王权很不一样的势力组成的,所以他们的政治辩论或共同意志达成,其实是一个在不断地对抗、妥协、调适的过程。但是,士大夫本质上是一群依附于皇权的知识分子,他们彼此又很同质,所以他们的出路何在呢?
我觉得一旦遇到像“熙宁变法”这样的事件,或者说一旦遇到北宋晚期真的需要奋起改变局面、解决冗兵冗官冗费这些根本问题的情况,很难有一个能让他们顺利推行改革的思想资源,或者达成一个共识的制度框架。
南方人物周刊:说起来还挺让人痛心的,这两个彼此水火不容的派别,实际上是一批很杰出的人物,至少领头的王安石、司马光、苏氏兄弟等人,无论是个人道德操守,还是身上的理想主义、学识和才华,怎么就弄成这种局面?
周思成:我有时会想,如果他们是明代张居正那样的人,或者是唐代刘晏(记者注:唐代经济改革家、理财家,为“安史之乱”后的唐朝经济恢复发展做出过贡献)那种更加务实的、更多以功利或技术的角度去处理问题的政治家,可能还会好一些,但是像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这些人都是大儒,都是大学问家,又是大道德家,他们把很多道德感带入了政治,而道德直觉是没有办法彼此说服的。就像我的书后面讲的,王安石认为地方豪强掠夺百姓不对,那就要国家出面去解决这个事情;司马光认为国家就是一个“必要的恶”,你最好不要给国家或官吏更多的机会来压榨百姓,你给的机会越多,压榨越厉害。
这两者之间的政治预设或者基本道德感就是不一样的,本身没有任何可以达成共识的机会。他们以为可以,因为他们觉得大家都是读儒家经典长大的,都是通过科举选拨当上官的,又都有从地方到中央的经历。但是,实际上他们的道德感没有办法调和,因为儒家思想和帝制中国的政治体制不能给一个出路。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最后陷入“党争”,诉诸权力斗争,选择利用人性的缺陷而不是道德感,大概是必然的。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徐琳玲
责编 周建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