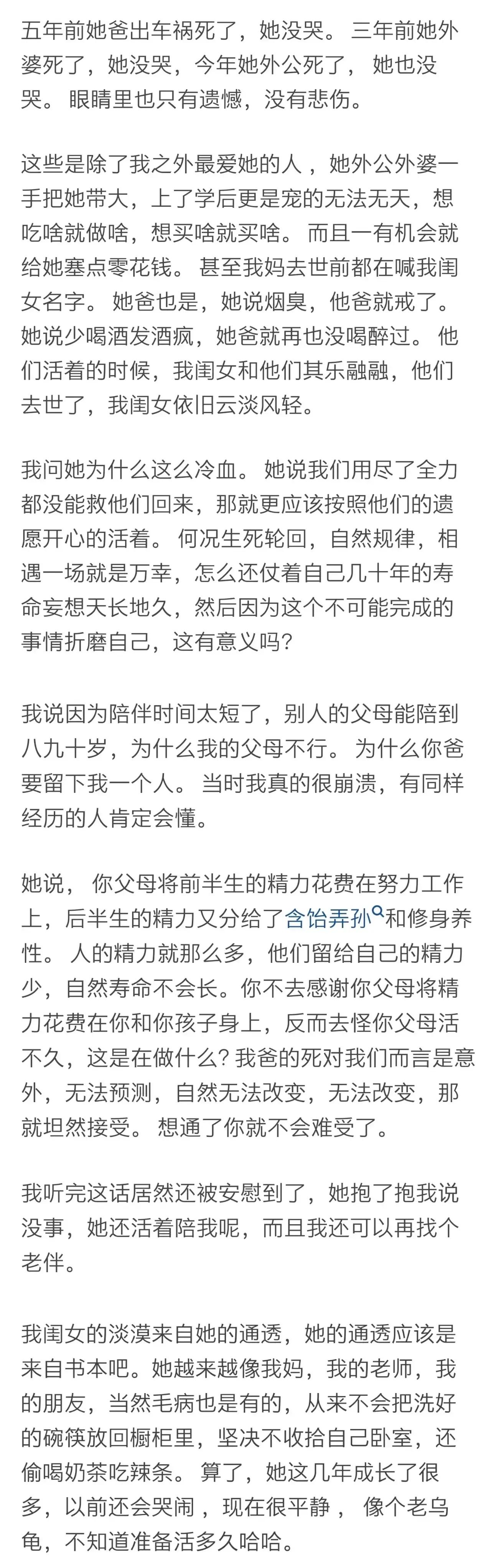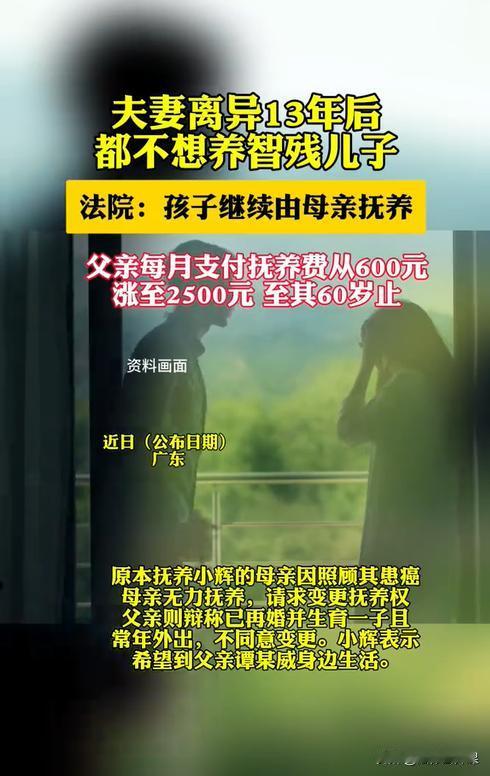1998年3月17日清晨,广东惠阳市(现为惠州市惠阳区)公安局驶出,朝着湖南方向急驶。车内一位六十岁开外的老者心乱如麻。车窗外的多彩景色一幕一幕地向后退去,但他无心欣赏。
老者名叫刘润琪,家住惠阳市郊农村。3天之前,他家被视为掌上明珠的两岁的小孙女刘雯与保姆凌春梅一起突然失踪,一家大小为此恐慌之极,出动数十人找遍了附近的乡村集镇,又通过新闻媒介寻人,但一切都无济于事。

3天过去了,正当一家人心急如焚而又一筹莫展的时候,头一天深夜忽然接到一个电话:“刘老头,你现在大概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了吧!”一个女人的声音说。
“你是谁?”刘润琪顿时警觉起来。
“哟!连我的声音也听不出来了?”对方挖苦道。
“啊,听出来了,你现在在哪里?”
“湘中安化的大山里。很抱歉,我没有征得你的同意,就把雯雯带来了。”对方的声音一直很平静。
“有事好商量,都怪我过去对你不好,你千万要带好雯雯。”刘润琪忙不迭地道歉,生怕惹恼对方。
“我会带好她的。不过我白白为你服务了那么长的时间,工资和身心损失费一点也没有到手,你的心也太狠了。”
“只要交还雯雯,要什么都可以。”刘润琪很慷慨地答应说。
“3天之后,带3万元现金到安化县城车站附近的欣欣旅社,一手交人,一手交钱。不要报警,如果报警,就别怪我不客气。”对方的口气变得有些强硬起来。
“行!行!一定照办,一定照办!”此时的刘润琪只有点头的份儿了。
放下话筒,刘润琪已是满头大汗,半天回不过神来。听到雯雯有了消息,儿子、儿媳立即凑了过来,但一听详情,又一个个急得毫无主张。一家人经过合计之后,觉得除了报警,别无良策。于是,一家人连夜敲开了惠阳市公安局的大门。
惠阳公安局便派三名干警和刘润琪一起乘车奔赴湘中安化。

那么这个女人到底是谁?
这个女人叫凌春梅,湘中安化与桃源接壤处有个叫金园沟的小村子。凌春梅嫁到金园沟是农村里一桩极普通的婚姻。她初中毕业没能考上高中,在家里做了几年闺女,父母便胡乱给她择了个对象嫁了过去。
金园沟的村名虽然带个“金”字,却是个穷得“屙屎都不长蛆”的地方。而凌春梅的婆家更是穷上加穷,一年到头吃不上几顿白米饭,穿不上几件像样的衣。这里交通极不方便,到乡政府办个事,到集市上赶个集,都得爬几十里山路。凌春梅的丈夫杨家和是个典型的山里农民,一年到头只会在那几分土地上转着圈圈。别看他挣钱无术,但却嗜酒如命。
几年过去之后,凌春梅先后生下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家里人口剧增,家庭负担犹如雨天挑稻草——愈来愈重。
又过了几年,孩子渐渐长大了,双双走进了学校,开始念书。
家庭收入微薄,但家庭开支却好像一个巨大的黑洞,拼死拼活弄来几个钱,怎么也填不满那个无底的洞,以致债台越筑越高。家庭经济紧张也就导致了家庭关系的紧张,两口子常常因为手头拮据而互相埋怨,有时甚至争吵不休。
夫妻俩心里都明白,这个家庭很需要钱。只有有了钱,才能消除家里的两个“紧张”。而捞钱,对于这对山旮旯里的农家夫妻来说,又谈何容易。

又是一个农村赶集的日子,夫妻俩挑着一担土产品去集市上交易。山里人别说省城、县城,就连这小小的乡政府所在地也难得来一回。卖完自己的产品,换回了一些日常生活品,双双踏上了归途。
肚子饿了,他们便走进路旁的一家小店,想吃点东西。店里坐了不少歇脚的人。他俩随便找了个座位,要了两碗面条。人们在胡吹乱侃:“要想富,广东去。听说广东那地方好挣钱。”
一个中年人说。“好挣个屁,卖苦力的同样不赚钱。”
一个穿T恤衫的年轻人显然很熟悉广东的情况。“去广东挣钱,男人不如女人,你看看,周围这些小洋房,大部分都是女人从广东挣钱修的。”
另一个穿白衬衫的年轻人用手朝外画了一圈说。“你没听说,哪家的房子最高,便是那家的女人最乖;哪家的房子最矮,那家一定只有崽。”
那位穿T恤衫的后生话音一落,立即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
杨家和与凌春梅也跟着笑了。笑过之后,两人又渐渐陷入了沉思。
杨家和瞟了一眼凌春梅,妻子虽然年过三十,但青春的光泽尚未褪尽,山里人确有些土里土气,但仍掩饰不住上天赐予她的几分姿色。凌春梅似乎受了些启发:同为女人,为什么别人能赚钱,自己就不能?

这天晚上回到家里,两人都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做着自己的梦。凌春梅似乎觉得广东那个地方,到处都流淌着白花花的钱,随便伸手一抓,就能抓上一大把。杨家和在想,让女人出去赚钱,实在是下策,但目前的困难处境又怎么解决呢?天穹深处,星星闪烁着,静静地窥视着地面,夜晚是多么温馨而幽美。
半夜了,凌春梅没有半点睡意,干脆坐了起来,用手推了推杨家和:“喂,我看与其在家里这么受穷,还不如出去想点办法,你愿不愿意我出去走一趟呢?”
杨家和听了凌春梅的话,许久没有作声。半晌,才叹了一口气,极不情愿地说:“我怎么会愿意让你去受那份罪呢?只是家里现在这个样子,出去挣点钱回来,缓解一下也好。”
“我走了以后,家里这一摊子都得你来担,你吃得消吗?”凌春梅有些不放心。
“孩子开始懂事了,他们会听话的。要去,你就不必挂心家里。赚上一点,就早回来。”
杨家和同意凌春梅出去了。
凌春梅眼里闪过一缕泪花,声音有些哽咽:“那么,这个家就交给你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心里永远只念着你和这个家。”
杨家和咬了咬嘴唇,没有说话,默默地让泪水流进了肚里。
凌春梅走进了广东惠阳市区的一家发廊。
她很不适应这种生活,且不说丝毫不懂所谓的那种“按摩”技术,更主要的是那种所谓的“服务”令人感到讨厌。
不过,既然出来了,而且是被贫困逼出来的,不适应也得强迫自己适应。
是邻村一个经常跑广东的年轻女人带她出来的。那个女人“经验”丰富,在这里颇能左右逢源,什么样人都能应付。相比之下,而凌春梅则显得别别扭扭,呆头呆脑。在发廊里,她在那些“顾客”面前显得局促不安,更不会卖弄风骚,因此,她的“按摩”生意要比别人差一大截。
一段时间下来,她几乎没挣到什么钱,连混下去都有些困难。她不得不学着别人的样另辟蹊径,住进了一家个体旅社开始接客。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别的女人生意十分红火,而她的房前却门可罗雀。

她开始恨自己无用,不得不承认自己与人家在捞钱方面有一定的差距。
她有些心灰意冷,出门前的那种热情已经荡然无存。
此时此刻,她很想家,想孩子和孩子他爸。直到现在她才有些怀疑自己来广东的主意是否欠妥。说实在的,家里是穷一点,日子不太好过,但毕竟处处可以体会到温暖,这个地方远隔家上千公里,举目一望,满眼都是陌生的面孔,别说挣钱,连生活都成了问题。
正当她打点行李准备回家的时候,一位嫖客的出现却改变了她的打算。
那天晚上,一个年约六十岁的老头走进了她住的旅社。事毕,他塞给她两张百元大钞,但没立即起身离去,而是紧挨着她坐了下来。
“看你满面愁容,好像有什么心事。”老头善意地问。
她望了一眼他那张苦瓜般的脸,欲言又止,她不愿意与一个陌生人谈自己的身世。
“我看你怪可怜的,一个女人孤身在外面闯,又没个男人在身边,长此下去怎么行呢?”他专拣那些她爱听的话说。
一句话勾动了他的心思,她的眼圈红了。
“不妨随便聊聊,我这个人最同情受苦人,在家千日好,出门事事难,出门的人难处一定很多,有什么困难尽管说,就算咱们交个朋友吧。”
老人有些讨好女人。她经不住老人的劝说,向他诉说了自己目前的处境。她说她与前夫感情不好,离婚之后才走上这条路谋生。
老头对她的身世似乎很感兴趣,在她介绍过后,也毫无保留地向她交流了自己的情况。他说他叫刘润琪,家住惠阳市区附近的农村里,今年刚过“花甲”,老伴早年去世,之后没有续娶。他要她不急于回去,他会常来,生活问题以后慢慢为她想办法。
直到第二天清晨,他才离去。
果然,过了两天,老头又来了,给她买了一身衣服,又给她带来了些吃的。
这是她出门后第一次感受到人间的温暖,她的眼里闪动感激的泪花,不知说什么才好。

他说他原来想为她找个打工的地方,解决一下暂时的生活困难,但跑了几处地方,都没有结果。不过,如果她愿意的话,可以先到他家里去住一段时间,与他做个伴,也为他操持一下家务。儿媳妇快生孩子了,将来还可为他带带孙子。
她很感激,但提到住到他家里去她又有些犹豫了。她是出来挣钱的,不完全是为了搞碗饭吃。
刘老头似乎看出了她的心思,连忙解释说:“我不是让你为我白干,包吃包住,还每月付给你800元工资。你如果要回家,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
她放心了。对于一个来自穷乡僻壤的女人来说,每月800元的固定收入不算少。因此,她欣然跟着刘润琪上了路。
刘老头领回了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自以为艳福不浅。凌春梅扮演的角色将是情妇加保姆,因此,他心里喜滋滋的,觉得自己一下子年轻了许多岁,也觉得自己干了一件很划得来的绝顶聪明的事。
刘润琪的儿子、儿媳对父亲的举动有些不太乐意,这个女人在家里继母不像继母,兄嫂不像兄嫂,觉得有些别扭。但他们明白父亲心中自有他的“小九九”,也不好横加干预。凌春梅既然成了这个家庭的临时成员,也就只好暂时把远在湘中山里的那个家搁下,把自己融进这个临时的“家”。
事实上,她已把自己“租”给了人家作妻子。
为了那个每月800元,白天,她主动挑起了全部家务,将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晚上,她就陪着比她大二十多岁的刘老头睡觉。不久,刘润琪的儿媳生下了一个女孩。一家人喜不自禁,刘润琪更是视为掌上明珠,给她取了个名字叫刘雯。凌春梅自然又成了刘家孩子的保姆。好在凌春梅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带小孩、照顾产妇是轻车熟路。那段日子,她真的忙得够呛。

凌春梅的表现使刘润琪非常满意,对她的身世更深信不疑。既然是离婚的女人,家里大都没有什么牵挂。因此,他暗地里盘算着要把春梅长期留在家里,留在自己的身边。
说来也怪,自从有了小刘雯以来,凌春梅感觉到日子比以前好打发得多。
小刘雯的圆圆脸蛋就像春天的花那样姣媚,小手小脚就像风吹柳枝那样撩人。尽管春梅与她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可日子长了,春梅对她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家务事情很多,有时她甚至感到有点累,但一抱起小刘雯,疲劳就立即跑到九霄云外去了。
小刘雯很乖,也很听她的话,与她关系很融洽。
这个原本十分复杂的畸形家庭居然和和睦睦地过着日子。
这年的春节到了,“每逢佳节倍思亲”,看到人家热热闹闹地准备过大年,凌春梅开始想家了,有时做梦也梦到自己的亲人。她向刘润琪提出要结清这几个月的账,回家看看父母,但她仍然没有向他讲自己家里的秘密。
像是遇到了一道难以解答的难题,刘润琪半天没有作声。
她要回去看看父母,理由是充足的,如果不放她走,说明自己一点也不通情理。如果放她走,他担心她一去不返。
他在房里踱着步,好一会他才开口说:“我真舍不得你走,更担心你走后不会再来,我想……”
“我会来的,你不必担心。你们一家待我很好,我不会无情无义的。”她生怕他不放自己走。
“行是行,不过,你既然肯定来,那么我想,你先拿一个月工资,其余的我替你存着,明年你来的时候我再一次给你。”他终于亮出了他的想法。
“你就全部给了我吧,我父母年老体衰,身体不好,盼我挣点钱给他们治病呢。”她几乎在哀求他。
他没有理会她的哀求,而是静下心来劝她:“钱我替你保管,没错。雯雯还很小,她很喜欢你,你一定要来,要把她带大。”
凌春梅回家心切,一时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带上那一个月的工资忿忿地上了路。

对于凌春梅的归来,一家人先是高兴了一阵子,但听说她没有带回多少钱时,杨家和如堕冰窟。她当然不能对杨家和如实相告,只是说外出时间短,外面开销大,所以积累的钱不多。如果再次去广东,一定能够挣上大钱。
面对妻子的解释,他有些听不进去。对妻子要再次去广东,他说什么也不同意。
春节本来是愉快的,但凌春梅的家里却笼罩着一层阴影。
几百元钱对于一个负债累累的农家来说,当然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多大问题。凌春梅自然想到那一笔属于自己但尚未到手而且不能向丈夫公开的钱。杨家和却认为她挣不到钱就没有必要再次外出。两人围绕着去与不去问题闹得不可开交。最后杨家和还是拗不过凌春梅,让她去了,只是叮嘱她挣不到钱就尽快回来。
在凌春梅回湘中的那段时间里,刘润琪没睡过一个好觉,没吃过一顿香饭。
凌春梅终于又回到了自己的身边,这使得他高兴异常,他暗暗为自己的计谋成功而庆幸。他生怕她再次从自己身边飞走,要想办法牢牢地控制住她。
凌春梅当然不想长期呆下去。住下没几天,就向他问起那笔钱。
他笑嘻嘻地拿出一本存折朝她面前一晃:“我替你存的是定期,今年的工资我也替你按月存着,到了年底一并给你。”
她瞟了一眼那本存折,上面赫然写着自己的名字和上年足额的工资数,心底倏地得到一丝安慰,忧郁的情绪也似乎舒畅了些。
她粗略地算了一下,到了年底,两年加在一起可以拿到一万多元,这是一个多么具有诱惑力的数字啊!于是,她留下来了。

春去冬来,凌春梅在无奈中又度过了一年。
1997年春节到了,她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住自己对家的强烈思念,便向刘润琪提出,她在他家已经快两年了,雯雯也已经差不多两岁了,她该回去了。
刘润琪说什么也不让她走,苦苦地留她:“你反正又没有一个固定的家,在这里不是一样过日子吗?”
事到如今,她觉得不能再隐瞒自己的实情了,于是,她尽量使自己平静下来,向他吐了真情:“老刘,我不该瞒着你。其实,我与我的前夫没有离婚,我有一个家,只是由于生活所迫,才来到外面闯荡。我请求你高抬贵手,付给我工资,放我回去,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的大恩大德。”
听完凌春梅的叙述,他先是眉头微皱,眼神暗淡,一种郁郁不乐的神情出现在他那黝黑的脸上。紧接着,脸色涨红,渐而发青,吼了起来:“你、你是个骗子,你欺骗了我的感情!”
凌春梅满肚子委屈,但是有口难辩,急得大哭起来:“你就行行好吧,看在我是个苦命人的面上,看在这两年为你服务的面上,打发我走算了。”
“世上有那么容易的事吗?你要走就走,要钱没有!”他把脸扭向一边,没好气地说。
凌春梅望了一眼他那张扭曲的脸,脑袋涨得像要爆炸,哭声也提高了八度:“你这个天杀的,不给钱,我死在你面前!”说着,一头朝刘润琪撞了过去。
刘润琪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有些手足无措。不过,他很快镇定下来,一把扯住她,吼道:“要死就死,你以为你死了我就会吃官司吗?你家里的人会千里迢迢来打架吗?我告诉你,你搭上一条命也是白搭!”
凌春梅止住了哭,想了一下刘润琪的话,觉得有些道理,来硬的看来不行,弄不好钱未拿到还搭上一条命,真不值得,对付这样的人,还得慢慢想办法。于是,她尽量使自己冷静下来。

过了一天,气氛有些缓和。她强忍着心中的痛苦和愤怒,再次向刘润琪哀求:“让我先回去过了年,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
刘润琪见她情绪好转,也就欣然同意,给了她路费和一个月工资,一再嘱咐她:“过了年再来,来了后什么都好说。”
就这样,凌春梅走了,带着一颗破碎的心。
凌春梅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进家门的。她觉得对不起丈夫,也对不起孩子,一路上,她走路都打不起精神。丈夫本来不允许她再次外出,但她不听,去了,而且几乎再次是两手空空回家。现在向丈夫怎么交待?
也许,她面临的将是一个破碎的家。
果然,她前脚刚刚踏进家门,杨家和就怪声怪气地问:“发财回来啦?”
她面容憔悴,无言以对。
“你怎么不死在外面!钱没挣到,脸让你丢尽。”杨家和破口大骂。
她两眼泪汪汪地望着丈夫,声音哽咽着:“你听我解释一下好吗?”
“解释有屁用,我要的是钱,钱呢?”杨家和越说越气,走上前去,“啪,啪”,就是两个耳光,扇得她眼冒金花。
她捂着火辣辣的脸,心里就像插进了一把刀,泪水顺着脸颊淌了下来。
“你给我滚,免得在我眼前刺眼!”杨家和连推带搡,将她赶了出来。
她如一只跑进了风箱的老鼠,弄得两头受气。她想自己的命真苦,便嚎啕大哭起来。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她跑回了自己的娘家。
她恨,恨杨家和没有一点儿夫妻情份;但他更恨刘润琪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是他害得自己有家回不得。
她的心里充满了仇恨,时时想到报复,有时甚至想到杀人,要泄泄这股心头之恨。

春节过去,人们又陆续开始了新的忙碌。凌春梅在家里呆了一段时间,心里实在闷得慌。她要再次南下广东,去要回那笔自己已经付出了代价的钱,要不回钱也要出出心头那口恶气。
刘润琪正为她的离去充满了惆怅。她的到来又给他增添了无限的喜悦之情。
他要设法将她留下来与自己长期过日子。但她却有着另外一番打算,只是没有表露出来。
她不冷不热地住了下来,问他去年年底对她说的话兑不兑现。
他没有立即回答,沉思了好一会,然后把手搭在她的肩上劝道:“你呀,就不必死心眼了,难道这地方就不比你那个穷山沟里强?回去离了婚,在这里与我一道好好过日子,我会使你永远幸福的。”
她推开他的手,起身走到窗前,两眼凝视着窗外,久久没有说话。她想到过杀人,但女人毕竟缺乏那份胆量。她想到过放火,但她知道那样做除了损坏他一点财产之外,自己又能捞到什么好处呢?她心里沉闷,不想做事,十分烦恼时就逗逗雯雯。一天,在雯雯那充满稚气的脸上,她似乎发现了希望:雯雯是他们全家的心尖儿,将雯雯控制在手中,就不愁刘润琪这老鬼不给钱。机会终于来了。
1998年3月14日,刘润琪的儿子、儿媳上班去了,刘润琪也一早进了城。她清理了一下自己简单的行李,然后将雯雯抱在手中,亲昵地问道:“你喜欢我吗?”
“喜欢。”
“我带你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去玩好吗?”她懂事地点了点头。
事不宜迟,她急匆匆地抱起雯雯出了门,在公路上拦住了一辆开往广州的中巴车……
广东警方在湖南益阳市安化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的配合下,在县城将凌春梅抓获,然而小刘雯却已经死在旅社的床下……

原来,当凌春梅带着小刘雯回到安化县的当晚,她们住在一家小旅馆。这天晚上,小刘雯一直吵着要回家,并且大哭,凌春梅害怕被人发现,所以用手捂住小刘雯的嘴,哪知凌春梅情急之下竟将小刘雯的口鼻都捂住了。后来当凌春梅发现小刘雯没有反应时,小刘雯已经死亡了……
凌春梅是既可恨又是可怜的,最终她被判处无期徒刑。
刘润琪的行为可鄙可恶,他除了受到舆论、道德、良心的谴责之外,法律对他能有什么说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