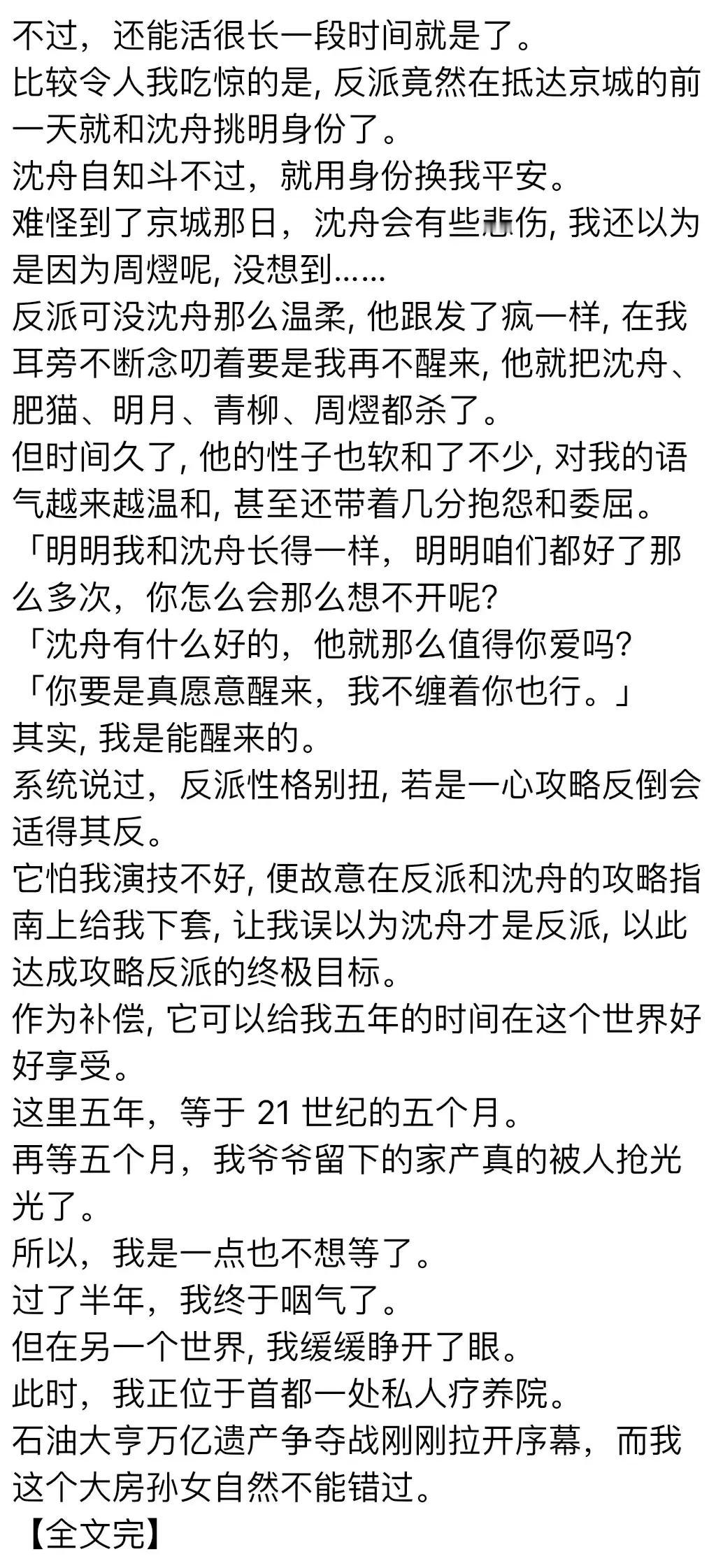简介:女主上一世就和自己的驸马斗智斗勇,互相看不顺眼,重生来过的女主想不通自己只是想安安稳稳的享受人生,奈何自己的驸马野心勃勃的要踏到权力之巅的地位,男主起初对女主自命清高的样子很是看不顺眼,婚后还时不时的对男配吃醋,从开始的不屑一顾,到后来无论前世还是这一世都无可救药的爱上女主!
【文章片段】
这次宫宴,不止皇室中人参加,一些权贵大臣家的公子贵女们也会参加,皇帝的意思,他们这些年轻人难得聚在一起。
萧续对萧裕嘱咐再三,勒令他一定得赏脸。
这是他们萧家入京之后参加的第一次大型宫宴,又是五公主生辰,萧裕怎么都要来,除此之外,还备上了给五公主生辰礼,进宫时候一并带上。
不过一次普通的用膳,萧裕没想那么多,他就遵照他父亲的命令,进宫,然后坐下安静吃东西即可,吃完便撤。
跟他一起来的萧子恒,看着满桌的新鲜菜肴,口水都快收不住了。
看着自家弟弟的样子,萧裕更加确定他弟弟就是为了吃才来的,也罢,吃饱了好回家。
他们兄弟俩刚入座,便有不速之客想来找不痛快。
萧裕对面的那个公子见他们总算来了,斟满一杯酒,开始寒暄。
“呦,萧子羡,你可算来了啊,你再不来,我还以为你萧家势大,不肯给陛下这个面子呢。”
萧裕悠闲坐下,回他:“不过是坐下来吃几口菜罢了,我自然不会驳陛下的面子。”
对面的那人却不打算就这么结束,他接着笑吟吟道:“我突然想起来了,今天,可是五公主的生辰呢,我就知道,你不会缺席的。”
萧子恒气不过,想要与他理论几句,被萧裕拦下了。
“萧子羡,你可知道,自从你们萧家拒婚之后,五公主可是一直待字闺中啊,你就没什么愧疚吗?”
萧裕道:“当年我拒绝指婚,是深思熟虑的决定,我远在关外,无法即刻赶回京城,五公主乃金枝玉叶,我自然不忍其闺中苦等,所以拒婚,望她能觅得良人。”
屏风的另一边,赵玉梳一边用箸夹着鹿肉,一边听着那边的争吵。
“五姐姐,你听听这萧二郎,还真是冠冕堂皇,还说什么望你能觅得良人,我看他当初就是不想娶,平白连累你的名声。”
赵玉珠做了一个“嘘”的动作。
萧裕对面的人依旧不依不饶:“可惜啊,你的美好祝愿落空了,五公主到现在还待字闺中呢,不知道是她眼光高,还是没人要啊。”
席间有人吃醉了酒,接着他道:“自然是没人要了,跟她的几个姐姐一样呗,萧二郎,要我说,你就发发慈悲,把她娶了吧,尚公主就尚公主,我瞧着五公主的性子还算温柔,不会辱没你的!”
萧子恒急了,这些人一阵撺掇着萧裕尚五公主,就是故意的,想叫萧家蒙羞罢了,这种屈辱他兄长受得,他却受不得。
他连肉也不吃了,拍了一下桌案拔地而起,指着那人道:“呔!你个猢狲莫要出言不逊,你要是缺婆娘,你就自己去娶!我父亲早就有中意的儿媳人选了,我兄长亦有了心上人,任那五公主再貌若天仙,我哥都不会看一眼的,更不会娶,我们萧氏百年望族,无须靠着当驸马来延续荣光!”
继萧子恒气急败坏之后,赵玉梳也坐不住了,她不顾赵玉珠的阻拦,起身就走到屏风的另一边,突然冒出个女人来,在场的人皆吓得不轻。
“刚才是谁说我姐姐没人要的?”
霎时间,所有人噤若寒蝉。
赵玉梳气道:“不知这位公子为我大齐领了多少次兵,杀了多少个士兵将领,挣了多少荣功,众目睽睽之下,竟然在宫宴上大言不惭,编排我五姐姐,不论如何,我姐姐都是大齐的公主,代表着皇室,是我父皇的脸面,我看是谁胆敢如此讥笑于她?”
萧裕对面的人瞬间哑口无言,只拱手:“是在下失言了。”
此女子既然称五公主作姐姐,自然也是公主。
赵玉梳再怎么气不过,还是被赵玉珠拉了好几丈远。
赵玉梳一边被她拉着,一边发泄着怒气。
“姐姐可瞧见了,那人简直张狂无度,咱们再怎么不济,也是公主,公主,公主!岂容他们折辱!”
赵玉梳从没有如此生气过,这也是她第一次体会到了皇权的式微,那些人就是知道如此说不会有任何后果,皇帝也只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他们仗着身后有家族撑腰,便无拘无束。
经过这一遭,她也更加坚定了自己心中的计划。
赵玉珠贴心地摸摸她的胸口,安抚她道:“好啦,你骂也骂了,消消气吧,白瓷,送你们公主去更衣。”
赵玉梳被侍女们簇拥着往东边的厢房走去,走着走着,她停了下来,或者说,她在原地来回踱步。
她握着手中的帕子,自言自语道:“不行,我不能去更衣,我得去离御膳房最近的那条道,计划得进行下去,我不能半途而废,否则,我姐姐可是白受了这么些委屈。”
-
“春晓!”
宫道上,侍女春晓正端着茶水低着头有着,听到一旁有人喊自己的名字,她停下,朝着声音的方向看去。
然后微微屈膝,行礼:“六公主万安。”
赵玉梳蹦蹦跳跳地跑出来,看了一眼她端着的茶水。
“这些是要送去那边的吗?”
“回公主,是的。”
“春晓,最近宫宴事情多,你辛苦了,这茶水我让白瓷帮你端过去吧,你去厨房忙剩下的吧。”
春晓疑惑地“啊”了一声。
“公主,真的要这样吗?”
“哎呀我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你真是聒噪。”
“是。”
春晓手上的方盘小心翼翼送给了白瓷,行了礼便退下了,赵玉梳打开那茶壶盖子,朝里面闻了闻。
“这茶还是挺香的,就是太烫了。”
白瓷贴心道:“公主,奴婢这就送过去。”
“哎,等一下……”
白瓷不明所以:“公主,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我都说这茶水太烫了,你这么端过去,不怕烫伤他呀!”
旁边的彩釉捂着嘴憋笑:“公主还没见萧将军几面呢,这就心疼上了。”
赵玉梳怼了彩釉一下:“你这丫头胡说八道什么,宫中到处都是耳朵和眼睛,你竟然如此坏我清誉,实在该打!”
彩釉倒不会真的怕了赵玉梳,赵玉梳从神情还是语气上看,都未真的生气,不过是与她打闹罢了,她们从小便服侍公主,公主的脾性她们最是清楚。
彩釉见四周没人,胆子也不小,接着揶揄道:“公主,奴婢现在不说,等事成了,再说也不迟呢。”
赵玉梳吩咐白瓷道:“你记得把这茶水换了,换常温的水即可,要不然,把人烫伤了可怎么好。”
“奴婢清楚了。”
赵玉梳不放心,接着提点她:“记得找准时机,力度大一些,要不然不痛不痒的,可能会出差错,你先去换水,我这就赶回去,咱们别一道回,恐叫他们怀疑。”
“是。”
赵玉梳吩咐完白瓷,便急匆匆地回了自己的座位。
大概过了一刻钟,萧裕想出恭,他起身询问旁边的侍从更衣的地方,刚走了几步,准备了多时的白瓷疾步而来,她看准了时机,与萧裕相撞,“砰”地一声,她手上的茶水尽数泼到了萧裕身上。
萧子恒大惊,他走上前,打量着萧裕的全身,询问道:“哥,你没事吧?有没有烫到?”
萧裕摆摆手,示意他没事。
萧子恒怒道:“你这贱婢,怎么走路的,这地方这么宽,径直往我哥身上撞,是不是别有用心?”
萧裕皱了眉头:“子恒,切莫如此咄咄逼人,我没事,只是衣裳湿了而已。”
白瓷即刻下跪,哭着求饶:“公子,奴婢有罪。”
赵玉梳眼见着这边的情况,知道该自己出场了,她故作惊慌状,闻声匆忙赶来,看到了跪在地上哭声不断的白瓷。
“这是我的侍女,她毛手毛脚的,惊扰到二位公子了,玉梳在这里,代她向二位公子赔罪了。”
萧裕颔首:“公主不必如此,我到底没伤到。”
赵玉梳微微歪着头,道:“公子,您的衣服湿了,不如我带你去换一件吧,天冷,衣服湿了可是会受凉的。”
萧裕愣道:“不……不必了。”
赵玉梳见萧裕有些迟疑,也不放弃,接着道:“还是换一件吧,衣服湿了也影响仪容。”
萧裕犹豫片刻,应道:“有劳公主了。”
萧裕知道自己真的很不争气,竟然就这么答应了,重来一次,他对赵玉梳这个女人依旧毫无抵抗力。
赵玉梳嘴角的笑意更浓了,伸手示意道:“跟我来吧。”
赵玉梳带着萧裕来了更衣室,她娴熟地打开一旁的柜子,仔细翻找着,萧裕在一旁看得一愣一愣的。
他还以为赵玉梳会吩咐侍女为他找来更换的衣物,没想到是她亲自动手……这也太亲密了些。
他抬手,想制止赵玉梳的行为,赵玉梳却抢先一步,抱了一件男子的宝石蓝暗纹长袍走到他身边,萧裕看着那衣服,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
赵玉梳笑盈盈道:“我见公子原先的衣服是玄色,但事发突然,我毫无准备,这更衣室并无玄色衣衫,还请公子将就一下罢。”
萧裕平静接过赵玉梳为他准备的衣服,在他接过来的过程中,他特意避开了与赵玉梳的肢体接触。
赵玉梳问他:“公子平日里喜爱玄色吗?”
“还可以。”
“这样啊,那我记住了。”
萧裕的心口不自觉地颤动了一下。
他们姑且算是第二次见面吧,上次也是不小心撞了一下,没说两句话她便消失在了黑夜里,如今,她却说她记住了他的喜好。
这还是他梦里的那个朝华公主吗?
她不是应该趾高气昂,目中无人吗?何以这般温柔,萧裕好像不知不觉沦陷了。
原来少女时的她也曾如今日这般温婉秀丽,不可方物。
这样的赵玉梳离他很遥远。
看着愣在原地的萧裕,赵玉梳把他拉回了现实:“公子,你愣着做什么,快去换呀!”
赵玉梳指了指屏风后面。
“啊……哦。”萧裕应声。
“你快去吧,我这就离开内室,公子不必拘谨。”
赵玉梳匆忙离开了,萧裕走到屏风后面,打算把自己身上被泼了一身水的衣裳换下来。
赵玉梳却不安分,她用小手扒着门框,一只脚迈过门槛,露出一双眼睛,贪婪地看着屏风后面换衣服的身影。
上次天黑,加上她没怎么仔细看,如今一瞧,当真是身姿卓尔,一看就是以前行军打仗锻炼出来的。
赵玉梳又晃了晃自己的脑袋:“赵玉梳啊赵玉梳,你怎么能如此轻易就被男色迷了心智呢,他里面还有中衣呢,又没露什么,你也真是的!”
责备了自己一通之后,赵玉梳乖乖地将脑袋缩了回来。
他一介武将,说不定警惕性很高呢,若是被他发现什么就不好了,切莫打草惊蛇。
萧裕片刻后出来,谢过赵玉梳后,便回了坐席那边。
赵玉梳看着他的背影,一种奇妙的感觉油然而生。
“他竟然没发现什么。”
要不然,就是刚刚赵玉梳弄得他心绪不宁,才导致萧裕疏忽了,或者,就是萧裕一个大男人,不拘小节惯了,总之,赵玉梳简直是撞大运了。
她本来以为她的手段如此低端,会被萧裕察觉到什么呢,原来这个男人这么好糊弄。
白瓷道:“公主,这样真的行吗?”
赵玉梳倒显得很淡定:“应该能行吧,慌什么,他如此平静地走了,应该就是没察觉,等他二两黄酒下肚,他更是昏昏欲睡,没问题的。”
白瓷只觉得,她们家公主的胆子还真是大啊,也不顾及一下自己的清誉。
萧裕回去之后,百无聊赖地坐了一会,大概在他六分饱的时候,酒也喝得差不多了,便打算离去。
他示意一旁的萧子恒打算离开,刚一起身,走了两步,一样东西就这样丝滑地从他的腰间掉了出来。
萧裕有些醉了,也没多想,只当是自己身上的其中一个玉佩或者香囊。
他刚要弯腰去捡,旁边离他最近的宫女眼疾手快,先他一步把掉在地上的东西拾起来。
萧裕伸手去拿,那宫女却是不让,而是走到赵玉珠跟前,将那玩意递给赵玉珠一看。
赵玉珠不明所以道:“这玉坠子散发出来的香味,这不是小六的贴身之物吗?”
赵玉珠不会认错的,这玉坠子是赵玉梳刚出生的时候,皇后去远山寺求来的,保佑小公主顺遂平安,这坠子还带着香气,这么多年了,经久不散,实是天下间独一无二的珍宝。
对赵玉梳如此重要的东西就这么出现在了萧裕身上,看来他们的关系,当真不一般。
此话一出,全场哗然。
还有些幸灾乐祸之人,趁别人不注意,掩面讥笑。
一个是皇家女,一个是权贵之子,上流贵族之间的那些风月腌臜事,大家都见怪不怪了。
太傅之女高翡窃笑道:“呦,怪不得呢,刚刚萧公子的衣服湿了,还是六公主张罗带他去换的衣服呢……”
去换了那么久,也不知道都干了些什么。
后面的话,她没继续说下去,点到为止,不过很多人也听明白了。
赵玉梳装作娇羞,好像她跟萧裕真有什么一样,她看了看高翡,又看了看赵玉珠,又羞又恼,然后便跺着脚离开了宫宴。
留下一群吃瓜群众还有懵着的萧裕。
赵玉梳离开之后,后面再发生什么就跟她无关了,她也不想去操心别的,反正她的目的达到了。
晚上,赵玉梳穿着里衣,头发披散下来,手中把玩着磁石。
其实今天的这步棋有些险,毕竟哪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出错,如果萧裕不跟着她去换衣服,那她叫白瓷泼他一身水则毫无用处。
而就算萧裕成功换上了她准备的衣服,他腰间的玉坠子也有可能掉不出来,那坠子如果不能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掉下,将毫无用处。
就这坠子放在他身上的那会子功夫,保证萧裕这几天身上都是她的味道,洗澡都洗不掉。
她在手中扔磁石还不够,还要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越走越兴奋,今夜都要睡不着了。
彩釉发问:“公主,奴婢有一事不明,您若是怕玉坠子无法及时掉出来,为什么不自己拿一件他的贴身之物,然后再扔出来呢?”
赵玉梳拍了一下她的脑袋:“你傻啊,东西是从我身上掉出来,还是从他身上掉出来,这可是有本质区别的。若是从我身上掉出他的贴身之物,那所有人的目光都会集中在我身上,这件事的主角就成了我,有可能是我在单方面思慕他,可若是从他身上掉出我的东西,这件事的主角就变成了他啊,思慕我的人是他,偷藏我贴身之物的人是他,大家都是先注意到他。总之,又要达到我的目的,但同时又必须要把对我名节的伤害降到最小,我到底是女子,岂能与他一个大男人硬碰硬,须得以柔克刚。”
她赵玉梳算计来算计去,当然不能吃最大的亏。
“哦……奴婢受教了。”
此时,白瓷慌张跑过来:“公主,五公主来了。”
赵玉梳一愣:“这么晚了,姐姐来做什么……”
还不等赵玉梳请她进来,她便火急火燎地闯入殿中,一来就握着赵玉梳的手,眼中满是担忧。
“小六……”
“姐姐,怎么了,可是有人给你委屈受?”
赵玉珠摇摇头。
赵玉梳急了,既然她没受委屈,怎么如此泪眼婆娑的。
“小六,今天那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原来姐姐是为了这事而来的。
赵玉梳淡定道:“没怎么回事,就是姐姐你看到的那样喽。”
见她如此不屑一顾,赵玉珠严肃道:“什么叫没怎么回事,那玉坠子,我如果没记错的话,那可是你的贴身之物,今日却从一个陌生男子的身上掉了出来,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赵玉梳想了想,试探道:“姐姐……你莫不是还对那萧子羡有情?”
“萧子羡?”赵玉珠又是错愕。
“就是他的表字啦。”
“你连他的字都知道,你何时与他如此熟稔了?”
赵玉梳掩饰着:“哎呀,他这么出众有名,知道他的表字有什么难的,打听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赵玉珠气急:“你还未出阁,打听一个外男的表字做什么?简直有失皇家的体面!”
好嘛,她姐姐又来了。
赵玉珠缓了缓自己的脾气,语重心长道:“小六,我之前说的话一字一句都算数,之前父皇虽然为我和萧家指婚过,但我只当他是一个未来郎君的人选,对他并未有什么男女之间的情谊,我今夜前来,不为别的,只为了你的名节,我是你的姐姐。”
赵玉梳有些不知道该怎么说,只道:“玉坠子这个事,有很多种可能啊,根本没你想的那么复杂,可能是我送他的那件衣服上带的,又说不定,是他爱慕我呢,所以才偷了我的东西,留作纪念呢。”
赵玉珠思索道:“照你的说法,你们之前没有私下见面?”
“当然没有了!我跟他到目前为止就见过两次,一次就是上元节那天不小心撞到他了,第二次就是今天喽,你知道的,他衣服被白瓷弄湿了,白瓷可是我的贴身宫女,他那个弟弟凶神恶煞的,看起来很不好惹,我这不是怕他们惩罚白瓷嘛,所以才自告奋勇带他去换了衣裳,就这么简单。”
赵玉珠半信半疑,见妹妹如此说,她也没再往下问。
她最后只叹气道:“你呀,记得要保护好自己,无论何时,女子的名节都是最重要的,即便你是公主。”
“姐姐,我记住啦。”
天色不早了,赵玉珠嘱咐完之后,就离开了藏春宫。
姐姐走后,赵玉梳将手中的磁石随意丢在一边,伸了个懒腰,对着彩釉慵懒道:“彩釉,我记得你平时八面玲珑的,跟各个宫的宫女侍从都熟悉,你记得把今天的事情再偷偷传一遍,听见没有?而且你传谣言的重点还得是萧子羡他对我单方面思慕,知不知道?”
彩釉机灵回:“放心吧,包在奴婢身上,不会让公主的计划落空的。”
赵玉梳用手指随意摆弄着她房中开得最娇艳的一株海棠花:“这一切才刚开始,还挺好玩的,那萧子羡嘛,他跑不掉,早晚是我的囊中之物。”
光有彩釉还不行,她这次得出手阔绰一些,多收买些人,最好闹到满城风雨,连承天门下要饭的乞丐都知道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
晚上,萧府。
对今天发生的所有事都毫无招架之力的萧裕回了府上,一路跟着他还有喋喋不休的萧子恒。
在马车上萧子恒就开始不依不饶了,如今回了家,更是要问个清楚明白。
“哥,今天到底怎么回事?
“你跟那个六公主到底什么情况?
“还是换衣服的时候不小心带出来的?
“你快说呀!
“我告诉你,我未来的嫂子我只认陆家姑娘,你听到否?
“你要是让陆家姑娘受了委屈,我肯定饶不了你,哥!”
萧裕被他弄烦了。
两个人停下来,萧裕回忆着今天发生过的一切,他深深叹了口气。
他正要对萧子恒说些什么,就看到他父亲身边的萧圆走过来,神色凝重。
萧裕道:“何事?”
“二郎,令公要见你。”
“知道了,”然后转头对萧子恒道:“今日的事,我一无所知,你先回自己房间,待我面见父亲之后,再去同你解释。”
萧子恒站在原地愤愤不平,看着萧裕跟着萧圆朝萧续的书房走去。
萧裕在见父亲之前,先把自己身上这件赵玉梳准备的衣服换了下来,再步行至萧续书房,轻轻推开书房的门,走了进去。
他恭敬喊道:“父亲,您要见我。”
萧续抬了一下眼皮:“嗯,从宫里回来了,一切可还顺利?”
看来他父亲还不知道那坠子的事,萧裕想,如此也好,要不然他还没准备好措辞怎么跟萧续解释这一切。
“顺利,一切都好。”
“嗯,那就好,裕儿,咱们父子俩有好些时候没说心里话了。”
“父亲但说无妨。”
萧续咳了两声,才开始进入正题:“我知道你不明白我为何突然回京,其实我也不明白陛下突然召我回京所为何事,但咱们还得多在京城多待一些时日,让陛下放心,也顺便摸清朝中局势,我这几日也会跟陆太尉多走动走动,北伐之事,暂且先等一等,不急于这一时,我的意思,你可明白?”
萧裕拱手道:“父亲高瞻远瞩,我自当遵从。”
“你明白这些就好,你年龄也不小了,如今咱们在京城久居,跟陆家的关系也可以更进一步了。”
“这……”
“嗯?”
“是,儿子遵命。”
萧裕只得先应下,反正又不是现在要他把陆浣云迎进门,以后再从长计议罢。
他走出父亲书房,又长叹了一口气,这一天,他实在太累。
其实他也想知道,那玉坠子怎么就莫名其妙地从他身上掉了出来呢?他当时身上穿的是赵玉梳给他的衣服,而且,怎么就那么巧,近旁的一个宫女就认出了那是赵玉梳的贴身之物,还拿到赵玉珠面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