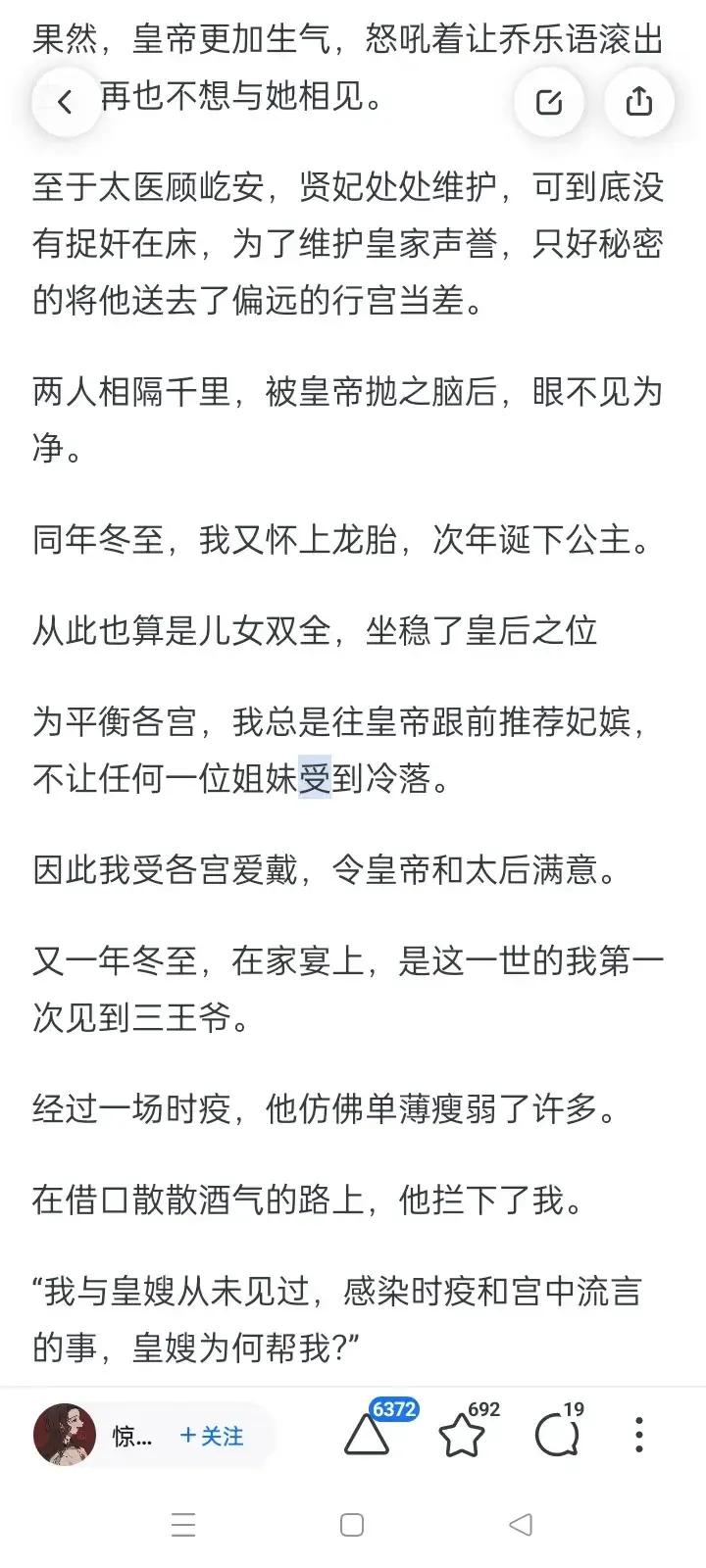简介:
为了江山社稷,她成了她爱的人与父亲手上的一颗棋子
与庶妹同嫁当日,被调换去了将军府,嫁了那狂夫
命数难逆,她只得假意迎合
用一寸柔情,斩他一身轻狂。

精选片段:
大元帝国63年春,冰雪初融,万物苏醒,南境战地飞鸽捷报,大将军战天涯领四十万大军攻破鞑人都城,大获全胜。
与鞑人僵持十年的战乱终于在史书上划上句点,迎来了大元盛世,天下太平。
少年背井离乡,十年生死茫茫,荣归故里的战天涯,手握朝中兵权,掌大元半壁江山。
老皇帝年世已高,心中忌惮战天涯拥兵自重,虽表面大大封赏他良田土地,府邸豪宅,但却时刻让人紧盯着他,寄望于太子尧,制横战天涯。
四海升平,八方静宁,然,下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撕杀与内斗,悄悄拉开了帷幕。
————
这年初冬,下了一场很大的雪,宰相府嫡庶两女,同时出嫁。
嫡女阮桑晚早已与太子尧订下婚约,而庶女阮瑾媗则是被老皇帝亲自下旨赐婚于大将军战天涯。
皇家嫁娶,本不可冲撞在同日,视为大不敬,何况还是太子,未来的大元新皇。
战天涯长年征战在外,虽是粗人却也懂得,只不过战天涯言辞砸砸,说是算命的术士为他卜了一卦,必须是这一年这一日成亲,它年它日的都不成。
若是择了它年它日,好的姻缘都会变成孽缘。这种话,鬼才信!
朝中大臣敢怒不敢言,老皇帝心中定然也是不痛快,可这战天涯现在是只吊睛白额猛虎,一毛也拔不得。
太子大婚,绝不可因为一介莽夫就改了日子,不然皇家的颜面往哪儿搁?
商量一番之后,终于做了这个决定,为了保皇家颜面不损,老皇帝召书天下,大将军戎马半生,战功累累,特允大婚与太子同礼遇。
于是,面子里子都有了,举国上下歌诵皇恩浩荡,对待功臣宽厚仁慈。
大婚前一天夜里,皇帝宣太子去书房议事,问他:“战天涯藐视皇家威严,故意择与太子同日大婚,太子可忍得?”
太子尧面不改色,沉稳自若道:“小不忍则乱大谋,古有卧薪尝胆,悬梁刺股,为成大事儿臣必须忍得。”
大婚之夜,太子东宫一片喜庆祥和,歌舞升平,前来送礼贺喜的大臣们络绎不绝。
太子尧翻着手中登记宾客的小册子,问了宫里的静姻姑姑。
“所有来贺喜的大臣名单可都在这儿了?”
“是的殿下。”
“叫管事公公与大内侍卫长过来一趟,本太子倒要看看,今日哪些大臣去了将军府又来了本太子东宫,哪些大臣去了将军府根本没来东宫,哪些从东宫离开又去了将军府!”
相较于东宫的繁华,将军府显得沉寂了许多。
“将军将军!您怎的还未换喜服?新娘子就要到了!”
大晚上的,战天涯还在练剑。贴身侍卫暗中翻了个白眼,嘀咕了句:“都这时候了,应该准备磨枪啊,怎的练起了剑?”
战天涯练了好一会儿,才收了势,回头冲年轻的侍卫问了句:“舒护将,本将军刚才自创的一套剑法,耍得好不好?”
说罢,抹了把下巴处的络腮胡子,举手投足满是豪爽之气。
“好!”舒狂狗腿的拍了拍手掌,撇了撇嘴:“将军,您该换衣裳了,还有这仪容是不是也该……”
话说了一半,锋利的剑刃已搁在了舒狂的脖子上,如寒星般的双眸射出两道利芒,咬牙道:“本将军不喜欢你啰嗦。”
自古忠言逆耳啊!舒狂紧实捂住了嘴,不敢再吱一声。
最后,舒狂勉强让战天涯黑锦外披了一件红色披风,才去拜了堂。
至于战天涯未何不穿喜服,用他的话说:“老子黑,穿了这一身红,黑红黑红的!管他什么喜不喜庆,不穿!!”
至于为何非得较着劲儿娶宰相府庶女,他是这样说的:“太子这小白脸能娶宰相之女,本将军为何不能娶?本将军还要与太子这小白脸在同一天迎娶!”
其实那宰相府的庶女,他见过一面,生得温婉动人,小家碧玉的,看着乖巧,他就喜欢这样的。
这么一想,娶她倒也不仅仅是和皇家赌气。
想他戎马杀场,在南境一守就是十年未曾归家,哪晓得那皇帝老儿狼心狗肺,反倒开始算计抵防着他!气得他干脆就把这罪名给坐实了先。
匆匆拜了堂,新娘子被搀扶进了新房。
话说这喜庆的日子,恭贺大将军新婚敬酒的不在少数,然而今晚在座讨喜酒吃的,却无一人敢上前敬战天涯的酒。
据闻,战天涯嗜酒如命,千杯不醉,他喝酒用的不是小盏,而是大碗。
南境十年驻守,又是武学世家,战天涯野性惯了,健壮的身子往太师椅上阔步一坐,‘吱吖’清脆一声,众人生怕他把那结实的红檀木太师椅给坐塌了。
好在那红檀木椅子晃了两下,很给面子的没塌,众人虚惊一场,暗暗轮袖抹了把额间的冷汗。
战天涯豪爽的抡过下人递来的大碗酒,抬手往前一拱,酒水淌了一小半,他中气十足的嚎了一嗓门儿:“来!喝!!”
众人顿时错觉,这感情不是来赴喜宴的,而是要上战场杀敌的壮胆酒。
酒过三巡,来宾渐渐散了,战天涯稳当的坐在太师椅上,酒一碗接一碗的喝着,直到宾客散尽。
府里的徐妈妈戚戚然的移步前来提醒了句:“将军,夜已深,该入洞房了。”
战天涯抹了把络腮胡,道:“且待本将军喝完这最后一坛女儿红。”
而此时的准新娘子,坐在艳红的喜榻上等了又等她这如意郎君,却迟迟不来,实在困得很。
喜帕未等这‘良人’来揭,自个儿一把揭了,朱唇轻启唤了几声:“春芽,现下是甚么时辰了?春芽?春芽!”
等了片刻,无人应答,安静得让新娘子打了个冷颤。
阮桑晚环顾了一下四周,秀眉一蹙:“这里怎的和太子东宫布局不太一样呢?春芽也不见了,太子哥哥可是还在忙着政务?”
才这样想着,新房外的长廊隐隐传来一阵沉稳的脚步声,阮桑晚心下一紧,赶紧坐回了榻上,将喜帕盖好。
战天涯踏着雪夜月华而来,有些微薰。‘咣’的一声推开了新房的门,这大动静吓了阮桑晚一大跳。
太子那般温文尔雅,怎会将门推得这般重?定然是喝醉了,阮桑晚如是想。
那人的身影遮过了红烛摇曳的光,让她心脏跳动得厉害。她想了许久许久,能有朝一日可以嫁给这万人之上的尊贵太子,今日夙愿当以偿了。
战天涯直接用手揭了新娘的喜帕,喜帕落地,她羞涩轻唤了声:“太子哥哥……”
平常那皇帝老儿与太子韦尧找他晦气也就算了,新婚之夜从自个儿娘子嘴里听到太子,委实难以咽下这口气!
想罢,他粗糙有力的手狠狠扣过了她的下巴,强行让她抬起了头来。
“好好看清楚,我是不是你那太子哥哥?!”
这人……阮桑晚当场傻了眼,满腔的期盼与热情化成疾风暴雨,将思绪扰得七凌八落,一片狼藉。
战天涯也是一怔,心中惊叹,这女子哪里是阮家庶女?
好啊!好啊!!竟然被韦尧给摆了一道,想罢,战天涯怒火中烧,如同扔破布般将那身娇肉嫩的阮家嫡女给扔到了地上。
“来呀!将这不知从哪儿来的奸细,给本将军扔出去,乱棍打死!”
将军一声怒吼,守夜的侍卫纷纷赶了过来。
阮桑晚当即吓得梨花带雨,不顾一切的爬到战天涯脚边,哽咽道:“你不能如此待我,我,我爹是宰相!我是宰相府的嫡女阮桑晚!”
前来带人的侍卫顿了顿,抱拳回道:“将军,您看这……”
战天涯沉思了一会儿,半眯着那双让人胆寒的虎目,压低着嗓音道:“阮桑晚?宰相府的嫡女?本将军娶的本是宰相府的庶女,这么说来……”
“这么说来,将军占了好大的面子呀!”舒狂一边穿着衣裳一边冲了进来,带着满脸的笑接了话。
看着这舒护将镇定自若,实则背后已被冷汗湿透,这战大将军杀伐果绝,他要起了杀意,没人能拦得住他。
战天涯摸着下巴想了许久,终是想通了,道:“说得似乎很有道理,是本将军占了韦尧的面子。”
“没错没错,正是如此啊!”舒狂连连点头,趁机奋力游说:“不如将错就错,狠狠打那太子一记耳光。来来来,将军您再仔细瞧瞧,这嫡女不仅比那庶女尊贵,还生得如此倾国倾城呢,将军真是好福气!”
战天涯细细打量这女子,果真生得眉目如画,美艳无双。与那阮二小姐不同,阮二小姐美得宜人静好,婉约动人。这阮大小姐,眉眼间天生媚态,十分艳丽。
阮桑晚自然是十分不愿意的,论才情,论外貌,这野人草莽哪比得上如谪仙般的太子?
可这男人权倾朝野,又武艺超凡,他动一根手指就能把她捏得死死的。
“将,将军,你……你放我回去,我定然把……把嫤媗妹妹给你送回来,一定,一定是弄错了,不可以一错再错。况且,我从小就与太子哥哥有婚约,心悦于他,你若强娶了我,也不会快乐。”
舒狂暗暗长叹了口气,究竟是谋划已久,还是造化弄人?
大将军固然人中龙凤,只是他这人从小就看惯了生离死别,长达几十年的无尽杀戮,早已练就了他铁石心肠,绝情绝爱。
这女子阴差阳错嫁到了大将军府,时也命也,是福是祸,也许只有老天爷知道罢。
战天涯出乎所有人意料,问了句:“那太子韦尧可是也心悦于你?”
阮桑晚听罢,以为他起了怜悯之情,立即点头答道:“我和太子哥哥青梅竹马待我极好,他自然也是心悦于我,非我不娶的!”
“呵呵呵呵……”战天涯阴恻恻的笑了许久:“好极!真是好极!!全都给本将军退下,本将军要、洞、房!”
“啊,是!”舒狂爱莫能助的看了眼阮桑晚,带着府里的侍卫退了出了新房。
阮桑晚踉跄往后躲去,他是豺狼是虎豹,在他嘴下哪还能留下‘全尸’?
“你,你别过来!你别过来!!”她退到了烛台边,那刺目的红烛此时此刻似乎满是嘲讽之意。
看她如小兔儿般受惊得厉害,反而激发了战天涯嗜血的本性,笑得阴戾邪气,如同猎食的猛虎步步逼近。
“叫啊,大声的叫,本将军爱听。呵呵呵呵……”
想到她就要被这种粗野之人给玷污羞辱,心中顿是十分不甘。这天底下,也唯有如太子韦尧那般皆上品的男人,才配得上她。
她折了那红烛,取了烛台将尖刺对准了自个儿的脖子:“战天涯,你这个佞臣贼子,粗鄙莽夫!我是宁死也不会委身于你的!!”
“好个以死相逼,你可知在本将军眼里,最不值钱的就是人命。”
针芒已扎破了那细腻的皮肉,迎着他无情的双眸,她却再也下不去狠手。
“你,你究竟要怎样才会放过我?”她软下了态度,手中的烛台无力的滚落在脚边,她还不想死,也不能死,怎甘心!?
“我不要你怎样。因为你不管怎样,都不能奈我何!本将军要做的事,无人能阻我。”
他将她如抗沙袋般抗在了肩上,大步朝床榻走去。
“脱衣裳!”
“不,不!”
“也罢,那锦帛撕裂声极是动人,即然你不愿脱,本将军就帮你撕了,也极是有情趣的一件事儿。”
他一寸寸将她身上的喜服撕裂,笑得邪肆狂放,撕裂的血红色嫁衣衬着那如凝脂般的肌肤,妖艳至极。
“战天涯,你别这样对我!求你……不要……”
她哀求着,哭得撕心裂肺,屈辱的泪水如断线的珍珠,滚滚而下。
若是一般男子见着这一幕,定会生出怜惜之情,可这战天涯却越加霸道残虐起来。
“哈哈哈哈哈……有趣,有趣!本将军很久没这么痛快了,怎的不叫了?继续求饶,本将军会考虑对你温柔点儿。”
她惨白的小脸蛋儿毫无血色,气得浑身巨烈颤抖,恨恨的盯着眼前这畜生。
“战天涯,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战天涯拿过自己的亵裤堵住了她的小嘴,笑得邪佞至极:“本将军更喜欢听你娇喘,而不是谩骂,夜还长着,这一晚必将让你终身难忘,呵呵呵……”
天光破晓了,然而这场噩梦还在持续,那一室的旖旎,将柔情蹂!躏得不留分毫,任她再如何求饶,却也不肯半点仁慈。太子东宫,繁华沉寂,新房里的红烛已快燃尽,那人却没有来。
她枯守了一夜,却也冗长的舒了口气。传闻那将军残暴嗜血,其实一开始就失宠,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她不求什么,只求此生平平静静的,不惹这乱世红尘。
因她心中已有一人,远远的看着便已足矣。
“他大概,不会来了罢。”想罢,阮嫤媗疲惫的取下了喜帕,准备更衣就寝。
正巧此时,外头传来一阵敲门声,静姻姑姑传话道:“太子妃娘娘,太子殿下传话,今夜事务繁忙,您且自行歇息了罢。”
阮嫤媗心头一紧,疑惑低语:“太子妃娘娘?莫不是她叫错了,可是……这怎会叫错?”
见门外掌灯的那道身影正要转身离开,她连忙起身拉开了门:“姑姑请留步。”
静姻姑姑回头笑了笑,匆匆打量了眼前这女娃娃一眼,好个碧玉佳人,清灵婉约。
姑姑行了礼,问道:“太子妃娘娘有何吩咐?”
“姑姑你……为何唤我太子妃娘娘?”她极是不安的问道。
静姻姑姑掩嘴失笑:“太子殿下明媒正娶将娘娘迎进这东宫,您自然便是太子妃娘娘了。”
“可是,可是不对呀,我应该嫁的是大将……”
“嘘~”静姻姑姑做了个噤语的手势,道:“没有应该不应该,只有天命所归。您即是注定的太子妃娘娘,就安安心心的侍在太子东宫,好好服侍太子殿下便可。”
阮嫤媗站在石砌前,好半晌都没有回过神来,她掐了下自个儿的手臂,传来切实的疼痛,才惊觉这并非是梦。
自那江舟湖畔一见,她便心悦太子韦尧多年,只是她知道太子韦尧与嫡姐有婚约在身,自己不过一厢情愿,痴心妄想罢了。
她从不敢,从不敢有半分这种念想,每夜渴切相思之苦,独自饮下。
是老天爷怜悯她?让她阴差阳错的来到了他的身边么?夜风冷彻,却点燃了那颗死寂了十六年的心。
又下雪了,大地银妆素裹,东宫凤凰楼台上的那人,披着一件狐裘大氅,独自一人赏了这半夜的雪景,看这天地浩瀚。
煨热的酒又凉,香案上只留一丝余香袅袅而上。
“殿下,宰相大人到访。”太子的贴身影卫范阳禀报道。
韦尧转身,只见当朝宰相一身青色鹤氅,风尘仆仆,双肩与胡须沾着未融的雪花。
阮墨松做了个揖:“殿下。”
“大人无需多礼,请随本宫入书房内详谈。”
阮墨松跟随韦尧一前一后走进了书房,入座后叫宫婢奉了茶。
“此事已成定局,太子殿下把握得当,必对您十分有利。”
韦尧拨动着手中那串血色琉璃珠,低垂的双眸,沉思了许久才道:“这颗棋子,安插得确实妙极。只是贵夫人娘家萧氏那边,不好交待。”
“殿下尽可放心,只说是迎亲时出了差错,人即已嫁到将军府,任萧氏如何讨要说法,也绝计不敢与战天涯撕破了脸。”
“趁此,暗中推波助澜,让萧氏与战天涯生出嫌隙,本宫便能与战天涯势均力敌,牵制住他。”
阮墨松点了点头:“道阻且长,就看殿下如何运用这颗安插在战天涯身边的棋子了。”
送走阮墨松,范阳飞身从暗处走了出来。
“殿下,您……”范阳欲言又止。
“你想说什么?”韦尧眸光骤然一冷,范阳猛然低下了头不敢再说什么。
过了一会儿,韦尧放下了手中的折子,道:“说罢,本宫想听你说,恕你无罪。”
范阳暗暗舒了口气,才道:“属下从儿时起便与殿下相伴,殿下从未像现在这般放不开。”
韦尧面上微愠,摔下手中血色琉璃珠,恼羞成怒极力否认:“本宫怎的放不开了?!”
“殿下对阮大小姐也并非无情,这么做究竟值得吗?!”
“值得不值得重要吗?”韦尧颤抖着声音,冗长的小心翼翼舒了口气:“值得吗?当然值得!当然值得!用一个女人换来万里江山,有何不值得?!”
“可是您并不快乐。”
“快乐?那是什么?呵呵呵……”韦尧冷笑了声,恢复了那一幅风清云淡:“范阳,生在帝王家,情爱这种东西本就是多余的,用情越深只会做茧自缚。我不要这些,只有权势握在手里,才会让我感到安心。”
范阳便也不再与他谈这阮大小姐的事情,只是问道:“那宰相大人,为何要做这般大的牺牲?属下实在不解。”
韦尧轻叹了口气道:“那阮墨松,曾经极宠爱府里的一个小妾,那小妾生得貌美又极讨阮墨松的欢心,引得萧氏很是嫉妒。
一年水灾,阮墨松出了远门,萧氏趁机强加了莫须有的罪名给那小妾,活生生将她折磨至死,包括那小妾肚里才刚成形的男婴。
待阮墨松赶回来,活生生的人成了一具冰凉的尸骨,从此天人相隔。他差点悲伤得发了狂,本要让那萧氏以命抵命,奈何萧氏已有身孕,再加上萧氏娘家那边的势力打压,阮墨松只能打碎牙齿和血吞。
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提此事,却是恨在了心上。萧氏生下阮家大小姐,他该给的也都给了,只是谁也不知道,他恨萧氏,连带萧氏生下的女儿。”
范阳暗暗叹了口气:“如此说来,阮大小姐却也是可怜之人。”
韦尧眉头一蹙,沉声道:“范阳,你莫忘了自己影卫的身份,容不得你妄动私情!”
他本无情,曾是殿下捂化了冰封的心。
如今,殿下无情,他却已知晓世间冷暖,又如何回到曾经的无情?
“殿下教训得是,属下铭记。”说罢,隐于暗处了去。
次日的雨雪越下越大,战天涯身为大元正一品镇国大将军职位,四更天起,习惯骑着黑鬃马赶去上早朝。
锦衣外披了件儿狐毛大氅,整个人精神奕奕,舒狂想着他们家将军把这以引为傲的‘美须’给剃了,那才真真是个标准的美男子。
天太冷地上都结了冰,马儿也跑不快,到宫门还有一段距离,战天涯发起了牢骚。
“一些个斯文败类,能用武力解决的问题,用得着叽叽歪歪?”
舒狂暗搓搓的抹了把冷汗,至于‘败类’这个词儿,也不想想他自个儿昨晚禽兽行径,估计那阮大小姐几天都下不得床榻。
天下苍生,江山社稷,民生经济,折子一本一本参上去,战天涯眼观鼻鼻观心,皇帝一问及他:“战爱卿有何见解?”
战天涯总是答:“啊,臣无异议。”
……
终于挨到下早朝,战天涯已是饥肠辘辘,赶着回府砥用膳食。
“战将军请留步,皇上有请。”
身后总管太监将时辰拿捏得很是及时,战天涯很想假装没听到,可似乎是不成了,李公公快步走上来拦截了他。
“战将军……”
他娘的!战天涯心中暗骂了声,转身时,笑脸盈盈。
“嘿哟,李公公。”不耐烦的抬手掏了掏耳朵,一双虎目瞥了眼宫门的方向。
“皇上有请战将军,入御书房内商议要事呢。”
“哈,我一介武夫,只会冲锋陷阵,不懂这些个治国的弯弯道道,皇上真是太抬爱了。劳烦李公公带路罢。”
“行呢,战将军请。”
经过重重叠叠的长廊花园,终于来到了皇帝的御书房,大总管进去通报了声,随后宣了战天涯进去。
走进御书房,皇帝还未将黄袍卸下,正在批着折子。
战天涯烦些个宫中礼仪,三跪九叩,慢悠悠的屈了个膝就等着皇帝老儿开口。
果真,皇帝赏了个面子道:“战爱卿免礼罢,赐坐。”
“谢皇上隆恩。”这么好说话?肯定有诈!
宫婢又送了茶水与点心,战天涯默默的吃着茶和点心,敌不动我不动。
皇帝悄悄抬头瞥了他一眼,满满的憎恨与杀气,可奈何这镇国大将军,功高盖主,明着是动不得的。
说话时,皇帝杀气敛去,脸上的笑容看着十分和蔼。
“北越国安宁公主和亲之事正在筹备,为免万无一失,朕与诸位大臣商量后,决定派战将军下泉州迎接公主进皇城,朕能信得过的人,便只有战将军了!”
皇帝一脸无奈,与他分析着厉害关系。
“咱们大元一统天下已有六十余载,放眼历史,改朝换代不过百载之年。朕老了,以后就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
四方诸候国,虽看似宁静,实则心里头都为自个儿算计着。国泰才民安,战将军,你可知晓朕的顾虑与担忧?”
战天涯暗暗轻嗤了声,皇帝老儿现在唯一的心病,就是他!把他弄死了,他才能高枕无忧的去死。
什么忧国忧民的屁话,都是虚的。
“臣惶恐,必当尽心尽力,替皇上分忧解难。”说着起身抱拳行礼。
“好!好啊!果然是朕的好臣子,是我们大元的好将军!你回去准备准备,十日后便出发。”
出了皇宫,舒狂早早便在宫门等候,见战天涯黑着一张脸,便断定皇帝又找他晦气了。
牵过黑鬃马,战天涯连连叹气。
舒狂察颜观色半晌,才试探性的问:“很麻烦么?”
战天涯:“有点。”
舒狂思虑了会子,追问:“哪方面的?”
战天涯想了想说:“那就要看咱们处理得高不高明,要是处理得高明利索,也就是关乎点小权小利,要是处理得不妥当,伤及身家性命。”
“哦……”舒狂若有所思点了点头,笑道:“那咱们就妥当的处理罢。”
战天涯扯嘴一笑,英姿飒飒越上了马背,往府砥赶去。
而被战天涯折腾了一晚的阮桑晚,意识渐渐苏醒,隐约听到耳畔传来一阵若有似无的啜泣。
她努力的睁开双眸,看到自个儿贴身婢女春芽哭得是梨花带雨。
“你哭何?我又还没死。”
声音沙哑,支离破碎的从肺里挤出,虽如是说着却又自个儿红了眼眶。
“大小姐!”春芽赶紧用袖子抹了把泪水上前查看,原本好好个人儿,现在满是怵目惊心的青紫伤痕,很是狼狈。
“送嫁之时,奴婢被人从身后打晕,再次醒来便到了这将军府,究竟发生了何事?大小姐怎会嫁到这儿?”
阮桑晚恨恨的几乎将下嘴唇咬破,强忍的泪水滚落眼角,因隐忍而浑身颤抖得厉害。
“别说了……”
“必定是有人从中捣鬼,大小姐怎咽得下这口气?必定要回去禀明夫人老爷,替大小姐做主!”
阮桑晚睁着眼,盯着纱帐上空也不说话。过了好半晌,才冷静道:“我要沐浴。”
“小姐?”
“此事需得从长计议。”
她还有什么脸回去?早已不是什么完璧之身,女子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从来都没有说‘不’的权利。
可如今,什么贤良淑德?这辈子也算是毁在了战天涯的手中,就算是死,也得拉个垫背的!
她连下床榻都困难,被春芽搀扶着走到了屏风后,沐完浴,身子清爽了些,听到外头人声攒动,想必是那粗莽之夫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