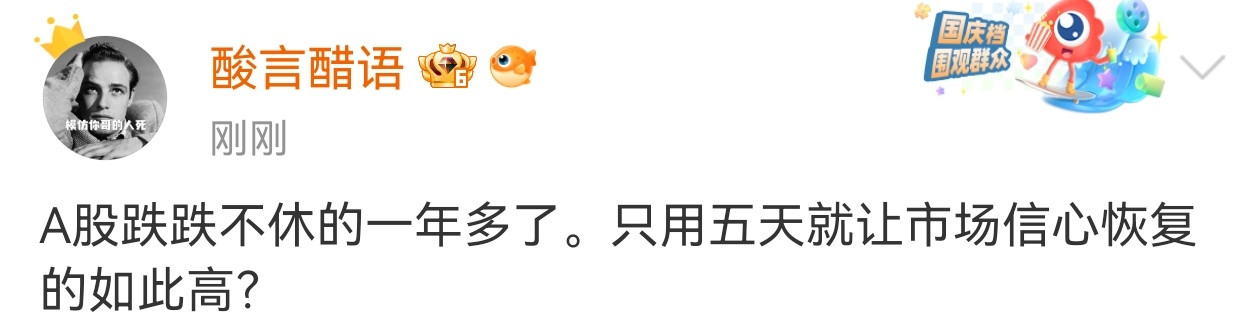小刘生孩子
1940年12月,何功伟从恩施寄信给我,说刘惠馨快要临产了,要我请假回恩施,照顾小刘坐月子。这当然是大事,我必须在小刘临产前,为她找好医院,为她置办产前产后一切必需品。并且要在她坐满月子后,把她和小孩护送回四川忠县我的老家去,同时还要把何功伟和许云生的孩子,也送到忠县老家,交给父母养育。我估计来来回回,没有两个月工夫是不行的。因此我去找督导处长请两个月假,说我家老婆要生孩子。我一开口,他就答应了,因为本来是给我安排的闲差事,有我不多,无我不少。
我回到恩施后,直接就回到我和小刘新租的农家房屋,就在羊家湾医院后面的山下。我才走下小路,没到房前,便已经看到小刘挺起个大肚子院后面的山下。我才走下小路,没到房前,便已经看到小刘挺起个大肚子站在门口,望着我笑。我急忙趋步向前,把她扶进屋里去,责备她:"这么冷的天,你跑出来站在门口,受了风寒,怎么得了?"
小刘却顺势挨我坐在床上,我发现她竟然泪流满面。她说:"大何告诉我说,你就要回来。我便天天望着这屋后通垭口的那条小路,希望看到你的归来。望呀望呀,望了好多天了,还是不见你的身影出现。今天早上我还是坐在后窗口望着那条小路,果然就看见你远远地从那条小路匆匆地走过来了。"在患难中结合的年轻小夫妻的恩爱,用什么文字描述,也显得苍白。
小刘起来,到外屋搭的偏厦下的灶上忙了起来,准备晚饭,她端了一个土罐,放到屋里的小桌上,我老远便闻到肉香味。她说:"我好像真有一种我不能说明的预感似的,我认为你今天一定会回来。我就杀了一只鸡,炖了起来。果然你就回来了,你有这个福气。"我说:"你怎么把留着给你补身子的鸡,炖来给我吃呢?"小刘说:"我还留得有好几只呢。况且我的身体一直比较好,我肚子里的孩子想来也长得好。你听。"她把我的头按在肚子上要我听,她说:"这小家伙很不老实,好像是想出来欢迎爸爸的归来,又用脚在踢了。"我实在没有听到什么声音,但是我顺着小刘的思路,拍一拍她的肚子说:"小家伙,你再也不要踢了,把你妈妈的肚子踢破了,谁来养你呢?"
我们吃罢晚饭,在桐油灯下,互相默默地望着,不知有多少心事想说,却不知从何开头说起。她把她这段时间缝制的小衣服小被子等小东西,拿出来给我看,我看一下,做工十分精细,她特别有兴趣地拿出一件大红的风衣,还不知从哪里买到了兔毛,给风衣沿了一个毛边,风衣上的小风帽,还用兔毛做成一个毛茸茸的猫头。我想那上面凝聚着一个母亲多少关爱之情啊。她还别有兴趣地从抽屉里找出一个自制的布玩具。我说:"你真是想得周到呀。"但是她不知道其实我也想得不比她差。我在外面的时候,也为孩子用竹片做了一个摇铃,做工虽然比较粗糙,却能叮当地摇动出声,最能引起孩子的注意。我还在外面为孩子买了一个木头人,五颜六色的。我拿出来交给小刘,她领会我的这片爱心,粲然笑了。她说:"我想这孩子将来一定是幸福的。"我想会是这样,这孩子送回我老家去由父母抚养,一定会养好的。
我出其不意地从我的提包里拿出一件小刘意想不到的东西,一件用软玉雕刻的女人头像。这是我在咸丰时买的一块软质土玉,思念小刘,百无聊赖时,我用我刻假印的工具,费了好大工夫,才照我所想象的小刘刻成的。虽然不很像,但是那老是微笑着的神色,就是小刘的样子。她拿在手里看了又看:"你这是刻的谁呀?"我说:"刻的你呀。"她哈哈大笑起来:"这能是我吗?"我说:"那就是你。"她说:"我看,一点也不像我,只是一个女人的头像。"我坚持说:"外表也许不像,但你如果打开,那里面肯定有一颗你的心。"她领会了,并且同意那就是她。她知道那个头像里面有她的精神,也有我的心血。
第二天上午,我陪着小刘到羊湾医院去检查。医生说,看来就是这两天就要生了。
果然第三天一早,小刘就发作了。疼得不行。她却勉强忍着,不哼一声。我说这里到羊湾医院,虽然不远,却要爬一个陡坡,我扶着她慢慢向山顶上爬,真是难为她了,眼见她忍着疼痛,一步一步向上爬,终于爬到了山顶上医院的门口。她的头上已经是大汗淋漓了。她进了产房,我在产房外等着,虽然外面风很大,很冷,我却心急火辣,倒像热锅上的蚂蚁,走来走去。过了大概两三个钟头,一个护士出来对我说:"生了,一个女孩,是顺产。"
我一路高高兴兴地回家,下山坡时,我又哼起我和小刘两个最喜欢唱的《进行曲》:"快乐的心随着歌声飘荡,快乐的人们神采飞扬……"
我回了家。第一件事就是给小刘杀鸡炖鸡。第二天一早,我端起鸡肉汤罐到了医院,我被准许进入产妇病房,我把鸡肉汤罐放在小桌上,紧紧握住她的双手,竟然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望着她笑,不自觉地把我的嘴贴向她的脸庞,亲了一下。我问她生产是否顺利,她说:"因为是头胎,当时感到十分痛苦,可是一想到我们的结晶将要实现,一种预期的快乐感,淹没了我的痛苦感,很顺利地生了下来。"
小刘住了三天医院就回家了,在出医院的头一天,大何因病去医院拿药,顺便去看了小刘一会儿。告诉她许云在重庆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大何还要小刘告诉我,要我约时间,他有要事要来商量。当天下午我就到大垭口公共厕所去,在一个坑位的木板壁上做了一个记号。
紧急应变
大何为了安全,他的住地是没有同志知道的,一般要和我们见面,都是采取单个约好的通知办法通知他,他照约好的时间地点来和我们见面。这次大何在大垭口公共厕所里看到我留下的记号后,就会按约好的时间到我家里来和我见面。而且他还必须看到我在后窗口挂的信号才能进我家。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安全是第一要紧的。
第二天上午,何功伟来到我家,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大事不好,我们马上研究一下。"小刘站起来,拿着衣服,端起盆子,装着坐在门口洗衣服,替我们望风。现在正是十二月的寒天,门口风大,她受了风寒怎么得了。大何叫她进来,她才把盆子端进房里来,仍然坐在房门里,替我们望风。
何功伟对我说:"我从可靠方面得到消息,全国的形势越来越紧了,反共高潮已经掀起来了,大事不好,看来敌人在全国都将有所行动。我们必须紧急应变。你马上再到南路各县走一趟,进一步检查,把应该疏散出去的赶快疏散。决定走还没有走的,马上走,特别是做领导工作的。"
我说:"可以,我这两天就出发。我从南路转到利川。小刘坐满月后,抱起奶娃到利川和我会合,回忠县老家。许云那时可能也到我家了,我们把两个孩子交给家里后,我们一块儿回鄂西。"
何功伟说:"可以这样。我已经叫王宇光回恩施前顺路送许云带孩子到你家里去了。你们的事情就这么安排,恩施这边和北路的事,我已经和王栋研究过。麻烦的是郑建安,上次开特委会时,钱大姐就决定疏散他,到现在还没有走。"
小刘插话:"我到羊湾医院生孩子,就是他替我去联系的,他说他们两口子要等放了寒假才走。"
我说:"这个人真麻痹,早就该走了,怎么还没有走?"何功伟说:"我叫王栋通知他快走。"
我和何功伟谈完工作后,他问小刘:"你去生孩子的医院医术还好吗?"小刘回答:"这是外国教会办的医院,医术可以说是这里最好的。"
大何说:"我打摆子一直不好,我到三里坝省政府的医院去看病,却偶然地碰到在武汉时的一个同学,我知道他是特务。我巧妙地摆脱了他.可是再也不敢到那里去看病了。我想离开恩施以前,到羊湾医院去看病,顺便还检查一下身体。因为我不久以前,曾经在农家院子外面被狗咬了,我怕那是疯狗,想拿点预防药。"
我听了,心里打鼓,这可不是好消息。给狗咬了,大半是家狗,倒不会有大问题,在省政府医院碰到特务那种狗仔,才是大问题。何功伟在武汉时便是出名的学生领袖,风云人物,他消失后,敌人肯定正在找寻他。特务既然在恩施发现了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我把这个意思对大何说了,并劝他再也不要出来活动了。他同意这个分析,他说他除了我出去后,有时来看望小刘,顺便到羊湾医院拿点药,他再也不出来了。
离别之夜
再过两天,我就要出发到南路去了,小刘现在正坐月子,我却没有工夫在家里照顾她,心里很不安。小刘却对我说:"我一切都好,你走吧,不用你操心。"我想在走以前的两天里尽力照顾她,其实也没有做什么,最多是上垭口买菜,回来烧火煮饭,在她沾不得冷水的时候,为小孩洗尿片,洗几件她和孩子换下的衣服,做一点杂事而已。我们的孩子晚上老是啼哭,使小刘睡不好觉,我不得不把孩子抱起来轻轻地拍,在屋子里不停地走圈子,唔唔地谁她,使她不啼哭,好让小刘安睡。其实小刘只在床上躺了几天,便起来活动了,而且几乎把全部的家务活担起来了。
虽然这次我和小刘只是暂别十几天,却仍然有依依惜别之情。出发前一天晚上,我们在一起,小刘又继续说她在坐月子中和我说过的话。她说:"在这两个月中,当我孤身一人时,我反复想过,像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由于国难当头,出于爱国热情,卷进了革命浪潮,并且入了党,担负着重要工作。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我们自己?党是这么信任我,让我挑重担子,我是不是尽了心力了?我觉得调鄂西特委来'坐机关'后,我做的工作没有以前多了,特别是我怀了孕,更受到限制,我做的工作更少,真感到惭愧。"
我听小刘对我说这样的话已经不止一次,于是打断她的话说:"我以为你调鄂西来后,做的工作已经够多了,不要老是自责。在鄂西特委,你担任了妇女部长,领导全区的妇女工作。你还下去兼过恩施县委的副书记、组织部长,专门在几所女子中学直接指导支部的工作。编制通信密码,保证通信安全;你建立了上对南方局、下对各县委的交通站,安排接待上下来往的同志,保证他们的安全;你筹措、接收和管理有限的经费,叫脱产同志的苦日子能够过下去;你还'坐机关',掩护我的安全,照顾我的生活,特别是我遇到困难的时候鼓励和安慰我。你还担任特委政治交通员,到南方局去汇报工作。你在那里拼命读文件(听钱大姐说,你的勤奋学习受到了周副主席的表扬)。你腆着大肚子,冒着风险,陪钱大姐到恩施来检查工作。你还亲自写了《支部工作纲要》和《革命气节道德教育提纲》,起了很好的作用。你还说你没有做多少工作吗?"
南路巡视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起来了,我热烈地拥抱小刘,长时间地和她吻别,然后使劲亲了亲我们的女儿,才出门上路。当我出门时,小刘抱起女儿送我,她握起女儿的手,向我摇手,女儿当然什么也不知道,小刘却是明显地落下泪来。这在她来说,真是稀罕的事。我也很难受,硬说一句:"我到利川等你。"便扭头上路,再也不敢回头看她。
我从小路走上大垭口,顺着从城里到三里坝那条大石板官路走下去。当我走到农场的外边,忽然看到郑建安和两个人一块儿从渡口走上山路上来了,我知道那是他回他教书的学校清江中学的路。他看到我走下山来,似乎有几分惊诧的样子。我和他原来自然是认识的,一般说来,在路上碰到了,自然要打招呼。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的,却没有和他打招呼,好像是下意识地感到,他的关系已经不在我的手里,按照地下党的秘密纪律,没有关系的同志在人面前是不能打招呼的。他们上了山垭口,我到渡口过河,穿城而过,出南门走了。
直到解放以后,郑建安这个叛徒被我们抓到,从他的口供里我才知道,那天早晨我和他相遇时,正是他刚被特务逮捕,两个特务押送他在回学校的路上。他在口供里提到这个,是想证明当时他并没有一被逮捕就叛变。我知道后感到后怕。如果那天早上我照平常那样,在路上和他打个招呼,我肯定会当场被特务抓了。
我从恩施南门出发向南走去。我只能步行,不敢去坐长途汽车。不仅车费我出不起,更因为在所有汽车站都有交警队的特务,盘查很严,稍有怀疑,马上就拉下车抓走,往往下落不明。所以我们通知下面,除非有可靠证明文件,否则不要去坐公共汽车。
我这一趟从恩施经宣恩到来凤,从来凤到咸丰再转利川,这一大圈有上千里路程,步行要走十几天,每天还不得少于七八十里,是够累的了。但是一想到到利川便可和小刘会合,又可以亲我的小女儿,还可以赶回老家去过年,也就不辞跋涉之苦了。
我从椒园转向宣恩,向李家河前进。我本来想去李家河乡下一个地主庄园找我们的一个党员,他是那个庄园的少爷。几个月前,我曾到他家去过,住了一天,那庄园颇为气派。因为上一次印象不佳,而且他的关系我已经交给来咸中心县委书记杨弟甫了,我想还是见了杨弟甫再说吧。
幸好我一念之后,没有去找这位少爷。后来见到杨弟甫,才得知那个少爷党员由于看到目前形势险峻,已经主动去国民党县党部自首了。
我从李家河经过,在一个幽深的山谷里踽踽独行,人烟稀少,山径凄冷,一个人感到十分落寞。不知怎么的,我心中忽然出现一种不祥的预感,-﹣我感到小刘已经被捕,而且英勇就义了。我竟然想到古人说人死了就是"骑鹤扬州去"的话,很奇怪地出口成章,说出"卿今骑鹤扬州去,后死何处觅香居"这样的诗句来。我想到这里,觉得太荒唐,使劲摇摇头,努力把自己的思路打断:"不想了,不想了。"继续在那冷清的山路上凄然独行。
我到了来凤,按约定的办法,找到了杨弟甫夫妇,他们二人才从延安回来,从南方局调来的。我和他们讨论了中心县委的工作。集中到一点就是把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把农村的农民党支部巩固起来。
我们讨论最多的还是当前形势恶化,随时可能发生突发事件,因此更要注意及早安排好应变措施。不过他们二人才调来,谁也不认识,只要能找好职业,就可以长期隐蔽地进行工作。他们也早已做了打算,租了一个铺面,准备做布匹行商,这样可以四处游走。不过我也向他们传达了上级的指示,如果形势突然恶化,以致无法坚持时,可以不经请示,直接到重庆南方局去交关系。
我离开来凤到咸丰去。那里的工作已经交给中心县委去管,我可以不再和他们接触了。那里县衙门里的军粮督导处,是我将来职业掩护的所在地,我不想现在和他们照面。我一直通过咸丰,向利川方向走去。
经过几天辛苦的跋涉,我终于走到利川南边三十里地的一小镇,找到了利川县委书记黎智,传达了特委关于应变的通知,也讨论了利川县委的工作。我特别提到,过去利川县曾经发展了一批乡保长入党,这使我们掌握了一些乡政权及其武装,这当然有很多方便处。但是这些当权人物的可靠性到底如何,是值得怀疑的。在革命高潮时,无疑他们会跟党走的,但是革命低潮来了,他们就未必可靠了。因此要做一些应变措施。有些人的关系要淡化以至切断,有的则要调开。并且我也告诉黎智,在紧急情况下,他可以直接到重庆南方局请示工作。
我从黎智那里出来,往利川县城走去。一路走来,虽然脚已经走跛了,脚板上的血泡破了又干,干了又破,可是我感到很轻松,这次南路巡视工作到底胜利完成了。剩下的事就是赶到利川去,准备迎接小刘和我的女儿,一起回老家过年。
我到了利川城,因为我有军粮督导处盖有大红印章的"派司",可以大摇大摆地住进一个旅馆。收拾一番,泡上一杯清茶,我静候利川交通站的同志带小刘到这个旅馆来和我会合。
但是一直等到天黑,还不见小刘的踪影。莫非是小刘在恩施出发前病了,或者小孩病了,因此没有照约定的时间出发,或者是出发了,但是在这冬天的雪山路上耽搁了,甚至是出了险了?我的心里真是七上八下,不知如何是好。天色又这么晚了,我不好去本地交通站去问,只好睡觉。但是我哪里睡得着,好不容易挨到天明,才稍微迷糊了一会儿。
大何小刘被捕
我在利川县城的旅馆里正迷糊地睡着呢,忽然听到有拍门的声音。我想,这肯定是小刘到了。我急忙翻身下床,直奔门口,我期待着热烈的相拥相抱场面就要出现。我打开了门,不见小刘,却是王栋。我问他:"小刘呢?"他不回答我,只管进得门来,很神秘地把门掩好,却不说话。见他那样,我心中的那种不祥的预感又涌上来,急切地问:"怎么啦?小刘在路上出了事啦?"王栋说:"不是在路上出了事,是在恩施出了事。"我更着急,问:"小刘在恩施出了什么事了?"王栋不禁低下头说:"小刘在恩施被捕了。"顿时,我只觉得天旋地转,五雷轰顶,差点没有昏过去。问起小刘被捕的日子,正是我那天产生预感的日子。这太怪了,真好像有什么现在人说的"第六感觉"似的。王栋以更沉重的声音说:"大何也被捕了。"我又是一愣,问他:"哪个大何?难道是何功伟吗?"他答道:"正是何功伟。"
这恶耗来得实在太突然,我简直被弄昏了头,真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不相信地说:"怎么会,怎么会是他们被捕呢?"王栋说:"出了叛徒了。"我马上就断定了:"一定是郑建安。"王栋说:"正是他。"我忽然想起我的小孩,问他:"我的小孩呢?"王栋说:"小刘抱着她一起进去了。"看来这消息是真的了,我一下跌坐在椅子上,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哎呀,怎么会是这样呢?天呀!"
王栋经受过第一打击,变得很冷静和理智。他说:"让我向你汇报我们到现在为止所了解的情况,赶快商量对策吧。"
是呀,这不应该是我悲痛的时候,特委的书记和秘书被捕了,情况十分严重,说不定有更大的打击,正在向我们袭来。书记被捕了,我这个副书记应该马上接上岗位,和组织部长一起,把情况弄清楚,赶快做出相应的应变措施来,把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王栋首先把他得到的初步情况告诉了我。他说:"我从北路回到恩施,马上按约好的办法,通知大何见面。等了三天没有应约来见,我感到奇怪,如果没有事,他是不会爽约的。我马上到农场通信处去找老张,看留有信件没有。谁知我一去,还没有走进农场大门,就感到气氛不对,有特务模样的人鬼头鬼脑地在那里游走。我远远看到平常挂在房檐下作安全信号的那串红辣椒不见了。我看到张太太在门口地坝边收拾什么,不时用眼睛瞟视。明显地告诉我,她那里出事了,很可能老张已经被捕。我马上就想到,郑建安过去管过交通站,虽然那时的交通站长是农场的技术员谢文煊,他并不知道后来接替谢文煊的是农场场长张翼,但他知道要谢文煊教育老张,努力争取他入党的事。现在谢文煊已经疏散去了四川,抓不着了,便咬出老张来邀功了。这个叛徒除开郑建安,还能是谁呢。"
我说:"毫无疑问是郑建安。早就感到他不可靠,所以决定不让他任特委秘书,把他疏散出去,谁知一切手续都办完了,他就是不走,有恃无恐的样子。"
王栋说:"我马上派人去郑建安教书的清江中学去打听,知道郑建安在大概半个月前就被捕了。但是我不明白的是,郑建安怎么知道大何和小刘住在哪里呢?莫非小刘让郑建安知道了她住在哪里吗?我想小刘历来是一个非常谨严遵守纪律的同志,她不会这样。"
我说:"当然不会。我们就是因为郑建安知道我们原来在五峰山背后的农居的特委机关,小刘才决定搬到夏家湾现在的农家的。我们这个家除了大何,谁也不知道,连你也不知道。小刘怎么会让她早已怀疑的郑建安知道呢?"
王栋继续谈他了解的情况。他说:"我马上到省政府找我们的情报人员了解,才知道这是全国性的大行动,配合皖南事变一起动手的。恩施这边,陈诚最积极,皖南事变一发生,马上就动手大搜捕。不露风声,一声令下,就同时抓了四百多人。但是据他们打听,第一批里并没有抓到大何和小刘,甚至也没有郑建安。据说,特务很偶然地在三里坝省医院发现了何功伟。何功伟是他们在武汉时就想抓的一个学生领袖,后来下落不明,现在偶然在恩施发现了他,特务就奉命决心要在恩施抓到何功伟。但是一直没有再发现他,以为他是从这里过路的。没有想到还是通过郑建安这个叛徒,把他抓到了。陈诚十分重视。"
我问王栋:"郑建安并不知道大何和小刘的住地,他怎么找到大何的呢?大何和小刘不住在一起,怎么会大何被抓后,小刘也被抓了呢?"
王栋也无法回答,但是他说:"他们探听大何被捕过程。据说是在一个医院里发现了他,跟他到一个农民家里抓到他的。"
"哦,我知道了。"我说,"他们说的这个医院一定是羊湾医院。就是小刘生孩子的那个医院,大何曾经到那医院去看望过小刘。大何打摆子,久治不愈,他就在羊湾医院买药。后来他被狗咬了,也是在这个医院医治拿药。但是除开小刘和我,谁也不知道呀,连郑建安也不知道呀,特务怎么到那里去抓他呢?"
王栋说:"他们就是这么说的。如果他真是在羊湾医院被发现和跟踪的,他去的农家一定就是你的家,所以小刘也一起被捕了。"
我说:"很有可能,因为我走以前,大曾经对我说过,他会常常去看望坐月子的小刘的。大何的眼睛有点近视,却不便戴眼镜。他被盯梢了,未必能觉察到,便把'尾巴'带到我家里去了。"
何功伟和刘惠馨被捕的过程,大体上就是这样。但是还有一些细节不大清楚。可以肯定的只是他们两个是由于叛徒郑建安的出卖而被捕的。
从解放后被抓到的叛徒郑建安的口中得知,他被捕后,供出小刘曾在羊湾医院生产,特务便赶到羊湾医院抓小刘,小刘已经出院回家。但是特务估计,小刘可能还会回医院复查,便守在医院里。不幸的是何功伟因病去医院拿药,被医院护士误指认是小刘的丈夫来了,特务因此偷偷跟踪何功伟,何功伟因为近视却又没有戴眼镜,不知道已经被跟踪,把特务"尾巴"带到小刘家里去了。特务等何功伟出来后,在外边抓了他,然后再去抓小刘。当特务起初误抓隔壁有小孩的女人时,小刘发觉了,如果她立刻出逃,也许可以逃脱,但是她没有,她从容地把家里的有关文件烧了,特务冲进去把正在烧文件的小刘抓了。他们被抓到特务机关后,郑建安向特务指认了特委书记何功伟和妇女部长刘惠馨。
没工夫悲伤
王栋把何功伟和刘惠馨被捕的情况谈完,最后说:"真是没有想到,小刘就是那一两天内,就要带着孩子到利川来和你会合,回四川去。大何也只待十天,等小许一回来,就一块儿到鹤峰去,便一切安全了,谁知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了娄子,真是太不幸了。"
我听了他说的话,低头沉默了,不说话也不看他。
王栋站起来说:"关于善后的问题,北路几个县,我已经作了安排,南路几个县的安排,等你休息一下,定下心来,我们再来研究罢。"
"休息一下。"他再一次重复这句话,便要转身离开。我这才感到全身疲惫无力到几乎站不起来,整个身体就像要散架了。我开始从麻木恢复到有知觉,我的眼泪好似要从眼眶里奔涌而出。我真想冲出门去,直奔到一个无人的旷野里狂走,我要呼号,我要痛哭,我要咒天骂地,我像一个点着了引线的炸弹要自我爆炸。
我知道,何功伟,我尊敬的领导和朋友;刘惠馨,我最亲爱的人,他们是永远不会回来了,还有那个才生下来不过一个月的小女儿,她没有招惹谁,大概也是注定地活不出来了。血呀,到处是血呀。从我入党以来,我看到的是到处在流血,听到的是到处在流血。多少革命志士倒下了。现在,血,突然流到我的脚边来了。钱大姐早对我说过,革命不流血是不成的。为了人民,为了祖国,为了革命,我们随时要准备流尽最后一滴血。大何和小刘已经流血在前面了,我也要准备跟着他们流血在后。我知道,敌人一定在千方百计地追捕我,我时刻准备随小刘而去。
但是血不能白流,我也要叫敌人付出血的代价。我必须活下去,为烈士们未竟事业而奋斗,公仇私恨,都要求我活出来,眼前的危难,同志们的安全,如何封堵被敌人突破的防线,如何不乱方寸地妥善其后,都需要我活下去,冷静地处理好眼前的问题。我没有理由去伤心,去痛哭。"我没有时间悲痛!"我终于对王栋喊出这一句来。
王栋留了下来,和我一块儿来研究眼前必须处理的紧急问题。第一件事情就是组织疏散问题。虽然我们完全可以信赖大何和小刘的坚定性,但是依照组织原则,还是要把各县委的领导人撤退或转移。把"红"了的同志尽快转移到乡下去隐蔽起来,有的则撤退到四川去,或到敌后的鄂中大洪山游击区去。北路几个县的善后,王栋已经在恩施作了安排,南路几个县还不知道特委出了事,要马上通知他们,做好组织疏散,至于县委领导同志目前先找地方隐蔽起来,如何转移,听候我们向南方局汇报后的通知。我们决定马上叫现在三十里外的一个小镇上居住的利川县委书记黎智,到利川县城来。他赶来后,我们向他作了交代,他除开做利川县委组织的应变措施外,还委托他马上到咸丰和来凤去通知来咸中心县委的杨弟甫和张师载,做紧急处置。他们的去留或转移,听南方局的通知。并且告诉各县委书记,如果南方局的通知未到而受到敌人的追捕,形势紧急,可以离开岗位到重庆南方局去找人,他们的组织关系由我们带到南局去。
眼前还有两件更紧急的事要处理。一件是鄂西特委的政治交通员王宇光,他到南方局汇报后,送许云和她刚生的小孩到我的家里去以后,算时间大概已经回到鄂西了,他并不知道大何已经被捕,他在恩施停留,是很危险的,于是王栋马上沿利川到恩施的路上一路寻找过去。算好,果然在黄泥坡的党员家里把他找到了。他回到利川和我见了面,我告诉他特委发生破坏事故,要他马上回到重庆南方局,先向领导汇报。他上路去了。
另外一件事更麻烦。王宇光奉何功伟之命,已经护送许云和她刚生的孩子到忠县我家里去了,许云正在我家里。她作为一个陌生人带着一个孩子住在我家里,身份不明,虽然我的父亲知道是我的朋友的孩子,可是没有对外人说。她处境不便,也许等我和刘惠馨老等不回来,她有可能把孩子交给我父亲后,自己便动身回到恩施找何功伟来了。那是很危险的。因此我们必须赶快从利川出发,向利川到万县的这条独路上,沿路拦截过去,希望把许云拦住。
这种在大路上的拦截活动,自然也是有很大风险的,但是何功伟已经落入敌人的魔爪中,绝不能再叫他的爱人许云也被抓住了。我们就是要冒险,也义不容辞。
我们赶紧在利川把需要紧急处理的事办完,改变装束,改变身份,马上动身从利川城出发,一路向万县拦截过去。三百多里的路程,我们两天便走完了,脚板磨起许多血泡,也顾不得了,救人第一要紧。
我们一直赶到万县长江南岸的陈家坝,却仍不见许云的踪影。我们分头在陈家坝的大路边茶馆等了两天,还是不见许云的滑竿过路。
我们两人带的钱快用完,不能再等了,于是我们决定王栋继续守在陈家坝,我赶到重庆去,向南方局汇报。我路过老家忠县时,不敢冒险回到乡下的家里,但是我知道家里,父亲有一条接县城的搭线专用电话机,我可以在忠县县城设法和里电话联系,打听许云走了没有。
我走以前,为了让王栋有多一点的旅费,我把钱全部留给他,我设法混上轮船"赶黄鱼"去。

【马识途(1915年1月17日—2024年3月28日),本名马千木,生于四川忠县(现重庆忠县),中国现代作家、诗人、书法家,曾担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四川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1936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同时开始了文学写作。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国文学系。1949年任成都军管会委员、川西区党委委员兼组织部副部长。1958年,奉命筹建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任分院党委书记、副院长。1960年,出版短篇小说《老三姐》。1961年,出版长篇小说《清江壮歌》。1980年,被选为四川省文联和作家协会主席并出版回忆录集《景行集》。1986年9月,任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2005年,出版《马识途文集》。2013年1月17日,被授予巴蜀文艺奖终身成就奖。2024年3月28日晚19时25分,马识途因病去世,享年11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