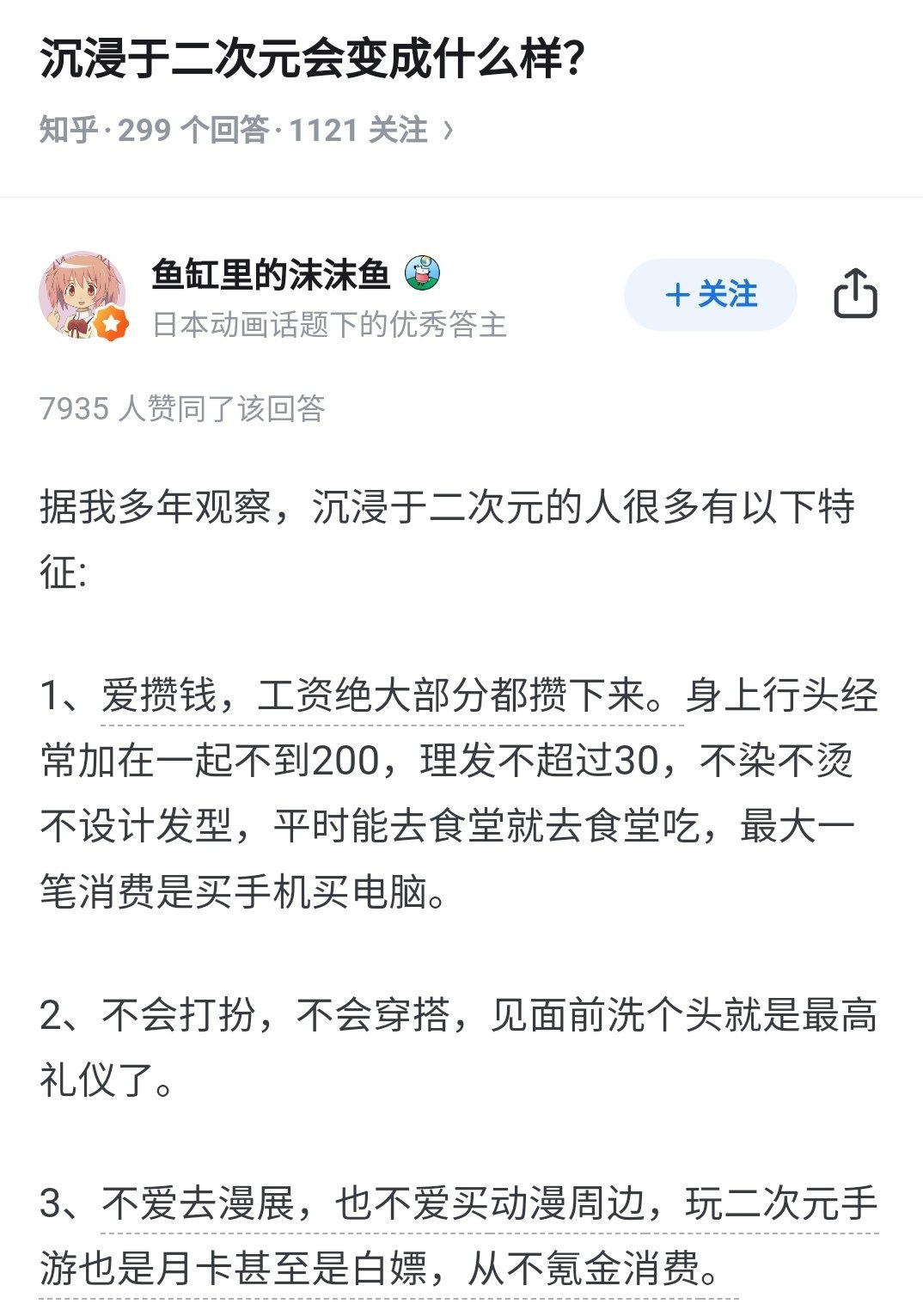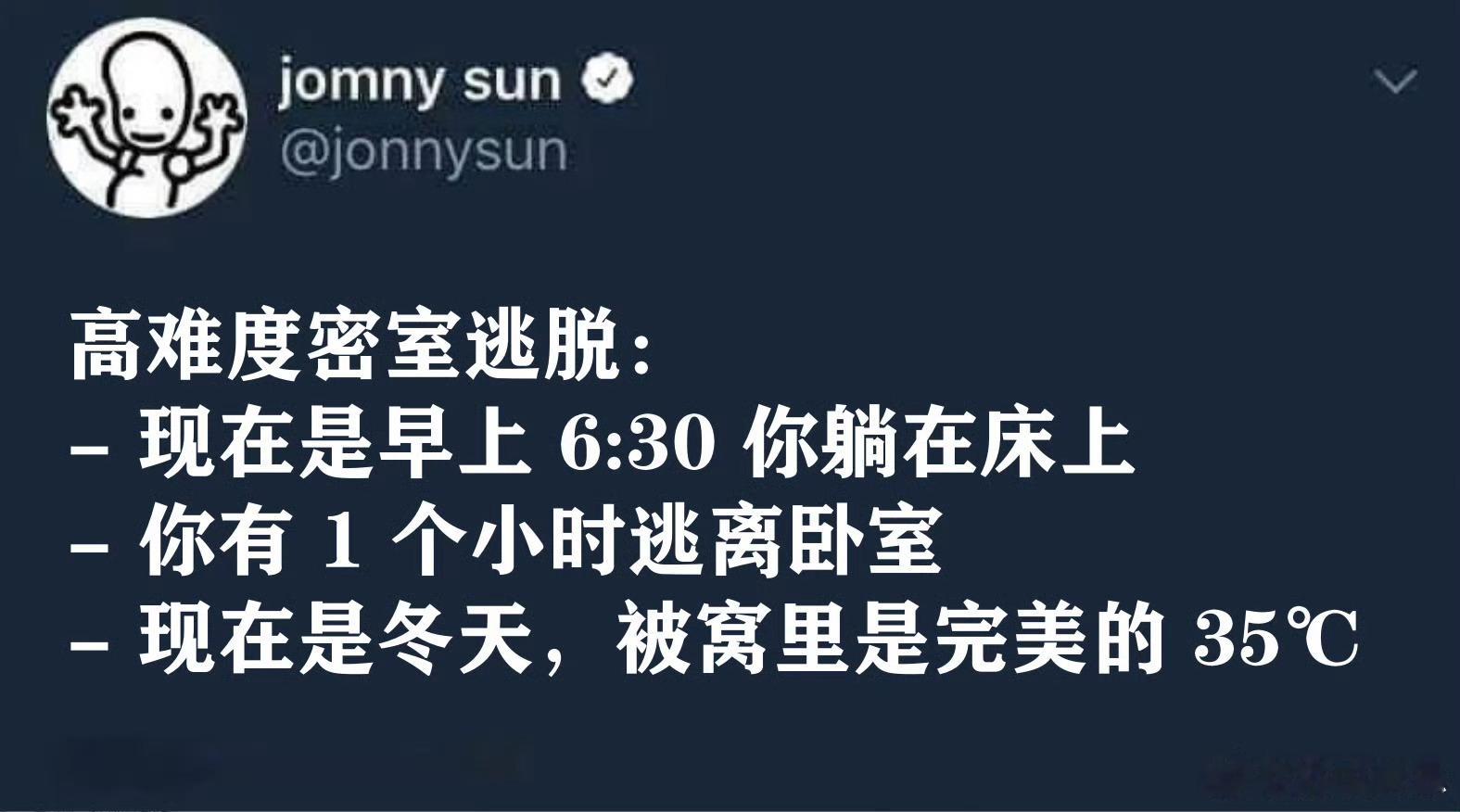作者简介
姚 瑶,作家,译者,著有《时光电影院》《失眠症患者的夜晚》等小说作品,译有《最后一刻的巨变》《心是孤独的猎手》《孤独故事集》等三十余部作品。在沉默的文字中,过一种喧嚣的生活。

春天时,我下定决心,搬离闹哄哄的市区,在北京的远郊,找到一处四面环山的山谷,开始了某种并不算彻底隐居的山居生活。
从市区到这里,只有一条路可走,朋友开玩笑说,若是深冬大雪封山,你出都出不来了。去往山谷,跨过水面宽阔的永定河后,要接连穿过两座隧道,分别名为苛萝坨与潭柘寺。
待车穿过两座山的黑暗山体,重入光明之时,原本朝同一方向行驶的车辆,高架边的万家灯火,属于城市生活的嘈杂声浪,尽数被隧道拦截,周遭骤然寂静,群山显现,静默环绕,天地间,仿佛只有我了。这是我为自己找到的某种“纵身入孤独”的方式,某种物理意义上的“与世隔绝”。
搬家的那一天,粉色山桃花开得漫山遍野,我朝着山的方向不断靠近,脑海中不断循环着同一句话,“如果我们纵身入孤独呢?如果那就是喜悦呢?”这句话来自我翻译的一本随笔集——《孤独故事集》,我忽然意识到,恰好是一年前的这一天,我交掉书稿,结束了探索二十一颗孤独心灵的旅程,仿佛一种暗示,整整一年后,我自己的生活完成了与书籍的互文,我终究“纵身入孤独”了。喜悦吗?的确是喜悦。同时也有一种隐约的希望,在未抵达山谷的半路上,我已经想象出在与世隔绝的山中,阅读,写作,隔离人事,尽情向内探索。所以我纵身扑入的,是名为孤独的希望,希望自然同喜悦相连,因为尚未实现,因为有实现的可能。
搬完家的第二天,我就收到了《孤独故事集》的译者样书。时隔整整一年,这一年的时间刻度上,又塞满了我翻译的其他作品,我自己写下的故事,所以这本书中的一段段人生碎片与细节,都被掩埋在了记忆的汪洋之下。但我没有急着重新阅读它,因为和它一起抵达的,还有另一本书,名为《我所告诉你关于那座山的一切》,初初搬到山中的我,自然先打开了这一本。但是在翻开这本书前,我并不知晓这会是一本让我如此心痛的书,我不知道作者刘宸君的生命定格在了十九岁,定格在了尼泊尔的山中岩洞;更无法想象与旅伴困守绝境四十多天的她,内心都经历了怎样的跌宕与煎熬,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写下那些笔记与书信?而她唯一的旅伴,又是怎样在她离世后,独自在山洞中又熬过了三天,最终等到了救援,带着她的遗体与遗稿,重返人间?书中有两句话刺痛了我。一句是她问自己的老师吴明益,“害怕孤独的人可以写作吗?”一句是她在洞穴中写下的,“我还是想要活下来。”在无情而短暂的一生中,她落入了名为孤独的绝望。
我看向窗外轮廓嶙峋的群山,它带来喜悦,也带来绝望;它亘古绵延,也转瞬崩塌;它已经存在了很久很久,并将继续存在。人步入山中,制造出千万种命运,一如步入孤独,缔结出千万种果。无论是主动寻求孤独,还是因惧怕而躲避孤独,最终,孤独好像都会成为最适合文学发生的土壤,拥抱孤独或惧怕孤独的人,都会以形形色色的痛苦与喜悦,浇出了一片疯长的花园。我想,孤独大概本就是文学的起点吧。古老先民在莽荒深夜点起篝火,结绳记事,凿壁作画,编织故事,口口相传,人类不就是靠着深夜的一点光亮和一笔故事,蹚过孤寂的深夜,打发无所事事,寂寞无聊,绵延到今天?从有了人开始,就有了孤独。正是在这样一个时刻,我重新翻开了《孤独故事集》,迎面又遇见那句“如果我们纵身入孤独呢?如果那就是喜悦呢?”二十一位风格与背景天差地别的作者,二十一段毫不遮掩的人生故事,这些小说家从虚构人物背后走了出来,撕碎语言上的重重委婉与粉饰,直白地写下了自己的脆弱,痛苦,不堪。随着我一篇篇重读,那些在这一整年中被遗忘的孤独的不同形态又逐渐浮出迷雾,一一被我打捞出水面,渐次清晰起来,而在翻译过程中的唏嘘与共鸣,也都如退潮的海浪重返潮间带,驻足海岸线的我,全都想了起来。我想起这本书里形形色色的孤独,关于性别、欲望、移民、成瘾、疾病等等,有许多孤独的形态,我都不曾切身经历,却完全可以感同身受。也许,就像这世上所有的山脉都是彼此相连,这世上所有的孤独也同样殊途同归,是同一片海洋里诞生的浪花,只是呈现出不同的色泽、形态与强度。只要我们体验过孤独,就能理解彼此的孤独,理解从孤独出发而创造出的一切。
隐于生活的B面
娜塔莉自幼病弱,常常要请假在家休息,因此度过了许多独自一人的时光。在拥有过多独处机会的漫长少女时代,她喜欢上了阅读,甚至主动寻求这种独处的时刻。她想到,这种被迫陷入孤独,又反过来拥抱孤独的体验,或许并非只在自己身上出现,因此决定编纂一本以“孤独”为主题的作品集。她向诸多作家发去邀约,回应她的女作家要远远多过男作家,所以她在序言中说,“这本书更多地容纳了她们对于孤独的观点。”全书有三分之二的篇目出自女作家之手。男作家们书写的孤独涉及种族问题,以及对梦想的追求,对科技社会的反思;而女作家们所写的孤独则更内向,更微观,更复杂,也更隐匿,隐匿于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隐匿于稀松平常的日复一日,隐匿于无比正常又寻常的一餐一饭。因此,我们是否也可以说,热热闹闹的现实生活,其实也更多地容纳了属于女性的孤独?抑或是,无数女性将自己的孤独隐藏了起来,所以生活才有了热闹的面目?这种隐匿的孤独发不出声响,无法慷慨激昂地表达,无法呼救,甚至饱含难以道明的矛盾。我们从这些女性故事中不难发现,女性往往和娜塔莉一样,一边感受着孤独,一边又追求着孤独。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同样身为女性写作者的我,仿佛参加了一场奇异的聚会。姐妹们坐在一起,聊着各自的生活,剖析各自的痛苦,信息密度极高,却又是不声不响的。我在这种无声的倾听与倾诉中,不断代入自我,不断回忆过往,不断点头,不断理解,忽然间,就弄清楚了有关女性孤独的那个悖论:原来身为女性,我们并不是一边感受孤独一边求索孤独,而是当我们看清并接受自身的孤独处境后,决定只身上路,看看孤身一人能走到哪里。我们不是去追求孤独,而是追求远方某个模糊的目标。我们并不知道自己能走到哪里,会得到什么,没有想过得到奖励,甚至从出发的那一刻就作好了被命运赠予一场空的最坏打算,我们只是决定离开此地,去往他方,亲身实践一场属于英雄的奥德赛史诗。就像海伦娜·菲茨杰拉德在《一种奇异而艰难的喜悦》中提及的,经典文学中满是英雄,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男性。他们之所以成为英雄,就是因为走上了孤独求索之路。在这样的追寻叙事中,男人斩断所有社会纽带,在孤独的试炼中完善自我,再高奏凯歌重返社会。《奥德赛》及它的仿效之作都是追随一个男人的成长展开,他在冒险与悲剧事件之中失去了所有同伴,也失去了与社会的全部联系,不得不找寻回归的路途,穿越重重险阻,孤军奋战。当这些男人最终结束英雄漫游归来时,社会仍旧原封不动地等着他们,因为女人们一直在照管一切。女性似乎从来没有这样的独立机会,也鲜少得到同样的机遇去冲破社会桎梏,去发现自我,并作为英雄回归日常,被褒奖,被传颂。恰恰相反,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因为不曾失去同伴,不曾切断与社会的联系,所以整个社会传统都期待她们通过社交与情感将一切人事物弥合起来,离经叛道的女性不是英雄,而是疯子。社会法则一厢情愿地认定,女性需要被保护,不需要承受试炼。仿佛是好意,是温情,而这,反而成为了女性孤独感的来源。最无助的是,一旦你表达出你因此而孤独,得到的回馈可能是“矫情”,因此你选择了沉默,将一切藏匿。难道这样的孤独就不值得书写吗?在我看来,这份孤独,反而更接近于人类真正的孤独,在女性的身上,往往寄宿着人本身的困境与出路。所以,当英雄神话的时代落幕,当代的女性们选择在人生中孤身上路。艾米·谢恩在《孤身行路的女人》这一篇里,就提及了这样一个女人。一个名叫莉莉安的东欧移民,忽然离开纽约,独自步行前往西伯利亚。对于她的出走,众说纷纭,但莉莉安自始至终不曾开口肯定任何一种揣测,回应任何一种争议。她于平安夜出发,身穿连衣裙,脚踩普通的网球鞋,戴一条头巾,沉默不语,一路向北。艾米在下班回家的地铁上,通过播客听到了莉莉安的故事。那一刻,她身处沙丁鱼罐头一样的地铁车厢里,被婚姻、家庭、工作、书稿压得喘不过气,她忽然不知道了,自己和莉莉安相比,究竟谁更孤独?纽约一如这颗星球上所有的巨型城市,因为太过拥挤,反而让人成为了人潮之中的孤岛,地铁上密密贴在一起的身体间,有着无法跨越的鸿沟。在这样的城市生活中,身体的距离越近,心的距离就可能越远。因而对莉莉安来说,独处,独自长途跋涉,投奔某个应许之地或应许之人,反而成为了最不孤独的选项。艾米忽然意识到,自己之所以感到孤独,好像正是因为自己从未孤身一人,她的身边始终有丈夫,有孩子,有密不透风的陌生人,所以她无比孤独。她渴望去一个静谧之地,有陆地,有天空,独自一人,头脑清醒,心中念着他人,而不是被他人占据头脑,连自己都被挤了出去。她渴望体验与世界有所连接的孤独状态,而不是身处熙熙攘攘的陌生人之中,却觉得自己如此疏离。就像安妮·林德伯格在《大海的礼物》中所写的,如果一个人与自己失去了联系,那么他就无法触及他人……只有当一个人与自己的内核建立联系,他才能够与他人建立联系。而这一内核,往往能够在独处中寻得。艾米选择用另一种方式对待家庭与工作,她搬了出去,为自己租了个小房子,从日常中剥离出了一小块空间与时间,把与丈夫毫无深入交流的朝暮相对、围绕孩子的公转运动统统屏蔽在门外。在这个由她亲手撕裂的时空中,她读书、写作、思考、听音乐、广交友,并计划着长距离的徒步,在写下这些时,她说她的不快乐业已蒸发殆尽。在这本故事集里,艾米不是唯一选择以孤独对抗孤独的女性,甚至不是少数派。在古老的叙事中,享受孤独,离群索居的女人被刻画成怎样呢?女巫,怪胎,熬制毒药,不怀好意。曾经,女性惧怕被这样看待,被这样评价,没人想成为那个“阁楼上的疯女人”;但今天,这本书里的女作家们却说,独居让人成为森林中的女巫,强大,警觉,沉默,让访客不寒而栗,她们在属于女巫的那口锅中,熬干了那份不快乐。这种身处闹市却形同孤岛的不快乐,正是隐匿于日常生活的B面,翻开来便意味着触碰了禁忌与羞耻。你明明有着幸福美满的婚姻,忠诚的丈夫,可爱的孩子,为何感到孤立无援?当你因为孕育新生命而承受诸多疼痛时,朋友与丈夫都愿意体谅你,理解你,为何你还是觉得无人能感受你的切肤之痛?为什么脱离日常生活的轨迹,剥脱熟稔的身份,独自在陌生城市工作、生活,走在真正陌生的人群中,会让你无比自在?当所有人都表现得很快乐,很合群,你为何要不合时宜,谈论一个不快乐的话题,成为冒出来的那颗钉?然而事实上,若我们认真审视自己的生活,会发现,正是这些被压抑、不见天日的“不快乐”,为孤独感提供了源源不绝的能量。不能与他人言说之困境,当然是一种精神上的隔离。如果我们始终无视生活的B面,那我们只是在假装生活。幸福绝不是来源于敷衍与自欺,所以作家们选择暂停欢愉的乐曲,抽出卡带,翻过B面,重新按下播放键,仔细聆听,深入思考,勇敢地自我剖白,笔亦如手术刀,径直探入自己体内真正的病灶。而如此对待自己,恰恰是因为,他们想要缓解这份孤独,找到与孤独温柔同处的方式。在这个求索的过程中,娜塔莉说,“孤独感纵然极具破坏力,但我发现,它也能充当通往美与探索的门户,这就足够动人心弦。”因此,有了这本《孤独故事集》。而开篇第一个故事,梅根·吉丁斯就鼓励想要写作的女孩们独自去电影院看电影。她认为,在开始艺术生涯时,无需考虑他人、只在乎自己的所见所闻与喜好的自由感是不可或缺的,而这种自由感可以通过独自去看一场电影来实现。我们完全可以“只看向自己的内心,由此去了解周遭的世界”,不要恐惧独自去做些什么,这份敢于在世间冒险的勇气,是写作所需要的,也是生活所需要的。因此她热衷游泳、皮划艇等诸多运动,甚至险些因此丧命湖中。她说得最多的话就是,“我不害怕。”深夜,我站在寂静山脚下仰望山的轮廓,漆黑的山在漆黑的夜空里勾勒出参差嵯峨的色块,不言不语,充满了压迫感,与白昼时它所展现的温柔连绵截然不同。在直面山的那一刻,我想到的也是,“我不害怕。”
“我不害怕”
其实,“我不害怕”与“孤身上路”都是作家们为自己的困境找到的答案。身陷孤独的囹圄,所以决定“孤身上路”;被迫面对未知与动荡,因此只好自言自语,“我不害怕。”生活中这些看似矛盾的行动,恰恰构成了文学之中的正当逻辑。书中这些用行动诠释“我不害怕”的作家,几乎可以说是别无选择,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所处环境中的那个“极少数”,与他人有着表面上醒目或内在上根本的区别,无论是被大多数人感知到这种不同,还是自我认知到这种区隔,都意味着一种“孤军奋战”的处境,这份身为“异乡人”的孤独,要与之共处,只能选择不害怕。比如身为黑人的杰弗里·艾伦,由在白人家中做女佣的单身母亲抚养长大,本就成长在夹缝求生的环境,偏偏又患有哮喘,因此不擅交际,沉默敏感。当他第一次在电影院看到李小龙的电影时,他为拳脚功夫而狂热。其实拳脚功夫不过是勇气的具象化表现,是他可能拥有的、对抗歧视的武器。比如用英文写作的华裔作家郭珍芳,无论是小小年纪跟随家人初到美国,还是结婚生子定居北欧,在西方世界里,她永远是个与众不同的面孔,永远无法抛弃属于东方人的思维方式。小时候,她贫穷困苦,在同龄人中得不到理解,于是她拿“雄心壮志”填补了这一切,通过自学,考入哈佛大学物理系,写出畅销书,把生活的主导权夺回到手中。这份雄心壮志,便是她的“不害怕”。再比如出生并成长于考文垂的英国作家彼得·戴维斯,在他的回忆之中,童年生活黯淡无光,乏善可陈,因为他热衷科幻文学与电影,但在考文垂,他找不到可以交流的同类。纵然考文垂是他的故乡,纵然家人朋友都在身边,纵然这就是他在世界上最熟悉的地方,可他仍觉得格格不入,人生于他,仿佛一场星际迷航,在茫茫的宇宙中,他只能独自航行,寻找能够并肩一段路的同伴。还有伊朗的作家蒂娜·耶纳里,少女时代,她和家人成为难民,背井离乡,非法移民到美国。她学会了在没有朋友的情况下生活,因为她发觉自己无法成为任何人的朋友,只能成为他人慈善的接受者,是所有人怜悯的对象。那时的她,做了和郭珍芳一样的选择,努力学习,取得成就,逃离过往。这个过程当然称不上顺利,她做过很多傻事,经历过很多次挫败,暴露过很多次脆弱,也隐藏了许多的不堪。无论她把生活粉饰得如何热闹,总有那么一个光照不到的黑色角落。在故事的最后,她是这样写的,“随着每一章徐徐展开,都有一个新的黑色角落出现,每一个都以自己惊人的方式丑态百出。但十年后,我仍然会说,下一次,我会勇敢的。”我忽然从这些截然不同的作者身上,看到了属于人类的共性,我们遇到的一切现实层面的难题,似乎都可以通过精神层面予以解决。无论那个现实的难题有多复杂,只消一句简简单单的“我不害怕”,好像我们真的就可以壮起胆子走夜路了。其实,在说出“我不害怕”时,就代表着他们已经感受到了胆怯的存在。但无人能给他们壮胆,他们也不能调头逃跑,所以只能自己推着自己,硬着头皮往前冲。这种人生经验绝对不是属于这些作家的个例。我始终相信,没有人次次都站在大多数那一边。在我们一生中的某个阶段,某些时刻,某些处境中,我们一定都成为过那个“异乡人”,我们一定都有过那种格格不入,与他人不同,无法融入的尴尬体验。大到只身留学、移民,进入截然不同的文化环境,小到参加一场派对,除了组织者外你谁都不认识,而在场所有人早已相互熟络,抑或是更换工作,承受新团队对你的防备与疏离,在这些时候,我们都会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异乡人”。消化这种孤独所需要耗费的时间、情绪、能量,都需要我们独自承担。无论是一晚上,还是一年,甚至十年,我们一定都像这些作家们一样,告诉过自己,“我不害怕”。是的,无论是我们,还是书中的作家们,在千差万别又殊途同归的异类感中,似乎真的没有更好的办法与经验可以模仿或传递。毕竟,我们都是孤身来到这个世界,也将孤身离开这个世界,这两者才是仅有的真正意义上的普遍经验,却没人能够传授给我们,因此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这世上永远的异乡人。
永远的异乡人
如果说上述种种孤独都是有解的命题,有一些“异乡人”所面对的,却是另一种孤立无援的处境。“我不害怕”纵然可以支撑我们走下去,但有些痛苦如同疤痕,终生伴随,隐隐作痛,哪怕遇到与你有相似伤口的人,也依然无法让你释怀分毫。同样的痛苦降临到不同的人身上,痛苦不会被稀释,每个人承受的依然是完完整整的痛苦。我在这本书里,就读到了这样的痛苦,几乎全部来自医院。身患多种慢性免疫疾病的依曼妮是住院部的常客,她知道自己以比他人更快一些的速度,走在通往死亡的道路上,这太残酷。作为一个内向的创作者,日常生活中她频繁赞颂独处的美好,可是一旦住到病房里,独处的慰藉便不复存在了,门外的脚步和嘈杂与她无关,她感受到被世界抛弃的寂静,独处在此刻成为了不能承受之重。我曾在体检时查出一些模棱两可的问题,在一次次的深入检查、不确定、等待、反复检查中,我第一次真正直面疾病与死亡的关联。此刻我才清楚地意识到,无论我在小说中虚构过多少种死亡,做过多少次练习,在亲自等待命运宣判的那一刻,那种全世界被消了音的寂静感,无法同任何人言说,哪怕是父母,哪怕是爱人。但与此同时,同恐惧、敏感、焦虑并存的,还有一次诡异的平静,在回想过往,想象将来的时刻,对身边的人们怀着更温柔的爱意。所以我非常理解依曼妮在故事的最后,用充满疼爱的口吻提及孩子,她说“孩子们散发的阳光,穿透了孤独,每一次都救了我”。孩子不必理解她的孤独,但孩子可以治愈她。正如我的家人无法理解坐在核磁共振检查室门口的我有多么孤独,但没关系,他们依然让我感受到了慰藉。另一个作者杰丝米妮在新冠期间失去了她挚爱的丈夫。他们拥有堪称完美的爱情,丈夫将大量时间与精力投入给她和孩子,几乎时时刻刻陪伴在她身边,是温柔细腻又可靠的伴侣。我向来很惧怕看到或想象这样的故事,因为我恰好也有这样一个细腻而可靠的伴侣,我常常想到数十年后,我们将彻底从世上消失,成为宇宙里的微尘,每念及此,我就会感到某种宏大的虚无笼罩下来。七年前,他曾因中枢神经感染突然晕厥,我人生中第一次拨打了120。他住进医院,直到三周后出院,都没有查出确切病因。他住的医院在北京最热闹的商区三里屯。那段时间正是临近农历新年,我每天顶着凛冽的朔风往返家中与医院,走在因为迎接新年而装扮起来的街头,觉得自己仿佛被罩在一个玻璃罩内,周遭的鼎沸人声与车流都显得那么沉闷,那么遥远,像远远退去的潮水,在我与海洋之间空出贫瘠裸露的滩涂,晶莹的浪花在远处跳荡,而我独自站在岸上,与世隔绝。我觉得自己变成人潮中唯一的灰色,与整座城市割裂开来,所有人的笑脸都令我厌恶,或者说嫉妒。此刻回想,那就是孤独,我在独自承受生活中的变数,哪怕知道与我擦肩的陌生人可能也同样在经历痛苦不幸,但我的孤独并不会因此得到丝毫缓解。说实话,我并不惧怕独处,我可以独自去餐厅吃九宫格火锅,独自去异国他乡旅行,独自看电影,独自思考,独自散步,正因喜欢长时间独处,我才选择了写作与翻译作为终生职业。主动寻求的独处是迷人的,但被动陷入的孤独却是致命的,所以我惧怕的是一种彻底失去某个人的可能。杰弗里·艾伦说,外婆去世时,母亲失魂落魄,说了一句,“现在我谁也没有了”。他不明白,他认为母亲明明还有他,怎么能说谁都没有了呢?可是,当他终于也经历了母亲的离世后,轰然间就有了同样的感觉,“现在我谁也没有了”。这是只有经历过或被虚晃过一枪的人,才能听懂的语言。
玛雅·朗恩也同样经历了失去母亲这一痛苦。但不同于死别,她所经历的是母亲罹患阿尔茨海默症,母亲一天天、循序渐进地将她遗忘,同她进行着缓慢但残酷的告别。她下决心亲自照顾母亲,时刻陪伴左右,但逐渐力不从心,眼看自己的世界不断缩小,自己的时间与家门外的时间出现了裂隙,外界一往无前,可她停滞不前,无法写出新的作品,无法申请教职,因此日渐孤立无援,对自己失望透顶。作为旁观者,我们当然可以轻飘飘地说一句,送去专业看护机构就好,母亲可以得到更专业的照护,女儿也不会因此搭上自己的人生。没错,说这话是出于关心,道理也是如此,但又恰是因为如此,像玛雅这样的女儿才会感到更加孤立无援吧?这就是我所说的,陷入了“永远的异乡人”的境地,只要落入这样的境地,从此你只能讲一门自己才能听懂的语言。照顾失智老人的辛苦难以想象。好友曾时常提及她的母亲,为了照顾失智的外婆,原本热衷唱歌跳舞、社交生活极为丰富的母亲彻底足不出户,成为二十四小时待命的全职女儿,并且要承受外婆认不出自己并辱骂自己的痛苦。她非常心疼母亲,但每次提及要不要换一种照顾的方式,母亲都会发脾气。我相信她母亲的内心一定被复杂的痛苦所占据,体力上的辛苦,精神上的消耗,情感上的剧痛,在陪伴外婆最后七载的时间里,母亲成为了那个无人能够理解的“永远的异乡人”。一切的关心对她而言都是不痛不痒的,是无效的。还有的作者写到了离世的父亲,夭折的孩子。最终你会发现,最具杀伤力的孤独,竟然不是心灵上的孤独,而是肉体上的隔绝,是物理意义上的不可触及与彻底失去。在那些看得见、摸得着、能够感知的困境面前,我们还能斗胆一战,可生死却完全超出了我们的维度。可生死却是我们唯一逃不开的孤独,只要我们活着,就一定会面临疾病和死亡,面临他人或自己的离开,面临人生的戛然而止,面临人事物的遗憾收场。我们习惯在遭遇不幸时说一句“时间能治愈一切”,但最不幸的就是,孤独这件事,似乎只会随着年岁的增长而越来越浓墨重彩,越来越像一匹脱缰野马。在很多描述永生的奇幻故事中,作者都将重音敲在永生之人的孤独上,因为他们将反反复复承受亲友的老去与离开,使得明明常驻这世界的他们,成为了那个真正意义上的“异乡人”。这些故事是用极端的情境告诉我们,我们终究得接受,哪怕全世界有几十亿人,哪怕我们从不缺爱与理解,可孤独无比公平,哪怕你此刻还未感知到,将来也一定会与之狭路相逢。但我想,这本名为“孤独”的故事集,给了我们一种很好的示范,就算孤独始终存在,不能被消除,并且可能随着时间推移更加突显,但这不代表我们不能做些什么,不代表我们做什么都是徒劳。当你感到孤单,与人隔阂,与世隔绝,不被理解,无人体谅,孤立无援,并因此悲伤、恐惧、愤怒、自怜、自艾,或许,你可以选择像书里的作家们一样,把你的孤独写下来,无论这种孤独是慢性疾病,还是急症发作,是痛彻肺腑,还是蜻蜓点水,你都可以把它写下来。毕竟无论你做或不做什么,这段孤独的时光都得熬过去,那不如就把自己内心的脆弱一笔一划地写下来。你可以对此追根溯源,向童年深处一路打捞,到任何人身上、任何经历之中去寻找原因。你也可以只记录当下的感受,像拆开被猫挠乱的毛线团一样,一根一根,一缕一缕,一尺一寸将内心的煎熬与疑惑记录在案,同时扮演倾诉者与倾听者,一人分饰两角。你也可以抱怨,可以咒骂,可以反思,也可以任凭意识流淌向任何地方,可以自责,也可以责怪他人,但重要的是,要对自己坦诚,不要感到羞愧或尴尬。已经有无数写作者证明,“写下来”这个举动就是这么神奇,在你写下来的时候,你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宽慰,并找到最强有力的陪伴——自己。这个答案或许不能令你满意,原来说到底,我们还是只有自己。但书里的二十一段人生故事,每一个都在讲述他们如何陪着自己度过人生中最孤立无援的日子,从而获得爱与理解的能力。在书中的《在地平线》一篇里,作者麦吉认为,我们对自己负有最基本、与生俱来的责任,哪怕使尽浑身解数,也不可能将其抛下,这份责任就是一种不可撼动的孤独。我们虽然可以用肉体与思想同他人建立联系,感受亲密,但这种亲密是有限的。那么怎样的亲密是无限的呢?麦吉结合自身经历与诸多素材资料,发现人处在生死攸关的情境或创伤中时,大脑就会创造出一种幻象,塑造出一个“第三者”,为我们提供某种陪伴、引导与鼓励。许多身陷险境,濒临死亡的人,他们拼尽最后一丝气力,幻化出的不是一顿饭,一张床,而是一个“同伴”,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在火光中看到的是家人。生而为人,我们仿佛是地球上最贪婪的物种,但生死关头,我们渴望的,只是不再孤单。如果人人都在不同时刻,不同地方,感到孤独,或许那恰好说明,解药不在任何他者身上。把我们的孤独尽数写下来,这样做,并不能让我们不再孤单,但能让我们划亮火柴,映照出人生路上最忠实的伴侣——自己。看看我们能够一起走到哪里,一起在这条孤独的路上,创造出一些什么。
来源:《山花》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