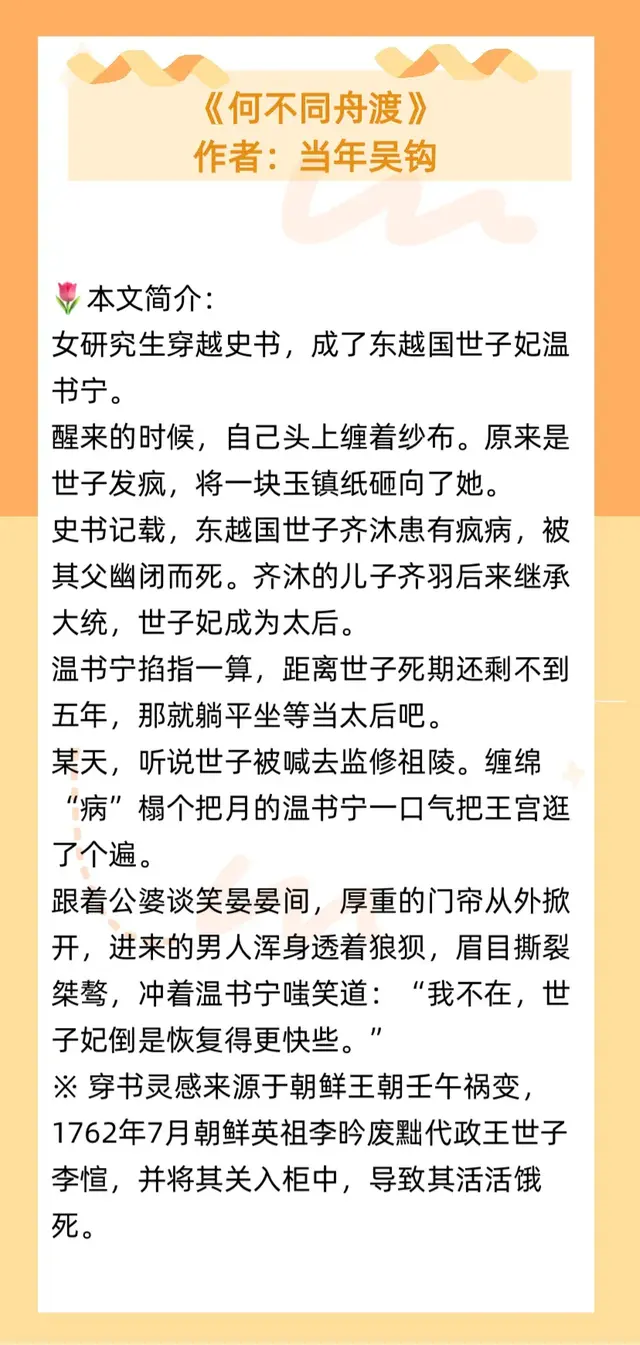简介:
女主视角:
叶翎第一次见到魏弦京时,她戴着雉鸡翎羽织成的羽冠,和杂耍班主一并跪在地上砰砰磕头,希求被冲撞了的贵人给予宽恕。
满座贵客皆勃然,只有魏弦京出面主持,道出是杂耍班主贪图小利遭人利用,惊扰了娇客,将其罚入牢狱。而后叶翎则懵懂地接过自己的身契,从此不再是任由班主斥骂责打的稚奴。
她是被魏弦京施恩的过的,万千百姓中的一个。
隔着庸俗的羽帘,她小心地回眸,将那面如冠玉的侯府世子记在了心里。
经年后,叶翎带着她不伦不类的杂耍班子,用毕生的积蓄贿赂了刑场守卫,换来和即将被处斩的魏弦京再次相遇。
可这一次,却是她站在熙攘的菜市口边缘的桅杆上,俯视着即将要被斩首的魏弦京。在落魄的魏弦京和前来送别的京城百姓面前,叶翎献上了她最出彩的一次表演,涅槃。
她只是万千黎民中的一员,无力对抗皇命,还魏弦京公道。她只能用她一生都在追逐精修的杂艺,为那并不记得她的恩人演上最后一出戏。
她腰挂细绳,从桅杆上翻身跃下,风拂过她胸前双臂上缠挂的鸟羽,正午日光熏干了她脸上的泪痕。
她像一片灼烧着的凤凰翎,骤然烙进了魏弦京的心底。
男主视角:
魏弦京的前七年,生在锦绣堆儿里,父亲是皇帝最器重的养子,母亲是镇国公府名满天下的贵女。
可到了他八岁那年,朝廷改弦更张,新皇登基,父亲猝死城外,母亲被迫改名换姓,成了新皇的皇后。
他被父母故交收养,成了备受新皇厌憎的侯府世子。旁人眼里,他魏世子风光霁月,盛名无双,唯有时运不济;可谁又知道他每一日睁眼,都在等待皇帝那一杯不知何时到来的鸩酒。
他是这世间最见不得光的存在。
直到叶翎如同一捧雪夜的新火,在深渊之中骤然点亮他的眼底。

精选片段:
京城菜市口熙熙攘攘,人头攒动。时值正午,酷烈的日光将街头巷尾的砖瓦映得纤毫毕现。
即便是巡捕营的兵丁将刑场围得水泄不通,却仍无法驱散越聚越多的人群,也无法阻隔看客们窥探的目光。
菜市口的石板早就被岁月搓磨得平整顺滑,今日却因频繁的踩踏显得格外肮脏崎岖。此刻人们似乎忘却了尊卑之别,草履和牛筋鞋底踏在同一片廉价的石板上,鞋子的主人们共同注视着那被罪人恶徒的鲜血滋润了百年,显得有些油亮的断头台,和断头台前身着囚服,沉默跪地的年轻男子。
那便是今日就要被处以极刑的镇南侯世子,魏弦京。在此聚集的看客皆为他而来,大多神色肃穆,甚至有人难掩悲戚,而其中,就包括了早年受过魏弦京恩惠,常年混迹于鱼龙混杂的南城的杂耍班主叶翎。
“时辰要到了。”
刚过午时一刻,正是日头最盛,阳气最足之时,可那日光落在叶翎身上却让她遍体生寒:
“阿姊,这是我自己的事儿,前途未卜,你犯不着把自己也搭进来。”
叶翎身旁的女子听闻此言,被遮掩在黑色面纱下的唇角轻轻抽动,发出一声嗤笑。
“你为了报世子的滴水之恩,能将这条命搭进去,我也不过是报你这些年的恩情罢了。既然都是报恩,我用不着你来相劝。”
黑纱女子语气厌憎,却并不退却,这下可急煞了叶翎:
“阿姊!若我此行带累了你,你是要我后悔一辈子吗?!”
“你是该后悔!当年魏世子帮你,不过是举手之劳,他根本没有正眼瞧过你这下九流的卖艺女!而今他就要死了,你又何必上赶着去送死?我看你就是个榆木脑袋,撞了南墙也不回头!”
“我知道,我知道。”
叶翎抬手正了正她头上鸟羽织成的头冠,遮掩了她微微潮红的眼角。她和黑纱女子站在人潮附近的一栋茶楼屋顶,俯瞰着菜市口周围熙熙攘攘的人潮。
“阿姊,你低头看看这些人,半个京城的百姓几乎都在这儿了。他们是来送他的。这些年,满城百姓谁人不知魏世子遭当今搓磨,南边儿的瘟疫,西边儿的马匪,北边儿的旱灾,凡是那儿遭了灾,世子便要亲往,皇上不给兵不给权,让他办的全是有去无回的差事。”
“年前京里地动又遭了瘟疫,皇上和贵人全都躲到京外园子里去,锁了城门,让一城的百姓等死。可魏世子呢?是他带着几个游勇,挨家挨户地周济,光说这南城的人家,哪家没有受过世子恩惠?我们那条街,十之五六是世子从鬼门关拉回来的?阿姊,你低头看看,他们今儿都来送他了。”
“我叶翎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卖艺人,但我忘不了他的恩情。这些年我苦练技艺,就是为了能让他瞧一眼我凤凰于飞的把戏,让他瞧瞧我是否比当年精进了。我想让他知道,当年他救我于水火是值得的。可如今他……我至少要为他最后表演一次,就算还不了他的大恩,至少遂了我自个儿的愿。”
“况且…阿姊,今儿半个城都来了,半个城都来了。他们记着他呢,也记着皇帝带着家眷跑出城,却将城门锁死的腌臢事儿,或许——”
“住嘴!你疯了?!”
黑纱女子厉声呵斥,因为急怒惊惧,喉咙里甚至发出蟒蛇般嘶嘶的声音:
“叶翎,你到底要做什么?皇上下令要处死他,朝廷官员拦者皆死,你一介草民,和今日的其他看客没有不同!你不要——”
或许是她的声音太过尖利,几乎要刺破她柔软的咽喉,引来了下方的窥视。黑袍女子只好堪堪收敛声音,低声说:
“——不要去送死。”
叶翎没有回答,她戴上用鸟雀绒羽织成的半脸面具,柔软的暖黄色绒羽覆盖了她潮红的眼尾,一个漆金的木质鸟喙搭在她鼻梁的正上方,为她那张娇柔婉约的面容平添了几分猛禽般的凌厉和高傲。
“时间到了,我要去见他了,阿姊。”
叶翎说着,紧了紧腰间悬挂的细绳,突然纵身从茶楼屋顶一跃而下。她双臂舒展,衣袖上缠绕的红色鸟羽在秋风中簇簇绽开,被炽白的日光一映,宛若镀上一层璀璨的鎏金。
这耀眼的色泽立刻吸住了在场百姓的目光,恍然间,他们仿佛看到一只火红的凤鸟划过天际,又隐入人潮,不禁惊叫出声。
叶翎拽着挂在屋舍檐下和桅杆上的细绳,灵巧地从众人头顶掠过,又在众人的惊呼中无声地落在人群让出的空地上,隔着巡捕营兵士组成的人墙,正对着等待受刑的魏弦京。
“恩公,小女乃一介杂耍艺人,昔日承蒙恩公搭救,今日听闻恩公受难,特来相送。我草民也,做的也是抛头露面的下流行当,可我苦练技法,希求终有一日将我这技艺献给恩公赏看。而今无法择日,我便在此刻为恩公献上把戏,为恩公送行!”
叶翎几乎喊劈了嗓子,只为使她清脆的声音传得更远,让在场的更多人听到。话音未落,她面前的着甲兵士像一根根沉默的柱石,向她倾轧而来,甲胄摩擦的声音如同蛇蝎低语。
可叶翎并不害怕。只因她身后沉默肃穆的人潮如他所所料般突然沸腾了,原本被压抑的交头接耳之声变得异常尖利,像一柄长矛,猛然刺向那看似坚不可摧的巡捕营兵卫,使他们沉默的脚步陡然一顿,不得不撑起护盾和钢刀,面对突然沸腾的人潮。
“…恩公啊!江湖卖艺女子尚且有如此知恩图报之心,我等惭愧,我等惭愧!!!”
“魏世子!年前家母染上时疫,是世子带着街坊将我母妥善安置!您也是我家的恩公!”
“世子是青天大老爷,前些年我父被污蔑作匪贼,押入牢狱,险些被打去了半条命!我四处求爷爷告奶奶,还是遇到一官员仰仗世子爷的名声,才替我父洗清了冤屈,世子是我们一家的恩公啊!”
“世子于南城百姓有大恩…”
“魏世子…苍天无眼,为何要残害忠良!”
一声声慨叹夹杂着啜泣在人群中屡禁不绝,而更加明晰的,是一声声夹杂着愤慨的嘶吼:
“下九流的卖艺者尚且如此知恩图报,你们这些兵丁,难道家中就无人受过魏公子恩泽吗?又为何如此不通人情,苍天啊,请您开开眼,给我等报恩的机会吧!”
数以万计的嘶吼声交织在一处,近乎有型的气势将巡捕营兵丁手中的盾牌都震得不稳。
座上监斩的晋王冷汗如瀑,目眦尽裂,颤巍巍地拿起一旁桌上冰凉的杯盏,茶水还没入口,便浸湿了他威严官服的前襟。
“刁民…刁民要反不成?!快!杀了那下贱艺女!”
他身旁的狗腿子抻着脖子往台下看了看,被百姓充斥着怒火的目光刺得一愣,伸手揩去鬓边的冷汗道:
“主子,怕是不成,那艺女夹在人群里,要杀怕是得都杀了。”
在百姓的一声声愈发尖锐的嘶吼中,晋王面色红胀,他本就生得疏眉细眼,此刻更是显得獐头鼠目,形容卑劣,即便是他周围的奴仆都不愿多看一眼。
他旁边的奴才见状,忙出声讨好道:
“主子,您大人有大量,何必跟那贱民计较?她要演这上不得台面的杂耍,您就让她演去就是了,难不成她一贱民,还能把这守卫森严的法场劫了不成?”
“劫、劫法场?!贱民岂敢!咳咳...”
晋王气得几乎背过气去,而他身旁的奴才忙伸手抚着他的胸口,声音谄媚地诱哄道:
“主子莫急,被这下贱之人气着了可就得不偿失了!这午时三刻还未到,王爷不若就让那下贱艺女演那什么劳什子杂技,拖过了这点儿时辰,再私下处置她的胆大妄为也不迟。当务之急,还得是完成圣上嘱托,把魏弦京这罪人宰了才好交待!”
晋王并未回话,一双蝌蚪细眼中闪过不甘,却被喧嚣的民怨压制得无从发泄。突然,他一脚将他身旁谄媚讨好的奴才踢了出去,斥骂道:
“狗奴才,本王做事要你来置喙!来人,将那些贱民驱散,谁胆敢不从,格杀勿论!”
说罢,他犹觉不够解恨,抽出腰间悬挂的玄铁长鞭,竟是要亲自上前抽打跪在铡刀旁,垂首沉默的魏弦京。周遭监斩的官员看在眼里,也不由皱起眉头,心中百般怨怼,却不得不派人去阻拦,免得这晋王闹出更大的笑话儿。
怒发冲冠的晋王有所不知的是,刚刚被他一脚踹倒的奴才滚在地上,一张挂了冷汗的脸却朝向百姓的方向,打出几个繁复的手势,被人群之中的有心者尽数看在眼里。
周遭喧嚣的一切,叶翎都充耳不闻。她只看见身负绳索,跪在广场之上的魏弦京突然半仰起脸,露出一张过分苍白的俊朗面孔。叶翎直勾勾地看着他,正对上了他一双亮如寒星的眼眸。叶翎看着他张开了干燥惨白的双唇,似乎想说些什么,却因长久的干渴发不出什么声音,最终只对人群之中穿着羽裳的叶翎轻轻摇了摇头,唇角微微抬起,露出一个带着歉意的笑容。
叶翎的心脏重重一坠,眼眸酸涩难言。她知道魏弦京并不认识她,那双令人见之忘俗的晶亮眼眸里满是陌生的神色,可他流露出的眸光温和如昔。
她是万千曾受过魏弦京照拂的人之中的一员,但这就够了。她想。
她不过是想要这目光再落在自己身上,不过是想沐浴着这和煦的目光,演一出她精心编排的把戏,换得恩人的一时欣喜,这便够了。
哪怕今日她也将命丧于此,有来无回,她也于心无愧了。
叶翎扯开唇角,绒羽面具下的眼眸里滑过一丝难以察觉的泪光。她伸手扯动着腰间悬挂的细绳,那细绳的另一端被系在悬挂旌旗的桅杆之上,又连于菜市口四周大小建筑的梁宇。
那是一张用不引人注意的细绳织成的网,松散地悬浮在菜市口周遭。这是叶翎用她漂泊至今的全部家当置办的戏台。
叶翎“飞”起来了。细绳一端受她扯动,飞快地收紧,下一瞬将她抛上了洒满日光的半空。她浮动的衣袖和裙摆上悬挂的禽鸟翎羽像火焰一般包裹着她。
她倒挂在这无所依凭的半空中,耳畔充斥着百姓的惊呼声,叶翎嘈杂的心声反而平稳下来。她借着绳索牵引的力道,展开双臂,任由风穿过她周身悬挂的,火焰一般的禽鸟翎羽,在半空中娴熟地舒展腰身,在人群之上“飞翔”起来。
而这落在旁人眼底,她就像是艳红的鸟雀化了人形,让风和日光都化作依托,如臂使指。
顷刻间,千万人的目光几乎都凝聚在在空中辗转腾挪的叶翎身上,包括那些手持兵刃的巡捕营兵士。
魏弦京仰起头,看着那自称报恩的年轻女子随着腰间细绳的收束,跃上了挂着旌旗的桅杆。她身姿翩然,在桅杆和细绳之上辗转踱步,如履平地。她并没有做繁复的手势,也没有动人的舞姿,却将这“飞天”的技艺研习得炉火纯青。
她并不似魏弦京曾经看过的杂技艺者,虽技艺娴熟但教条刻板。她悬在半空中的模样闲适又轻盈,仿佛天生便是会飞翔的,天生就是风的宠儿。
此刻,叶翎足下踏着看上去一触碰即断的细绳,轻轻扬起头,口中模仿起鸟儿啼鸣之声。她舒展手臂,任由日光映照着她的每一片翎羽,华丽繁复的衣摆仿佛是凤鸟华贵的尾羽,其上细腻的纹路如同鳞片一般在日光下灼灼生辉。
不多时,天边竟有鸟儿飞掠的踪迹。雀鸟陆陆续续从南城的屋檐或是大户人家的园子里钻了出来,竟违逆本性飞向这人头攒动,人声沸腾的菜市口。
叶翎继续模仿着鸟类的轻声啼鸣,她知道,她这些年在市井之中闯荡遇到的几位故交此刻也在菜市口边缘,为她引来鸟雀。
天空中雀鸟飞翔的踪迹愈发无法忽视,半空中的叶翎背光而立。日光刺目,在众人眼中,叶翎周身泛着金红的光芒,犹如火焰燃烧。她引颈轻鸣,看上去竟像凤凰神鸟在召唤拥趸。
地面上,黑纱女子穿过熙熙攘攘的人流,慢慢接近了菜市口正中。她身披黑色斗笠,身材高挑,肩宽体阔,周身蔓延着草木被捣碎时的诡香。
她站在叶翎的下方,猛地掀起斗笠,黑色的衣摆横扫,使周遭的百姓退避几步。下一瞬,她面前骤然出现一只成人大腿粗细的巨蟒!
巨蟒落地,周遭百姓皆惊叫起来,而单足立在绳缆之上的叶翎也在雀鸟的拱卫之下俯瞰,正对上黑纱女子冷淡讥嘲的眉眼,霎时泪眼婆娑,喉中梗塞,竟有些啜泣起来,原本轻松写意的站姿也随风簌簌而动。
叶翎知道,她最终还是连累了黑纱女子,让她来成全自己演这一出有来无回的戏码。
在叶翎身下,那巨蟒仰首吐信,嘶声不绝,对叶翎和漫天的雀鸟虎视眈眈。而黑纱女子腰身轻摆,竟围着那巨蟒慢舞起来,引逗那巨蟒变得更加凶恶可怖,竟成吞天灭日之势。
半空中,脚踩纤绳的叶翎似乎感受到巨蟒的威胁,在半空之中如同鸟儿一样舞动起来,她手臂上的翎羽随风浮动,闪耀着鎏金一般的光泽。她脚下每迈出一步都让看客觉得胆战心惊,却偏偏没有一脚踏错,仍然在日光和风中翩然起舞。
她手指翻动,引逗着雀鸟相随。鸟鸣声更加尖锐急促,像鼓点一般敲打在诸人心头,她曼妙的舞步有一种奇特的韵律,应和着风声的嗡鸣,涌动着勃勃生机。
突然,黑纱女子将一物掷于地面,黑烟瞬间将她和巨蟒包裹,而悬浮半空的叶翎也轻轻捻动衣摆,她身上的赤羽突然无火自燃,爆发出明艳的火光,而她在下一瞬后仰,手臂弯折,像鸟儿被折断羽翼,以一种决绝的姿态直坠地面,迎向了巨蟒的尖锐毒牙。
看客惊呼不止,就连即将被斩首,已然满心死寂的魏弦京也被这陌生的杂艺女子扯动了心神,死死顶住那宛若神鸟坠落九天的场景。
黑烟散去,黑纱女子和巨蟒都以不见踪影,唯有仍在燃烧的叶翎悄然伏于地面。她身上的赤羽仍然在燃烧,可灰烬之下,竟有金光浮动,原是另一套赤金色的羽翼,藏于原本的红色翎羽之下!
随着红色翎羽被焚烧褪尽,叶翎缓缓起身,抖落了赤金羽翼上的灰烬,对斩首台上的魏弦京长长一揖:
“小女子献丑了,此戏名《涅槃》,意凡遭人所污、所害者,皆有神鸟庇佑,勿论生死,终将涅槃。承蒙恩公不弃。”
话音未落,她直起身子,振声喊道:
“昔日恩公有恩于我,亦有恩于天下,在瘟疫横行,家国有难之时,救百姓于水火。今日我等汇聚于此,是为恩公送行,更想问问满天神佛,何来天理,何来公道?”
“凤鸟可以涅槃,恩公再生之日,又在何时?!”
短短几句话,让本就因那精彩绝伦的演绎而心绪动荡的百姓群情激愤。他们心中的声音越来越清晰:是啊,魏世子在瘟疫肆虐,皇帝百官弃城而逃之时,救半城百姓于水火,可就因他功高震主,反倒让皇帝老儿心生妒忌,百般构陷,竟安了个莫须有的“结党营私,沽名钓誉”的罪名,当街处斩!
天理何在?公道何在!
“魏世子无罪!魏世子无罪!”
“魏世子对我有恩,我若眼睁睁地看着恩人血溅三尺,岂非人哉!”
“救了百姓,赢了名声哪里是罪,我看望风而逃、胆小怕事才是罪!”
“我等并非魏公子同党,难道帮扶他人也是结党,受人感激就是营私?”
“实在荒谬!放了魏世子!”
“……”
魏弦京睁大双眸,望着激愤的人群,眼底渐渐爬上红丝。他自幼受皇帝百般迫害,只因他生父乃是已故镇国将军,在皇帝潜龙时期便与他有宿怨。这些年魏弦京每每被安排必死无疑的差事,年前京城瘟疫,皇帝将他和百姓一道锁在城中,不过是要他顺理成章地死于瘟疫罢了!
即便他挺了过来,可救百姓之功太大,名气过盛,便也注定了今日死局。
魏弦京没想到的是,到了如此穷途末路,这些布衣百姓中竟还有人念着他曾做过的事,还愿意来相送,甚至还他一句公道。
监斩的晋王此刻犹如困兽,额角青筋凸起,面色青白交加。巡捕营已经受到百姓的冲撞,原本整齐的人墙变得东倒西歪,竟有溃散之态!而这让原本趾高气扬、满身戾气的晋王收敛不少,此刻竟没有出声要求兵士斩了那些刁民。
到底是宫中长大的,最基本的察言观色的本事还在。他看得清领头那些百姓眼底激昂的怒意,直到今日若是落下第一滴血,怕是他也不一定能脱身。所以即便是被这些大胆刁民气得浑身发抖,他也没有失态,反而隐到幕后,将同来监斩的刑部尚书推了出去。
刑部尚书齐之轩面儿上挂着苦笑,实际心里为魏弦京松了一口气。魏弦京早些年曾被皇帝安排入刑部听差,专办那些得罪人的案子。皇帝意在败坏魏弦京的名声,可谁知魏弦京愣是把事事理顺,半个人都没有得罪。皇帝气闷无法,便将他调入别处搓磨。
即便是短暂的,不甚愉悦的相处,齐之轩也感念魏弦京的能耐,暗中赏识他八面玲珑的本事。而今看到他落得如此荒唐下场,虽不能相助,此刻在百姓的声势下拖延片刻,确是不违本心的。
“诸位!诸位!我乃刑部尚书,诸位可听我一句?”
他站在台前,抬手下压百姓的声浪,可收效甚微。巡捕营兵士纷纷以刀柄捶打地面,方才堪堪压住百姓的声讨:
“诸位,魏弦京之罪乃百官议罪,圣上裁决,即便他曾施恩于尔等,尔等也犯不着为他劫法场!若是圣上降罪,尔等可就要被诛九族了!尔等还是想清楚为好,莫要行差踏错!”
他的这番劝诫犹如火上浇油一般,一下让百姓心头的怒火剧烈燃烧。几个巡捕营兵士被撞到,被踢打了好几下,瞬间鼻青脸肿。而隐藏于百姓之中的几个身材魁梧的壮汉交换了一下神色,纷纷喊道:
“何来天理,何来公道!”
一时之间,千万张唇舌像是找到了同一种韵律,纷纷喝对着监斩者喝道:
“何来天理!何来公道!何来天理…”
叶翎被夹在人群之中,她用来混饭吃的华丽的羽裳被黑纱女子扯下来,掷于地面,被万人踩踏,很快便脏得如同杂色的鸡毛掸子。可叶翎一点儿都不在乎。她边流泪边无声笑着,转头对黑纱女子说道:
“阿姊,阿姊!或许成了,或许…”
“别废话了,再不跑便跑不了了!”
黑纱女子重新将巨蟒缠在身上,掩盖在黑色斗篷之下。她死死拽着叶翎,想将她拽离这乱局:
“趁现在还没被通缉,我们立刻离开京城,去南边,兴许还有命活!”
“阿姊!等等,他还——”
叶翎轻微挣扎,不顾黑纱女子的巨力,执拗地扭头看向铡刀旁边的魏弦京,正与他对上了视线。
泪水先模糊了叶翎的眼,等眼眸恢复清明时,她的视线已被人群层层阻隔。
就在这时,马蹄声炸起,一个尖锐得过了头的男声遥遥喊道:
“圣上口谕,罪人魏弦京,斩刑押后,重入刑部候审!”
“什么?”
“太好了!公道自在人心!”
“虽是好事,可就怕是安抚人心的伎俩!我等就在这候着,若是之后魏世子遭难,我等还愿意以身相保!”
“正是正是!我愿同往!”
“……”
刑部尚书齐之轩狠狠松了一口气,此刻也不愿再伺候晋王这尊大佛,只派人将魏弦京的锁链除了,重新押入囚车,恨不得挖一条地道赶回刑部。可偏偏百姓久久不散,看架势是想等魏弦京被当场释放才肯散去。
这便是万万不能的了。齐之轩对着神色麻木的魏弦京使了个眼色,便兀自爬进自家马车里躲晋王去了。
晋王死死盯着魏弦京,难言的暴虐在他的眼底肆虐,可他最终竟一反常态地没有发作,而是让王府侍卫在人潮中强行开出一条道来,迅速离开了。
“起轿,回衙门去。”
齐之轩吩咐道。他带着押送魏弦京的囚车前往刑部衙门,数千百姓紧随相送,惹得齐之轩都苦笑不止:
“年少气盛,名声太过啊——与其父其母一般,都是这样不肯收敛、不肯将就的德行!”
他心里想着故人,嘴里喃喃念叨着,却不知说与谁听。
——
到了衙门,齐之轩入室换了衣服,竟轻车简从地从衙门侧门出去,行至一栋不起眼的酒楼。
楼上包厢里,一面白无须的男子已静候多时。
“今日为何拖到午时三刻之后?那卖艺女子,可不像你安排的。”
房门刚闭合,齐之轩便开口询问,语气熟稔。
“那女子不是杂家的人。或许是魏侯安排的,阴差阳错,倒也拖足了时辰。”
“若是你援兵来的快些,何苦到这命悬一线的境地!今日之事,不是早就支会过冷宫那位了吗?”
齐之轩本来是说了句打趣儿的话,可谁知却换来文旭公公一脸难色,不由当即惊诧道:
“她真不肯求情?魏弦京可是她亲生子!”
“纵使那位不肯为世子爷求情,只要她还活着,当今圣上便不至于对世子爷下死手。”
“呵,她面子可真大。”
齐之轩牙疼般地靠上椅背,以手指按揉突突跳动的额角。他到此刻才知道今日局面比想象中更加危困,只觉得后怕:
“若不是那不知何处前来的女子出面搅局,我们今日又当如何收场?我的好公公,你可知就算我今日把我身家性命搭进去,等不来皇帝那一道旨,魏弦京也会被斩首!朝中因给魏弦京求情而被革爵下放者如过江之鲫,我齐之轩又算老几?我实话跟你说,他的事儿我一丝一毫都不想管了。我是与他生父有旧,但如今他亲母都不顾惜他性命,我这不是狗拿耗子,上赶着多管别人家的闲事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