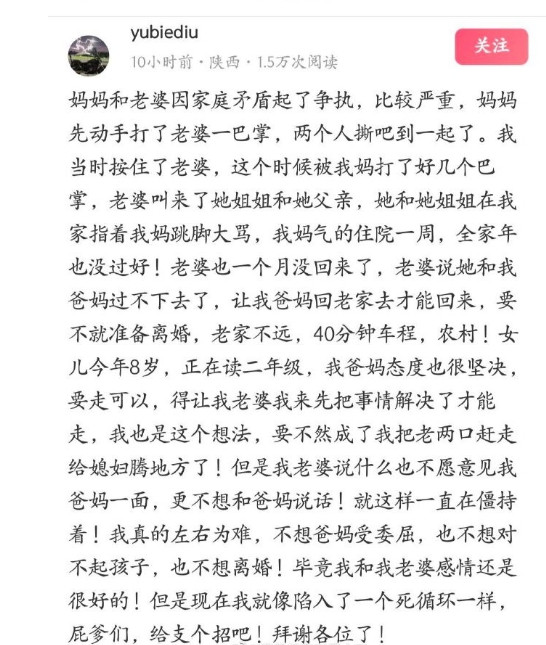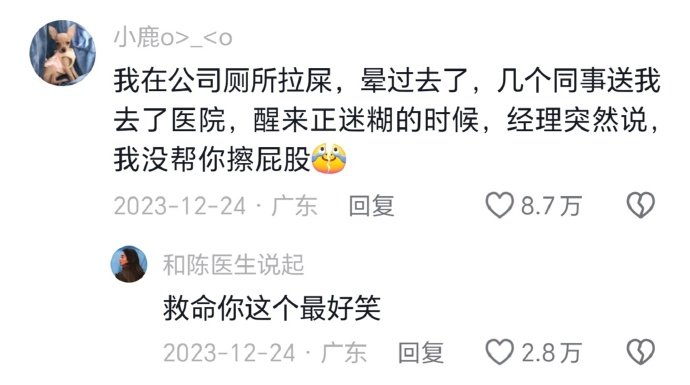“板凳仙”是个残疾人,老光棍,五保户。
老辈说,他是外方人,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讨饭讨到村里,就不走了。
老辈说,他刚来时,三十出头,口音南腔北调,听不出是哪里的。他是哪里来的?他不说,村里人也不问。
早年,靠给村里打更讨口饭吃;后来,帮村里的个体户看店,挣一个“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虽然苦了一辈子,但他很乐观,脸上成天挂着笑。
“板凳仙”缺了一只小腿,膝盖以下的裤管空空荡荡。他的小腿是怎么没的?他不说,村里人也不问。
他用高脚板凳充当拐杖,拄着板凳在村道行走,从落更开始敲击,“咚—咚,天干物燥,小心火烛!”敲击着、吆喝着,一直到五更。
乏累时,他就坐在板凳上歇口气。
老辈说,当年他打更“走”在村道鹅卵石上,板凳“呱嗒呱嗒”脆生生响,比打更声还更催人入梦。
“板凳仙”好喝酒,酒量大得惊人。
尽管穷得叮当响,但他从不缺酒喝。村里红白喜事、大小宴请,都会叫他陪酒,插科打诨讲故事。
他有请必到,逢酒必喝,却很少酩酊烂醉,只是越醉笑得越厉害,痴然而又飘然。

喝差不多的时候,他开始动嘴,打开了故事匣子。讲到精彩之处,他都喝上一口酒,酒碗挨到唇边,嘴还咂巴着,好像要跟酒一块品味似的。
“板凳仙”平日几乎不说话,逢人就是咧嘴笑。
一旦醉酒,他就一反平日的拘谨和卑微,变得健谈开朗,热情大方,就像掀开封盖的陈年酒缸,把发酵的故事,带着酒气反刍出来。
山妖水怪、花精狐仙、牛鬼蛇神、传说异行……他的肚子里,蓄满了说不完的民间故事。
有一天,“民间故事集成”采集小组,来到山村,找到了“板凳仙”,请他口述故事。他欣然同意,但有一个条件:请他喝酒,而且一定要喝到半醉。
微醉的、傻笑的、贫嘴的“板凳仙”对面,坐着心智平庸却自视甚高的小年轻。
那个小年轻,就是八十年代末的我,民间故事采集小组成员之一。
当时的我认为,“板凳仙”嘴里的妖异故事,充满劝善惩恶、亡魂救度、因果报应的元素,言者益妄,听者益真,囚禁了村民的心灵,完全是愚昧、执拗、凝滞的环境产物。
然而,我大错特错,愚笨偏狭的,恰恰是我。

“板凳仙”不成体统的逸闻奇谈,宛如临水照人、显现自身,映照人性的种种缩影;稀奇古怪的故事里面,隐藏着隽永绵长的人生道理。
“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蒲松龄的鬼故事,从来就是红尘折射。
如今,一旦我颓丧无助,内心夸张地控诉社会亏欠了我。这个时候,“板凳仙”就会在我记忆里,不依不饶地敲打我。
不经意间,耳畔响起爽朗的笑声,浮凸一张两颊凹陷、充满喜感的老人的脸,因常年拄着板凳,变成猩猩一般下垂的肩胛。
人到老了,脸颊皱纹就成了唯一的面具,内心的微笑就成了唯一的引擎。
这时,隐约感到“板凳仙”形影不离的板凳,紧挨在我的脚边:一个笑呵呵、醉醺醺的半痴汉,洋溢着卑顺却热切的神气,鲜活富有灵性。
后来才知道,“板凳仙”是国民党的兵,打过小日本。
如今,驾鹤仙去的他,到天上去讲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