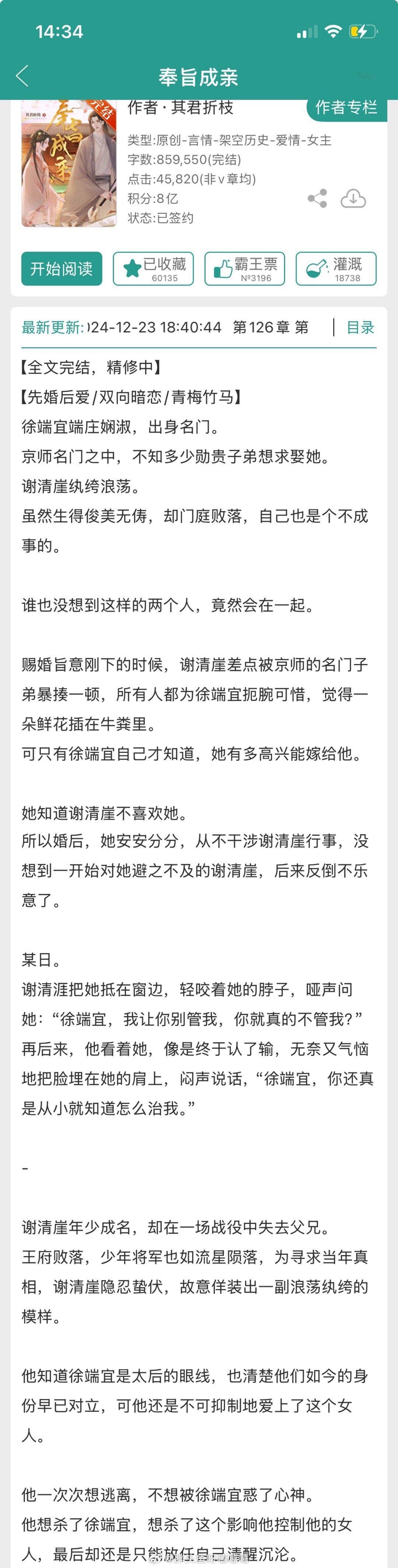我和许景言自幼青梅竹马。
状元放榜那日,他求了陛下恩典,一道赐婚圣旨成全了世人眼中的佳话。
我成婚三年无子,他却从未纳过任何一房小妾。
坊间无不盛赞我们神仙眷侣、伉俪情深。
可三个月前,我发现了他养在府外的外室。
那外室,偏偏还是我的闺中密友。
我离开后,他却疯了。
1
“顾小侄,你确定要卖掉这两间铺子吗,这可是长安大街的两间铺子,地段极好。若是肯花些心思,日后许府的公子小姐的嫁妆彩礼,也是能丰厚几寸的。”
面对亲舅的再三询问,我坚定地点点头,将母亲留下的嫁妆单子递了过去。
“不必了,都卖掉吧,昨晚我梦见娘亲了,她说不会怪我的。”
谈及自己的娘亲,亲舅无奈地叹口气:“罢了,你是个有主意的,许小郎到底年轻,银钱上若有什么难处,倒也不必你变卖嫁妆。”
我神色淡淡,垂头一笑:“不关许侍郎的事,一切都是我的主意。”
亲舅只能收下地契,转头嘱托道:“顾小侄,我便暂时替你代管了这两间铺子,你若哪日宽裕些,随时来寻我。”
舅舅将厚厚的一沓银票塞给我,又从腰间解了钱袋,贴补几张:“顾小侄,莫逞强,只管渡过眼前难关,许小郎君他,也很辛苦。”
辛苦吗,费尽心思掩盖木兰香,也着实辛苦。
只是那木兰香却是我从前为柳姝亲手调制的方子,旁人也便罢了,我却是能嗅出那一味暗香来。
哪怕是同一种香,不同的人本身的气味与香料融合后,也会产生全新的香味。
柳姝是我儿时形影不离的旧友,那香味我再熟悉不过。
原本我还抱着一丝侥幸,以为不过是巧合罢了。
前不久一封寄到许府的书信,却让我浑身犹如掉进冰窟。
2
三个月来,我一点一点变卖掉手中的地契,如往常一般挨个拜别了我的旧友。
顾玉书要走,虽不会大张旗鼓,但也必然不会落荒而逃。
这是顾家将门遗孤的气节。
回到府中打开妆匣,里面的烫金婚书一时让我有些愣神。
这场赐婚隆重而盛大,京都最炙手可热的少年郎,冉冉升起的新秀。求陛下金口玉言为这场婚礼加冕。
顾家满门忠骨尽忠报国,唯有一个孤女既不能承袭爵位,又不能领兵作战,原本战功满门的顾将军府,也逐渐沦为空壳。
皇帝为我赐下公主仪仗出嫁,那日十里红妆,万人观礼。
母亲原本病重,听闻许景言如此情重,又光耀了将军府的门楣,欣慰地支起身子为我添妆嫁礼。
在京都,那日将军孤女嫁新科状元,无数人前来贺喜。
十里流水席,持续到深夜才堪堪将歇。
那日掌管婚书的礼部小吏宣读完誓词后,在众人的目光下。
他缓缓道出多年前我曾在他赴京投奔亲戚,却遍寻无果昏倒街头时,是我无意撞见,又遣人画了信物的样子,才助他成功寻亲,在这京都安身立命。
这一段几乎是故事里才子佳人的情节,瞬间赢得了京都百姓口口相传的赞誉。
由此衍生的话本更是长了翅膀一般飞出京都,哪怕是江南那边的小姐来京,也会借故来拜访我们这对传说中的碧人。
如此情深义重的恩爱缱绻,情深义重,更是让皇帝看重。
许景言自此平步青云,不到三年就做到了工部侍郎。
俨然是朝中新贵。
借故献礼的人很多,其中也不乏各种奇珍美人,许景言都一一回绝了。
许景言当真两袖清风的廉洁,却也无更多银钱。
我谋思虑,算财经,用将军府最后的人脉搭建起几间丝坊,又苦心钻研许久,才能贴补整个许府上下的花销。
堪堪护住一个朝廷重臣脸上的薄面。
但我也因维护生意,思虑过重而身子日渐清瘦单薄。
那时许景言常夹带了风雪回来,又想着怕靠近我时,身上未散尽的寒意惊扰我休息,在偏房更了衣裳,将身子焐暖些再来歇息。
逢着暑热,他则会在庭院处吹吹风,散去炎热的暑意,再来寻我。
我做丝坊,偶尔也会听到些许他在朝廷中历经几次危机,但他独自将风雨独自揽下来。等他回府时,必然又是温润如玉,波澜不惊的模样。
他面对帝王的任命,朝臣的压力,清清白白做了三年官。
真真切切让穷苦的百姓安了家,京都这片繁华的地界,已经许久没有来过流离失所的乞丐了。
我明白,他是帝王爱重的信臣,是百姓喜爱的清官。
只是后来,他眉间的忧思越来越重,像是严冬时化不开的冰一样。
他的同僚到底有些手段,知道烟花柳巷的地方他定然不会去,便授意寻了一名如花似玉的姑娘被他正好英雄救美。
柳姝的父亲曾是京都重臣,奈何沾染了私盐官司,被皇帝罢了官,妻眷皆奔走四散。
柳姝离京那日,我不过十二,将自己积攒不多的荷包塞给了她,后面一两年虽有书信往来,可渐渐地,柳姝家中生了变故,自此杳无音信。
没想到再次相见,她竟然已成了许景言的外室。
久别重逢的消息,在剖开时竟如此荒唐。
要调查整件事,对心细如发的我来说自然不难。
许景言当时对落难的千金伸手,或许只是对曾经来京城无助的自己的拯救,可他到底隐瞒了这件事,后面再发生什么故事。
不过也是一个编造的意料之外,笃定的情理之中。
3
许景言回府越来越晚,他没回来的时候,我的脑海中总是忍不住浮现出过去的画面。
母亲临走那日,我尚未及笄,许景言曾在病床前庄重许诺,瘦削的肩膀撑起大梁:“许景言永远不会抛下顾玉书。”
我权当他只是为了母亲宽心的几句说辞。
未曾应允他。
后来将军府中掌家的重任落在我肩上,那些人欺我到底年轻,又是闺阁女子
常有泼皮无赖流窜府外,京都贵女都不敢与我轻易走动。
那年春日我前往长兴街铺面时,被几家小门小户的公子拦路调戏。
许景言自城东书坊感到城南的街上,将我护在身后。
他说:“许景言会永远保护顾玉书。”
那时他已在书院崭露头角,我自知他将鹏程万里
出手相助不过是对孤女的垂怜罢了。
我依旧未曾应允他。
后来他来了许多次,我眼见着我身边的嬷嬷从最开始的对外男防备,慢慢地竟也常在我面前念叨起许景言的好来。
“小姐,许公子这样的人儿,赤诚有余,旁的倒也无妨。”嬷嬷忍不住开口劝我,“纵是做戏,哪有人能做戏这许多年呢。”
我折下初春的红梅:“许公子注定要扶摇直上,我们何必去纠缠那遥不可及的念想呢。”
我知道那日许景言在墙外,一墙之隔,他身上悠悠的冷香卷入风中,很快又随着风雪沉寂下来了。
后来,许景言再没出现在过我折花的墙外。
只是后来坊间一直有传言,许景言发了疯地读书,竟是一心扑到功名上去了。
果然,春闱后,许景言成了陛下钦点的状元郎。
那日高头大马上的他如此意气风发,又在金殿前求下恩典。
有了陛下金口玉言的赐婚,我便不再是摇摇欲坠的将军府遗孤。
有最尊贵的人为良缘作保,这份殊荣足以让京都贵女自愧弗如。
那日,许景言满面春风地请了圣旨,还有婚书和见证人。
他说:“许景言会爱顾玉书一辈子。”
隔着红盖头,我双目微红,却也郑重道:“顾家家训,夫妻一体应如是,若有二心,再无转圜。”
他双目灿若星辰,喜帕下的手稳稳包裹住我的手:“玉书,我,好欢喜。”
那时的许景言,待我极好。
哪怕是长风掠过堂前,也担心我像一片纸片一样飞走。
4顾玉书是什么时候也喜欢上了那个少年郎的呢?
连我自己也忘了。
不管是母亲离世前那道稳重的身影,还是那日许景言将我护在身后的轮廓,亦或是高头大马上那春风得意的少年将圣眷的同享的荣光。
这日,许景言傍晚托了口信回来,说是工部有要案要勘察,他晚些回来。
我叫嬷嬷撤走了凉掉的饭菜。
坐在红梅树下,一坐就是新月初上,寒风料峭。
嬷嬷说:“夫人许久没用晚膳了,阿嬷自作主张热了一碗桃胶羹来。初春寒凉,莫冻坏了身子。”
“夫人挂念郎君,也要爱惜自己的身子才是。”
我捧了桃胶羹,浅尝两口。
桃胶羹刚出锅的那炉味道最好,而今凉透了再熬煮,却凭空多了几分酸涩。
“多谢嬷嬷。”我一口饮尽,“夜深了,今夜且歇息吧。”
我回了屋,将那夜的风雪彻底隔在门外。
5再次惊醒的时候,是被晚归的许景言躺在身侧的寒意惊醒的。
他当时方才解开外裳,坐在床头,而那料峭的寒风,却从他身上浸出。
见我睁眼,他起身拢了大氅。
“抱歉,玉书。”
等他身子暖和些了,才靠近我来,将我紧紧抱住:“我想你了,玉书。”
我没有避开他,只是如往常一般询问:“何事回来得这样晚?”
“工部的一些小事罢了,睡吧。”许景言含糊其词。
“我情愿你不要这样辛苦。”我坐起身子,用剪子去挑烛心。
剪了烛火,卧房里就剩下一片寂静。
“玉书,我不能走。”黑暗里,许景言叹了口气。
他重复了好几遍:“我不能走。”
随即又掖好被角:“家里的事,只能多劳你费心了。”
也许是黑暗里,五感更加敏锐,我鼻尖总是晃悠着那一缕淡淡的木兰香。
许是天公不作美,今晚的雪下得格外大。
不久后,外面传来细碎的交谈声。
随后许景言的贴身小厮前来报信。
“许官人,城东的灾民房被雪压塌了,请你过去看看。”
许景言里面披衣下床,在我额头落下一吻:“你且睡吧,一切有我。”
他行色匆匆地走了。
我却起身点了烛火,烛光摇曳跳动,似乎门外的风雪要压断这缕小小的火苗。
城东的灾民房是今年初秋才修建起来的,于情于理,都不能这样脆弱。
才半夜的风雪,就叫屋子塌了。
从前户部的银子到工部,再往下虽层层盘剥,可到底没出过这样的事。
现今外面的积雪,不过刚到脚踝而已。
想到那时为了修建这么一片灾民房,许景言常忙到深夜。
又从府中支取了银子,支撑到那片屋子完工。
不对,还是不对。
我起身翻了账簿,初秋时工部刚刚开工。
可后续从府中贴补的银子,却频繁地出现在三个月前。
那时,许景言说,朝廷的银子只够搭建了灾民房的主体,后续的修缮和安置朝廷却不管。
前前后后,竟然支出了七千两纹银!
足足抵得上我那丝坊一年的经营营生。
这七千两几乎是这几年我们攒下的全部家底。
我合上账本,等那外面的风雪会不会停下。
直到外边天边翻起鱼肚白,许景言才顶着一身疲惫回来。
他看到桌边的我,愣了一瞬,随后叮嘱道。
“玉书,你不必担心我,房子塌了的事情已经妥善处理好了。”
“你继续睡吧,我上朝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