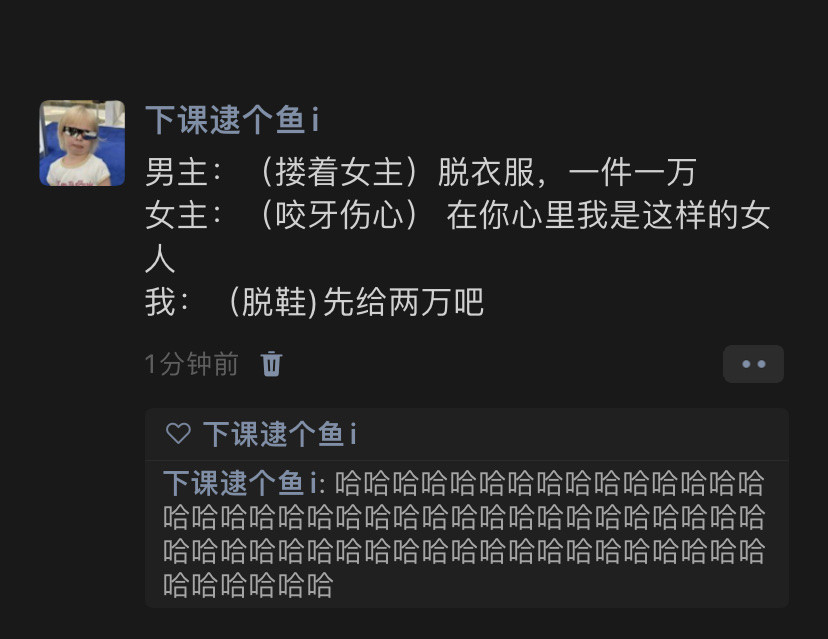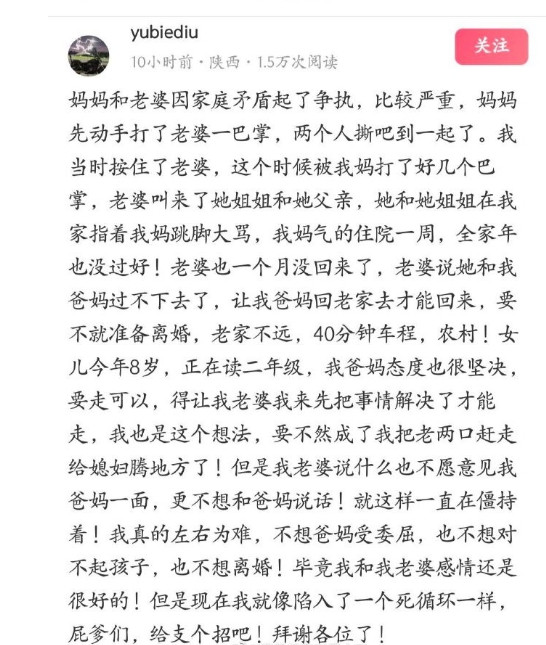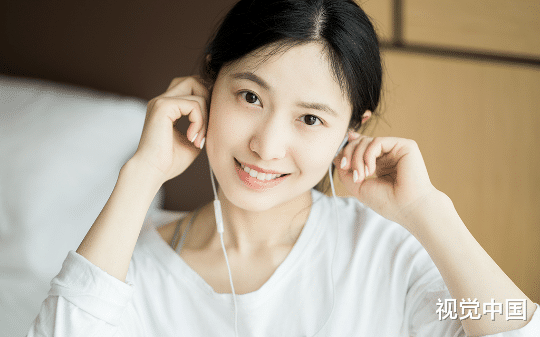我是景亲王的男妻。
景亲王是城中出了名的泼皮。
成婚之时,他许我正妻身份,千金为聘,我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以男子之身披上嫁衣,赌一个相携白首,赌他年年岁岁,待我情真意切、矢志不渝。
一晃两年过去,楼台依旧,人事已非。他转头另娶,我输了,输得彻彻底底。
我怎么忘了,他性情乖戾,本性难移。
也忘了我曾幼时遭难,被医侍断定活不过及冠。
00
我跪在王府游廊外。
膝下是一对青花缠枝莲梅瓶摔过的碎瓷。
这对花瓶曾是王爷爱物,搁在我屋中案前。
春桃,夏荷,秋菊,冬梅,他闲时便折来几支,信手赠予我。
春生夏长,秋来冬往,这成了我与他不必言说的默契,像是他在告诉我,我们还有数不尽的将来。
瓷片的碎茬子很利,扎穿了皮肉,膝头的布料被血濡湿大半,捂在袍子底下,黏糊糊的难受。
他新纳的侧妃清丽婉约,手劲却很大,一巴掌下来,扇得我耳鸣眼晕。
正午日头也大,头上更无片瓦。我这两年身体底子愈发差劲,跪两个时辰,后背冒的却全是冷汗,顾及着脸面将腰背挺直,血液倒往头顶上蹿,叫人恨不能当即匍匐在地晕死过去。
“王妃?”她低嗤一声,道:“王爷一纸休书下来,你不过就是个下堂妇!”
游廊外,不时有侍从路过,皆低头与同伴窃窃私语,侧妃并不加以约束。
她要的就是底下人都来看我笑话。
“呀!”她似乎自觉失言,借丝帕捂嘴,远远绕着我踱了两圈:“是妹妹的不是,一时忘了咱们景王妃是男子之身,怎么能称作下堂妇呢。”
下堂?又是个没听过的词汇。
我暂且记在心中,思绪却不受控制地飘远,我想,下糖啊,下的会是什么糖?红糖,白糖,方糖,还是王爷从前说与我听的果葡萄糖、零蔗糖……
中原人真难懂。
01
思绪飘啊飘,又倒回到从前。
从前,我是吴越的十三皇子。
我前脚助六皇兄登上皇位,后脚就被他卸磨杀驴,扔到了中原。
吴越从东十二部首领战将逝世后,屡战屡败,又逢国内政权更迭,迫于形势,无奈与中原议和。
我是以质子的名义与使团一同入境的。
当使团最后一匹马的马蹄越过城门,真正踏上乩朝边境领土那一刻,两道如庞然大物的木制门扉沉沉阖拢。我于马背上回头,深深回望一眼,忽觉悚然。
冥冥之中,有种怪异的预感涌上心头,我意识到自己或许再也没有重回吴越的那一天。
……
使团入都城,在城中礼客楼下榻,等候中原皇帝传召前,我们好吃好喝待了三日。
带队使团的元大人是皇兄心腹,过来的路上,已经足够他摸清中原大致情况。
中原乩朝如今也元气大伤,吴越夺嫡,大乩也没好到哪里去,大乩元帝先后死了两个儿子,自己也是个短命鬼,留下的皇位给了四公主。
乩朝如今是年轻的女帝当家——这就有意思了。
在礼客楼的头一日,元大人摸着胡须,将我上下打量一通,眼珠子滴溜转,没憋好屁,招呼我道:“殿下啊?”
我给自己倒了杯茶,没理他。
元大人凑过来:“乩朝天子才登基,正是后宫空置的时候,你来乩朝为质……只是为质,未免有些浪费。”
我不以为意:“乩朝天子后宫再空,也轮不着我一个吴越质子去填。”
“那是自然。”他摆摆手:“乩朝人尚且虎视眈眈,哪轮得到你一个外人去当君后。这君后当不成,你就给她做小嘛!”
“——噗。”一口茶水呛进嗓子眼,我差点咳死过去。
元大人掸了掸被我喷满水的衣袖,满目的恨铁不成钢。
在礼客楼的第二日,元大人在探听消息,举棋不定。
在礼客楼的第三日,元大人面色凝重,对我道:“殿下啊,这乩朝天子,不得了,可不得了。”
我当真以为出了岔子,急道:“她要把我们如何?”
“她呀。“元大人愁眉紧锁:“难办,她好像是个女同。”
我呼出一口浊气:“那你就别在她身上下功夫,左右都是铁板一块,歇了这份心,高高兴兴入乩,平平安安回乡。”
“家国大义在身,臣岂能置身事外?”话到此处,元大人挺直了腰板:“我如是,殿下亦然!
“再者,十三殿下姿容妍丽,姝色无双……可也使得!”
“使得什么?”我不解。
元大人一招手,唤侍者呈上一件青色罗裙,正是乩朝女子间时兴的样式。
我顿了片刻:“使不得!”
“这有什么要紧的。”元大人身边的副官插嘴道:“殿下从前在吴越,不是早做惯了这以色侍人的……”
这人话音未落,便挨了元大人一巴掌:“下官治下不严,让殿下见笑了。”
我扯了扯嘴角。
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无非是做给我看。
我知道的,这是皇兄的意思。
02
我到底穿上了那件青色罗裙。
朝会之后,女帝在前殿单独接见我。
以元大人为首,整个使团安心地舍我而去,像甩掉了什么大包袱。
女帝居高座,我单手抚肩,在阶下遥遥朝她执吴越的礼。
她有双锋利的眼睛,像父皇生前常喂的那只鹰。
沉静威严,看人时蓄势待发,预备随时咬下敌人的一口肉来。
她招招手,唤我上前,我绕过了她的书案,打算低头数数案侧的镂空雕龙有几只,她尤嫌不够,让我再近些。
近无可近,她抬起我的下颌,笑道:“果然像她。
“妆化得不错,像了七八成。
“使臣们费心了,才来大乩几日,竟连朕的私事都探听得一清二楚。”
我当即退后,却被她攥住脖颈处的丝带——这丝带还是我特意搭的,与裙子同色,此时被她拉住了尾巴,一把拽开:“怎么不答话?”
我摸了摸勒红的喉结,出声道:“说了话,就不像了。”
我的音色与女子还是相差甚远的。
也是离得近了,我方才看清,她案上摆着一副丹青,画中女子叫做广藿,着青色罗裙,飘然若仙——难怪让我扮成她做替身,难怪坊间总有传闻说女帝或有磨镜之好。
“我并非想羞辱于你。”她沉声道:“只是明珠与珍珠,松柏与青竹,终究不同。”
后来我才知晓,画中的女子是从前的三皇子旧部,她割下了我东十二部首领的人头,与女帝争夺乩朝皇位,女帝登位后,甚至赐毒酒要了她和三皇子的命。
“吴越使团打错了算盘。”女帝轻抚着那副画,眸光中难得有几分动容:“朕不喜欢女子,朕只是欣赏她,无关于情爱。遑论如今大乩百废待兴,朕无心风月。”
“是使臣们僭越了。”我退后一步,跪道:“我既入乩朝为质,便是乩朝的臣民,一心想着,了解乩朝风物和君主喜好是分内之事,谁知弄巧成拙……”这回行的是中原的礼。
她垂眸,俯视我道:“巧舌如簧!”
这个成语有点难,我反应半天,连忙俯身,不敢再辩:“听凭陛下处置。”
“好啊。”她拂袖:“既然你这么想留在朕身边,朕就偏不让你如愿。
“朕身边,也不缺伺候的侍从。
“左右你也要留在乩朝,去我阿弟身边吧,给他做个伴读,可好?”
也没给我留拒绝的余地。
只好俯身一拜。
03
女帝的阿弟,是乩朝现下唯一的皇子,与女帝是一母同胞,贵不可言。
女帝瞧着年轻,她的弟弟自然更年轻。
才十八,未及弱冠的年纪。
但也是十好几岁的人了,我的皇兄们在他这个年纪早就上过战场,策马趟个满身泥,十皇兄更是死在与乩朝的对战之中,死时比他还小一岁。
是以,我想不通——这么大的人了,哪用得着我一个不通乩朝文化的外乡人做伴读?
两日后,任我做侍读的圣旨果真下来,命我速速入宫。女帝继位后,封亲王的旨意迟迟未下,太后那头又心疼儿子,舍不得撒手,因而女帝的弟弟还住在宫中。
进浮锦阁的头一日,我刚托侍从置好行李,就听得有侍女前来通传。
想来常山殿下也有事要叮嘱,我迎她进门,只见一个俏生生的丫头蹑手蹑脚跨进来,背着手凑到我跟前——
然后给了我一闷棍。
半死不活之际,我听见门口有脚步声,一开口,似乎是个内侍:
“哎哟!咱家说什么来着?死丫头!让你点安神香安神香!
“往茶水里放点蒙汗药也成啊,拿棍子作什么?真要闹出人命,当心那群蛮子割了你的脑袋!”
“公公……知错了,知错了,别戳我脑门。”
……
转醒的时候,是在床上。
不是我先前收拾好的那张床。
那大概就是常山殿下的床了。
是下人们自作主张,将我送到这里。
我腕间缚着红绸,红绸绕过双腕打了死结,紧紧系在床头,瞧来颇有几分喜气。多新鲜啊,知道的以为我是来暖床,不知道的还当我今晚要成亲。
我侧过头,隐隐听见了外头的脚步声,吵吵嚷嚷,阵仗不小,应当是正主回来了,只是不知为何,脚步声顿在门口,犹疑良久。
一颗心悬起又落下。
那人推门而入,绛紫外披,玄色内衬,里衣领口规规整整束到锁骨,长发以鸦青缎带低束,颇为温良的打扮,偏生了双潋滟多情的桃花眼,下颌清晰,薄唇锋利,而最为惹眼的,是右手的食中二指——从指根处齐根斩断,接驳了两根工艺精湛的玄铁假指。
这假指也有说法。
说是女帝受封皇太女之前,前头还有位名正言顺的太子,太子行二,是女帝和常山殿下的兄长。太子储妃是氏族裴家的女儿,早早与太子定下亲事,从小在乩朝宫中养大,与储君青梅竹马,且当时裴家势大,轻易招惹不得。
谁料常山殿下色胆包天,轻薄了储妃,后被亲姐斩下两指,以儆效尤。
本是乩朝皇室秘辛,却连我这个外人都能轻易知晓,想必其中有女帝的授意。
——毕竟乩朝都城中人尽皆知,常山殿下是个贪花好色的草包。
他捏住我的下颌,冰凉的铁指冻得我魂魄归位,一对漂亮的眼珠转动着,上上下下地打量我,眸中分明写满了慈悲——是的,慈悲,不掺讥诮,也无关于欲望的,纯粹的慈悲。
想要问的话还未来得及说出口,我瞳孔骤缩,很快就得知了缘由。
一柄匕首从他宽袖中滑出,他当即握住,直直扎向我的心口。
剧烈挣扎间,我抓住他的袖子,顺势将他摁进怀中,扒开他的衣襟,在逐渐模糊的视线中认准了他的脖颈。
我好恨,恨那养尊处优的,白皙的皮肤,和底下清晰的血管……他躲闪不及,被我咬住了脖子,就像大漠里走错路被狼盯上的猎物。
拼却这条命,我也要咬死眼前这个人!
脚踝上的链子摇动,链上三颗狼牙齐齐撞击着我的踝骨,发出骨牙制品独有的闷响。
六皇兄……阿羌这回恐怕真要死了。
04
我叫阿羌。
羌之一字,取的是奴隶的含义。
我的母妃是中原人,被父皇掳到了吴越,日日望乡而哭,吃不好,睡不着,熬到生下我之后,便点了一把火,将自己的宫殿烧了个干净。
依稀记得,那是个月圆之夜。
殿中侍奉的二十八位宫人,当夜被遣散干净,独独留了我与母妃二人。她是想带我走的,临了却转变心意,将我护在打湿的被褥中,只身赴死。
独独我活了下来。自此,吴越视我为不祥之兆。
十余年间,我受尽宫人与兄长们的冷眼。吴越皇子众多,人多了就不金贵,今日你与我结下梁子,明日就约在演武场死斗,皇帝忙着征战和杀伐,死个把儿子也觉得无伤大雅。
我是依附着六皇兄活下来的。
我替他杀人,我算不得聪慧,力气也小,胜在存在感低,没人把我当回事,也没人把我当人看。我是块愿者上钩的饵料,谁要真来舔一口,就能得个被咬穿喉管的下场。
后来吴越宫中总有人传我以色侍人,乃至勾引皇兄,弑杀亲父,其实容色如何……那不过个杀人的引。
吴越少雨,印象中一年也有一两次,大雨滂沱,电闪雷鸣,唯独有一回,雷雨出在十五夜里。我潜进六皇兄宫中,告诉他我怕,雷声太响,我怕报应。
他笑着抚摸我的头,手指穿梳过我的发丝,而后俯身,替我在脚踝系上一条链子。
链上坠着一颗狼牙,磨掉牙根,只剩小巧的尖,是他亲手猎来的,希望能辟邪除祟,佑我喜乐安宁。自此以后,每死一位皇兄,便多一颗狼牙,三颗之后,我抱怨太重,就此作罢。
其实远不止三颗。
那脚链是传说里勇者的腰带,挂着战败者的头颅,好借此炫耀过往的战绩,而今我却高高在上,将其踩在脚底。
……
果真祸害遗千年。
那刀还差一寸伤到心脉。
我又没死成。
常山是个怪人,捅了我一刀,又亲手侍奉我汤药,见我喝不进药,急得满地踱步,甚至想以口渡给我,生生将我吓活了过来。
他眼中布满血丝,眼底两抹青黑,当真为我的伤口熬过几个大夜的模样。
我见过吴越满城风雨,见过刚直不阿和阴谋算计,这么莫名其妙的男的,还是头一回见。
这段话用了四个成语,我的中原官话又有了不小的长进,真厉害,我自己。
常山朝我解释,他说我生得像他皇姐丹青上的白月光,那女人是他皇姐的白月光,与他却有些过节,他甫一回房,见白月光复活,吓得给了我一刀。
这番说辞错漏不少,我懒得计较,笑着点头,不置可否。
他打了温水,替我擦拭脸颊,说我有泪痕未干。泪痕?我全无所察,伸手去接帕子,却被他摁住:“我来吧。”
这双手拿得了匕首,也玩得动温情的把戏,他轻柔拭过,向我陈情:“捅伤十三殿下,是在下的过失,万不敢辞。”
我挑眉,静看他要耍什么花活。
他将我抱到小榻上,我不肯配合,他花了好一番力气,末了还替我垫上腰靠。
我坐好了,他方才拿出一方木匣,打开盒盖:“里头备好了纱布、伤药。”
又指指门口:“外头有三位医侍候着。”
说罢,袖中滑出那柄匕首,就要往自己心口刺去。
“慢着!”我喝道:“我已经大好,还不至于拿不动刀。”
他当真把刀递给我,转头爬上了床,平躺好,闭上眼,一副任君宰割的模样。
我满心疑虑,握着匕首在指尖把玩:“我若杀了你,可还出得去这个门。”
“我保你,尽管放心。”他偏过头:“院外另有四名暗卫,听凭差遣,定能送你安然出城。”
我心下稍安,腕间发力,当即抬手掷出那柄匕首。
他紧阖双眼,眼皮颤抖。
只见那匕首飞去,正正插在他分开的双腿之间,钉入床中三寸,割破衣料,有血沁出。
门口打头的太医探出了头:“殿,殿下,阉了?”
也不知是唤的哪位殿下。
我冷声道:“没阉。”
此时常山方敢睁眼,那匕首擦过腿根,只是擦破了点皮。
这便算揭过了。
05
我养伤的这段日子,听说女帝发作了一批前殿的侍者,连元大人也没放过。
虽说两国邦交不斩来使,元大人回去时却瘸了一条腿,女帝的人做事细致,他抓不出错漏,也就告不了状。
随我来乩朝的侍从,个个都是皇兄的眼线,我一个也没留,让他们跟着使团走了。
常山给我送了不少宫人来,我原本不想用,可看见那个抡我一闷棍的宫女在其中,遂点了她留下。
小姑娘畏畏缩缩,似乎是怕我报复。
当然要报复,我说:“既然跟了我,那我替你改个名字罢。”
她仰起脸,半是畏怯半是期待:“什么?”
我敲敲她的额头:“便叫做阿棍,怎么样?”
她眼中含了一汪泪,显是不满意。
“阿棍好啊。”打南边窜出来了个常山,手里携一支荷花,递与我:“你主子叫阿羌,听着就像一对儿主仆。”
我接过那花,举在眼前细看。
那花瓣半开,斜斜舒展,朝我额上撒了颗露,珠子似的顺着眉眼朝下滚,最后缀在我鼻尖。
常山失笑,极为自然地替我拭掉,后突发奇想道:“阿羌可还有别的名字?古人……啊不,中原人,大多要取字的。”
我摇摇头,听得阿棍插嘴道:“两位殿下都未及冠,哪就取了字了。”
“我有的。”常山正色道:“告诉了你们,以后就莫要叫我常山,以表字相称,更显亲昵。”
我不懂隔了夜的仇人,如何就要与他亲昵,只是不好拂了他的面子,点点头。
常山清了清嗓子:“叫我张根号。”
“张……”我怔在当场,“这怎么还,连名带姓的。”感觉自己的中原官话知识体系遭到了重击。
“殿下不知道。”阿棍凑过来,在常山眼皮子底下跟我嚼舌根:“常山殿下这是脑子进了水了,还未缓过来。”
我好奇地睨着她:“怎么说?”
“上个月常山殿下同几个宫女戏耍。”阿棍撇撇嘴:“吃醉了酒,其中一个宫女的手钏子掉进了鲤鱼池,几个宫女们起哄,央殿下去捞,殿下当真去了,呛了水,昏死过去三天三夜,醒来后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阿棍!”常山作势打人:“你家殿下我还没死呢!”
阿棍猫到我身后,我伸手替她拦着常山:“孩子还小,当心吓着她。”
扭头又压低声音,对阿棍道:“回头常山殿下走了,你再悄悄说与我听。”
……
说起宫女,阿棍告诉我,浮锦阁中的宫女,十个有九个都是常山收用过的,个个都等着常山封王立府,一并跟着出去,挣个侍妾当当。
话及此处,阿棍拍着胸脯,感慨还好自己入宫晚,赶上了好时候。
我心想,除了起初那一刀,常山殿下的确算得上性格温和,许是生死关头走一遭,人也宽容豁达不少。
阿棍却说,天塌了有个子高的顶着,有我在前面,常山再如何也不会把视线放到她身上。
……这丫头还是护早了,该她挨两板子的。
06
【二十一世纪的人总说,名字是最简短的魔法。】
我叫张根号。
十八岁生日的晚上,我一个人对着蜡烛许愿:
神啊,赐我一个老婆吧!
神没有听见我的祷告。
但魔鬼听到了。
我就这么莫名其妙穿越到乩朝,绑定了系统3452。
“欢迎来到架空位面,当前位面编号569。”脑内的系统音冷冰冰,像小时候的深夜,拨我妈电话后对面传来的忙音,“系统听到了宿主的愿望,应邀而来。
“宿主需完成任务:修正世界线,抹杀炮灰反派。
“任务达成后,系统将实现宿主心愿,并将宿主传送回原世界位面。”
“不做任务就回不去?”我咬着后槽牙:“闯你爹的鬼。”
“不仅如此。”牲口3452继续暴言:“位面世界不允许宿主长期滞留,过时未完成任务的宿主,将受到系统相应惩罚并随机放逐。”
我做了个深呼吸,听系统给我进行朝代背景科普。
……
乩朝有两个太后,一个姓裴,是名义上的母后,一个姓王,是女帝和常山的生母。
裴家自女帝继位后,日渐式微,裴太后早年丧子,早失了与人争斗的兴致,常年深居简出,与青灯古佛相伴。我顶着常山的身份,需要应付的只有王太后。
我醒来的第一日,王太后坐在我床边,攥着我的手,神色很是关切。
恍惚间,我以为系统对我还算眷顾,将我送到这个鸟不拉屎的鬼地方,却送了我一位爱护我的长辈,聊以慰藉。
“醒了?醒了就好,你若是再不醒,娘亲也要随你去了!谁叫你喝那么多酒,你知不知道你差点将娘亲急死!”
我摇摇头,示意自己往后不会再犯,却听得她道:“那些个害你进鱼池的丫头,有一个算一个,昨日通通都已经杖毙了,以后身边的人,可得仔细点!”
我瞪着她,盈眶的泪水又憋了回去,只觉一阵恶寒,胡乱点了点头。
“你的命才是贵重的。”她放低了声音,拍着我的手喃喃道:“这乩朝上下,谁的命能比得过你的命金贵。
“你皇姐坐得了那皇位一时,坐不了一世,她终究只是个女子,只有你,我的皇儿,只有你才能!”
周围的宫人闻言,皆跪地俯身,作惶惶然状。
……
毕竟一母同胞,我以为女帝也会来看我,系统提示的信息有限,又时不时卡机,提心吊胆几日,见无事发生,才将心放回了肚子里。
看来这女帝跟我关系是真不行,连样子都懒得装。
安生了几日,系统上线了,一上线就在我脑子里蛐蛐:“吴越使团不日即将抵达乩朝都城,炮灰反派也在使团之中,请宿主注意把握时机。”
“炮灰反派是什么身份?”
“吴越第十三皇子,祁连羌。”
07
自从祁连羌出现后,系统空间就多了一块数字大屏。
起初上面的数字是“1095”,过了一天之后,就变成了“1094。”
喔,原来是任务时间倒计时。
我刚高考完,最看不得这种东西。
系统催得紧,我决定先下手为强,山不来就我,我便去就山。
我冲去女帝的书房,等了五个时辰,才等到她的召见。
女帝单手支颐,关节抵着太阳穴,倦怠地抬眼看我:“说吧,什么事?”
“皇姐,我要那个吴越质子。”我模仿着常山的口吻。
“原也不是什么大事。”她揉着额角:“吴越皇帝那边也放了话,说十三皇子在吴越与奴隶无异,让朕也不必优待,但是放到你手里,朕总归有些……
“慢着。”她抬起头:“你叫我什么?”
“泽兰。”我改口道。
“晚了。”女帝起身,走到我跟前:“去岁,你在重华宫第三棵树底下埋过什么?”
我心头一跳,狠狠咽了口唾沫:“酒?”
“猜对了。”女帝抚掌,凑到我耳畔:“这两天忙,没空收拾你,你倒好,主动凑到朕跟前来……你当朕与太后一样好糊弄吗!”
我浑身一颤,她见状,撤了一步,旋身大笑:“瞧,这不就试出来了。”
“你是何人,意欲何为。”她仍挂着笑,笑意却未达眼底。
她屏退了左右,门口仍候着两列奉茶持扇的宫人,出了殿门,二十余位禁卫军轮岗巡察,宫中严防死守,插着翅膀也没有逃出去的可能。
心脏跳得发疼,一腔热血上头,我决定赌一把。
“我是谁不重要。”我答:“或许我只是京郊的一位乞丐。
“但是我在常山殿下的身体里,只要我在一日,就能替陛下稳住太后。
“稳住太后,也稳住世家王氏,让他们不敢染指皇位。
“陛下想让我做纨绔,我就做纨绔。
“陛下想让我铺路,我也能为陛下铺路。”
她饶有兴味看着我:“若是你造反怎么办?”
“生杀予夺在您。”
“那你究竟想要什么?”
“陛下,我是个乞丐。”我笑望她:“乞丐哪管皇位上坐的是谁,我只想要吃饱穿暖,想要有屋可住,最好再有个从吴越来的漂亮质子给我当媳妇。”
“准了。”她颔首:“记着把你的忠心掏出来给朕看。”
……
数字屏倒数到了“1092。”
这一日,我回到浮锦阁,气氛有些微妙。
一个老内侍,一个拎着根粗木棍的小宫女,双双候在我寝殿门口,见我回来了,小宫女撒手扔了木棍,朝我讪笑。老内侍拉着小宫女朝我见礼,然后跟我挤眉弄眼。
“殿下,还是老样子,人洗干净了绑在您床头。
“您只管洞房花烛就好,要备下的东西,奴才们知道的。”
气得我太阳穴突突直跳,你知道个屁你知道。
牲口3452也在系统空间里吱儿哇乱叫:
“目标在直线距离120米内,请宿主注意把握时机。
“目标在直线距离110米内,请宿主注意把握时机。
“目标在直线距离100米内,请宿主注意把握时机。”
我袖中藏着把匕首,兜在袖内夹层,原本不算重,此时存在感却强得有些厉害。
走到门前,我停下脚步,这寝殿的门我推开过很多次,这会儿却重若千钧,叫我不敢推开。
那里头是个活生生的人,他被人摁在砧板上。
我就是那个刽子手。
见我不懂,3452又添了把火:“这祁连羌不是什么好人,为了苟活,勾结吴越六皇子,杀了前头六七个皇子,甚至毒死了自己的生父,死有余辜。你杀了他,不仅可以修正世界线,也是在替天行道。”
我终于推开门,直朝自己的床榻而去。
我看了他许久,想将他的脸记住,记在脑子里,刻在骨头上——我欠他的。
我强迫自己别抖,我想做得利落些,好叫他少受些罪。
我一刀贯入他心口,手上没松劲,恶人的名头,不能使我自洽,恶人漂亮的脸蛋,吴越的身世,甚至咬我的那一口,也难以使我动摇——我会杀了他。
——杀了他。
——回家。
——结束这个远古蛮荒的噩梦。
他咬着我的脖颈,利齿嵌进我的皮肉,眼泪却悄悄掉进我的颈窝。
滚烫的,好像要将我的良心生生烙下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