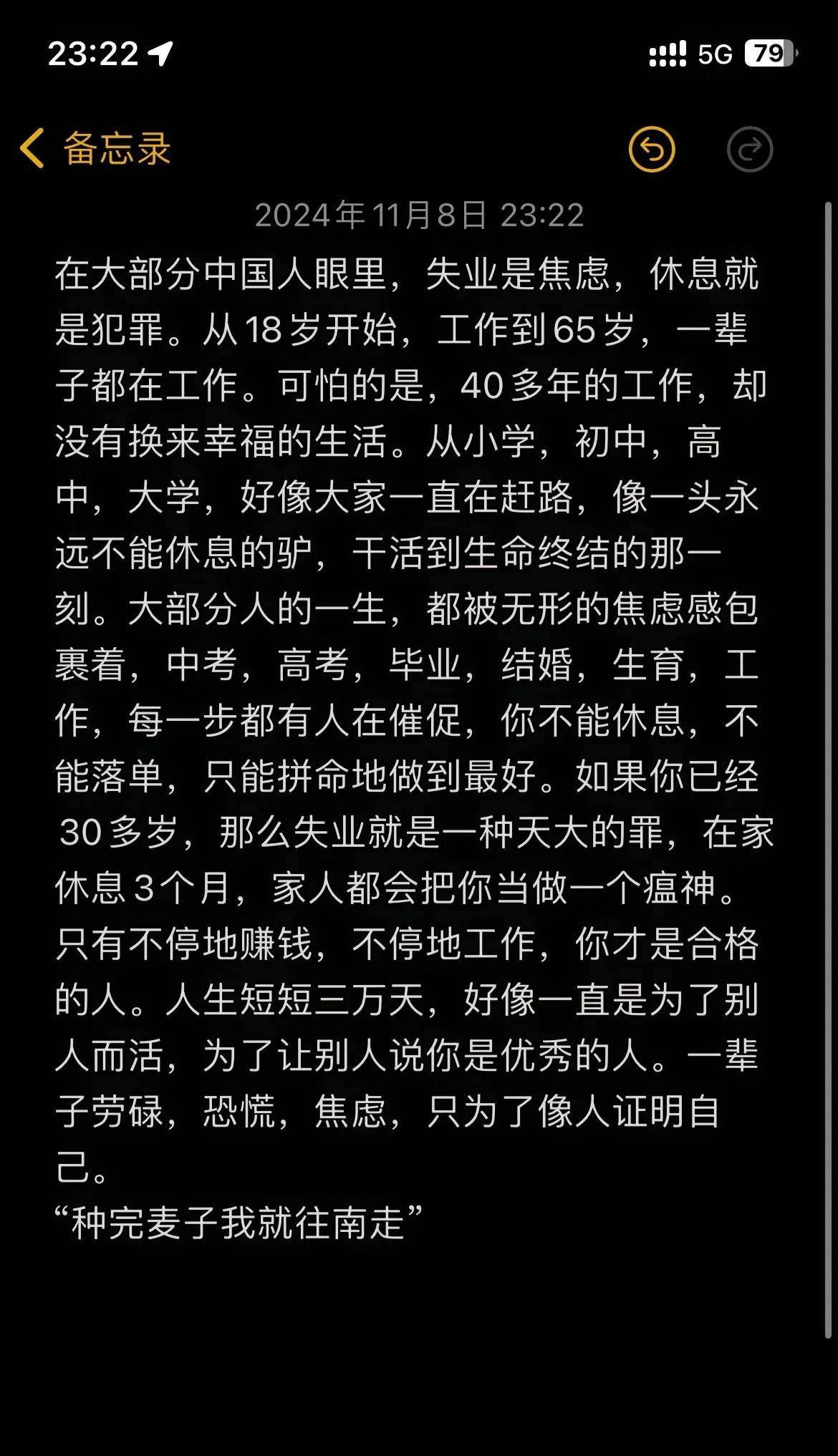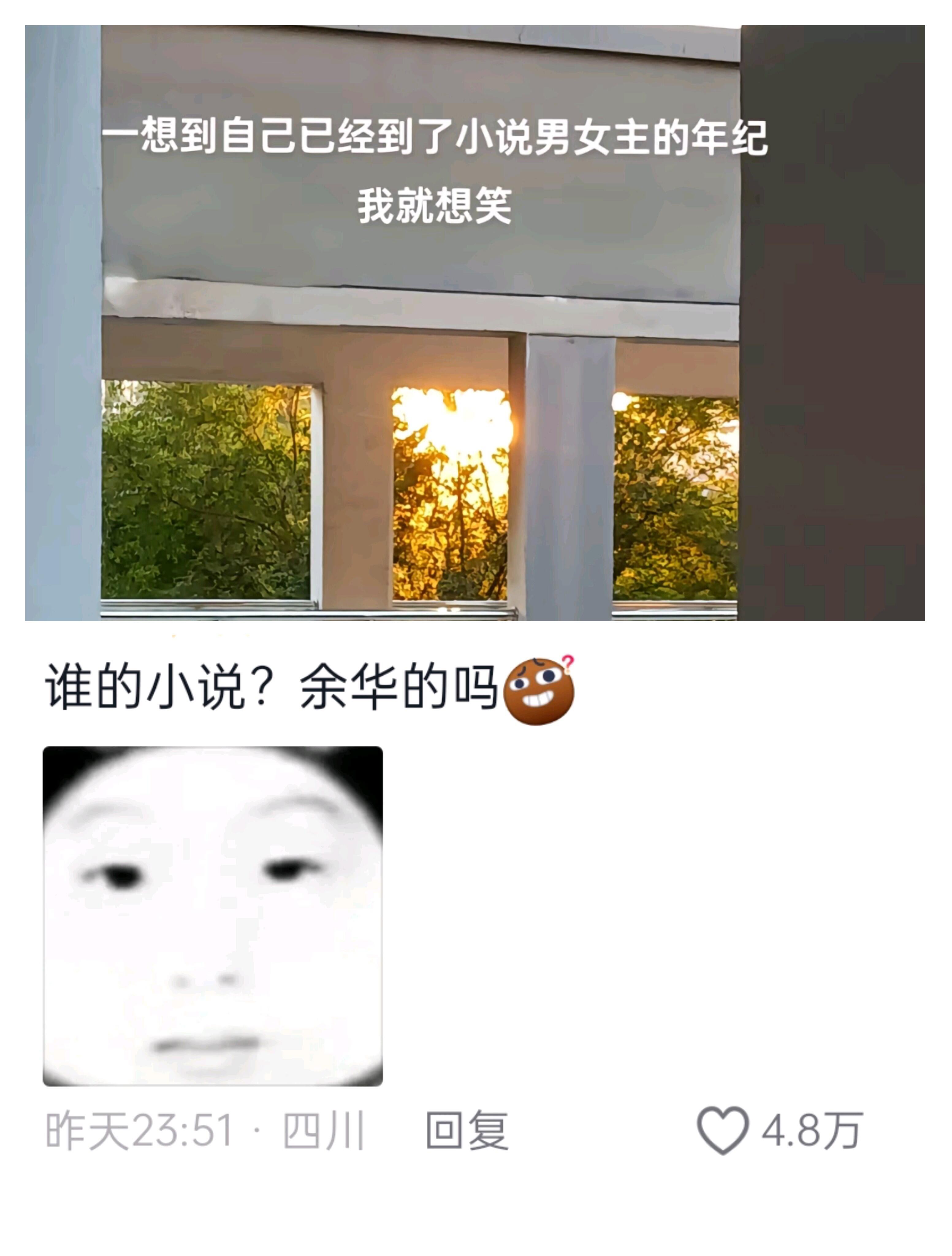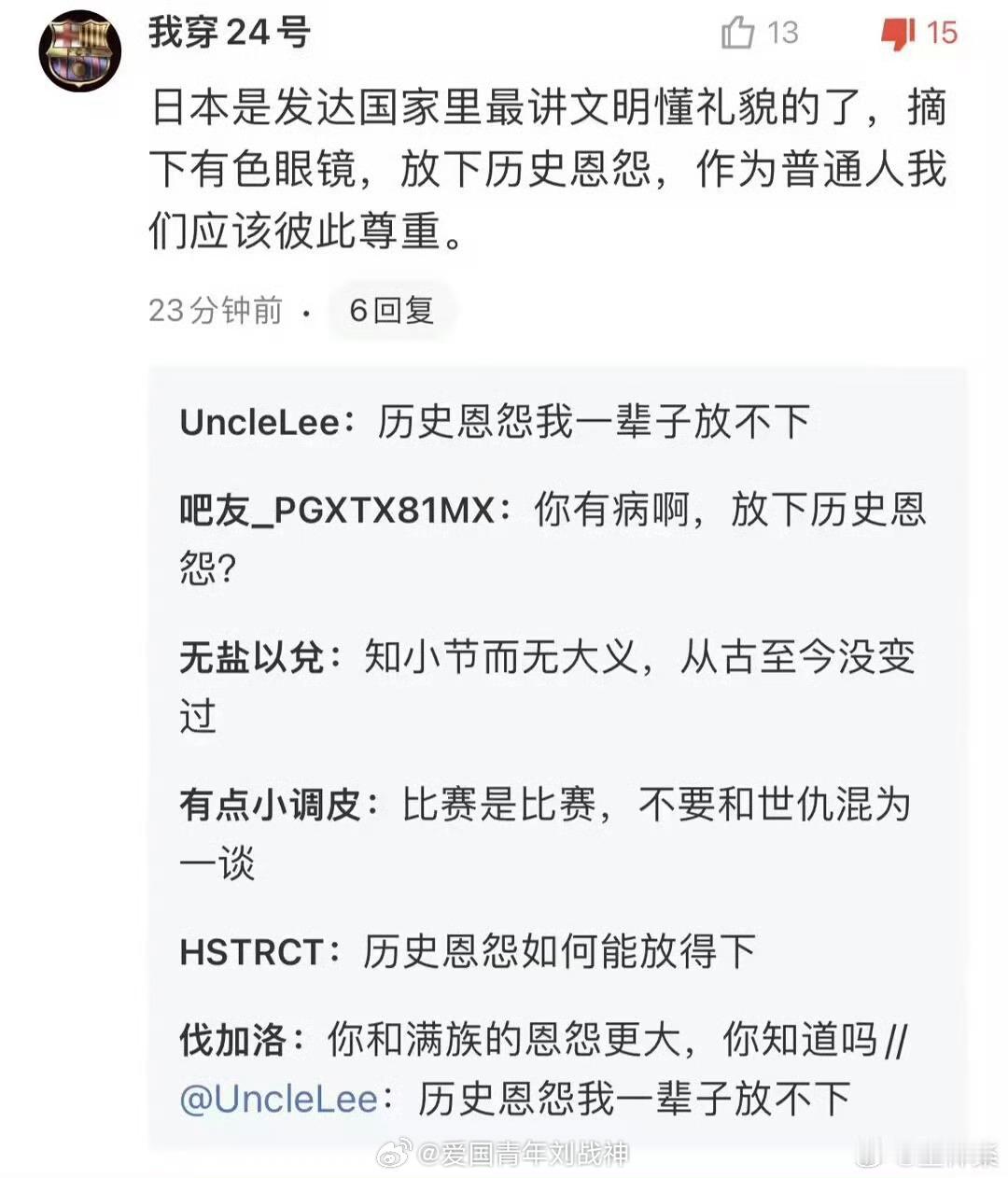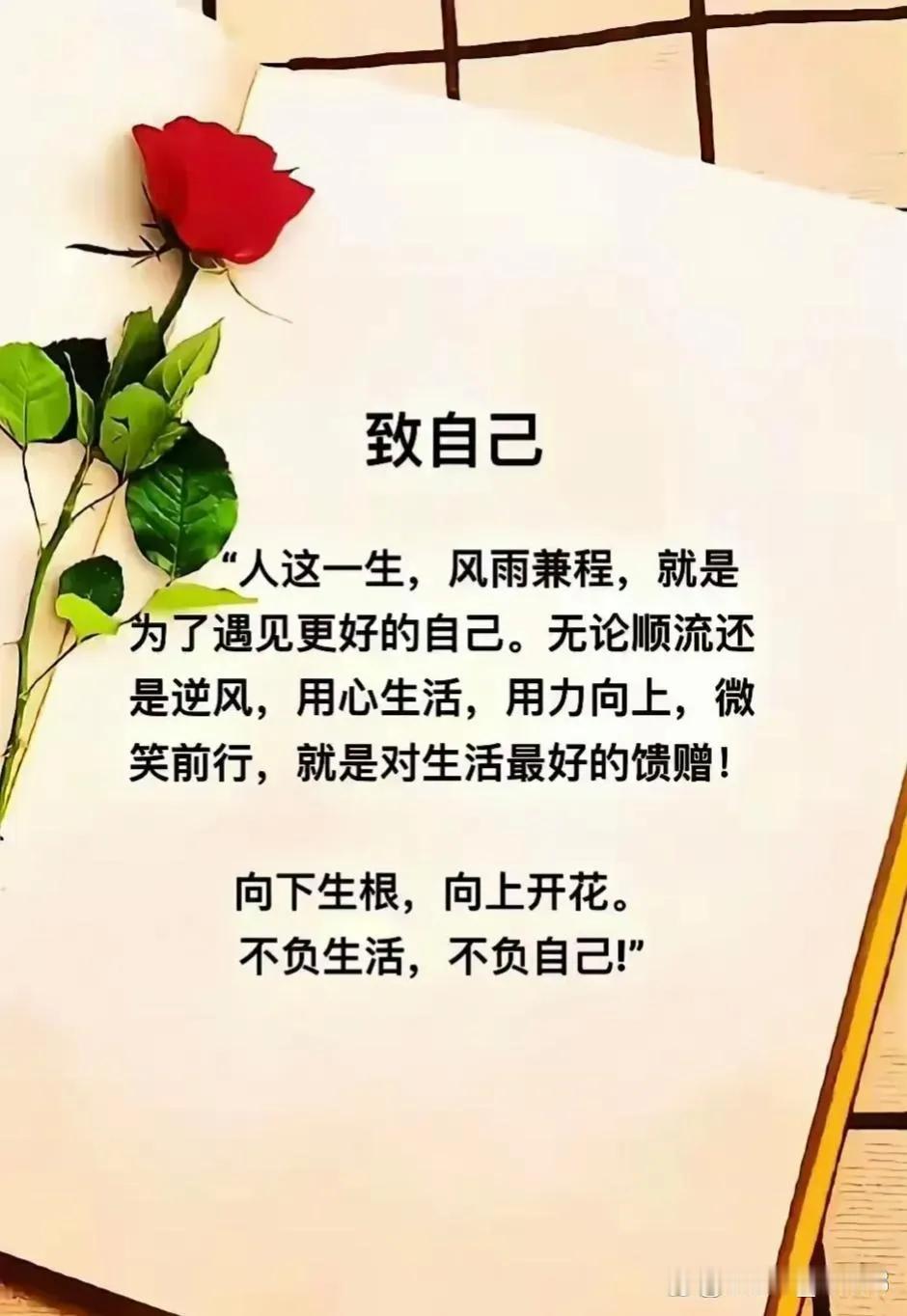“具象化”火了,渐渐也遭人反感了
游走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刷照片刷视频,总会遇见一两次“xxx具象化了”的说法。博主们记录下某栋建筑某处风景,或是见了某个朋友,选择几张上传发到社交账号,写下第一反应:“这一瞬间我理解了秋色的具象化”“这一刻我感受到光的具象化”“相由心生在这一刻具象化了”。或是评价一个人,赞叹对方是某概念的“具象化”。
网络流行用语大多都发端于小规模的使用——类似于圈内人的“接头暗语”——随后阴差阳错往外疯狂地蔓延,其含义也在这一过程中被改写;在它们泛滥之际,对它们的反感已经浮现。
“具象化”也一样。只不过我们使用它,除了新鲜感,也的确有见到真人实物的振奋(某个概念终于和现实对应上了),充沛的情绪注入让这个词显得有些不一样。
我们使用“具象化”好似“守株待兔”,先有了概念然后等待见到实体。一旦“具象化”,画面定格,人或事也被直接定性了。

撰文|罗东
瞬时感受
前不久刷到一条短视频。博主拿脱了粒的玉米棒当作话筒,采访一位女性。拍摄地为农村。
对话是这样的:
“请问你有iPhone手机吗?”“我安分守己。”
你笑了吗?
反正我随手转了“文件传输助手”收藏,因为这个谐音梗成功地戳中了我那过低的笑点。自然展开的对话,还是经过设计的摆拍?提问者一本正经,受访者一丝不苟,如此手法差点骗过观看的人。唯有作为收音道具的玉米棒在真诚地提醒我们,恶搞剧本罢了,观者不必对此太认真。

古装剧的搞笑话筒。图为《武林外传》(2006)剧照。
当然,知道完颜慧德的人不会同意最早是从这个采访知道“安分守己梗”的。2023年某天晚上,心理学博主完颜慧德在直播中讲女性做人当“安分守己”,怎料有连麦粉丝忽然问“不用iPhone手机,可以用华为手机吗”,完颜慧德一脸茫然,问连麦者怎么跑题提手机,毕竟与直播主题毫不相干。她此时显然掉进了连麦人挖的坑,其“女德观”在众人的围观下被解构得体无完肤。“iPhone手机”和“安分守己”这个古怪的关联由此一夜爆红。其实,最初是哪个人发现了两者的相似性不可考证,能考证的,不过是哪个账号首次在网络上使用它们。真实情况未可知,或是某个正在学习拼音的小孩子随口一说被大人发现,或是某个大学生返乡和老人聊天偶然产生了奇妙的误会,或是某个人对着聊天窗口发语音说“iPhone手机”,系统自动识别为“安分守己”。

《托斯卡纳艳阳下》(Under the Tuscan Sun,2003)剧照。
因为平台的算法推荐,我很快又看到一些,“请问你如何看待非主流”“如何看待小奶狗”还有“diss(指怼)”,总之村民被问的关键词五花八门,种种答非所问。
此时,套用时下的说法,我们就可以说这是“已读乱回”的“具象化”了。
假如使用批判的或反思的视角,我们可能会说这是城市知识(这里指的是词汇量)对农村知识傲慢的可视化,由褶皱的衣服、外露的牙齿、放肆而不加管理的表情构成的图像,成为被观看的素材。农村人掌握的词汇被认为多是前现代的、落后的、陈腐的。只有明白“城与乡”“新知识与旧知识”的二元结构才能听得懂这其中的错位,也才会发笑。作为旧式道德的“安分守己”,与作为现代技术的“iPhone手机”,把这种冲突展现得淋漓尽致。与其他段子不同,被冒犯者大概都不知道自己为何成为笑料,当他们被纠正后,可能脸红羞愧,也可能噗嗤一笑。重要的是,在观者接收的图像里,二元结构在这个时候已经“具象化”。一条短视频走到这一步也就实现了其全部效果。
“他者”“凝视”“消费”“观看”,能联系到的每一组术语,都可以说在这条短视频上“具象化”。

《疯狂的石头》(2006)剧照。
这不就是“举例子”“打比方”?某画面是某概念的“案例”,也就是某画面是某概念的“具象”。同一个案例有多个方面,解读的角度有多少种,它就是多少个概念或命题的“具象化”。
不过,人们在网上使用“具象化”并没有这么长的链:是在刹那间直接了当的感受,不需要多少“百转千回”的思考,比如“这一瞬间我理解了爱的具象化”“这一刻我感受到光的具象化”“相由心生在这一刻具象化了”。多是一种瞬时的体验。
那么“安分守己梗”这种视频对我来说,其实是“塑料普通话”的“具象化”。据说每个有口音的人都曾经自满自足地以为自己讲得可标准了,是标准的普通话,直到听到别人因为口音闹了笑话时,画面感也就有了:“我在别人眼中不就是这样的么”。这才是我的第一反应,“小丑竟是我自己”在这一刻“具象化”,而不是停下来借用一些理论框架去思考这件事这个现象意味着什么,对此可作何种解读。
毕竟不是实体

《失控玩家》(Free Guy,2021)剧照。
最近在读一本农业史新书《世界文明中的作物迁徙》(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4年10月版),多人合著,第一作者是在科技史学和农业史学有极高声誉的白馥兰(Francesca Bray)。她在中文版序言里说多年来“钻研”,“在技术和性别方面进行了长期且成果颇丰的研究”,没有哪个作者会如此形容自己的工作。是翻译导致的吗?由于是作者特定撰写的中文版序言,读者也没有英文版对照。不知序言最初是什么样的,书中并未注明是否为翻译。白馥兰还是一位汉学家,本人应该比较了解中文,这让人多了几分困惑。
如此措辞,我们似乎只在“民科式”著述中才会读到,其特征是表达不克制,恨不得让读者马上得知他在这方面多么厉害。而克制才是现代学术灵魂——至于过度克制导致学术视野的狭隘是另一个话题。所以哪怕再傲慢的学者也不得不借助一些专业术语来遮盖内心的自大,或者换个角度,请人写序言,借助他人的夸赞来表达某种自满。不会有人直白地形容自己钻研成果颇丰。白馥兰本意可能只是指在技术和性别方面做了许多研究,“词不逮理”“文人自负”在这一刻“具象化”,像极了我们用错了英文的敬辞谦辞。

《世界文明中的作物迁徙》,[英]白馥兰等,于楠译,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中科书院 ,2024年10月。
有意思的是,多看几遍这行字,又有了意外的感受:“我就说我的钻研成果颇丰,怎么了?”至少不虚伪。“潇洒自如”又在这一刻“具象化”。
如果我们在生活中认识一本书的作者,或者私下有一些情感交流,多少都了解其为人,一般不会因为一句话就改变印象。如果这句话与长久以来的印象冲突,我们倾向于认为在这当中必定误会了什么。要是通过读某位作家学者的书成为其仰慕者,某天忽然见到大活人,观其言谈,果然如此:“有趣的”“有爱心的”“有正义感的”知识人在这一刻“具象化”。相反恐怕就是“名不副实”“伪君子”的“具象化”了。这些年,每当有名望的人(包括“学术偶像”)因为性骚扰、抄袭、数据造假等问题“塌房”,我们总是会反复提醒自己不要对“偶像”产生什么美好的幻想,不要被其光环迷惑,哪怕下次还是会不禁被某个人表露的学识、胆识吸引。
这种情况不仅适用于人,也适用于物。在今天,游客往往都是通过文字和图像认识了景区才去实地游玩,有的还做了攻略,那么在进入它的那一刻,是否被震撼,是否感知到某个美好印象的“具象化”,将得到验证。“不去遗憾,去了后悔”这一游客经常念叨的经验,其实就是对未能成功“具象化”的总结。
或许将词与人、物分离,没有设想,也就没有幻灭。

《观念的力量》,[英]以赛亚·伯林著,胡自信、魏钊凌译,译林出版社,2019年4月。
设想是什么?是靠名词形容词堆砌起来的。以赛亚·伯林讲观念有唤起人为之行动的力量,他的《观念的力量》(译林出版社,2019年4月版)这本集子收录的形色人物、种种案例,让读者意识到观念如何改变了20世纪。观念也得依赖词语,词语当然同样隐藏着观念,不过不同于观念,词语未必是“成群结队”出现——观念则是一个体系——它可以是琐碎的、散装的。从命名、描述、阐释到推理,每个步骤都由这些词铺就,而每个词都有让人去想象的力量。在脑海里成像的那一刻对于想象者本人来讲就是真实的,人的感知和体验也是真实的——哲学者梅剑华《于是集》(华夏出版社,2024年2月版)在关于“元宇宙”的论述中还提出虚拟的世界也为真实一说。有了图像,再去比照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实体。追究起来,这与遥远的唯名论、唯识论以及风靡于20世纪的存在主义也都有关系。就看解读的角度是什么了。

《于是集》,梅剑华著,华夏出版社,2024年2月。
问题是,我们本就生活在“具象”的本“象”里,一些人和事原本也寻常,为什么要说“具象化”呢?
除非我们从未见过它们;除非我们生活在想象里。
二手的“象”

《大都会》(Metropolis,1927)剧照。
在上世纪20年代《大都会》这部电影上映前,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未曾目睹过这样一种宏大景观的全貌:超大规模的,整齐而庞大的人群和建筑集合。
排列组合是极致理性意志的体现。它带给人的是一种震撼,是人看到了无法把握的并且无限大的数字或力量之时产生的惊惧。在美学上也可称之为崇高。过去,人们即便路过能一瞥,也不过是平视某个局部罢了,将军王者登上城楼或其他高台才可能见到如此景象。瑞士艺术批判家奥布里斯特(Hans Ulrich Obrist)在《当代艺术的十九副面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版)就曾谈过希特勒可能看过《大都会》并受其影响。现代电影艺术将这种画面描绘给了城市中产者,随着电影的普及和技术的发展,又穿越阶层传播给更多人。从此以后,人们或多或少都可以想象这种普通人原本最不可能想象的画面。至此人世间的人和事的确没有什么是不能想象了。虚拟现实技术“VR”的突飞猛进也加速了这一进程。

《异次元骇客》(The Thirteenth Floor,1999)剧照。
网络年代经常被定义成人类信息爆炸的时期。一方面这意味着人越来越多的活动和行为都转化成了数字信息,另一方面这些信息也反过来影响和重塑人的认知和举止。
一个还不会写太多字的孩子已经拿起手机接收四面八方的信息,并且因为算法在学习孩子的习惯,很快会越来越善于推荐能吸引他们的内容。有一天,我在楼下碰到一个叫圆圆的男孩,今秋刚上三年级,他说起小区的流浪猫用的都是要“护它周全”。人们讲“现在的孩子越来越聪明了”,新一代的人类学习能力直线上升,这个判断实际上是指获取的词语越来越多。他们的词汇量是惊人的。当然,变化在更早些时候已经开始,至少十几二十年前,90后和80后也都曾经历。与信息增长相反的是,我们在现实世界中的活动却在减少。在电梯在街边,除了上下班高峰期,我们大多时候很少见到行走的人,最多的还是正在赶时间的外卖员快递员。所谓“非接触社会”形容的也就是这种情况。
脑海里装满了一大堆词汇,但是没有怎么见过其真貌(名词),也没有怎么体验过其感受(动词、形容词)。见到真人实物时,实体忽然“具象化”,久违的“真情实感”涌上心头。只有关于网络和屏幕本身的词语,在捧着手机这个动作中才能“具象化”。除此外大多数都是无实体的“具象化”。具象的“象”是二手的,是由他人在特定角度和美颜效果下拍摄的图像。我们时下体验的大多数“具象化”不也是如此吗?

《唐伯虎点秋香》(1993)剧照。
或许是人们对实体实感的呼唤,使“具象化”成为一个网络流行用语也未可知。大多数时候,我们虽然在技能和道德上承袭前人,却主要是通过阅历形成对人对事的看法,在现实生活中碰到一个人、一件事、一种现象,观察一番,形成看法,接着找词语去形容。在逻辑上是个人经验的归纳法。“具象化”则相反,在逻辑上是个人经验的演绎法,好似“守株待兔”,先有了某个概念然后等待见到实体。是拿词语去找实体(某个概念终于和现实对应上了),而不是看到实体后搜索个人的词库。如果经历多了、见得多了,见惯不惊,反倒不会讲“具象化”了。
这让人想起马克斯·韦伯用的“理想类型”。他以此为方法定义了不同种类的合法性来源、理性类型等。我们在脑海里首先接受了一个或一组概念,游走在人世间,等待感受“具象化”的瞬间。也唯有那些完全符合概念界定的人和事才可能有人为之欢呼或为之愤怒。一旦“具象化”了,画面定格,人或事也被简单地定性了。但是韦伯有补充,他认为理想类型是出于分类和思考的便捷,是被讲述的世界。他这一提醒在讲述一个简单道理:在真实世界,各种因素和性质都掺杂一些。某人某物在这一刻是A概念的“具象化”,下一刻钟可能就是反义词B概念的“具象化”。

《天使爱美丽》(Le Fabuleux destin d'Amélie Poulain,2001)剧照。
以上这些或许都是多余的话。
过段时间,还有多少人愿意开口说“具象化”呢?从兴起、流行、泛滥到被抛弃,直至消失,是它不可能摆脱的网络流行用语命运。
它迟早会回到它曾经被运用得最广的地方,比如ppt文案、课题申请、小说艺术创作之中的图形、绘画和细节描述。在那里,“具象化”是一个工具、一种表达手法。
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作者:罗东;编辑:西西;校对:薛京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