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勒泰的精灵
阿勒泰的精灵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不光养人,长庄稼,还长文学。
一个地方,拥有一个或两个卓越的文学表述者,是这块土地的福气。
就像北平有了老舍,江苏高邮有了汪曾祺,湘西有了沈从文,山东高密有了莫言,黄土高原拥有贾平凹和陈忠实,而新疆阿勒泰,幸运地有了李娟。
有人说,她的出现,就像当年的萧红一样,是天才的出现。李娟和阿勒泰的关系,就像萧红和呼兰河的关系。
作家王安忆评价说:她的文字一看就认出来,她的文字世界里,世界很大,时间很长,人变的很小,认识偶然出现的东西。那里的世界很寂寞,人会无端制造出喧哗。
刘亮程说,我为读到这样的散文而感到幸福……只有像李娟这样不是作家的山野女孩,做着裁缝,卖着小百货,怀着对生存本能的感激和新奇,一个人面对整个山野,写出不一样的天才般的鲜活文字。
而刘亮程正是发现李娟的“伯乐”。当时,十七八岁的李娟拿着一篇散文到编辑部投稿,有人怀疑她是抄的。刘亮程却坚信不是抄的,“我们的文学中有这样鲜活的文字供她抄袭吗?”
经常在《读者》读到李娟的文章,她的文字跟网络公号热门文章不一样,显得更端庄;她跟严肃纯文学作家也不一样,她显得无法归类。索性买了她的书来读。冬夜,万籁俱寂,拥被卧读她的书,温暖干净,清新不俗,博大端庄的文字像清泉汩汩滋润心田,一种平和安宁的幸福感在心中油然而生。
在文学圈,李娟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她的文字辨识度很高。比如她特别善用一些表面看起来很清浅俗白的文字,写出特别的效果(“车门一开,涌上来一群小家伙。我眼明手快,逮着个最胖的,一把捞过来抱在膝盖上,沉甸甸的温暖猛地严严实实罩了上来”。“孩子们更是被捆扎的里三层外三层,一个个圆乎乎的,胳膊腿都都动弹不了,拎起个孩子往地上一扔,还会反弹回来”——《坐班车到桥头去》)既清新温暖,又明快幽默,细心人一读就知道是李娟。
著名作家王安忆对李娟文字的评价为:“有些人的文字你看一百遍也记不住,有些人的文字看一遍就难以忘怀。”
有人说,李娟是“野生的作家”。1979年,李娟出生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家乡四川上学,高中辍学毕业后,到了阿勒泰跟着母亲做裁缝,常被人家称作“裁缝的女儿”。在牧区开过小卖部铺卖东西,也跟随牧民扎克拜妈妈一家辗转于四季的牧场之间。此后她曾到乌鲁木齐打工,做过流水线工人。
生活的贫困艰辛,漂泊流浪的经历,使李娟过早地体验到人生的悲苦艰辛,懂得人间的世情。身在其中,再苦,她也没有被苦所淹没,而是始终以一颗作家的心眼在跟现实保持距离,在打量着自己所受的苦,并把苦化成了文字。如果吃过的苦,仅仅化作了一堆“看透”,那就白受了。
她安静地漂泊流浪,受外婆和母亲的影响,形成了她活泼开朗、积极乐观,但又多愁善感的复杂性格。这种性格使得她对细小的事物有敏锐的观察力与好奇心。她善于从平常生活中发现不一样的东西,后来这也成了她创作的动力和源泉。
在这种特殊的生活环境下,李娟凭借自己的才能,创作出了散文集《阿勒泰的角落》和《我的阿勒泰》,并且都在2010年出版。这些作品几乎每篇都有李娟自己的故事,这里有最原始荒凉的土地,最淳朴善良的牧人,最古老的毡房,还有李娟最初的或多或少或喜或悲的回忆。
李娟受教育程度并不高,她也从未受过系统的文学写作训练。她的书,被同行看到感到惊讶:“这种文字是教不出来的。”“她的文章有一种浑然天成的灵气”。所以,有人叫她“阿勒泰的精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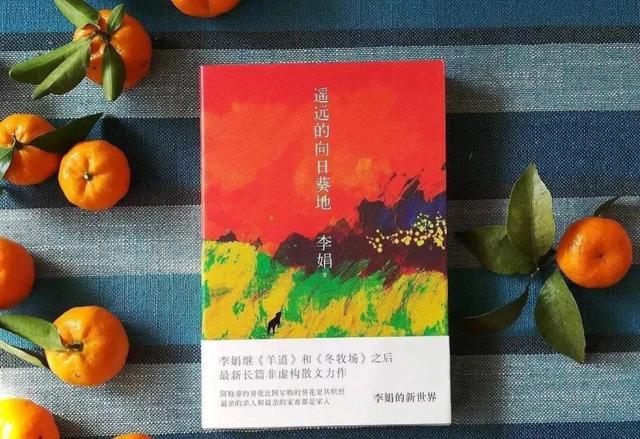 遥远的喜欢向日葵地
遥远的喜欢向日葵地十年前,李娟的妈妈在阿勒泰戈壁草原的乌伦古河南岸,承包了一块200亩的向日葵地。她们母女俩,还有一位叔叔,一起在向日葵地劳动。这自然是一段艰辛同时又充满奇迹的耕种生活。向日葵地历经黄羊啃食、毁了再种,种了又毁、三次补种,又接连遭遇干旱、虫害,直至收获,中间是微弱的希望和漫长的等待……
“当我在葵花地生活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总有一天要把它写下来,就一直是这个想法,然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段记忆就越来越深刻,如影相随,耿耿于怀的。然后过了十年的时间,我就慢慢开始写,第一篇我记得写的是《繁盛》,后来慢慢就一篇一篇出来了,就成了一本书。”这本书就是《遥远的向日葵地》。
按照一般的操作,这样的艰苦生活,李娟表达的肯定多是亲人们的坚韧辛劳,他们内心的期冀与执着。但这不全是李娟。跟李娟以前的散文作品相一致,勤劳乐观的母亲、高龄多病的外婆,大狗丑丑小狗赛虎,鸡鸭鹅,地窝子。
天底下至平凡无奇的动物植物,通过李娟的笔,拥有了旺盛的生命力,包裹着一层动人的情感光泽。
《遥远的向日葵地》的叙述一以贯之的质朴、明亮、幽默。比如去往“向日葵地”初始的《九天》,只用了九天,寸草不生的荒野平地上诞生起一座蒙古包,“第四天鸡开始下蛋”,生命开始得以繁盛。这一“创世纪”般的行吟,将种种艰难化为生存的乐趣与尊严。
“水渠通水那几天跟过年似的,不但喂饱了葵花地,还洗掉了所有衣服,还把狗也洗了。家里所有的盆盆罐罐大锅小锅都储满了水。幸亏我家家什多,可省了好多打水的汽油钱。那几天鸭子们抓紧时间游泳,全都变成了新鸭子。放眼望去,天上有白云,地上有鸭子。天地间就数这两样最锃光瓦亮。”
李娟一家人刚搬到向日葵地的时候没有房子,只在地上挖一个坑住在里面,新疆叫“地窝子”,钻进去,窝在那里面。李娟写出来,没有一句抱怨、哀叹、悲观,所有这样的词都没有。
她是这样写的,“抬起头一眼认出床板上的旧花毡,接下来又认出床前漆面斑驳的天蓝色圆矮桌,认出桌上一只绿色的搪瓷盆。没错,这是我的家。又记起之前有过好几次,和此时一样,独自去向一个陌生的地方,找到一座陌生的院落。和此时一样,若不是我的赛虎,若不是几样旧物,我根本不知那些地方与我有什么关系。面对农村、荒漠,李娟的写作,却没有很多写农村题材的文学常有的陈旧、消沉的气息。
苦而不丧,这是怎么做到的?李娟说,比起真正的农人,真正的牧民,“我这种乐观还差的远的很。我很少见过他们怨天尤人,大部分时候他们都是很顽强。他们才是真正的乐观。按照我的理解。农人生活的确是辛苦又单调。他们得为自己的生活找到希望,找到乐趣,才能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如鱼得水生活下去。如果他们不乐观,不热情,不对生活充满希望,大概是很难生活下去。我真的特别钦佩那样的人。我也渴望我是这样的人、我讨厌自己的虚弱,讨厌自己的矫情,所以我愿意去赞美他们,我觉得他们的这种状态才是正常的、合理的。所以我就更注重这些闲暇时期的小欢乐,有趣的东西。”
 没有秘诀,就是写出来的
没有秘诀,就是写出来的对一个作家来说,仅有生活经历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强烈的表达意识和独一无二的表达能力。
有人追问李娟:写作的秘诀到底是什么?李娟说:“我可以很狡猾的回答一下,就是写出来的。但是我知道这样是很不负责任的,哪里来的?所以说我是一个作家嘛,可以有很奇异的强大的自信心,我就觉得我这样写比那样写好,就是有那样的判断力写出来的。我是从小就喜欢写,慢慢写,才开始写得不好,就喜欢阅读,是一个书呆子。什么书都读,只要有文字的东西,我不挑剔,读到最后我大概就有一个审美和判断力了。真正成篇幅的东西还是要认真的构思。我不像别的作者那样牛,一遍成稿,一下就能写出来。我写得很缓慢,慢慢地去操实,慢慢地去经营。准备得也缓慢,主要还是修改,反复地改来改去的,基本上是改得面目全非,最后才会定。反复修改,反复质疑。写完之后修改,然后放一放,写别的东西,过段时间再去看看,再去修改,一直修改到我觉得这个东西挺像个样子的,和我想象的一样好,差不多就成了。有的人是越改越不好,我是越改越好。我的文字好像一气呵成,其实背后也是有很大量的工作的。”
虽然拥有大量忠实粉丝,但李娟本人一直低调淡然。这几年,打工、写作就是她全部的生活。经过这几本书的磨砺,李娟的文字能力和艺术水准也逐渐得到提高,或许在荒野中处乱不惊的心态就是她的法宝。
她说:“在四川,我在童年时代里常常在郊外奔跑玩耍,看着农人侍弄庄稼,长时间重复同一个动作。比如用长柄胶勺把稀释的粪水浇在农作物根部,他给每一株植物均匀地浇一勺。那么多么绿株,一行又一行。那么大一片田野,衬得他无比孤独,无比微弱。但他坚定地持续眼下单调的劳作。我猜他的心一定和千百年前的古人一样平静。我永远缺乏这样的平静。”
李娟用心沉淀着更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