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编了一部《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David Der-wei Wang ed.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简称《哈佛新编》。在这书的导论中,王德威教授谈到一个重要观念:“世界中”的中国文学(Worlding Literary China)。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Worlding Literary China是什么意思?中国文学作品不论好坏,总是在地球上人类世界中写成的,中国文学一向都“在世界中”呀!
原来,王德威教授的意思是:编写中国文学史,固然以中国文学为中心,可是,中国文学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不同文化之间互动而产生的(尤其是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与“外界”的关联更是密切)。这是一种“开放”的观念。
换言之,编写中国文学史,执笔者不宜一个劲只谈汉文学如何如何、不宜目光如豆、不宜只知有己不知有他人,否则论述时就自我锁闭,可能自外于“世界”。
不过,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张隆溪教授却认为《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内容零碎,可以用“乱麻”来形容。
那么,“世界中”的中国文学(Worlding Literary China),有可行性吗?这编写取向,怎样落实?
说到“世界”“世界文学”,张隆溪教授所撰英文版《中国文学史》(2023年)没有多谈,然而,他的书正是他从事“世界文学”研究(World Literature)的产物。在书外,张教授大声疾呼: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须占一席位。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在张教授写成的文学史书中,Worlding Literary China 有无踪迹可寻?
“世界”中的文学、“世界文学”
张教授新书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Routledge, 2023),内容以远古到清代文学为主(殿后的是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只占了一章的篇幅)。
张教授似乎比别的文学史家更重视中土和异文化之间的往来,亦即跨文化交流,例如,他特别为天竺佛教入华写了一个专节 (Early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Texts, see pp.48-49)。记忆所及,文学史书专设一节畅谈佛经翻译,案例似不多见。 另外,张教授对日本遣唐使和留学生在大唐的文学活动也津津乐道(张教授说:In Tang China, every year hundreds of students from Korea and Japan came to study; some of them went back, but some stayed in China and even took on positions i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rough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在涉及王维、李白的章节中,张教授都特别提到唐人和Abe no Nakamaro (阿倍仲麻吕) 的关系。

《阿倍仲麻吕传研究》
笔者经眼的其他中国古代文学史书没有一本叙及大唐诗人与阿倍仲麻吕之间的文学因缘。因此,“唐人与阿倍仲麻吕”这话题,应该是张隆溪教授的首创,可谓用“特笔”书写。
阿倍仲麻吕与大唐诗人有何关系?
阿倍仲麻吕不是平庸之辈,他在中土参加科举考试,顺利入仕。公元717年阿倍随日本遣唐使来华,此后一直没有回归日本(严绍璗《中日古代文学交流史稿》,页109—119)。阿倍取了一个中国名:晁衡,又与许多唐人为友,例如王维、李白 (张教授提及:He adopted a Chinese name, Chao Heng, and became a friend of many Chinese poets, including Wang Wei and Li B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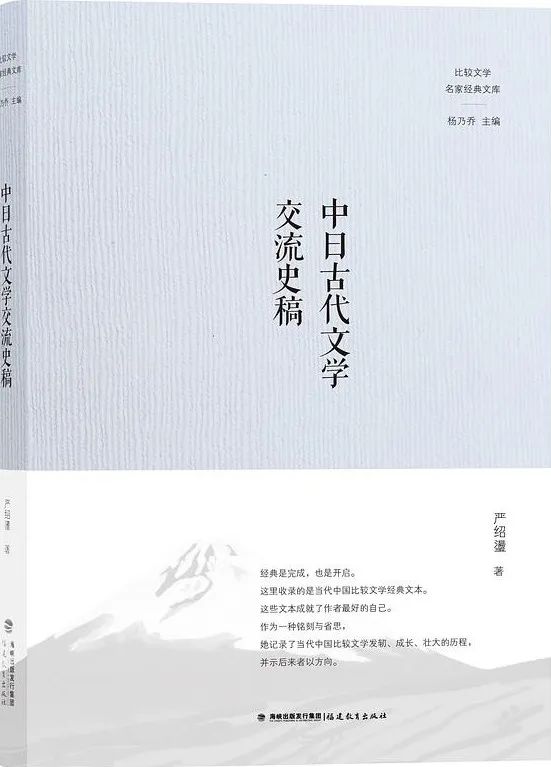
《中日古代文学交流史稿》,严绍璗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
张教授还指出,阿倍仲麻吕本身是个诗人: Abe was a poet himself, and one of his waka poems is preserved in the Japanese anthology Ogura Hyakunin Isshu (Collection of One Hundred Poems by One Hundred Authors), and his poems written in Chinese can be found in theComplete Collection of Tang Poetry. 按:Waka poem(和歌)是一种古典日本文学的诗歌形式,而Ogura Hyakunin Isshu (小仓百人一首) 是日本古典和歌集,由一百位诗人各自创作一首和歌而成。另外,张教授说: 阿倍仲麻吕所写汉诗,收入《全唐诗》。
张教授重点论述中土诗人怎样对待阿倍,反而阿倍的诗作不获论析,日本和歌传入唐朝概况也不见叙述。
《全唐诗》卷一百二十七有盛唐诗人王维《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一诗。“秘书晁监”应该就是阿倍仲麻吕。
关于《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张教授评论道:This poem indicates China’sclose relationshipwith Japan and the other East Asian countries during the Tang and much of the historical past, especially the close connections in terms of culture and literature.(p.114). 这首752年写成的王维诗,见证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景況。

中华书局版《全唐诗》
然而,所谓close relationship 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关系?是亲密关系吗?下一节,笔者略予解说。
所谓close relationship with Japan是怎么一回事?
王维《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之前附有一大篇序文。这篇序文说到:“海东国,日本为大。服圣人之训,有君子之风。正朔本乎夏时,衣裳同乎汉制。历岁方达,继旧好于行人。滔天无涯,贡方物于天子。同仪加等,位在王侯之先。掌次改观,不居蛮夷之邸。我无尔诈,尔无我虞。彼以好来,废关弛禁。上敷文教,虚至实归。故人民杂居,往来如市。”(《王右丞集》卷十二)王维对于日本人慕华学华表示欣慰。
由于日本倾慕中土文化,派学生到中土来学习大唐文化,因此,唐人认为日本人有“君子之风”,而且日本的制度似“汉制”,再加上日本经常遣使往来(“贡方物”),所以,当时的日本得到大唐政权另眼相看:“同仪加等,位在王侯之先。掌次改观,不居蛮夷之邸。”也就是说:中土大唐没有把日本看成蛮人夷人。

《王右丞集笺注》,赵殿成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然而,在个人层面,王维寄望阿倍仲麻吕“去帝乡之故旧,谒本朝之君臣。咏七子之诗,佩两国之印。恢我王度,谕彼蕃臣。”(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页220。)王维以中土为“帝乡”,自以为本国有“王度”,视日本人为蕃属之臣。王维希望阿倍仲麻吕回到故乡后也不忘弘扬中华王度。
笔者这里特别提出王维序文,因为王维希望阿倍做到汉文化输出。张教授撰写英文版《中国文学史》的初衷是要让中国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因此,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实际上也是文化输出的产物 (“让中国文学的经典成为世界文学的经典”)。这个目的,在张教授的书外演讲中表述得比较清楚(例如,2022年10月15日上海“撰写文学史的挑战”学术讲谈会上的发言)。
然而,王维《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诗的背后,有“宗主”“蕃臣”观念。王维的诗序显然有中土“文化中心论”的口吻。简言之,当时唐、日之间的关系可以是close, 但是双方地位不平等。

《王维集校注》
《全唐诗》卷二百零五还有包佶的一首送别诗《送日本国聘贺使晁巨卿东归》:
上才生下国,东海是西邻。
九译蕃君使,千年圣主臣。
野情偏得礼,木性本含仁。
锦帆乘风转,金装照地新。
孤城开蜃阁,晓日上朱轮。
早识来朝岁,涂山玉帛均。
“晁巨卿”就是阿倍仲麻吕。包佶这首诗也流露出中华为天朝上国、日本为“下国”的观念。“蕃君使”,是把对方看成蕃属国的使者。“圣主臣”指唐帝為主人。“野情”的“野”,就不必解释了。
王维、包佶都表现了“我为上国、汝为蕃臣”的高姿态,他们两首诗送到日本人手上,读者发视自己被诗人视为“蕃”“野”,心里会舒服吗?为何日本被写成下国?

《中国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傅高义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
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 722fcd8e-0648-0649"="">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 uploaded="1" data-infoed="1" data-width="491" data-height="695" data-format="jpeg" data-size="42279" data-phash="B3F04C07393EC4CD" data-source="outsite" outid="undefined">无论如何,日本不是永远的下国蕃臣。838年,日本最后一次向大唐派出朝贡使(傅高义《中国和日本: 1500年的交流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9年,页27)。
十世纪中期修撰成的《旧唐书》,其《东夷传》分述倭国和日本。1060 年左右,《新唐书》编成,其中《东夷传》只有关于日本的记载,没有“倭国”的记载。《新唐书》在日本天皇的演变过程中慎重地指出了670年以后“倭”变成“日本”一事。
日本大化革新(645年日本大和王权实行的一系列社会政治改革)之后十多年,日本国力强盛起来,便欲通过白江口之战(公元663年8月17日,唐朝、新罗联军与日本、百济联军战于白江口)向华夏王朝展示日本的政治独自性,谋求对等关系。此时候,唐、日之间的relationship就不见得有多close (亲密)。
简言之,当年日本政权的主体意识转强,渐渐产生日本型的华夷观念,即以日本为“华”,他者为“夷”的观念(步平、[日]北冈伸一编《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古代史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页39)。这是“大和(民族)中心论”。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古代史卷》,步平、北冈伸一主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至于说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other East Asian countries,也不是恒定的。亚洲的实际情况甚是复杂,例如,在唐朝的统治下,越南之地设交州,由安南都护府来管理,都护府不是纯粹的民政机构,含军事管制意味。到了唐朝末期,交趾(今之越南)逐渐寻求脱离大唐。如此这般,双方有亲密关系(close relationship)吗? 陈志海《中华文明圈:从中华王朝看世界》一再叙及越南抗华的史实,读者可以参看。

陈志海《中华文明圈:从中华王朝看世界》
唐朝时期,674年起,朝鲜半岛的新罗王国与大唐在朝鲜半岛的统治权上发生了争端,双方交战多年。双方会有稳定的亲密关系(close relationship)吗?
哪些中国文学的代表作可以进入“世界文学”之列?
2023年10月6日,张隆溪教授在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就“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中看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rld Literature"之题发表演说,他指出:“目前在全世界流通的文学,基本上就是英、法、德等西方主要文学传统中的经典,而非西方文学,包括中国文学,也包括欧洲小语种的文学,都没有超出自身语言文化的范围,在世界上广泛流通。”这是张教授为中国文学争取平等地位的原委 (cf. 白江口之战,日本谋求“对等”。) 这次演讲的关键词是World Literature。 王维寄望阿倍仲麻吕回到日本后“咏七子之诗,佩两国之印。恢我王度,谕彼蕃臣”,这似是“世界文学观”的唐朝版本: 王维希望中土的“文化代表”七子之诗流传于日本(按:流通, 即circulation,是“世界文学”的重要观念,参看哈佛大学David 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此书的中译名称:《什么是世界文学?》)。

David 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七子”是谁?“七子”就是“建安七子”: 孔融、陈琳、阮瑀、徐干、王粲、应玚、刘桢(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页225)。张教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 一书也有专节记述建安七子之事,可是,书中有“七子”之目,却连七子的姓名都没有叙述完整(pp.57-58),而且这个部分所附的诗篇,只有四篇。 换言之,建安七子没能各有一篇代表作获得青睐而被载录于张著史册,那么,现在看来,中国文学作品之中,真正称得上是经典的,有哪些?建安七子的作品,还有多少代表性?
在章培垣、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中,建安七子只有孔融、王粲、刘桢三人获得“专节”讨论的待遇,其余四人只沦为“建安七子中的其他诗人”(页256)。台湾叶庆炳《中国文学史》更只为“王粲、刘桢”立了专节(页136)。北京大学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也是一样只有“王粲、刘桢”专节(第2卷页38)。民国廿九年序本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也是只标举王、刘(页187)。
以上事实隐约反映了一点:历史书写未能做到七子均沾。其实,不是“未能做到”,而是“有所不为”,史家大多选择如此处理。 也许可以这样理解:建安七子之中,王粲、刘桢是比较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但是,为什么王、刘作品的文学价值较高(论hierachy of literary values)?换个角度发问:为何其余五人的作品生命周期 (life span) 较短?他们为何面临“几乎被文学史书除名”的窘境? 这是需要解释的(参看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

《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陈国球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王粲、刘桢以外的五子,其作品在他们自己的文化范围里流通都后劲不足,这样,怎能指望五子成为汉文学的代表流传于外?
由此可见,哪些人、哪些作品有资格担当中国文学的代表(成为文化经典),是有待研究的课题。我们只能说,在王维的年代,建安七子甚有“代表性”,所以,王维才指望阿倍仲麻吕回到日本还“咏七子之诗”。
可是,到了现在二十一世纪,建安五子(王、刘以外的五人)恐怕难有诗作足以代表“中国文学”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现今的日本人大可质疑:汝国文学史书中,连一篇诗作都不获载录的作家(五子),何足道哉?五子哪里有伟大的作品?
这情景迫出一个问题:“中国文学的经典是哪些?”如果需要定义某作品的“文学性”“经典性”,我们可以怎样进行?哪一本文学史书能清楚告诉我们可以怎样做?谁自称有能力和权力代表国家挑选出代表作?如果真有此人,他是不是自许的(self-proclaim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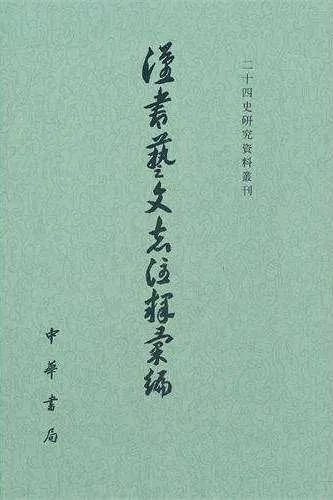
《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
编修《汉书・艺文志》时,这类问题就已经出现:有些文学类型被史家判定为“不入流”。不过,史家自身,持论就一定是公平、是正确的?
大唐“排外”“排他”事件引起的思考
在许多人心目中,唐朝是气度恢弘的王朝,对外来文化一般是持开放态度,能做到百川会聚、文化融和,关于当时的盛况读者不妨参阅Edward H. Schafer (薛爱华),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一书。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
不过,唐朝也有些人“自我中心”意识比较强,例如:唐高祖时,已经有朝臣反对天竺佛教;唐宪宗元和十四年 (819),韩愈上《谏迎佛骨表》(《论佛骨表》)谏阻天子迎佛骨,认为“佛本夷狄之人”,佛教自外于天下国家,又有违儒家伦理;唐武宗李炎在位的会昌期间(840年-846年),推行了一系列的“毁佛”(消灭佛教)政策,以会昌五年(845年)七月颁布的敕令为毁佛的高峰(参看洪涛《佛教跨文化传播的个案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人间佛教研究中心,2020年)。

洪涛著《佛教跨文化传播的个案研究》
简言之,唐高祖、唐宪宗时,士人和朝臣之中,辟佛者大有人在。到唐武宗时,则是君王动用国家的力量对付外来的佛教。
上面这些史实说明了一点:佛教经过几百年的翻译,仍然未能在晚唐中国站稳脚步。鉴往可知来:中国文学要傲立于世界文学之林,不单纯是语言转换之事。译本在异文化背景中的接受(reception)更是关键,其中涉及许多非文学因素(extra literary factors)。译本须有“软实力”相配,才能得到较佳的流通。
唐武宗灭佛,其旨意能代表唐朝的“主体性”吗?谁说他(唐武宗一个人)就能代表整个大唐?
总之,在编写文学史书这方面,王德威教授特别重视跨文化互动,张教授似乎也不轻视跨文化。王张两家的分别只不过是王教授集众人之力而为之(155人)。

《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文版
笔者不相信“令中国文学跻身世界文学之林”这件大事可以由一个人独力完成(single-handedly)。
至于为什么“不相信”,此际无暇细说。笔者近月就相关课题发表过三篇小文章,读者如果看过想必有领会。当然,这话题往后还可以续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