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昏暗的房间还在坚持着自己的编剧梦,面对极具诱惑的稳定工作,为了梦想,还是选择了拒绝。
这是电影《不虚此行》中的主角闻善。
深夜不睡觉,发了一条“退圈去种树”的微博,被一堆人嘲发疯。

随后还继续发丑自拍外加怼粉,更显出不管不顾来。

当时有粉丝在评论区开玩笑“又怎么了我的大小姐”
这是闻善的扮演者胡歌。
胡歌在一次采访中曾提到,自己和闻善有着相似底色。
出演这部电影是不是他放飞的导火索,我们不得而知。但,胡歌看起来很想像角色一样,为追求自我而固执一次、如正经文青那样浪漫一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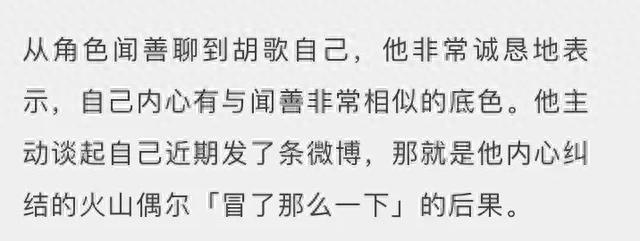
来源|人物《胡歌 爱使人自由》
只是,这座火山活动期太短,基本几瓶盖子水就浇灭了。
胡歌很快重回稳定状态,继续很商务地宣传新片。
而网友、包括他的粉丝都已经见怪不怪了。
他就是闲不得的主儿,脑子空下来就想一出是一出。

这时,我脑子里突然出现了爹妈糊弄小孩的既视感。
小孩是胡歌,他总说他要去浪迹天涯,拯救地球,创造奇迹,有一大堆不切实际的想法。
家长是我们,咱的回应是拍拍头:乖,别多想了,多刷几套题就好了。
这也即是问题所在。
为什么在人们眼中,胡歌就只配拧巴,而无法成为真正的闻善?
换句话说,他怎么就成不了自己想当的“文青”?
先聊聊,闻善是个怎样的人。
电影《不虚此行》说的是蛮简单的一个故事。
胡歌扮演的闻善是个不成功的编剧。
因为接连写的几部作品都未如期发表,不得已找了个给殡仪馆写悼词的工作,聊以糊口。

外人眼里的闻善,是丧的。
但导演并不想让这个角色一直丧着。
他有理想,即使是写悼词,也没放下创作者的尊严。
应该说,他有一份和世俗格格不入的执拗和天真。
不同于其他同行,闻善会一家家走访逝者家属,采访逝者的亲友,为的是让悼词不是全篇套话,而真正属于逝者本人。

这显然不是划算的买卖。
可闻善不在乎,他做了。
这便是他的“天真”。
当多数人只能顾及营生时,只有他,还在企图从艰难里抓到一点理想的影子。
说他“文青”,不仅因为他有一些外化的浪漫行径,更因为他有内在的精神追求,比一般人要的更“形而上”一些。
这,大概也是胡歌自认和闻善的相似之处:
一个坚定的内在自我。

有一说一,角色那种郁郁不得志的丧劲儿,胡歌还是拿捏住了。
眼神涣散,面容憔悴。

总是佝偻着背,仿佛早已经被现实打趴下。

和白客扮演的工作人员一起抽烟闲聊,他要么惜字如金,要不直接不发一言,似心有千千结。

然而在胡歌不断强调着他自己与角色的相似时,二者间的差异又在拉开。
闻善的“文艺感”是由内而外的,他内里固执且理想化,但在外界的打压、束缚之下,他便表现得沉默并颓丧。
胡歌却不一样。
他看起来总是太乖驯,恰到好处地拿捏着和世界沟通的姿态。
他的“文艺感”只存在于少数豁出去的瞬间。大部分情况下,他表现出的毋宁说是一种“书生气”。
一种在社会文明中训练出的周全和温润。
而这与闻善执拗、野生的精神自由,恰恰是两回事情。

《繁花》
换句话说,胡歌与善闻确实有底色的相似,可面对同样的世界,他们注定会过不一样的人生。
善闻是撞了南墙也不死心,路再硌脚也要曲径通幽。
而胡歌的社会化程度太高了,他的“豁出去”只在一个范围内,做不到“从内而外”。
你让他去多刷几套题,他可能犟不过几秒即就范。
正因此,他成了永远羡慕“文青”,却无法真正“文青”起来的人。

并非妄言。
这些年来,胡歌似乎一直在想办法借演戏释放内在的冲动,实现迟来的叛逆。
从他近些年的选角,不难看出端倪:
从《你好,之华》《南方车站的聚会》到《繁花》,再到与文淇合作的《驯鹿》,未官宣的各种传闻饼也是一水儿的严肃剧情片。

今年刚杀青的新片《走走停停》,介绍第一句就是“落魄北漂文艺青年”,简直把胡歌狂喜元素拉满了吧?

然而在“文艺片”这个不大严谨的标签下,中年叛逆的胡歌却注定会比其他演员困难些。
首先,他的面相太英俊,也太乖了。
近年出圈的章宇、蒋奇明都胜在自带野性,是一股在丛林挣扎存活的猛兽气息,往布景里一杵,黑乎乎的一个人儿,与环境是融为一体的。

至于看似同样俊美、温顺的如梁朝伟,张震,实际比前两例更难得。
若章宇、蒋奇明是社会驯化不了的困兽,叛逆又脆弱。
那他们则压根是在抗拒社会化。
他们的眼神纯真到好似未经过任何世俗的侵染,因而生出忧天悯人的神性。

《悲情城市》
而在调动出原始欲望时,他们更能表现出不通人情的狠辣,这是一种更彻底的动物感。

《色·戒》
飘无意对比拉踩。
气质、个性、风格,本就是每个人独属的本钱,各有长短。
但恰如前文所言,胡歌的帅,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温润和周全。
这是他的幸运,后来也成为他的某种束缚。
在念书时,他是一打眼最出挑的秀气少年郎。

出道时,他则是从游戏照进现实的“翩翩潇洒美少年”。

但文艺片更想捕捉的是人更本真的东西,是一种原始、天真的样貌。
打个比方说,这类电影寻找的是浑然天成的璞,而胡歌已经是抛光过的玉。
别人能很自如地“展示”自己的内在。
胡歌呢,或许是他的内在被压抑太久,他只能努力去“表演”出他想象的自由。
就比如,同样出演过赖声川话剧,赖导对胡歌的夸奖是这样的:
不管是排练或者演出
他都是使出全力

凤凰视频《胡歌 顺流逆境》
而对张震演的江滨柳,赖声川的评价则是:
不管我给出什么指令
他(自己)已经在往前走了
他已经占据了这个角色

当然,没有人会觉得胡歌应该去跟梁朝伟和张震比,这不是一个合理的参照系。
但不聊演技、仅看状态,你会发现,胡歌一面渴望释放,一面又总是活得最圆滑玲珑的。
2011年,他上郭德纲的访谈节目。
郭德纲的风格荤素不忌,提问都十分大胆甚至“无礼”,但胡歌面对这些极具攻击力的问题,几乎做到了有问必答,又温驯真诚。
一场访问下来,郭德纲也对他赞赏有加。

《今夜有戏》
而在力求本真的文艺片里,“滴水不漏”有时会变成劣势。
就如《南方车站》里他演的周泽农,一个偷电瓶车的小头目。
打眼看,这演出确实有美感。
但对于一个三餐不准时,作息不规律的混混而言,这种美又显得太自律了。

“自律”是一个很精准的词。
说白了所有的“律”原都来自外界,只是被人认定为是遵从内心。
胡歌就是这样一个人。
而他觉得已经很自我的东西,其实还不够“自我”。

算起来,胡歌已经是入行近20年的老手。
但哪怕到今天,他还是会像犯了错的小朋友似的,一边倔强地瘪嘴,一边用蚊子叫似的声量认错。
之于我,其实更愿意他放开胆子任性到底。
胡歌的书生气,就在于他在娱乐圈表现得太像个应试考生。
他曾多次说过,甭管对演戏还是演话剧,他都是很紧张的。比如演《如梦之梦》的五号病人时,他就一度紧张到睡不着。

凤凰视频《胡歌 顺流逆流》
这份紧张,不难猜测是来自他的不自在。
胡歌自然不是张、梁这样的天才型演员,需勤能补拙。但勤奋到顺从的程度,也压抑一位演员的自信心和天性。
刚出道时剧组三班倒,他为了配合剧组,经常困到可以站着就睡着。
拍《射雕英雄传》时也因强度大,困到鞋底被篝火烧穿了都没知觉。
这些不适,他从不抱怨,通通忍了下来。
前老板蔡艺侬得知后要去跟剧组理论,还被胡歌拦下,因为他觉得自己能演李逍遥就很满足了。

《大V朋友圈》
和胡歌同一年的章宇,也是认真的演员,只是他的方法要粗野得多:
为了找到人物感觉,曾在小破旅馆整整住了一个月,不告诉任何人身份,住到后面老板都忍不住要给他介绍工作。

人物《此人不叫黄毛,他叫章宇》
在《无名之辈》前,他也确实还是无名之辈。
可在片场他和导演赌气、吵架,借着酒劲埋怨。
原因是他更喜欢电影另一个悲剧结局,他希望自己的角色通过死得到圆满。
“后来章宇非常痛恨我
有一次喝多了还说我为什么不让他死”

《新京报》
而对于一个社会化程度很高的考生,要回去找野孩子的感受,是极其困难的。
哪怕是他的所谓“发疯”现场:
在渴望“对得起一生”时,他先冒出来的是三句带着歉意的“我尽量”。

先向他人承诺会听话,再去表达自我。
这是已经固化的、仅属于乖孩子的思维模式。
就像本质还是好学生的余淮,他能想象的叛逆,就是放学后跑去打打游戏机。

换成路星河这种浪漫鬼+破坏狂,在学校都开始炸喷泉了。

我会为胡歌感到些许遗憾。
正如他说的,一生很短暂。
他已经乖觉了40年,再不任性还有机会吗?
在一个全民盛行“发疯学”的时代,怎么还是轮不到他失常一下?

《不虚此行》中的闻善,不在乎外界目光去了殡仪馆,也不在乎社会的运行规则,用完全不成比例的付出,只为写一篇不令自己羞愧的悼词。
这种格格不入,才可谓真正的“文艺”。
它是一种不计成本的神经质,不符合世俗规则的天真。
胡歌大可以学学他,活得再“疯”一点。
真的想做什么还报备个啥?干嘛不直接试试看?
在这个谈“自我”几乎等于讲笑话的名利场,能窥见明星真我的机会,都太罕见了。
演了这么多自由的灵魂,本人却还只能在深夜emo,这着实是巨大的矛盾。
万一在撒野的尽头,就是一个更好的胡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