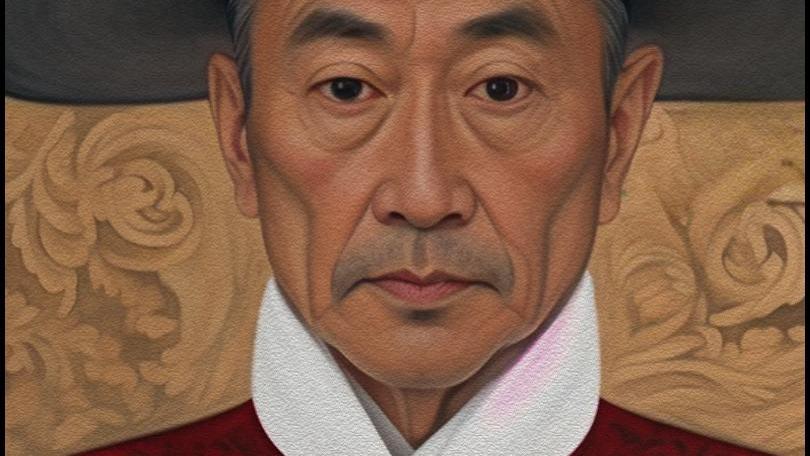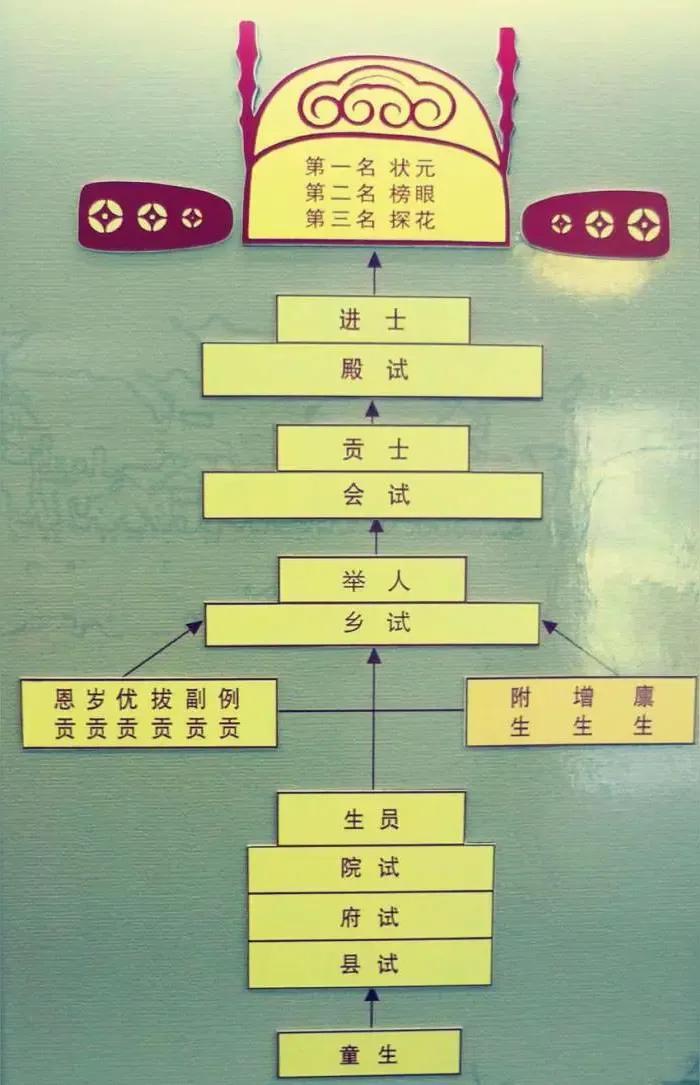6月21日下午,身处偏远西南贵州的我,突然接到一位久未联系的北京老师的来电,说他今天很高兴地在北京见到张新民先生。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但其相遇的欣喜之情如在目前。末了嘱咐我说,贵州虽然远离学术文化的中心,但因为张新民先生在,子居九夷,何陋之有?希望能一往如昔,向他请教。
放下电话,多有感慨,与张新民老师的交往亦如画卷一样徐徐展开……
第一次知道张老师,还是在读大学时期。那时,我无意中读到贵州人民出版社的《传习录全译》,当即被序言所吸引,阅读过程中,不时回头看作者姓名。 “张新民”三个字自此刻入脑海,不时生起“想见其人”之感。不想后来考入贵州大学读研究生,居然见到了想象中的张老师。读研究生的三年之间,我就经常与张老师的研究生一起,聆听张老师的许多教导。一个朦胧的感觉是,天地开始变得广阔起来……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到珞珈山从刘纲纪先生读美学。其间修习、旁听了中国哲学、宗教学等许多课程,在受益武大诸多老师时,脑海里不时浮现张老师的音容笑貌……后来我有一次回到贵州大学拜见张老师。他说,书院已经完全建好了,欢迎你回来工作。从此,我就离开了荆楚大地、长江之滨而到了云贵高原、花溪河畔,得以随伺张老师左右……

张新民先生近影
一、“这三本书是我研究贵州地方志的心血之作”在放下北京那位老师的来电之后,我上网一查,方知此时正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第三十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张老师主编的《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考释》参展,方有两位老师的盛会欣逢。
《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考释》是张老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最终成果之一。我早就知道张老师所主持的这个项目,但因为自己学习的领域与之多有距离,所以没有参与。但是,这不由得想起张老师的学术生涯。

《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考释》简介
今天与很多人见面,他们一般都会关切地询问张老师的视力情况。追溯其因,这与他早年的学术有关。
张新民教授今日以儒学研究知名于世,但最早是从历史文献开始,代表著作或可谓为“张新民贵州地方志三书”。被贵州士林誉为“贵州文化老人”、对推动贵州地方志收集整理研究做出巨大贡献的陈福桐先生曾经说,有了张新民的《贵州地方志考稿》,就可以按图索骥,到各地去查找方志。
“我的《贵州地方志考稿》一书,是在读研究生期间完成的。”1981年,张老师考上贵州师范大学研究生,师从周春元先生。1982年初入校。当时全国各地的上百名图书馆学、目录学、地方志的专家学者们正联合编修《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目的在于对浩如烟海的地方志遗产进行分地区的研究。周春元先生希望张新民能承担贵州地区的撰写工作。于是,“1982年,我开始着手这项工作,用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来搜集资料、制作资料卡片。1984年我因为用眼过度,导致视网膜脱落,休息了半年。”1985年后,张老师陆续出版《贵州地方志考稿》《贵州地方志论纲》《贵州地方志举要》。“这三本书是我研究贵州地方志的心血之作,也凝聚了我对贵州地方志的热爱之情。”但与此同时,因为“抄录资料太多,看字太多,坏了一只眼睛,到后来几乎看不见东西。”自此张老师留下眼疾。

《贵州地方志考稿》封面
傅振伦、来新夏、陈福桐等先生则对张老师的地方志研究褒勉有加,“来新夏先生与我长期通信,他的鼓励也给我很大的精神动力。陈福桐先生与我交往最深,他的奖赞常使我汗颜。傅振伦先生远道赐序,那时他已八十岁高龄,破例为我动笔,也令我感动不已。欧洲汉学家魏查理教授主动联系出版,最终使此书(《贵州地方志考稿》)能以中文形式在欧美传播,而黔省史地文化研究也提高到全国乃至全世界瞩目的地位。回想旧事前后经历,真有无尽的感慨!”
二、“早年打下的文献学基础”在从事地方志研究之时,张老师也对文献目录学多有研究。“我自1972年起就从父亲学文献学,受过严格的版本目录学训练。”张老师的父亲张振珮先生以治《史通》而知名,所撰写的《史通笺注》一书在八十年代初次出版后,即获傅振伦、程千帆等著名学者的高度赞誉。是书出版后,坊间早已难获。庆幸的是,该书去年被中华书局纳入“中华国学文库”再版,终解学界之悬渴。而同样值得高兴的是,他自己的《贵州地方志考稿》也将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张振珮:《史通笺注》(修订再版本),中华书局,2022年
从中国传统治学路径来看,目录学是治学之首要课程。清代学者王鸣盛便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著名史学家章学诚更明确地提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要求,认为这是“推阐大义”、 “宣明大道”必不可少的方法论途径。张之洞认为读书这件事“宜有师承,然师岂易得?书即师也。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此句话影响深远,许多老辈学人视为治学之不二法门。张老师也如此,“我自己则从《书目答问》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入手,慢慢走上了学术的道路。”
作为一个未曾受到古典学术训练的年轻学人,我深感文献训练之不足所导致的重重困难,所以暗下决心进行补课。前几年的一天,我遇到张老师,说自己买了来新夏等先生做的厚厚的两大册《书目答问汇补》(中华书局,2011年版)一书。张老师听后马上说,哎呀,早知道我送给你啦。因为该书出版后,来先生送了我几套呢。来新夏先生之所以如此,与张老师的《书目答问》研究密切相关。
来新夏先生的《书目答问汇补》可谓迄今为止《书目答问》研究之集大成之作,所采录之材料也可谓该研究之精华。
众所周知,古籍整理中,底本的选用至关重要。来新夏先生此书“选用的底本为清光绪五年贵阳校刻本(王秉恩、陈文珊刻)作为底本。”可知该本之重要和价值。无独有偶,张老师等贵州学者不但早已关注此本,而且还做过深入研究,其成果即为由贵州师范大学吕幼樵校补、张新民审补的《书目答问校补》(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
在“汇补方法”上:“一般以每一种书作为一个条目,先录贵阳本正文,次列诸家校语。”《书目答问汇补》尤其推崇张新民教授及其父亲张振珮先生的成果,“本书采用校本(语)凡十七家,首为江人度校刊本,殿以汇补者‘按’。”十七家皆以方框显示,醒目而易于识别。其中,张振珮先生也为其一:“张:张振珮按语。附载吕幼樵撰书目答问校补(2004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后,题‘张振珮批校、张新民补书目答问斠记’,今逐条摘出,作为一家言,分别置于本书相关条目之下。文中‘珮按’之张振珮校语,‘今按’之张振珮子新民校语。简称‘珮按本’。珮按中所言筑本指贵阳本。”由此可知,在来新夏先生看来,张振珮、张新民父子的《书目答问》研究之重要。
张老师早年由地方志进入方志学,进而由《书目答问》入目录学。其思想、精神或可集中体现在其早期撰写的《中国古代书籍世界的目录学窗口——张之洞〈书目答问〉散论》一文中。张老师在文中不厌其烦地强调目录学对于治学的重要,与其说这是在对传统学术路径和特点的介绍,毋宁说是张老师之“夫子自道”,是对自己治学途径和思想关切的表达。记得自己在读硕士研究生时初读此文时,如受电击。所获得是并非只是目录学的知识,而是初窥做学问的见识。在一般人看来,《书目答问》一书不过枯燥之目录学专书,但是张老师在此文中深刻揭示了传统知识分子的价值、文化关怀,从而使泛黄之旧书获得了思想的辉光。在此辉光的照耀之下,文献古籍别开生面,也进入了年青学子的视野。1998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曾出版张老师的一部论文集,题为《中华典籍与学术文化》。窃以为之所以如此题名,不仅是该书内容的反映,更为重要的是展现了张老师将抽象之思想与具体之典籍相结合的治学思想。
“我的不少知识直接来源于古籍,能够独立思考,判断别人立论的坚实与否,从不跟风时髦作文,显然也与早年打下的文献学基础有关。”从目录和文献入手,这并不只是为学先后的问题,而是一个学风的问题。文献、目录学涉及到大量的考证,表面看来相当的枯燥无味,但长期浸淫其中的学者,无形中又会养成严谨求实、稳健踏实的学风,进而影响其研究的方向和特点。张之洞曾言:“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范希增《书目答问补正》附二)究其根本而言,张之洞之所言在于探讨任何一门研究是否可信(属实)的问题。在他看来,要达到这一目的,应该具有相应的前提。如无此前提,其研究虽然可以标新立异,但究其实不过哗众取宠而已。张新民教授熟谙《书目答问》,对张之洞的意旨以及传统学术之门径、程序不但领会于心,而且身体力行。从而使他在后来的儒学研究中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特色。
三、历史辉映下的儒学研究前两年去世的史可资先生是贵州大学图书馆老馆员。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从北京来到贵州后,直到去世,一直在图书馆默默无闻地工作。贵州省文史馆一位馆员曾经戏撰一联——“万卷藏书史可资”,巧妙地将史可资先生的姓名与工作岗位联系起来,别有韵味,可谓精妙,但苦无下联。某一日,我与张老师谈及此事,临时凑了一个下联——“一点良知张新民”。拙意以为,张老师近年来从事儒学,特别是阳明学的研究,“良知”为阳明学之核心要点;“新民”又为《大学》之三纲之一,“张”则有动词之义。张老师听后一哂,不置可否。张老师虽然自述年轻时即对义理、思想感兴趣,但真正进行专门的研究,则可能要到中年以后。此时他已经完成了文献、目录学以及历史学的基本训练和长期积累,取得了丰硕的硕果。也因此,他一直是历史学专业教授,而非时下学科分科体系下的哲学系教授,这可能也让很多人意外。
张老师曾自述自己学史的最初经历,其中一个很大原因是与乃父张振珮先生的导引有关。在张老师小时,“贵阳的古籍旧书店原在城区的金沙坡。有时候父亲逛旧书店也会带着我一同前往。他的‘二十四史’是散佚后又重新慢慢配齐的。‘文革’刚结束时购到《清史稿》,记得书到家时他十分高兴,毕竟最后‘二十六史’也置齐了。家中的书,史部最多,集部有也不少。善本并不多,但都很实用。我在家中随便乱翻,也增广了见识。”

张新民先生与父亲张振珮先生合影,摄于1986年
作为一位知名的儒学研究者,张老师特别强调历史的重要性,“我们要记住历史,要从更广大的时间和空间维度看问题,避免局限于一个短暂的时间维度。如果能这样,我们的路会走得更好,从个人修养、家庭伦理到国家发展,更好地维系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脉。”
近年来,地方历史文献、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成为学术界的热点。2011年,由张老师担任首席专家的“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对这一看似纯粹文献的项目,张老师也赋予其深远的关切。在他看来,贵州毕竟是多民族聚居区,恰好清水江文书的庋藏分布地虽然极为广泛,但都集中在苗侗汉混杂聚居区。通过对清水江文书的整理、研究,不仅国家长期经营开发西南边陲的经验值得认真研究和讨论,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的经验也值得反复分析与总结。
今天,在现代学科的分科体系下,儒学研究主要被划在“哲学”。由此带来的问题是,《资治通鉴》以及“二十四史”,乃至《诗经》《读史方舆纪要》等其他学科的典籍是否应该属于儒学研究者的必读书目?张老师早年的史学修养使他突破了这个藩篱限制。早在读研究生时候,“我最初通读《资治通鉴》,就是用家中的四部备要本,作为日课一天读一卷,用红铅笔在上面断句。”“《通鉴》总共二百九十四卷。我差不多每天读一卷,一年读完。自此获得了一种眼光和格局。”或许正是这种眼光和格局,使他的儒学研究别具一格。
时下,犹如其他任何一个学科一样,儒学研究也涌现出很多种形态,总的形式是“XX儒学”。有同仁说,张老师的儒学研究或可谓为“历史儒学”。张老师不置可否。在我看来,任何标签虽然具有提示作用,但何尝又不是一种束缚呢?不过,强调儒学研究者的历史修养至关重要。如果我们放宽历史的视野就会发现,早在“哲学”最初进入中国时,就有“哲学”与“历史”的纠纷。仅仅以章太炎先生为例。在太炎先生看来,“夫讲学而进入魔道,不如不讲。昔之讲阴阳五行,今乃有空谈之哲学,疑古之史学,皆魔道也。”“与国家有害者,哲学家是也。以哲学家之目光,施于政治,其害最巨。”章太炎先生的言论需要具体分析,但其对“哲学”的反思以及儒学研究与历史素养的关系值得今天的“中国哲学”的研究者反思。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和宏大的格局下,我们更能明白张老师所具有的深厚的历史素养之下的儒学研究的特殊价值和重要意义。
或许正是这样的史学修养,使张老师的儒学研究带有非常浓厚的史学色彩,从而给人一种踏实可靠、醍醐灌顶、恍然大悟的感觉。这一点,我深有感受。这几年,承蒙张老师的抬爱,每有人来访,我都有机会随侍左右。有一次,一位“大人物”来访。让周围的人大吃一惊的是,张老师没有一见面就谈抽象、高深的中国“哲学”、思想,而是从中国传统的山川大势、地理走向开始,谈中国古代的治国智慧,最后再进入抽象的思想。其中,每一个抽象的概念、思想都与历史的坎坷、肌理联系起来,盈科而进,曲折而行,具有了鲜活、灵动的生命。最后使这位大人物听得津津有味,乐而忘返。也有很多政界官员给我说,每次听张老师谈话,都敬佩于他对历史的清楚了解和对现实的深刻洞察,往往能提出令他们自己都感到意外的切实的建议。他们很是不解。其实在我看来,这很好理解。清末民初著名经学大师皮锡瑞就曾说过:教育应该培养这样的人,他们“兼通中西之学,于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皆了然于胸中,虽闭门读书,而已神游五洲、目营四海,不必识其器而能考其法,不必睹其物而已究其理。”
四、文之“雅驯”与中国学术的典雅表达今年四月底,著名学术期刊编辑田卫平先生来贵州讲学。其间,与张老师会晤于中国文化书院。在谈到中国学术论文的写作、表达问题时,田卫平先生认为“中华语词具有凝练、传神之美”,中国学者的学术写作应该充分借鉴、学习,发扬中国语言文字本身的特点,在追求准确之时,也使学术语言有一种动人的“美感”。我对田先生此言深有感触,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2024年著名期刊编辑田卫平编审访问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与张新民先生合影
在我看来,新民老师的文章或许正是田卫平先生所强调、所提倡的风格。所以在田先生讲此话时,脑海中马上浮现出张老师的文章。也因此,有一次与几位师友谈到张老师的为人为学。一位友人请我谈谈我的看法。我说,张老师的学问、思想姑且不论,在我看来,张老师作文之典雅或许为时下学界非常特殊而罕见的现象。
中国历来强调文章的修辞。《乾卦•文言》:“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左传》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从而强调“慎辞”。司马光在《史记•五帝本纪》的“太史公曰”中也言:“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强调“文”的“雅驯”。《文心雕龙》将之提升到“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文心雕龙•原道》)的高度。
这涉及到一个宏大的问题——中国学术的文字表达。作为一个独具一格、历史悠久、思想深邃的中国文明、思想,它的呈现形式也与之相应,表里如一,独具一格。如果一位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学者缺乏对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娴熟而贴切的掌握、运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表明他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理解是否准确、深入。因此,张新民先生独特的文字表达也就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其次,文字不仅关系达到思想的呈现,也是文字写作者人格修养的感性显现。“夫子继圣,独秀前哲,熔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性情,组织辞令,木铎起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文心雕龙·原道》)换言之,在对语言的锤炼之中,写作者自身的人格也得到锻炼。一种对符合中国思想的语言的娴熟运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恰好是将语言运用者自身置入中国思想之中,从而达到与中国思想浑然一体的状态。文字的表达具有范铸、陶冶写作者性情、行为的巨大作用。拒绝中国传统语言文字的表达,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意味着拒绝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教化功能和中国传统思想所开创的文明形态。

左三为张新民先生、左四为田卫平先生,右三为本文作者王进教授
张老师不仅是文字表达,而且为学的途径和思想的关切,都似乎使他自远于目前学术中心和流行形式。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张老师经常说自己远离中心而身处边缘的话。在我看来,如果这样的“中心”只不过是异域思想的异地呈现,那么这样的中心也远非中国文明、思想的中心。因此,张老师这样一种站在边缘对中心的眺望,或许反而能进入中国思想的核心。每一次,聆听张老师关于儒学的言论,都有一种深中中国儒学肯綮之感。张老师年轻时,曾经陪同乃父张振珮先生前往武汉参加张舜徽先生第一个博士生张三夕的博士论文答辩。每次听张新民老师谈论,我都不由自主地想起张舜徽先生(1911——1992)生前常讲的一句话,“吾离后人近,而离今人远。”否极泰来,一阳来复,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特别是“中国古典学”学科的建立,我相信,后来者一定会对张老师的作文风格、治学途径和思想关切感到亲切……
二十多年前,张老师从贵州师范大学调入贵州大学工作,主持中国文化书院的创建工作,是为中国高校第一个传统书院。当初在做清水江文书研究时,张老师深入清水江腹地贵州锦屏县文斗村考察。该村古木参天,600余株参天古树枝繁叶茂,默然伫立,不仅目睹了清水江的舟楫往来、渔歌唱晚,也见证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历程。时值深秋,村中的一棵千年银杏树老干虬枝,一片金黄。在众人都在仰头赞叹那金黄叶片时,谁也没有注意到,年过六旬的张老师默默低头捡拾那无人关注的果实,然后小心翼翼地怀揣回贵大,悄悄播在贵大中国文化书院北墙边。十年树木,历经沧桑、光耀千年的银杏树的一片金黄辉映校园,又闪耀在年青学子的眼眸之中……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参考了《〈寻城迹·贵阳市文化名人口述史:集众萤之火共亮——张新民口述史〉》《〈百年贵大口述史之张新民:寻找大学中的人文精神传统〉》《贵州方志人物访谈——张新民》《文化学者张新民:研究贵州是为了追求生命之真理》等相关文章,不再注明具体出处。特此说明,并感谢相关作者授权同意引用。作者王进系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