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科举盛而儒术微”[1],科举制度不仅影响了学术兴衰变化,也左右着科举中人的现实生活,甚或波及整个社会。自唐朝起因科举考试而形成的人际关系,即科举关系,发展至明清时期已空前完备并影响深广。

《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
在科举关系中,最基础也最重要的始终是师生关系和同年关系,因之而生的师恩年谊现实影响巨大,由此不仅得到了史笔记载,也激发了史外书写,《儒林外史》便是叙写士人师恩年谊的典范之作。
审视《儒林外史》中的师恩年谊关系,或可为探求吴敬梓用以实现小说空间转换、结构《儒林外史》的叙述动力提供一种有效路径;亦能对吴敬梓为儒林写外史所用书写方式和讽刺笔法的特殊性,略窥一斑。



“明制,科目为盛”[2],不仅继承了宋元时期形成的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考试体制,也在正统九年(1444)创设了科考。即明代科举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四个递升的考试层级[3],依次为科考、乡试、会试和殿试。
作为一种分层级的考试,科举考试中的科考、会试能否通过,分别决定着士子是否有资格参加乡试、殿试,也就是它们关涉士子的应试资格,而乡试和殿试则更直接地决定着士子在不同科举阶段的具体功名。除殿试外,其他各级科举考试皆会产生座主与门生关系。
乡试、会试历史最悠久,体制也相对完备,其座主门生关系因社会影响巨大而一直备受关注。明朝生员“一登科第,则有所谓主考官者,谓之座师;有所谓同考官者,谓之房师”[4]。
在乡试、会试中都有主考和同考,其主考官皆由二人担任,即在乡试和会试中被录取的考生与两位主考官都会形成门生与座师关系。但考生基本上只会将直接录取自己的同考官视为座主,奉之为房师,这种规则也适用于乡试考生对自己与同考官关系的界定。

《稀见明清科举文献十五种》
此外,因乡试和会试层级不同,又有了乡试座师和会试座师以及乡试房师和会试房师之分。
这些师生关系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它们直接关系着考生的科举功名,而明代科举考试竞争空前激烈,考生被录取的几率很小,如归有光虽“九岁能属文”[5],于“嘉靖十九年举乡试”却“八上春官不第”,在“四十四年始成进士”[6]。
座主与门生关系一旦确立,便会在士人求取科名的过程中持续发挥作用,譬如会试能否通过,决定着士子是否有资格参加殿试,所以乡试座主一般都会为门生积极延誉,以助推其会试中式,如马孟祯“万历二十五年举乡试,主考官叶向高奇之,为延誉,声名大振,明年成进士”[7]。可以说正是科名荣誉,推动着考中举人、进士的士子感激座师和房师的知遇之恩。
同时,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下诏,“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8],自此之后,科举功名便与士人的仕途遭际密切关联起来。

《明代科举史事编年考证》
这意味着士子通过科举考试而进入官场后,也会对拔取自己的座主心怀感恩,如万历二年(1574)状元孙继皋,在给其会试座师陈蕖的信中这样写道:“饮水则思源,依木则思荫;一冠一组,安所非老师赐也。”[9]
在明代的科举考试体系中,四级考试是紧密相联的整体,科考虽开设最晚,但也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着士子是否有资格参加乡试。自正统九年(1444)起,科考便是明代士子科名的起点,也是他们日后走仕途入官场的根本,所以被拔取的生员自然会对科考座主——主持各级科考的知县、知府,尤其提学心怀感激。
在科举社会中,同年关系与座主门生关系一样源远流长,由顾炎武提出的“今人以同举为同年”[10]可知,明清时期同年关系形成的唯一前提是在科举考试中同年登榜。
尽管因科举考试竞争激烈,士人考中的可能性很小,但他一旦登榜,便与榜上其他所有士子皆是同年,其数量也远超座师和房师的人数。科举不断发展,同年之义也随之丰富,所以“又有序先后同年者”[11],这更扩大了同年关系的覆盖面。
同年之间的情谊首先源于科考不易的现实,一同登科的考试结果不仅让士子自身得偿所愿,也让他们因经历相似而产生情感共鸣。同时,科举考试是分层级的,举人和进士都不是科举功名的最高点,一般情况下士人都会参加接下来的会试或殿试。
因此,他们不仅在考中后的同年会上,也会在为接下来的会试或殿试备考过程中,有意愿也有机会以文会友、互相切磋,这无疑会增进他们的同年情谊。也因自洪武三年(1370)起“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12],考中举人和进士的士子便能很自然地成为官场中的一份子,而他们的同年情谊也会随之延续到官场,转化为利益关系并发挥作用。

《明史》
在明代如果不是由科举出身进入仕途,缺少这种科举制度上的同年关系,便“自然在人际关系上要比科举出身者小得多”[13],而往往在仕途上难以显达,这便推动着科举中人更加珍视同年之谊。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古人素来重史——“善恶书于史书,毁誉流于千载”[14] ,进而形成了“史贵于文”的文学价值观。因此所有著书者的最高目标便是其作品被称为“史”,小说家亦莫能外。
那么,好为稗说且以稗说传的吴敬梓书写《儒林外史》是否也是出于史心呢?我们可以从吴敬梓的史学涵养和追求方面进行考察,以推求吴敬梓的创作初心。
身为“家声科第从来美”[15]的全椒吴氏后人,在“专储制举才”[16]的“父师训”影响下,吴敬梓虽秉承了父祖的“授书志”,一度奋发于制举,但其知识储备却不局限于八股制义,自幼博览群书的他具有相当完备的知识结构。

吴敬梓塑像
这也是吴敬梓颇为自诩之处,从其诗词中可窥知一二:“辛苦青箱业,传家只赐书”,“无聊爱坟籍,讵敢说书淫”[17]。
而在《移家赋》中,他更是坦言自己自少年时代起便养成了热爱读书、锻炼写作的良好习惯:“梓少有六甲之诵,长于四海之心”,“熏炉茗椀,藥臼霜砧,竟希酒圣,聊托书淫,旬锻季炼,月弄风吟”[18],极力宣扬自己不同于一般世家子弟的追求。
吴敬梓孜孜矻矻地“笙簧六艺,渔猎百家”[19],得益于此,在“千户之侯,百工之技,天不予梓也”[20]的情况下,他犹能骄傲地说“独文梓也”[21]。这绝非吴敬梓的自矜之辞,从亲友对他的评价中便可见出。
唐时琳在为《文木山房集》作序时称赞吴敬梓“研究六籍之文,发为光怪,俾后人收而宝之”[22],而唐时琳也正是由于深信吴敬梓学优才赡而荐举他参加博学鸿词科的;程晋芳因族伯祖丽山先生与吴敬梓有姻连,且族祖绵庄与吴敬梓为至契,而对吴敬梓的个人经历及治学追求十分了解:“绵庄好治经,先生晚年亦好治经”[23],他虽因吴敬梓以稗说传而深感遗憾,但仍对吴氏的学养给予了客观的定位,指出“其学尤精《文选》,诗赋援笔立成,夙构者莫之为胜”[24];吴敬梓广博的知识也曾得其堂兄吴檠激赏:“何物少年志卓荦,涉猎群经诸史函”[25],这与金榘对吴敬梓的描述若合符契:“见尔素衣入家塾,穿穴文史窥密函。不随群儿作嬉戏,屏居一室同僧庵。从兹便堕绮语障,吐丝自缚真如蚕”[26];宁楷与吴敬梓“交称密契”,曾言:“赠君方欲注《云笈七籤》,未果”[27],“赠君方著《史汉记疑》,未毕。[28]”可见,吴敬梓知识结构之全面是亲友公认的。
众人对吴敬梓才华的揄扬亦非虚誉,《移家赋》的用典情况便是明证。《移家赋》是吴敬梓用赋体写就的家族史和自叙传,因其高度重视,用力甚深,自然是彰显吴敬梓诗赋成就的代表作。

《吴敬梓集系年校注》
爬梳《移家赋》的用典情况便可对吴敬梓的知识结构有一个基本了解。“孝”是吴敬梓先人代代承传的家庭传统,从吴谦起吴氏一族便“讲孝友于家庭”,但“君子之泽,斩于五世”,面对今昔对比的巨大落差,吴敬梓满怀崇敬地追述其嗣父吴霖起[29]的孝行。
在这段叙述中,用典共计19处:其中源自“十三经”的有4处,源自“二十四史”的有8处,源自先秦诸子的有4处,源自汉唐著作的有3处。
综上可见吴敬梓知识面之广,而由12/19的比例可知吴敬梓经史功底了得,这是四位亲友评价皆曾论及之处,也是吴敬梓的毕生追求:“三十诸生成底用,赚虚名、浪说攻经史”[30],虽是失志抑郁之辞,仍可见其对经史尤为重视。程晋芳所谓吴敬梓“晚年亦好治经”是仅就其治经成果《文木山房诗说》而言的,事实上吴敬梓少治《毛诗》并终生治经。
这得益于全椒吴氏研治《诗经》的家庭传统:其高祖吴沛著有《诗经心解》,曾祖辈吴国鼎著有《诗经讲义》、吴国缙著有《诗韵正》。但如同其叔祖吴晟著有《洪范辩证》及《周易心解》一样,吴敬梓治经也不局限于《诗经》,而对儒家“十三经”皆有研读。

《吴敬梓诗传》,李汉秋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9年7月版。
此外,吴敬梓的治经范围还突破了儒家一家,他对道家经典《庄子》也颇为熟习,仅在《移家赋》中就六用其典[31]。与此相关,吴敬梓对道教典籍亦颇感兴趣,对《云笈七籤》尤为精熟,在《移家赋》中曾三用其典[32],与宁楷所言一致。
宁楷的自注不仅证实了吴敬梓治经范围之广,而且说明了吴敬梓于“史汉”用力甚深,在《移家赋》中吴敬梓就常用其文其典。
梳理《移家赋》的用典情况,不难发现吴敬梓所用史籍文典除源自“史汉”外,还包括《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新五代史》《宋史》《明史》等正史 ,18/24的比例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吴敬梓确曾潜心攻史。
吴敬梓还深谙《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先秦史书,在《移家赋》亦曾数用其典,兹不详述。
吴敬梓对《东观汉记》《九国志》也有所涉猎:“白衣尚书”即用东汉章帝时期人们对郑钧的称谓,而“彼钱癖与宝精”中的“宝精”正源自后蜀善相者对王处回的指称。
如果说吴敬梓治经有家庭传统的影响,那么攻史则与大环境有关。所谓的大环境既是指中国自古重史的文化传统,又是指吴敬梓所处的特殊时代。
第一个方面是共识,兹不赘述。第二个方面的影响是更为直接且有力的,更需关注。胡适先生指出“看我这篇年谱的人,可以看出吴敬梓的时代恰当康熙大师死尽而乾、嘉大师未起的过渡时期”[33],并再次胪列了学问、文学两方面逝去和未起大师的姓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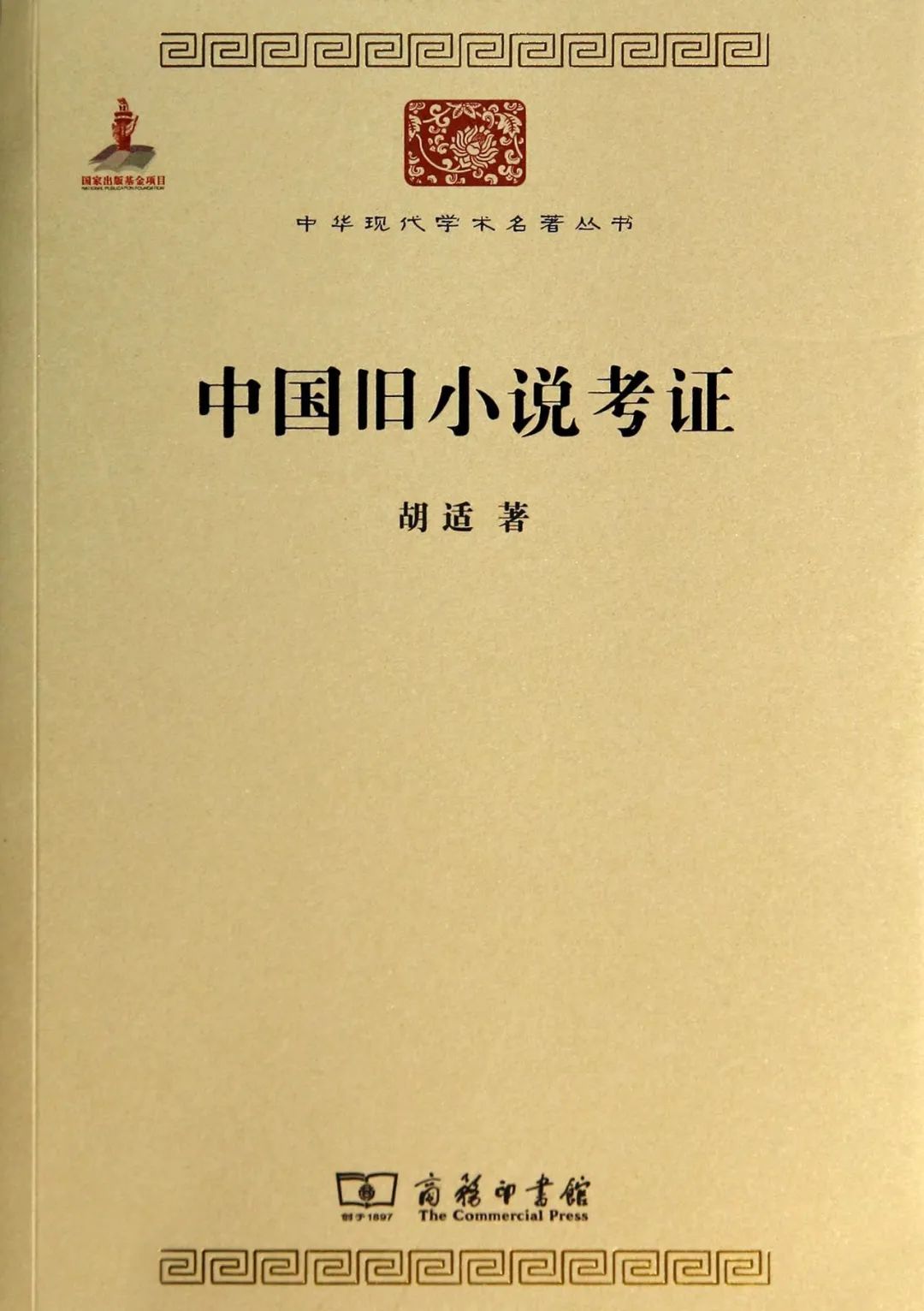
《中国旧小说考证》
笔者按照胡适先生的思路重读了其《吴敬梓年谱》一文,整理了相关史学家的生卒情况,发现当吴敬梓出生时,黄宗羲、顾炎武已去世多年,而其青少年时期,参与纂修《明史》的万斯同、尤侗、朱彝尊、毛奇龄等人在一七〇二至一七一六年间先后谢世,参与修纂《清统一志》的阎若璩也于一七〇四年逝世;史学家全祖望在吴敬梓五岁时才出生,而章学诚出生时吴敬梓已三十八岁了。
胡适先生所谓的“这个青黄不接的时代”[34]是就经学、史学和文学整体而言,单就史学而论其断档尤甚。明乎此,我们也便懂得了吴敬梓于史孜孜以求的动因,更理解了其以《外史》纪儒林的史心。
此外,从更为现实的角度考量,吴敬梓也会有意识地研读史书。清代科举考试除经学还涵盖史学,如乾隆元年的博学鸿词科考试便有《史论问》这一策题,此次考试吴敬梓虽止步于南京,但为了应试他事先当有准备。
当然,这种准备应是长期的,而非临时突击。这既是由史学本身的难度决定的,又与清代“科举考试大纲”的规定密不可分,乾隆元年曾明确规定乡试、会试策题必详引《通鉴纲目》中的事实和人物,叙述历代的制度沿革。

程十发绘吴敬梓像
吴敬梓历康雍乾三朝,于康熙五十九年中秀才,乾隆元年博学鸿词科后便不再参加乡试。仅从对修纂《明史》的态度看,便可知除晚年康熙秉持历史虚无主义外,三位皇帝整体上都重史,这自然对科举考试的内容有重要影响,而主要参加雍正朝乡试的吴敬梓为了博取功名自然会潜心攻史。概言之,主观追求和客观需要合力促使吴敬梓用心于史。



欲为儒林写“外史”的小说家吴敬梓,用“叙述一再告诉我们,舆论和人际网络的力量远远大于任何个人”[35],对生存在科举社会的儒林中人来说,师恩年谊在他们的人际关系网络里,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而这也正是吴敬梓用以实现小说人物空间转换、结构《儒林外史》的叙述动力之一。
明代“选举之法,大略有四:曰学校,曰科目,曰荐举,曰铨选。学校以教育之,科目以登进之”,而“科举必由学校”[36],可见科举制度与学校教育密切相关,其中存在着多重人际关系——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同年关系,而师生关系、同年关系在《儒林外史》第二回至第二十回前半回[37]中得到了充分应用,成为吴敬梓结构小说部分章回的隐性线索。
自唐朝实行科举考试起,“凡乡、会试同科取中者曰同年”[38],指在乡试、会试中同科登榜的考生之间形成的人际关系,这种科举关系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师生关系则需从两个角度考量,即教育和科举考试两个层面。

《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
就教育层面而言,具体可分为官学和私学。官学有二:曰国学,曰府、州、县学[39],私学主要是指乡镇塾馆。由此产生了两类师生关系,即学师与门生、业师与门生,而业师则包括蒙师与经师两种[40]。这两类师生关系在《儒林外史》前二十回中皆有表现,但并不多见。同时,它们虽有利于塑造人物性格,却难以独立支撑小说结构。
真正承担结构功能的是科举考试层面的师生关系。所谓“师”总分为两类:“亲受指示讲读者为受业师,入学及中举、中进士、复试、殿试、朝考阅卷者为受知师”[41],这意味着随着科举考试范围的扩大,科举关系中的师生关系也得到了延展。
“受知师”正源于科场知遇,即前述“座师”,而“座师门生之谊自唐而重”,至明朝“乡会坐主亦如之”[42]。受此影响又产生了一种“拜老师”的风气,“提调官与弟子员之间的关系,已渐渐被师生关系所取代。
生员对提调官,已不口称‘老大人’,而是称‘老师’”,“虽名为拜师,其意却不在送文请益,不过彼此谋利而已”[43]。

《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
正是座师、“老师”与门生的关系构成了科举考试层面的师生关系,而吴敬梓也是以此为线索来结构小说第二至第七回、第十六回至第二十回前半回的。同时,他综合运用同年关系和师生关系,辅之以亲缘关系、友朋关系,巧妙地连缀第八至第十五回中的人物和故事,使小说结构松而不散。
吴敬梓以科举社会中的师恩年谊为主要线索结构了第二回至第二十回前半回,具体又可以分为三个段落,即第二回至第七回、第八回至第十五回、第十六回至第二十回前半回,这主要是根据阶段性中心人物的不同而做出的人为划分,与作者以师生关系、同年关系为结构线索的本旨并不矛盾。
自正统九年(1444)起,科举考试体制共分为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四个递升的层级,其中为选拔人才参加乡试而创设的科考,属于制度范围内的资格考试。但只有生员,即秀才,方有资格参加科考。
明代“凡士子未入学,通称为‘童生’”[44],这意味着童生为获取秀才身份必须参加四级科举考试之外的另一种资格考试——童试,“即考核这些童生并选拔其中俊秀者入学的考试。”[45]
与科考相同,童试也包括县、府和提学院道三级考试,在这个过程中,童生对每一级让自己通过考试的考官都感激不尽,对最终将他录取为秀才的提学御史更是感恩戴德,奉之为宗师。
因此,南海、番禺两县童生考试时,将范进取为第一名、使之成为秀才的周学道便成了其“恩师”,也就是科举入学考试阶段的“受知师”、此前论及的“老师”:吴敬梓巧妙地运用了这种师生关系来结构小说的第二回至第七回。

《明代科举与明中期至清初通俗小说研究》
根据叶楚炎对《儒林外史》整个地域流动所做的统计,其第二回至第七回流动,如下所示[46]:
山东兖州府汶上县(周进)——山东济南府(周进)——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范进)——广东省肇庆府高要县(严监生、严贡生)——京师(范进)——山东兖州府汶上县(荀玫)——京师(荀玫、王惠)——江西南昌府(王惠)——
纳监使周进暮年登第成为可能,而故事以他“到京会试,又中了进士,殿在三甲,授了部属”[47]收束依然完整,但作者却又使其三年后“升了御史,钦点广东学道”[48],“广东”这个地点使得地域流动成为可能,也使二进之间的师生关系有产生的可能。
至此,完全可以用叶楚炎提出的地域流动视角来理解小说的结构。但是仅凭科举考试带来的地域流动并不足以解释第二回至第七回的整个流动,至少从周进拔取范进为秀才起,整个地域流动的内驱力就变成了科举社会中师生关系的交叠。
众所周知,吴敬梓惯用“伏案”法叙述小说情节,而由此入手亦可见出他是有意识地以师生关系的交错为线索来结构小说的:

儒林外史汇校汇评(典藏版)
第三回,周进临行前将范进叫到跟前说道:“我复命之后在京专候”[49],如果将这视为地域流动的伏笔未尝不可,但是第七回范进进京会试,周进对他说道:“况学生已把你的大名常在当道大老面前荐扬,人人都欲致之门下。你只在寓静坐,揣摩精熟。若有些须缺少费用,学生这里还可相帮”[50],而“会试已毕,范进果然中了进士”[51]。
我们必须注意到“果然”二字,它意味着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周进此前的“荐扬”,这也与范进的实际才学相吻合。
综上可见,范进由童生成为秀才得力于周进的拔取,而由举人成为进士亦有周进之功,所以他自言:“门生终身皆顶戴老师高厚栽培”[52],并且在视学山东时力报师恩。
这里有两处需要进一步解释,即范进中举及荀玫进学所涉及的师生关系问题:吴敬梓为展现科举制度对包括普通人在内的全社会的荼毒,在范进中举后放慢了叙事节奏,而严贡生和严监生的故事发生在高要县,范进身在南海县,在范进丁忧不能应考期间作者再次以师生关系为结构线索实现了这种地域流动——范进乡试时的房师汤奉是高要县县令,而汤奉正是乡绅张静斋先祖的门生。
如前文所述,所谓“房师”是座师的一种,座师中有乡试座师和会试座师之分,乡、会试中因有房考和主考,又各有房师和大座师之别。因去取权力都在房师手中,且相对于所有取中的考生都是门生的大座师来说,房师与其数量有限的门生之间的联系也会更紧密。
所以作为门生的范进去高要县问候乡试房师汤奉是合情合理的,因此张静斋力邀他一起去打秋风,使故事背景转换至高要县——这再次印证了吴敬梓是有意以师生关系为线索来建构小说的。

连环画《周进与范进》
与范进不同,荀玫进学是个人实力的展现,但荀玫这个人物身上交叠着两重师生关系——业师与门生、“老师”与门生。周进既是荀玫开蒙的师父,也是范进的“老师”。
范进由京师至山东的地域流动,是吴敬梓为其“报师恩”而精心设计的,这从两点可见:一是数年之后,钦点范进为山东学道,而“山东”正是周进的故乡,这使范进的报恩之举与地域流动得以结合;二是荀玫完全是凭借自己的能力得以进学,反倒是冒认周进为业师的梅玖得以免除责罚,由此可见这依然是周进与范进师生关系的延续、扩展。
至此,周进与荀玫之间蒙师与门生的关系与其跟范进之间“老师”与门生的关系实现了功能重合,而成为小说的结构线索。
综上所述,以周进为中心的两种师生关系,与以范进为中心的双重师生关系相互交叠,共同构成了第二回至第七回情节演进的线索,使其形成一个看似散漫实则紧密的结构。
王惠与荀玫一同中进士,对此第一个叙事段落起首便有伏案——王惠正月初一日“梦见看会试榜”,与他同榜的“第三名也是汶上人,叫做荀玫”[53],尾声再次突出了王惠作为荀玫同年的身份,而他恰巧也是第二个叙事段落的起点式人物,因而承担了衔接两个叙事段落的结构性功能。

《儒林外史》邮票首日封
第七回结尾荀老夫人去世,吴敬梓借此再次揭示了功名对人心的毒害之深,荀玫本人、荀玫的“同年”王惠、荀玫的两位老师周进、范进,无一例外地都愿为考选一事而尝试匿丧。但作者就此彻底放下周进、范进二人,以后他们只是别人偶尔提及的“符号”,同时借丁忧一事暂时搁置荀玫。如此一来,王惠便成了衔接两个叙事段落的关键人物。根据叶楚炎的统计,这一段地域流动如下所示[54]:
江西南昌府(王惠)——浙江湖州府乌镇(王惠)——浙江嘉兴府(蘧公孙)——浙江湖州府(娄家二公子)——浙江湖州府德清县新市镇(杨执中)——浙江湖州府(蘧公孙、鲁小姐)——浙江绍兴府萧山县(权勿用)——浙江湖州府(娄家二公子)——浙江嘉兴府(马二先生)——浙江杭州府(马二先生)——浙江杭州府(匡超人)
其中,首尾两端为笔者所加(原本分属叙事段落一、三),用以强调王惠及匡超人在段落衔接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可以说吴敬梓充分发掘了王惠这个人物的作用,借他的宦途遭际使故事发生地进入浙江,并且通过他引入蘧公孙这个人物。
当蘧公孙进入叙事视野后,便发挥了贯索作用,先是引入了娄府两位公子,因两家的亲缘关系使得这一操作并无难度。此后吴敬梓先后展开了对娄府两位公子与杨执中、权勿用相与全程的叙述,并设立了“名士大宴莺脰湖”一节,在将名士风范推向高潮的同时也使得全书的叙事节奏呈现出消歇状态。

《儒林外史》戴乃迭英译本
其实这种消歇只是表面现象,因为以“举业”为核心而形成的师生关系一直在暗中推进情节的发展。这与蘧公孙的婚姻也是密不可分的,其岳父鲁编修正是娄府“先太保做会试总裁取中的”[55],可见鲁编修与已故娄太保之间正是门生与座师的关系,这使蘧公孙有机会可以富室招亲。
据陈和甫所言:鲁老先生在娄府“会见南昌蘧太爷的公孙,着实爱他的才华”[56],结合日后鲁编修和鲁小姐对蘧公孙的失望,可知所谓“才华”不仅包括诗才[57],更有八股之才。父女二人臆想出身于科举世家的蘧公孙“举业已成,不日就是举人、进士”[58],而后者则是鲁编修招赘蘧公孙的深层动因。
当鲁编修、蘧太守先后谢世,娄府两位公子闭门谢客后,转而求贤问举业的贯索人物蘧公孙在嘉兴,遇到了八股文选家马二先生。这既引发了相应的情节演进,也借其“性命之交”[59]马二先生“要往杭州”[60],推动小说的叙事转向杭州。

邮票《马二先生游西湖》
在后文的论述中,我们会发现第三个叙事段落是以师生关系为线索建构的,而其核心人物则是匡超人。换言之,第二、三两个叙事段落的连接点是匡超人这个人物,而这种连接得以形成的前提正是马二先生在杭州选文时与匡超人相遇,并对他进行举业宣讲。
由此可见,蘧公孙、马二先生、匡超人之间,虽然皆不存在科举关系中的师生关系、同年关系,但他们的交际却在这一部分叙事中不可或缺,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绾结而言,正是凭借对“师恩年谊”这一科举关系和亲缘关系、友朋关系的综合运用,作者成功地使第二个叙事段落的地域流动得以实现,使小说内部形成了完整严密的结构,也为第三个叙事段落预留了伏笔。
在明代,成为秀才“是科名的起始,入仕发达的根本”[61],吴敬梓深谙于此,所以在他的书写里,八股文选家马二先生语重心长地对匡超人说“你如今回去,奉事父母,总以文章举业为主”,“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62]。这正是作者预留的伏笔。
第十六回匡超人在事亲之余便读起了文章,且适逢童生考试,由此建立了与李知县的师生关系:李知县不仅在自己负责的县考中将匡超人取为第一名,资助其府考、院考的盘费,而且为他在学道前下了一跪,大加揄扬[63],而学道果然将其取中乐清县第一名入泮[64]。
在匡超人由童生变成秀才的过程中,最终的决策权虽在学道手中,但李知县却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匡超人送过宗师,忙了几日后主动进城去谢知县,并拜他为“老师”。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朝廷制下的学里老师派人传匡超人去见,他却百般不愿[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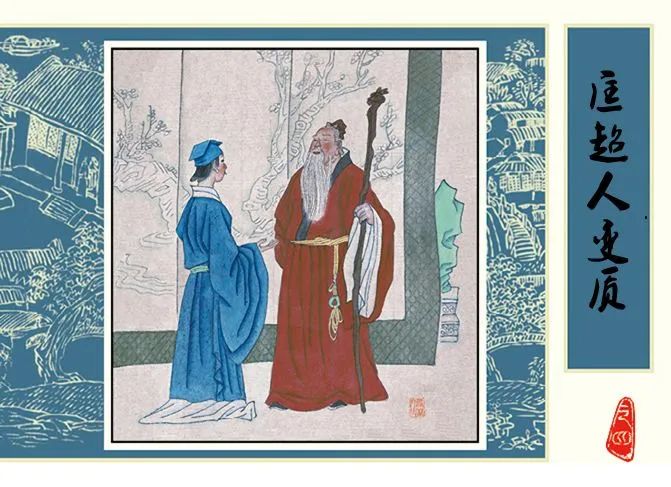
连环画《匡超人变质》
其中依次涉及科举社会中的三种师生关系:门生与“老师”、门生与座师、门生与学师,而在匡超人博取科名的轨迹中其重要性也是相应递减的,且第一种师生关系贯穿始终,因此成为这一部分的结构主线。
匡超人成为秀才后其行踪如下:
浙江温州府乐清县——杭州府——绍兴府——杭州府——温州府——杭州府——京师——杭州府——京师
其初始流动,即由乐清县前往杭州府,正是他与李知县之间的师生关系使然,“县里老爷坏了”,而据潘保正说:“衙门里有两个没良心的差人”,把匡超人也密报了,说老爷待他甚好,也一定在内为头要保留。[66]
匡超人为避祸事而前往杭州,不仅做了八股文选家,而且还相与了以赵雪斋为首的杭城名士,并往来不绝,而作者为此用了近三回的笔墨。
但吴敬梓用意在科举,所以他借匡超人代考一事使叙事重新回到科举轨道上来,也便有了杭州府——绍兴府——杭州府这一段地域流动。但从科举情节的演进来看,以上皆可视为匡超人科名道路的“停滞”。

庐剧《匡超人》剧照
续起匡超人科名之路并推动情节发展的依然是李知县与匡超人的师生关系:李老师“因被参发审,审的参款都是虚情,依旧复任。未及数月,行取进京,受了给事中”,并寄书来约门生匡超人进京,“要照看他”[67]。
但我们注意到匡超人并没有直接进京,而中间又出现了杭州府——温州府——杭州府这一段地域流动,这是由于宗师按临温州,匡超人回去应岁考。此次岁考的意义不仅有引发地域流动,还通过考试的结果为后文伏案:“考过,宗师着实赞赏,取在一等第一;又把他题了优行,贡入太学肄业”[68]。其意义在于使他具备考取教习的资格。
可见,匡超人与宗师的师生关系在此亦是不可替代的线索。但它的作用只是局部性的,而贯穿始终的主线依然是李知县与匡超人之间的师生关系,原因有二:
一是在应考前,匡超人已经给李知县回信,表示“不日整理行装,即来趋教”[69],由此看来他是一定会入京的;二是岁考使匡超人“补了廪,以优行贡入太学”[70]。
优贡在保和殿朝考后,“钦派阅卷大臣评定甲乙,取列一二等者以知县、教职二项录用,三等者就训导选用,由吏部带领引见,知县分发各省,教职交部铨选”[71],但并不是所有优贡都能考中,而时任给谏的“老师”在考前却对匡超人说:“贤契,目今朝廷考取教习,学生料理,包管贤契可以取中”[72],因此匡超人顺利地考取了教习。
此外,考取教习需要回本省地方取结,所以便产生了匡超人故事的最后一段地域流动,即京师——杭州府——京师,亦可溯源至李给谏与匡超人的师生关系。

连环画《匡秀才》
至此,不难发现,匡超人与李本瑛之间的门生与“老师”关系一直左右着他的科名之路,同时也相应地影响着他的行迹变换。就群体而言,是科举制度本身左右着科举中人的功名利禄和行迹,但对匡超人个人而言,李本瑛与他的师生关系却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综上所述,匡超人身上汇集了三种师生关系:李本瑛与匡超人的师生关系是贯穿第三个叙事段落的结构主线;温州新任学道与匡超人的师生关系在其入学、优贡时亦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因而具有结构伏线的意义;学师与匡超人的师生关系主要是为了表现匡超人的势利以及学师备受冷落的社会现实,不承担任何结构功能。



《儒林外史》“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而其人之性情心术,一一活现纸上”[73]。审视匡超人在进学后对宗师、知县与学师的不同态度,便能窥见科举功名对士人品性的影响,亦可体悟吴敬梓对师恩意义的现实续写,而这与小说“结构”在实质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电视剧《儒林外史》中宗峰岩饰演匡超人
匡超人考完童试院考,被“提学御史学道大老爷取中乐清县第一名入泮”[74],便与其形成了科举考试中的师生关系,所以“直到四五日后,匡超人送过宗师,才回家来。”[75]
小说客观叙述了匡超人恭送宗师的行为,表现了他对宗师的感激,揭示出其追求功名富贵的心思。其后,匡超人到家“忙过几日”,“又进城去谢知县”,并按对方要求拜之为“老师”[76]。
通过文字表面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师生关系是从科举考试中的“座师”“宗师”与“门生”的关系演化而来的。事实上,知县李本瑛只是在主持童试县级考试时,将匡超人“取了第一名案首”[77],而他们之间的关系与科举制度并不相关。
李本瑛的提议符合明代通行的“拜老师”风气,老师是为培植自己的羽翼,而学生则是求庇护、谋利益,是现实利益推动他们建立起师生关系。不难发现,匡超人对童试中有助于自己进学的主考官是非常重视的,他一直是积极主动的拜谢者、顺从者。
但听到“学里老爷”要传他去见,“还要进见之礼”[78],匡超人却恼了,并说“我只认得我的老师!他这教官,我去见他做甚么?有甚么进见之礼?”[79]
由此可见,匡超人对科举教育层面的师生关系的漠视,而他正是典型的“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彼时在旁相陪的潘老爹则劝道:“你不可这样说了!我们县里老爷虽是老师,是你拜的老师,这是私情;这学里的老师是朝廷制下的,专管秀才。你就中了状元,这老师也是要去认的。”[80]
也就是吴敬梓借小说人物潘老爹之口,自然而然地说出了从明代科举制度出发,知县与匡超人的师生关系是有名无实的。

漫画《匡超人》
相应的,在匡超人的心里和口中,学里老师与他的师生关系虽有制度支撑,却是有实无名的。其后到约定日,匡超人按照潘老爹的建议给“每位封两钱银子”做进见礼,“去见了学师回来”[81]。
在这个过程中,作者对匡超人待宗师、“老师”和学师的态度始终不予置评,仅用“送”“谢”“见”三字便昭示出科举功名对士人品行的真切影响,也彰显了《儒林外史》“虽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82]的讽刺特色。
如前文所述,吴敬梓继续利用匡超人与知县李本瑛的门生与“老师”关系,驱遣匡超人行动,借其轨迹牵引小说叙事空间由浙江温州府乐清县转换至杭州府,并结合匡超人与温州学道在科举考试中形成的师生关系,合力推动小说叙事不仅在杭州府和温州府之间流转,也延展至京师,进一步促成了《儒林外史》叙述空间的大范围更迭,这正是吴敬梓以科举社会的师恩关系结构小说的必然成果。
众所周知,《儒林外史》的空间转换是异常频繁复杂的,甚至堪称中国古典小说之最。但并非无迹可寻,理顺其地域流动的关键在于掌握小说人物之间的关系,因为吴敬梓正是通过对人际关系网络的灵活编织和使用,才得以自如驱遣人物流动,有条不紊地推动叙事演进,进而使《儒林外史》呈现出与其他小说迥然有别的结构样貌。

《李汉秋讲儒林》
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是其社会性,所以人自然处于诸多社会关系之中。故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吴敬梓不是单独使用某一类型的人际关系作为叙述动力,而是综合利用多种关系的合力推进叙事演进。
在本文讨论范围内,即《儒林外史》第二回至第二十回前半回,吴敬梓所用的人际关系包括师生关系、同年关系、亲缘关系和友朋关系,这一叙事段落的空间转换和情节发展主要是依靠师恩年谊关系来推动实现的,而师生关系和同年关系同属于科举关系。
吴敬梓对师生关系的使用是受正史《儒林传》启发的结果,正史《儒林传》的结构线索便是师生关系,但吴敬梓又不为正史《儒林传》的体例所拘,因为二者所用的师生关系有着质的区别:正史《儒林传》中的师生关系源于学术传承,而《儒林外史》中的师生关系与学术传承毫无关联,却与科举考试密不可分。
此外,正史《儒林传》中不同的师生关系之间大多彼此独立,而史传叙述中也缺乏相应的过渡,但吴敬梓利用科举制度衍生出的同年关系及有所异变的师生关系巧妙地消弭了这一分隔,叙述也因此顺理成章。
可见,吴敬梓创作小说,不仅以儒林中人身上所负载的其他社会关系的合力作为叙述动力,用正史《儒林传》之所未用;在以科举关系为小说叙述动力时,也会根据明代科举的具体情况而有诸多改造,发《明史•儒林传》之所未发。

《儒林外史资料汇编》
总而言之,吴敬梓创变小说叙述动力的意义不仅在于实现了小说人物大范围、高频率的空间转换,使小说结构呈现出一时难以辨认的状貌,还在于创立了一种不同于《明史•儒林传》甚至全部正史《儒林传》的书写方式。
注释:
[1](清)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222页。
[2](清)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75页。
[3]科举考试包括乡试、会试、殿试三级是学界基本共识,但考虑到“科考”创设后在明代中后期科举考试中的实际影响,洪武二年创设的庶吉士之选,自永乐二年起考选与否不定,所以本文批判地吸收了郭培贵《关于明代科举研究中几个流行观点的商榷》(《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一文的合理成分。
[4](清)顾炎武撰,华忱之点校:《顾亭林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3页。
[5](清)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382页。
[6](清)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383页。
[7](清)陈鼎撰:《东林列传》,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8册第428页。
[8](清)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95-1696页。
[9](清)孙继皋:《宗伯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1册第334页。
[10](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全校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000页。
[11](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全校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001页。
[12](清)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96页。
[13]林丽月:《明代的国子监生》,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95页。
[14](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304页。
[15](清)吴敬梓著,李汉秋、项东升校注:《吴敬梓集系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62页。
[16](清)吴敬梓著,李汉秋、项东升校注:《吴敬梓集系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622页。
[17](清)吴敬梓著,李汉秋、项东升校注:《吴敬梓集系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10页。
[18](清)吴敬梓著,李汉秋、项东升校注:《吴敬梓集系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7页。
[19](清)吴敬梓著,李汉秋、项东升校注:《吴敬梓集系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页。
[20](清)吴敬梓著,李汉秋、项东升校注:《吴敬梓集系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页。
[21](清)吴敬梓著,李汉秋、项东升校注:《吴敬梓集系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页。
[22](清)吴敬梓著,李汉秋、项东升校注:《吴敬梓集系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612页。
[23](清)吴敬梓著,李汉秋、项东升校注:《吴敬梓集系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66页。
[24](清)吴敬梓著,李汉秋、项东升校注:《吴敬梓集系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66页。
[25](清)吴敬梓著,李汉秋、项东升校注:《吴敬梓集系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18页。
[26](清)吴敬梓著,李汉秋、项东升校注:《吴敬梓集系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24页。
[27](清)吴敬梓著,李汉秋、项东升校注:《吴敬梓集系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11页。
[28](清)吴敬梓著,李汉秋、项东升校注:《吴敬梓集系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19页。
[29]吴霖起是否为吴敬梓嗣父尚有争议,胡适认为吴霖起是吴敬梓生父而非嗣父,孟醒仁、陈美林则认为吴霖起是吴敬梓嗣父而非生父,分别见胡适著,李小龙编:《中国旧小说考证》,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年,第419 页;孟醒仁著:《吴敬梓年谱》,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至9页;陈美林著:《吴敬梓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64页,笔者倾向于后出观点。
[30](清)吴敬梓著,李汉秋、项东升校注:《吴敬梓集系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62页。
[31]分别见《移家赋》注44、111、184、239(两处)、300,(清)吴敬梓著,李汉秋、项东升校注:《吴敬梓集系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8、31、47、59、70页。
[32]分别见《移家赋》注38、112、130,(清)吴敬梓著,李汉秋、项东升校注:《吴敬梓集系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7、31、36页。
[33]胡适著,李小龙编:《中国旧小说考证》,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435页。
[34]胡适著,李小龙编:《中国旧小说考证》,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436页。
[35]商伟著,严蓓雯译:《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184页。
[36](清)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75页。
[37]《儒林外史》现存的最早版本是嘉庆八年(1803)刊刻的卧闲草堂本,共五十六回。《儒林外史》的原貌问题因程晋芳“又仿唐人小说为《儒林外史》五十卷”一语而颇受关注,历来聚讼纷纭:鲁迅等先生认为《儒林外史》原书为五十五回,胡适、吴组缃、章培恒、叶楚炎、耿传友等学者持吴敬梓原作为“五十回”说,赵景深、房日晰、陈美林、商伟、郑志良、李鹏飞等学人则持“五十六回”说。争论者各持己见,至今莫衷一是。本文分析的取样是基于笔者所认为的不可能有争议的部分,那些有争议的、笔者认为有争议的都不作为样本来采用。此外,因第一回为隐括全书而独立的楔子,故不予论述。综上所述,本文以《儒林外史》第二回至第二十回为具体分析对象。
[38]商衍鎏著,商志馥校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16页。
[39](清)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75页。
[40]叶楚炎:《明代科举与明中期至清初通俗小说研究》,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437页。
[41]商衍鎏著,商志馥校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14页。
[42](明)沈德符撰,杨万里校点:《万历野获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16页。
[43]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43页。
[44]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22页。
[45]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22-223页。
[46]叶楚炎:《地域叙事视角下的<儒林外史>结构——兼论<儒林外史>的原貌问题》,《明清小说研究》2013年第1期。
[47](清)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4页。
[48](清)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4页。
[49](清)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6页。
[50](清)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91-92页。
[51](清)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92页。
[52](清)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92页。
[53](清)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7页。
[54]叶楚炎:《地域叙事视角下的<儒林外史>结构——兼论<儒林外史>的原貌问题》,《明清小说研究》2013年第1期。
[55](清)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31页。
[56](清)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35页。
[57]鲁编修认可的蘧公孙的才华是否真的包括诗才,尚有讨论空间。从二人初次会面的场景推测应该包括诗才,但黄小田认为鲁编修“非爱其诗才,大约以貌取人,谓必可中了去”亦不无道理。
[58](清)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42页。
[59](清)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73页。
[60](清)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84页。
[61]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67页。
[62](清)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00页。
[63]参见(清)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13页。
[64]参见(清)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17页。
[65]参见(清)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17-218页。
[66]参见(清)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19页。
[67](清)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47页。
[68](清)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47页。
[69](清)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47页。
[70](清)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52页。
[71]商衍鎏著,商志馥校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40页。
[72](清)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52页。
[73](清)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87页。
[74](清)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17页。
[75](清)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17页。
[76](清)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17页。
[77](清)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13页。
[78]参见(清)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18页。
[79](清)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18页。
[80](清)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18页。
[81]参见(清)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18页。
[8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5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