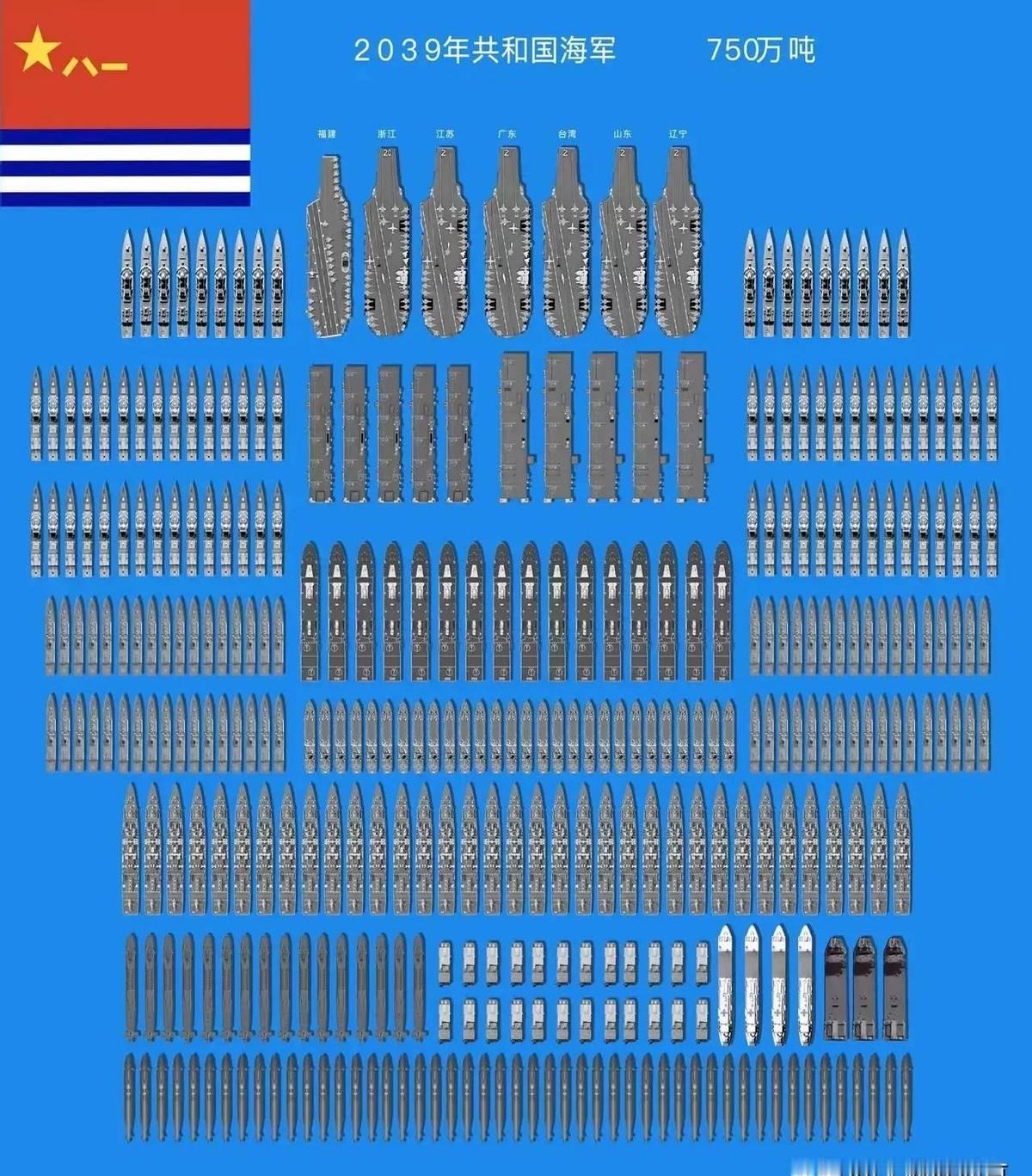"老王,你小子运气真好,提干这事儿有戏啊!"我还没来得及高兴,排长刘铁军就把那封信重重地拍在桌上,脸色铁青得跟锅底似的。
1976年的春天,北方军营的早晨冷得钻心。操场上的积水结了薄冰,踩上去咯吱作响。远处的山峦在晨雾中时隐时现,像是被蒙上了一层灰纱。
我正带着全排练俯卧撑,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混着细雨打湿了领口。
"一二三四!"我扯着嗓子喊着,浑身的肌肉都在发颤。身旁的战友们你看看我,我瞅瞅你,眼里都带着笑意:"王建军,等你当了军官,可别忘了咱们这帮糙老爷们啊!"
这话让我想起了老家那个小山村。土坯房的墙角长着青苔,泥巴路上总有鸡鸭在晃悠。爹是个木匠,整天扛着工具箱在村里转悠,帮人修修补补,挣的钱勉强够家里开销。
妈的病一年比一年重,吃药打针的钱像流水一样往外淌。每次我放学回家,都能看见妈躺在炕上,脸色发黄,咳嗽得直不起腰。
要不是姐姐王秀兰去纺织厂打工,我连高中都念不起。记得姐姐第一天上班,手都磨出了血泡,可她硬是咬牙坚持下来。每个月发工资,她都给我留出学费,自己就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裳。
李秀芳家在村口,她爹是小学老师,家境比我们好些。小时候,我俩总一块儿放牛,她坐在草垛上,给我讲课本里的故事。
那会儿她就说:"等我当了老师,你当了军官,咱们的日子一定美。"谁知道现在,就因为这军官的事儿,闹出这么大动静。

那天早操回来,我正用毛巾擦汗,排长就把我叫进了办公室。那封信摆在桌上,纸都被捏皱了。"建军,你自己看看!"排长的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信是李秀芳写的,说我家庭成分有问题,怕影响部队声誉。我脑袋"嗡"的一声,手脚都凉了。入伍时家庭情况都摸得清清楚楚,咋会有问题?
晚上,战友们围着我,七嘴八舌地议论。李德福神神秘秘地说:"听说是村里那个叫张月的知青,整天在秀芳耳边说闲话,说当了军官的男人准变心。"
想起前几天,机关来人说要推荐我提干。战友们乐得跟过年似的,给我开了个庆功会。老张拿出半个月的津贴买了汽水,李德福掏出珍藏的花生米,连平时不大说话的小刘都笑得合不拢嘴。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起姐姐为了供我上学,手都磨出了厚厚的茧子。想起李秀芳在草垛上给我讲故事时的笑脸,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
对面床铺的老赵扔给我一支烟:"别愁了,连长说了,给你做主。"黑暗中,香烟的火星一明一暗,就像我那会儿起伏不定的心情。
张德明连长雷厉风行,第二天就去了我们村。他走访了村支书,找到了那个知青,又去了李秀芳家。回来时,他表情缓和了许多:"建军啊,我都打听清楚了。你家里清清白白,秀芳也是个好姑娘,就是让人说动了心。"
没过几天,李秀芳来了部队。她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站在营院的白杨树下直抹眼泪。远远看去,她还是那个坐在草垛上给我讲故事的小姑娘,只是眼睛里多了分愁苦。

"建军,对不起,我太傻了。"她掏出一封检讨信,声音哽咽,"那个知青总跟我说,提干后的军官都会变心。我一害怕,就......"
她说着说着就哭了,泪珠子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掉。想起小时候,每次我被人欺负,她都会挡在我前面,红着脸替我说话。
排长听完前因后果,拍着桌子说:"感情要讲究个真心实意。建军这孩子,我看得准,实在得很。"
连长也笑了:"秀芳啊,你也别自责。这事反倒证明你们感情深厚。年轻人嘛,难免冲动。"
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年底,我顺利提了干。李秀芳特意从家乡带来了她亲手织的毛衣,说是要给我当新年礼物。她织毛衣时,手上的针扎出了好多小洞,可她愣是一声没吭。
战友们看到毛衣,都起哄:"嫂子好手艺啊,啥时候请我们喝喜酒?"李秀芳的脸一下子红了,低着头不说话。
临走那天,我送李秀芳到车站。她掏出一张泛黄的照片,是我俩小时候在晒场上的合影。照片上的我们都黑瘦黑瘦的,笑得傻乎乎的,身后是一片金黄的稻谷。
"建军,咱们都长大了。"她说这话时,眼里闪着泪光。我知道,她是在为自己的冲动道歉,也是在表达对我的信任。
火车的汽笛声远远传来,站台上的人群开始骚动。我帮她提起行李,看着她瘦小的身影消失在车厢里。心里突然明白,这份感情,经过风雨的洗礼反而更加坚固。

多年后再回想起来,那封举报信反倒成了考验我们感情的一块试金石。前几天,老连长张德明都当上团长了。他常说:"军营就是咱的家,战友就是咱的亲人。只要心里装着真情实意,啥事都过得去。"
那年的白杨树早已长成大树,树皮上的沟壑像是岁月留下的痕迹。可那份真挚的感情,和战友们的情谊,我一直都记在心里,就像那张泛黄的老照片,永远定格在记忆深处。
有时站在军营的操场上,看着新一茬的小战士们训练,我就会想起那个春天。想起战友们的关心,连长的明理,还有李秀芳的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那时的我们,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