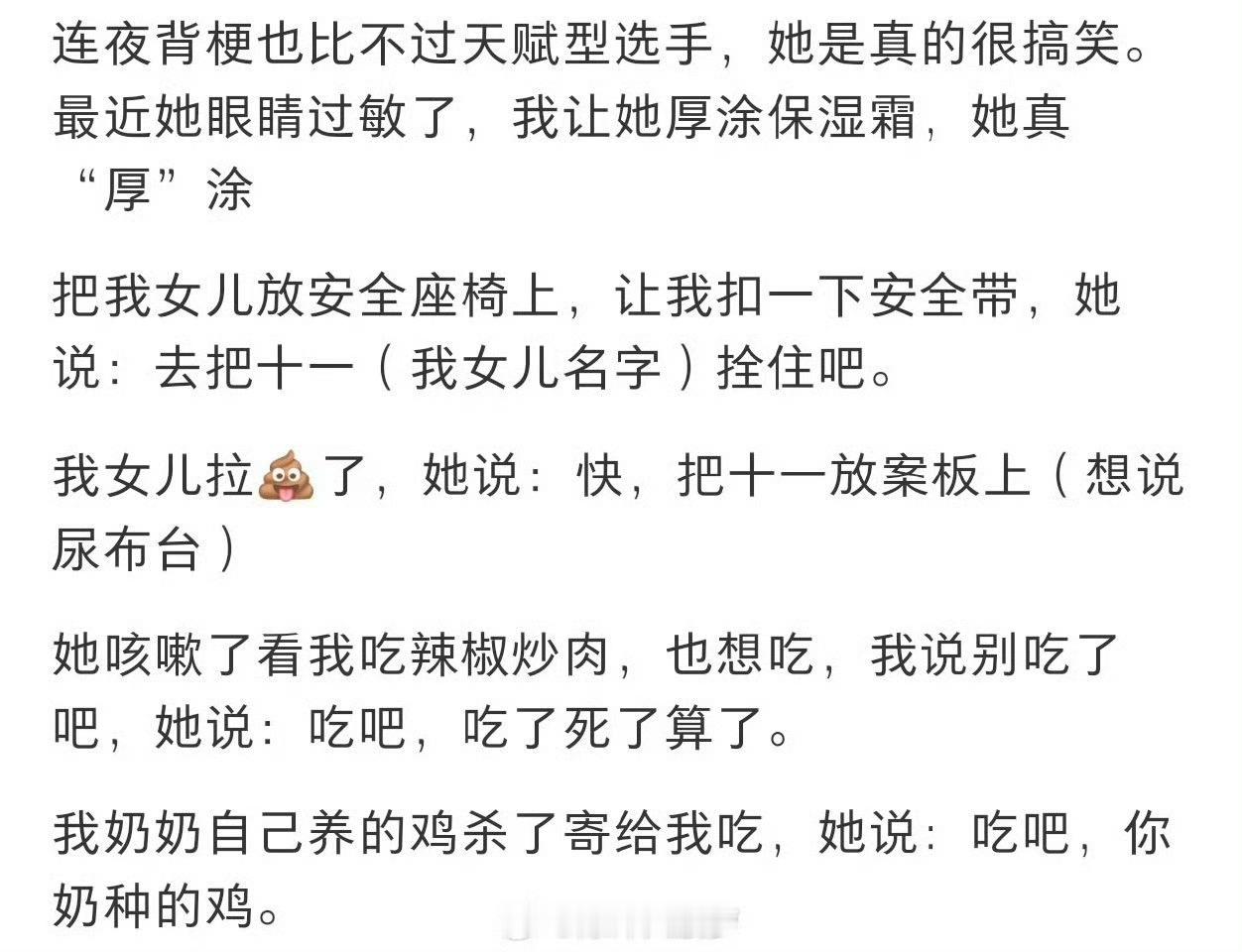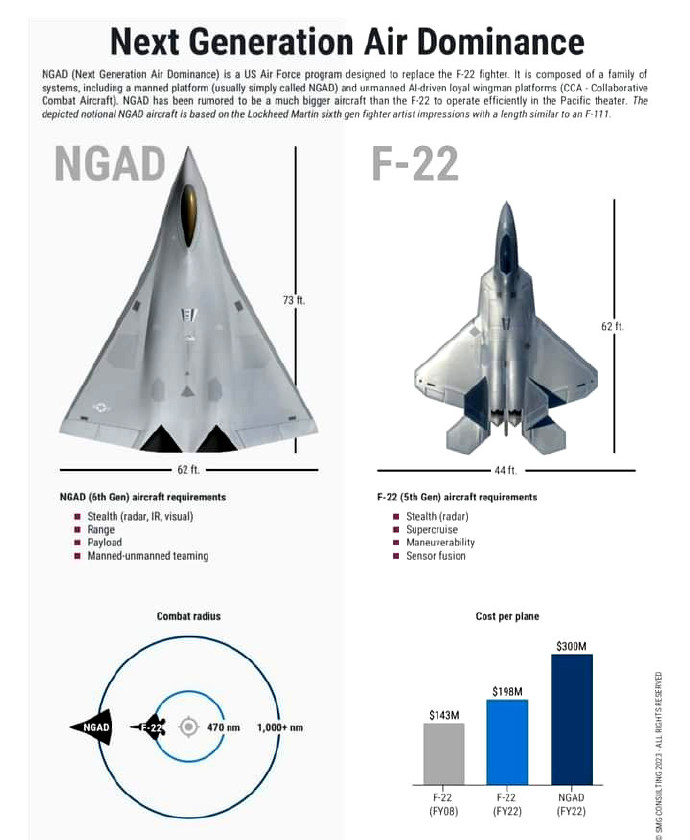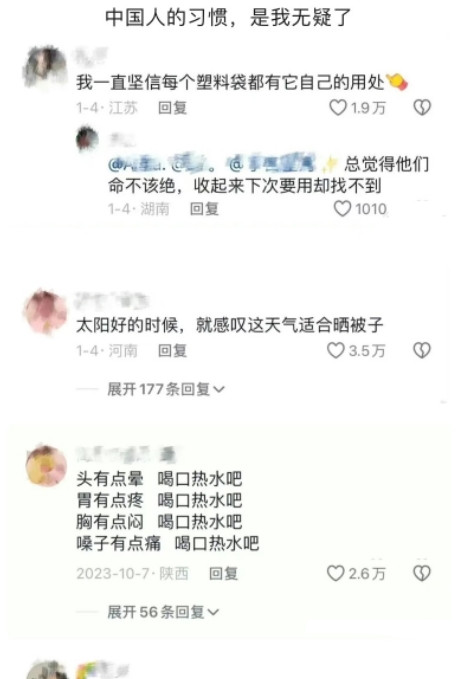口述人 吕清林
1980年我高中毕业后就毅然报名参军入伍。拿到入伍通知书后,我们这一批新兵便来到了陕西省的铜川市。紧张严肃的新兵训练结束后,我们便全部被分到了连队。我有幸来到那了211团的一营三连三排七班当了一名机枪手。

由于我在部队刻苦努力,踏实肯干,时时事事都高标准严格,因此两年后,我不但光荣入党,而且还被提拔为三排七班的班长。当时我们排的排长叫柳长明,与我关系特别好,听说他父母都是大领导,知道的小道消息也特别多,1982年的元旦见过,他就告诉我,部队可能有行动。
果然那几个月我们连队的干部调动非常频繁。连长调走了,指导员也调走了。并且我们连队还从其它部队补充了许多新战士。就连空缺了好几个月的副连长也补上了。
那是一个星期日,柳长明拿着一瓶酒拉着我的胳膊说:“走,咱们出去喝点。”部队明文禁止喝酒,当然很多同乡好友偷偷的在外边喝点酒,也并非没有。只要不过分,领导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作为干部的柳排长,今天突然邀请我喝酒,我还是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柳长明可不管我吃惊不吃惊,他拉着我的胳膊就把我拉出了营区,我们在一条河边坐了来。柳长明拿出早就准备好的一个缸子,倒出一半洒递到我的面前:“清林,咱们今天可能是最后一次在一块喝酒,告诉你,母亲正在为我办理调动手续,不出意外的话,最近几天就有了结果。”
我不解的问:“你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调走,这提拔,你恐怕还没到年限吧。”
柳长明拍了拍我的肩膀:“你是真傻吗,还是装傻,部队要上前线,我前边不是给你透露过消息吗?”
我苦笑了一下:“上级没有宣布作战命令,小道消息满天飞,我该相信谁呀?”
柳长明喝完瓶子里的
酒,然后叹了口气说:“其实我根本不想调动,你想,大家都上了前线,而我却悄无声息地办了调动,这不是软蛋懦夫吗,以后我还有脸在部队待下去吗?”
我说:“你既这样想,那为什么还要办调动?”
柳长明无奈地说:“我妈非要办,我也拦不住,今天她才打电话告诉我的。我和她吵了半天,她竟然要一意孤行。”
我们喝过酒一个多礼拜后很多人都在背地里悄悄地议论部队要上前线的消息。军人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前线与否也不是战士能左右的,心态端正,该干什么,还是照样干什么。
不过柳长明的调动却没有办成。部队已经宣布了命令:探亲的,调动的,如果没有离开部队,现在一律停止离队,分别在原单位参加战前准备。至此部队上前线的消息才正式被公开化。
接下来的时间部队就进入了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检查、配齐武器弹药,擦拭枪枝,保养火炮和汽车。
柳长明问我怕不怕,我很坦然回答他,怕有用吗,别人都不怕,我怕什么。当然说不怕那完全是假的,我一个人睡在床上常常在想,一颗子弹打在头上,悄无声息地送你去了另一个世界,也没什么。但是如果丢了一条腿,或者一条胳膊,那这一生就完了。虽然国家可以保证吃喝不愁,但那份折磨,那份痛苦无论如何是别人无法替代的。想着想着就浑身发抖,偷偷地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又过了一个礼拜,上级下达了作战命令。三天的战前动员,从团长到连长一个一个都作了长篇大论的动员报告。决心书,请战书,一封接一封地飞到连部,特别感人的请战书还贴在了连部的大门两边。

接下来上级又宣布了战场纪律,一大堆的不准,我也没听清,反正跟着大伙的脚步走,又不当想当逃兵,那一大堆的战场纪律好像与我关系也不大。
出发的那一天,师首长来到营区,与上车的战士一一握手,场面肃穆而又悲壮。
下午2时整部队正式出发,经过宝鸡、汉中、广元、宜宾、昭通最后到达昆明。在昆明休整了三天,战士们洗澡理发,然后领取弹药帐篷等军用物资,以及压缩饼干和罐头之类的生活用品。
部队休整了三天后继续向南开进,有一个服役四年多的四川老司机竟然能在大白天把卡车开下路基。车上的战士都好好的,他却跳车造成小腿骨折。还有一个湖北籍战士竟然在卡车行进途中跳车,也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自残,当然最后都被军法处带走了。后来怎么样了,出没人知道。
经过一天的南行,我们部队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城镇休整了两天后次日凌晨便全部到达前线。趁着夜幕的掩护,我们悄无声息地进入了各自的阵地。按照上级的安排我与另外一名供弹手张贵荣被安排在007号哨位。
007号哨位其实就是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猫耳洞,最多也就是只能容纳4个人。听说别的哨位更小,就是扩容后也只能勉强容纳一个人。
待在猫耳洞内只能蜷缩着身子,睡觉的时候连腿也伸不直。更为严重的是白天的温度高达30多度,就是只穿一条短裤浑身的汗水也像滚豆子似的不停的流淌,张荣贵索性连短裤也脱了,一丝不桂的爬在我的身旁。

然而这些还不算什么,更让人讨厌的那些蚊子,一巴掌拍下去,手上全是血,拍了这里那里又被叮。时间长了我们干脆就不去管了,任凭蚊蝇叮咬。几天下来身上就像蟾蜍一样全都是小疙瘩。有时还会看见一条小蛇从你的腿上爬过。
猫耳洞里不能有大的动作,稍不注意就会引来一串子弹,或者炮弹的袭击。进入阵地半个月后的一天中午,008号哨位的一个战士不小心把一块大石头撞翻后滚落到了山下,立即引来了敌人的一阵弹雨。过了五分钟柳长明悄悄爬过来看情况,刚到我们哨位的洞口前,突然敌人的几发炮弹就打了过来,等我和张荣贵把柳排长拉进猫耳洞后,柳排长已被炸得浑身是血。
还没等我和张荣贵反应过来,柳排长就大声喊道:“快,给我打,敌人冲过来了。”
我立即就向浓烟升起的地方打出了一梭子,柳排长又大声喊道:“不要停,继续扫射!”我一口气便打光了机枪里的子弹,周围几个哨位也传来了枪声,就这样,谁也看不见谁,只是相互对射,这种对射一直持续了两天两夜,我们三个除了隔一会射出一梭子子弹外,只能静静地蜷缩在猫耳洞,每个只吃了几块压缩饼干。喉咙已经干得直冒烟,但是没有一滴水。柳长明已经昏过去好几次,晚上的时候我用钢盔在岩石上滴了一点臭水来喂排长。
直到第三天的晚上,双方枪声稀疏起来后,后方才送过来了一点水,还补充了一点弹药。还来了一名叫陈瑜的女卫生兵。

陈瑜对柳排长的伤口进行紧急处理。又给柳排长喂了水,柳排长的气色终于好了许多。由于枪声虽然稀疏,但并未停止,柳排长还是不能即时送到后方。
四个人挤在猫耳洞里,必须人挨人,人挤人,否刚随时都会被外面乱飞的子弹射中。有了女人,我和张荣贵只好穿上了衣服,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光着身子,突然穿上了衣服,感觉浑身的每一块肌肤都痒得难受。到了中午,每个人的衣服已经全部被汗水湿透。
突然陈瑜发出一声尖叫,我急忙扭头一看,一条小蛇正在她的身上游走,我急忙告诉她别动,我一把抓住小蛇的尾巴甩了出去。还没等小蛇落地,越军密集的子弹就射了过来。柳排长忙说:“注意观察,别让敌人偷偷摸了过来!”

我刚把头抬起来,柳排长就急忙把我的头按下去,一串子弹射过来,柳排长的胳膊又一次中弹。
柳长明急忙喊,扔手榴弹,随着几颗手榴弹的爆炸,趁着浓烟,我立即打光了机枪里所有的子弹。敌人的火力终于被我的机枪压了下去。
又过了两天,前沿阵地一片寂静,再也听不到枪炮声了,趁着天黑,后方才派人过来接走了柳排长和陈瑜。第二天我就被任命为三排的代理排长。
一个月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接下来的时间除了白天时不时的会传来枪炮声外,晚上战士们便可以走出猫耳洞透透气了。只是由于天热送到猫耳洞的蔬菜水果很快就会腐烂,一个多月没有吃地水果和新鲜蔬菜,尽管蔬菜和水果已经坏了,但战士们也不敢随便扔掉,他们就在烂掉的水果蔬菜里面找稍微好一点的吃下去。
老山阵地属于亚热带气候,雨水特别多,并且一下就是好几天。由于猫耳洞都处在低洼地,洞里又没有防水设施,遇到大雨,洞内就会有很深的积水。为了避免被敌人发现,我们只能泡在水中。如果腿上有蚊蝇叮咬过的地方,一天泡下来,伤口就得化脓溃烂。
没有积水的时候,粪便还可以接在罐头盒子里面倒掉,有了积水,就只好把粪便排在水里,那股恶臭味,真让人恶心。
三个月的猫耳洞生活终于结束,我们走出猫耳洞时身体已经虚弱到了极点。没想到平时感觉非常轻便的机枪竟然把我压得摔了一个大跟头。要不是张荣贵扶我,恐怕凭我的一已之力永远都无法爬起来。
经过短暂的休息,我们连队列队离开了前线,没想到一次小小的失误却让我丢掉了代理排长的职务。

三个月来,除了手中的武器弹药,我们没有接触过任何人,那天我们正走在路上,突然前边不远的地方竟然出现了一位姑娘,这姑娘提着半篮子杏准备去卖。平时非常守纪律的战士竟然没有经受住那又黄又大杏子的诱惑,他们一拥而上,半蓝子杏子一时三刻就被抢光,看着姑娘那满脸的惊恐,我只好上前给她一边赔情道歉一边从口袋时摸钱。没想到我的口袋里摸了半天也没摸出一分钱。
姑娘知道我们是从前线下来的后,一连声地说:“不要钱,这些杏子也值不了几个钱。”我详细的询问了姑娘的住址和姓名,并保证会把钱即时送到她的手上。

我们刚回到了驻地,上级立即就找我谈了话。我也说明了当时的情况,然而领导却说,什么样理由也不能成为你哄抢农民东西的理由,尽管我与指导员一块亲自把钱给姑娘送去了,但我还是被免去了代理排长的职务。